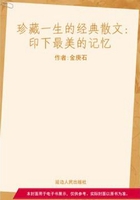孔丘来到卫国,不觉已过数月,春夏皆去,迎来早秋。这一日,风清气爽,天蓝云白,孔丘与子路乘车出了闲居园,顺着一条小溪缓缓行了三四里。溪流渐宽,路径渐直,一棵硕大的垂柳傍溪而立,柳下一块青石,平整光滑如几。孔丘见了,叫子路把车停下,孔丘从车上取下磬来,盘腿在石上坐下,双目微闭,静坐了一回,然后睁目举槌,急敲骤打,音响铿锵,声调激越。敲不多时,一个农夫挑一担箩筐,筐里盛满青草,从路上下到溪边,听见孔丘敲磬,停下脚步听了一听,自言自语道:“这磬也敲得算是不错的了,只可惜心绪过于褊激,好像在诉说:‘这世上没人理解我呀!这世上没人理解我呀!’没人理解还不就算了?《诗》不云‘深则厉,浅则揭’乎?”说罢,抬腿踩下溪水。水中歪歪斜斜露出一行石头,那农夫既不经意去踩这些石头,也不经意去避开这些石头,高一脚、低一脚,随意踩过溪水而去。子路目送这农夫走远了,道:“山野之人居然也会引《诗》,想必是位隐者。”孔丘停下手,叹口气,道:“这人对我的批评,好像是严厉得很!”子路道:“我看这人有些犯傻,夫子何必在意他的批评。”孔丘道:“何以见得他犯傻?”子路道:“他嘴上说‘深则厉,浅则揭’,其实却并不注意水的深浅,也不挽起裤腿,乱行胡踩,好像这水根本就不存在似的。”孔丘听了一笑,道:“这人的《诗》学,比你可精多了。”子路不服,道:“何以见得?”孔丘道:“你只知道照字面的意思,把这‘深则厉,浅则揭’理解为‘水深,就这么过;水浅,挽起衣裳再过’。他却知道‘深则厉,浅则揭’,不过就是‘随心所欲’或者说‘听其自然’的意思。”子路听了一怔,道:“这两句诗的含义原来如此,夫子怎么不曾这么讲过?”孔丘道:“我不是反复说过:‘学而不思则罔’么?字面的意思不懂,可以问师傅;内在的含义如何?得靠自己去思考、去体会。否则,问一知一,不能举一反三,岂不就成了俗话所谓的‘读死书’?”听罢,举起磬槌,正要敲下之时,却听得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而近。孔丘与子路扭头一看,见是子贡拍马而来。孔丘道:“你也来凑兴?”子贡把马勒了,笑道:“不是来凑兴,却是来扫兴。”孔丘道:“怎么?难道庄上出了什么事情?”子贡道:“事情倒没有,不过来了个客人,急着要见夫子。”孔丘道:“客人不曾自通名姓?”子贡摇头,道:“不曾。只肯说是受夫子故人所托,有要事奉告。”孔丘听了,略微一怔,自我解嘲道:“我的故人?这世上不是没人理解我么?怎么还能有故人?”子路解开拴马索,把车套好,请孔丘上车,道:“何必琢磨?回去便知。”
卫侯与弥子瑕在卫宫后花园清香阁内并肩而坐。一名宫女双手捧一青铜托盘走到卫侯跟前,将托盘呈上。卫侯俯首一看,只见盘中盛两枚仙桃,殷红如滴。卫侯道:“是谁遣你送这桃来?”宫女道:“夫人。”卫侯道:“原来如此。”卫侯一边说,一边伸手取出一枚,递与弥子瑕,弥子瑕受宠若惊,慌忙起身,双手捧桃送还卫侯,道:“臣何敢!”卫侯不接,却从盘中取出另一枚,道:“寡人这儿不是还有一枚么?有什么不敢?快坐下!”弥子瑕看着宫女侍候卫侯吃毕,方才将桃放在嘴边浅尝一口,喊一声:“好桃!”取餐巾揩过流出嘴边的桃汁,将桃送到卫侯口边,道:“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的桃,主公快来尝一尝!”卫侯把嘴凑过来,就在弥子瑕手上将桃咬了一口,道:“果然比寡人方才吃的那一枚更好!你自己快吃。”说罢,用手将桃推到弥子瑕嘴边,弥子瑕又咬了一小口,仍把仙桃送到卫侯嘴边,道:“这么好的桃委实难得,主公快快把它吃完。”两个人推来送去,你一口我一口,好半天方才把那一枚仙桃吃毕。
卫侯携着弥子瑕的手站起身来,一起下了清香阁,顺着松径折东而去。两人手牵手穿过一扇月亮门时,险些儿与迎面而来的卫侯夫人南子撞个正着。卫侯见了南子,慌忙甩开弥子瑕的手,面上微露赧颜。南子掩口一笑,道:“哎哟!看你,还怪不好意思的!以为谁不知道呢?”卫侯嘱咐弥子瑕道:“你先回到清香阁去等一等。”弥子瑕扭扭捏捏而退。南子望着弥子瑕的背影一笑,道:“难怪你喜欢他,连我看着都觉得可爱。”卫侯道:“你有什么事情要找到这儿来?”南子又一笑,道:“看你说的,好像这后花园没我的份儿似的,哪天我也把我那人儿带来,同你这人儿比个高低。”卫侯道:“快别胡说!叫外人听见了,像什么话?”南子嗔道:“这儿哪有外人?除非你把我当外人。”卫侯赔笑道:“好了!好了!我不同你争,有事尽快说。”南子道:“看你急的!你那人儿可得在清香阁里久等了。”卫侯道:“什么意思?”南子道:“赵鞅常驻这儿的使臣在勤政殿等你接见。”卫侯听了,略微一怔,道:“他什么时候来的?”南子道:“来了有那么一阵子了。”卫侯道:“你怎么不早来告诉我?”南子笑道:“你不觉得这使臣长得风流倜傥?”卫侯道:“什么意思?”南子道:“所以我就陪他多坐了一坐。”卫侯道:“休要哄我!你无非是想对他盘问盘问。”南子听了,得意地一笑,道:“男人谁也经不住我一问。”说罢,顿了一顿,又道:“也许像你这样的男人除外。”卫侯不理南子的取笑,转身要走。南子道:“等等!你要上哪去?”卫侯道:“你这不是明知故问么?赵鞅的使臣既然在勤政殿等我,我还能去哪?”南子笑道:“我说他在等你,不过是哄你,我其实已经把他给打发走了。”卫侯道:“你怎么把他打发走了?他来自然是有要紧的事情。”南子不屑一辩地道:“这我还不知道!”卫侯道:“他究竟为什么事情而来?”南子道:“他说佛兮派人来跟孔丘接头,叫你无论如何把孔丘留住,不能让孔丘去中牟与佛兮合伙。”卫侯道:“佛兮怎么会来同孔丘接头?赵鞅又从何得知?”南子道:“佛兮是孔丘的老相识,曾向赵鞅推荐过孔丘。佛兮派来的那人行事不慎,让赵鞅的手下一路跟踪。那人一入卫境,就向人打听孔丘的住处,所以走漏了风声。”卫侯道:“原来如此。不过,孔丘是我的客人,并不是我的臣下,我怎么能拖住他不放?”南子道:“依我看,晋国这回内乱,赵氏必然获胜。你若不答应赵鞅的请求,早晚受祸。”卫侯道:“你难道已经答应了?”南子笑道:“我不答应,能打发他走吗?”卫侯听了,略一踌躇,道:“你有留住孔丘的办法?”南子点头,道:“不错,只看你是要施软,还是要施硬?”卫侯道:“如何施硬?”南子道:“把他软禁在闲居园,叫他即使想走也走不脱。”卫侯摇头,道:“软禁客人,岂是君子待客之道?这办法不行。传出去,让诸侯看我的笑话。”南子道:“你既然不愿意施硬,那就只有施软。”卫侯道:“如何施软?”南子道:“让孔丘以为你要重用他,他难道不会自愿留下?”卫侯道:“我已经将国事托付给大夫史鱼了,岂可出尔反尔?”南子笑道:“我只是叫你让孔丘以为你会重用他,谁叫你当真?”卫侯道:“他怎么以为,我怎么控制得了?”南子伸出右手食指对卫侯一招,道:“过来!”卫侯趋前,南子对卫侯一番耳语。
孔丘在庄门口送走不速之客,回到书房,子路接着,问道:“这不速之客,来得神秘,走得匆忙,究竟为谁而来?”孔丘吩咐子路把门关好,压低声音道:“不要声张,传出去不好。”子路悄声道:“难道有什么秘密?”孔丘略一迟疑,道:“你还记得佛兮其人么?”子路道:“前几天听颜浊邹说,晋国发生内乱,六卿分成两拨捉对儿厮杀,赵氏的中牟宰又据中牟城反叛赵氏。我问这中牟宰是谁,他说是个姓佛名兮的人。这姓与名都很特别,我想一定就是夫子在雒邑结识的那位故人。”孔丘道:“不错,方才这人,就是他遣来的使者,他想请我去中牟与他一起共举大事。”子路听了,冷笑一声,道:“举什么大事?不就是一同造反么?”孔丘作色道:“休要胡说!晋国六卿全然不把晋侯放在眼里,各自争权夺利,业已造反在先,佛兮不过是拒绝跟从赵鞅反晋而已。”子路道:“佛兮是赵氏的家臣,并非晋国的大夫,身为赵氏家臣而不听命于赵鞅,就是造反,无可置疑。”孔丘摇头一叹,道:“你只懂小理,不明大义,同你讲不通。”子路略一踌躇,道:“难道夫子真打算应佛兮之请?”孔丘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况且,我又不是匏瓜,怎能系而不食!”子路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话我懂。夫子自比匏瓜,是什么意思?我就不明白了。”孔丘道:“乡下人把匏瓜风干之后,用丝带系着,挂在厨房墙上作为装饰,你难道没有看见过?”子路道:“见倒是见过,不过,这同夫子的处境有什么相干?”孔丘道:“来卫之后,卫侯问我在鲁俸禄多少。我说粟六万斗。卫侯道:‘寡人也与你粟六万斗。’在鲁,得粟六万,是执政的俸禄。在卫,无官无职,无所事事,也得粟六万,难道不是把我当作匏瓜,系而不食么?”子路笑道:“原来夫子是闲得无聊,所以才要到佛兮那儿去凑热闹。”孔丘听了不悦,道:“什么话!”孔丘的话音刚落,门外传来脚步声,接着是敲门的声音。孔丘道:“进来!”子贡应声而入,道:“卫侯遣使者到,在客厅候见。”孔丘略整衣襟,疾步而出。
子贡目送孔丘走远了,笑道:“夫子同你关着门讲什么秘密?”子路道:“夫子自比匏瓜。”子贡道:“卫侯既遣使者来,这匏瓜也许是当不成了。”子路叹口气,道:“但愿如此。”子贡道:“听你这口气,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似的?”子路不答,从几上拿起磬槌,在磬上一通乱敲。敲不多久,廊下传来孔丘的声音道:“你乱敲些什么!”子路慌忙住手,退到一边,道:“夫子怎么回得这么快?”孔丘不答,径自走到书案之后坐下。子贡瞟了一眼孔丘,道:“卫侯遣使者来,想必是有要事?”孔丘摇头,道:“卫侯不过想请我去趟郑国,先遣使者来探探我的意思。”子路道:“我怎么没听说卫、郑之间有什么事情需要交涉?”孔丘道:“事情要是公开了,也许就用不着我去了。”子贡道:“这么说,难道卫侯是想请夫子去谈件秘密?”孔丘尚未作答,子路抢先道:“是秘密也好,不是秘密也好,总之,去郑远比去中牟好。”子贡听了,略微一怔,道:“难道先前那不速之客,竟是佛兮派来的?”孔丘不答,却道:“你两人今日在这儿听见的话,切不可外传,明白了?”子路与子贡一起点头。
子路与子贡刚刚退下,春梅自外而入,道:“自从来到这庄上,门可罗雀,今日怎么一连来两位不速之客?”孔丘略一思量,道:“卫侯想请我以私人身份去趟郑国。”春梅微微一笑,道:“我听不明白这话的意思。”孔丘道:“这么简单的话,你怎么会听不懂?”春梅道:“既然是以私人身份,怎么要他请?”孔丘道:“当然是托我暗中替他去办点事情。”春梅止住笑,道:“说正经的,卫侯请你去郑,可有危险?”孔丘摇头。春梅道:“既无危险,何必不公开?”孔丘道:“卫侯想替太子娶郑伯之女,担心婚议不成,徒成笑柄,所以想请我去私下探个口风。”春梅道:“卫侯既以私事相托,想必对你信任有加,说不定你从郑国回来,就会以国事相托也未可知。”孔丘听了,沉默不语,过了半晌,方才道:“当年我在雒邑的时候,去过一次郑国,与郑相子产一见如故。如今子产已经死去多年,我倒是早已有意去他墓前祭扫一番。”春梅道:“那你这次去郑,就以祭扫子产为名?”孔丘点头。春梅道:“什么时候动身?”孔丘道:“我明日去见卫侯,把细节商量妥当,后日起程。若无意外,不出两旬,将可返回。”春梅道:“你打算叫颜刻驾车,还是叫子路驾车?”孔丘略一迟疑,道:“叫子贡。”春梅嗔道:“你这人也真够麻烦的,一个车夫,也要换来换去!”孔丘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春梅道:“此话怎话?”孔丘道:“工匠想要把活做好,必须先把工具磨快。”春梅道:“这跟叫谁驾车有什么关系?”孔丘道:“用人也是同一个道理,人虽不能由你磨,却可以由你挑。谁胜任,就用谁。有时候车夫就是车夫,所以要驾车的功夫好。有时候车夫也是游伴,所以要兴致相近。有时候车夫兼充助手,所以要能办事。这次去郑,也想顺便交结郑国的大夫。”春梅听了一笑,道:“原来如此,所以你要带个会说话的同去。”
一场秋雨过后,凉意陡然而生。郑邑东门之外,一座青冢面向郑城,背临异水,青冢之上,白石砌就一个四方形的坟墓,墓前一块白石墓碑,碑上刻着“郑相子产之墓”六个篆字,填作墨绿之色。碑前的草地上放着一个深黑描金漆厢,厢里盛着三牲。五步之外,孔丘一身缟素,拱手行长揖之礼。墓侧松林之后,停着一辆马车,子贡垂手,恭立在车旁。孔丘行礼既毕,又面对墓碑静静地立了一刻,叹口气,道:“古之遗爱也。”说罢,不禁掉下几滴泪来。孔丘从怀里取出帛巾,将泪水揩去,口喊一声:“子贡!”子贡应声而出,拱手道:“夫子有何吩咐?”孔丘道:“《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何所指?”子贡道:“施政宽和,或许能致民于小康。”孔丘点头,道:“不错。‘无纵诡随,以谨无良’呢?”子贡道:“意思是:对于贪官刁民,绝不能手软。”孔丘道:“这四句诗,说透施政必须宽猛相济之道。执法过严,民不聊生,何能小康?包庇贪官,刁民效尤,何能太平?近世执诸侯之政而深谙这宽猛相济之道的,只有子产一人而已。”说罢,又叹一口气,吩咐子贡道:“将三牲撤去,把墓前墓后仔细打扫一番。”
孔丘师徒二人从子产墓地回到郑邑南门,子贡忽然内急,只得把车在路边停了,下去方便,回来却不见孔丘,正彷徨无计之时,一个老者过来道:“你左顾右盼,神色张惶,莫非在找人?”子贡点头。老者道:“老朽方才见着一个人,额头长得像尧,脖子长得像皋陶,肩膀长得像子产,失魂失魄,恰似丧家之狗。你要找的,莫非就是这个人?”子贡尚未作答,那老者提起手中拐杖向右边横街一指,又道:“那儿有个书市,你怎么不到那儿去找?”说罢,不待子贡回答,拄着拐杖,踱出南门。子贡顺着老者指点的方向走去,行不过数十步,果然看见一个书市,孔丘正在书摊之间徘徊观望。看见子贡,孔丘道:“我以为你会在车上等着,怎么知道找到这儿来?”子贡道:“全凭一老叟指点。”孔丘道:“这老叟如何说?”子贡道:“他说看见一个人,额头长得像尧,脖子长得像皋陶,肩膀长得像子产,失魂失魄,恰似丧家之狗,往这边书市去了。”孔丘听了大笑,道:“你听他胡说八道!谁见过尧?谁又见过皋陶?不过,说我‘失魂失魄,恰似丧家之狗’,这话倒是说得一点儿也不错。”
卫侯寝宫之内,烛影摇红,薰香缭绕。猩红锦被之下一阵翻滚之后,钻出两个人头来,一个是卫侯,另一个不是南子,却是弥子瑕。弥子瑕披衣欲起,卫侯道:“你急什么?”弥子瑕道:“主公不怕夫人进来撞见?”卫侯听了一笑,道:“别瞎担心!她正在春草池中如鱼得水,哪会上这儿来?”弥子瑕道:“原来主公早已有了安排。”卫侯道:“可不是么?寡人特意从宋国接来夫人的旧情人公子朝,安排他在春草园中住下,好让她两人在春草池中尽情戏水。否则,寡人又岂敢明目张胆地把你接到寡人的寝宫中来?”弥子瑕道:“夫人虽不见怪,依臣之见,仍须小心,否则,让左右侍从把这事给传出去,岂不是坏了主公的名声?”卫侯道:“外面有人议论寡人与你的事?”弥子瑕略一迟疑,道:“听说孔丘对他的弟子说什么‘为政最忌男宠’。所谓‘男宠’,难道不就是指的我?”卫侯道:“寡人待孔丘不薄,孔丘这话,恐怕不过是泛泛之论,未见得就是说的寡人与你。”弥子瑕道:“听说孔丘本来安心作客,感激主公待他以上宾之礼。自从去郑国回来,却心怀怨望,满腹牢骚。”卫侯道:“休要胡说!寡人待他始终如一,他怎么会凭空改变态度?”弥子瑕听了一笑,道:“主公原来有所不知。”卫侯道:“寡人有什么不知?”弥子瑕道:“主公请孔丘去郑国,他误以为主公要重用他,从郑国回来既不得重用,于是乎大失所望。”卫侯听了,沉默不语。弥子瑕又道:“孔丘这种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依臣之见,还是不如打发他走人为妙。”卫侯道:“孔丘是个人望,寡人虽不能用他,待之以上宾之礼,足以显见寡人崇德好仁的胸襟。”弥子瑕道:“卫国今非昔比,早已沦为一个小国,夹在晋、楚之间,左右为难。养这么个人望在卫,未见得就是卫国之福。”卫侯道:“此话怎讲?”弥子瑕道:“主公如此优礼孔丘,晋侯、楚王说不定误以为主公有复兴卫国的雄心壮志,凭空招来麻烦,难道不是有弊无利?”卫侯听了,沉吟半晌,道:“你有什么不露痕迹的好主意?”弥子瑕略一思量,凑到卫侯耳朵跟前,对卫侯一番耳语。卫侯听毕,点头道:“就按你这计策去试一试。”
三日后,孔丘在书房与子路对弈,冉求与颜回在一旁观战。子贡匆匆从外来,道:“卫大夫公孙余假领着十来个士兵,要进庄来搜查奸细,夫子快去看一看。”孔丘听了,放下手中棋子,道:“岂有此理!”孔丘一边说,一边起身,踱出书房,众弟子跟在身后。孔丘一行来到庄门口时,颜刻正领着一帮弟子与公孙余假在门口僵持不下。孔丘分开众人,趋前向公孙余假道:“弊庄除孔丘家室与弟子外,别无外人。公孙大夫既是要搜查奸细,恐怕是找错了地方。”公孙余假冷笑一声,道:“这庄上虽然不见得住着外人,住在这庄上的人却未必不同奸细来往。”孔丘道:“说话不能凭空臆想,不知公孙大夫这话可有实据?”公孙余假道:“上个月有人亲眼看见佛兮派来的奸细走入这庄里来,难道不就是实据。”孔丘听了,略微一怔,道:“所谓‘有人’,究竟是谁?这人怎么就能辨认佛兮的手下?就算这人不曾看错,把佛兮的手下说成奸细,难道卫国什么时候成了赵鞅的附庸不成?”公孙余假道:“我不同你狡辩,我只是奉命行事,你庄上既无奸细,何妨让我进去看个究竟?”孔丘听了,略一迟疑,道:“请便!”说罢,向拦在门口的众弟子挥手示意,让开一条道来,令公孙余假一行鱼贯而入。公孙余假领着手下在庄上各处随便走了一趟,并不曾仔细搜查,径自回到庄口,不辞而别。俟公孙余假走远了,孔丘对跟在身后的子贡道:“郑国那老叟说我如丧家之狗,果不其然!”子贡道:“夫子的意思难道是要离开卫国,投奔他邦?”孔丘道:“公孙余假来,所谓搜索奸细不过是个托辞,其实是来下逐客之令。既下逐客之令,我还不走,岂不是太不识趣?”子路道:“夫子想上哪去?是不是该乘桴浮于海了?”颜回听了不懂,道:“什么‘乘桴浮于海’?”孔丘道:“休要听子路胡说。赶紧去收拾行装,后日一早起程取道匡邑去陈。”颜回道:“夫子难道不去见卫侯?就这么不辞而别?”孔丘道:“不错。卫侯之所以叫公孙大夫如此而来,目的正在不留痕迹。我要是去辞行,就是逼他正式表白态度。不留痕迹,留有回来的余地。正式表白态度,这余地岂不是就没有了?”颜回道:“夫子原来还有回来的打算?”孔丘道:“打算也谈不上。不过,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卫侯也许只是听了谗言,一时糊涂。留有余地,于卫侯、于我,都是有利而无弊。”
夕阳西下,倦鸟归林。颜刻驱车来到匡邑东门之外,孔丘在车上回头一望,不见随行弟子的车辆,吩咐颜刻减速慢行。颜刻道:“动身前我同众弟子约好在门外会齐一起进城,夫子既是先到,何妨在城外先转一转?”孔丘道:“也好。”颜刻听了,将缰绳一提,拨转马头顺城外壕沟往南而去。行不数十步,但见城墙曲折之处有一段倒塌,城砖黄土散落在壕沟里,黄土堆中冒出几丛酸枣来。颜刻见了,把缰绳一勒,举起手上马鞭往城墙缺口一指,道:“这段城墙塌了至少五年了。”孔丘道:“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难道你五年前来过这儿?”颜刻道:“可不是!五年前鲁军来攻匡邑,我驾着阳虎的战车,正是从这缺口冲进城去的。”孔丘听了,叹一口气,道:“原来如此。”孔丘与颜刻在缺口之外观望了一回,掉转马头,回到东门,子路、巫马子期、冉求、子贡、高柴等先后赶到,唯独不见颜回。久等不至,巫马子期道:“天色不早,夫子不如先率众弟子进城去歇息,我留下来单等颜回。”
孔丘一行正要进城,城里忽然传来一片呐喊,孔丘举头一看,但见城门里奔出几条汉子来。为头一人,双手握槊,口中喊道:“休走了阳虎!”跟在后面的人,或执刀剑,或拖棍棒,口中也一发乱喊:“休要走了阳虎!”孔丘听了,不禁一笑,在车上拱手施礼,道:“鲁人孔丘,也正要捉拿阳虎。敢问先生尊姓大名?想必是认错人了。”为头那人听了,冷笑一声,道:“我匡简子行不改姓,坐不改名。不像你阳虎无赖,居然冒充孔丘,方才我分明看见你与你的车夫在那城墙缺口之处指指点点,说什么五年前正从那缺口冲进城去的,你还想哄谁?”颜刻听了,赔笑道:“不错,五年前是我驾阳虎的车从那缺口进的城。不过,如今我是孔子的车夫,车上的人不是阳虎,而是孔子。”匡简子听了,又一声冷笑,道:“笑话!阳虎与孔丘是死对头,怎么会用同一个车夫?你既是阳虎的车夫,你车上的人不是阳虎,还能是谁?”说罢,向身后喊一声:“你们看那车上的人是不是阳虎?”众人七嘴八舌,都说就是阳虎,绝对没错。孔丘问颜刻道:“我当真有些像阳虎?”颜刻略一踌躇,道:“远看有七八分像,近看有三四分像。”孔丘听了,道:“既然如此,也就怪不得这些人了。”子路道:“怪不怪,都得找条出路才好,叫他们围困于此,总不是个事。”子贡趋前,向匡简子拱一拱手,道:“匡简子千万不可造次!阳虎从齐国逃出,投奔晋大夫赵鞅,现在当在晋阳,怎么会在这儿?”匡简子道:“孔丘去鲁至卫,现为卫侯之客,当在卫国都城楚丘,又怎么会在这儿?”子贡道:“孔子自卫去陈,所以经过匡邑。”匡简子道:“阳虎倘若自晋去陈,不是也要经过匡邑?”子贡道:“阳虎是个臭名昭著的恶人,怎么会有我们这样一帮儒生弟子?”匡简子道:“阳虎一向以儒者自居,上次来匡时,满嘴里讲的也都是仁义道德,他怎么就不能有你们这样的儒生弟子?”子路趋前,叫子贡退到一边,道:“同他这样的糊涂虫,有理说不清。”匡简子听了,勃然大怒,抄起木槊,弄个饿虎擒狼之势,对子路道:“有种的过来同我一搏,谁输了谁是糊涂虫!”子路听了一笑,道:“听你说话的口气,倒像是十五前的我。你既要胡闹,休怪我刀下无情。”说罢,从腰下抽出朴刀来,使个饥蛟取虎之势。两人正要动手,忽然人群之外传来一个声音道:“匡简子不得无礼!还不向孔子赔罪,更待何时?”匡简子听了,慌忙举头一望,顿时收了架式,跳出圈子,把木槊丢到一边,向孔丘拱手道:“匡简子误把孔子当成阳虎,失礼冒犯,盼孔子多多包涵,不予计较。”说罢,又拱一拱手,转身退下,跟来的汉子也一哄而散。子路见了,也把朴刀插回腰下,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但见两匹高头卷毛白马拉一辆漆红描金马车,停在不远不近之处,车厢两边各插一面三角锦旗,旗色深蓝,正中用白线绣作“宋”字。车窗锦帘掀开,露出一张男子的脸来,年纪大约三十上下,长得眉目清秀,须髯飘逸,神气不同凡响。子路正注目之时,车窗锦帘重新关上,马车徐徐起动,往东南方向去了。孔丘问子路:“看清了那人是谁?”子路道:“人倒是看清了,只是不认识。”孔丘道:“车上插着宋国的旗帜,想必是宋国的公室。”子贡道:“匡邑是公子朝的封地,难道那车中之人竟是公子朝不成?”孔丘尚未作答,却听见后面有人说道:“谁说不是?”孔丘扭头一看,见是卫大夫蘧伯玉,不禁喜形于色,道:“你怎么在这儿?”蘧伯玉道:“这话该我问你才对。我月前出使陈国,如今经匡回卫。你不在卫,却来此地有何勾当?”孔丘道:“哪有什么勾当!不过被人误会成阳虎,要不是公子朝一言解围,还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蘧伯玉道:“上次阳虎来匡,掠夺甚多,所以匡人恨之极深。你最好不要在匡停留,免得又遭误会。”孔丘听了,叹口气,道:“我如今是丧家之狗,无处可去。”蘧伯玉听了,吃了一惊,道:“卫侯不是以上宾之礼相待么?难道有小人从中挑拨离间,所以你才不得不出走?”孔丘不答。蘧伯玉略一踌躇,道:“一定是弥子瑕从中使坏。不过你放心,不出一个月,我担保能令卫侯回心转意。陈大夫司城贞子是我的好友,这一个月,你不妨先去他那儿住下。我在楚丘城里有座别业,专为待客而设,唤做“待贤馆”,景致也许不及闲居园,不过毕竟在城里,人来客往比较方便,一个月后我接你回卫,就搬到待贤馆去住如何?”孔丘笑道:“丧家之狗,敢不从命?”
卫都楚丘春草园,山抹微云,枫染轻霜。一泓温泉流入一座松木便殿,殿内薰香袅袅,烛光摇曳,四面重垂锦帐,中央一池温汤。南子与公子朝两个脱得赤条条,尽情放任,在池中挑逗戏水。两人在水中几番云雨既毕,气喘吁吁,登上池岸,各自披上绣花浴袍,仰卧在池边便榻之上,双双闭目养神。一阵沉默过后,公子朝睁开眼睛,道:“你猜我前日在匡邑看见了谁?”南子两眼半张不合,微微一笑,道:“只要不是女人,我才懒得管他是谁!”公子朝道:“真所谓‘近墨者黑’!”南子睁大眼睛,道:“此话怎讲?”公子朝道:“卫侯对女人没了兴趣,你跟着就对男人没了兴趣,难道不是‘近墨者黑’?”南子听了,不禁大笑,道:“原来如此!”说罢,顿了一顿,又道:“天下的男人,经我阅历过的也不算少了,能像你一样令我满意的,还真是不多。”公子朝道:“我前日看见的这男人,你要是看见了,准会有兴趣。”南子听了,眼睛睁得更大,问道:“这人究竟是谁?”公子朝道:“孔丘。”南子不屑地一笑,道:“我道是谁,原来是他!”公子朝道:“怎么?你见过他?”南子摇头,道:“不曾。我倒是想见他,无奈他推辞不肯。”公子朝笑道:“你还真想见他?”南子嗔道:“休要胡调!我想见他,不过是慕他德高望重之名。”公子朝道:“难道你没听说他身材魁伟,仪表出众?”南子道:“怎么没有?我小时候就听说过。不过,他如今年纪已过半百,难道还不是早已老态龙钟?”公子朝摇头,道:“我前天看见他,虽然不能说还年轻,可是绝无老态,而且另有一番雍容高雅的气象,令人望之不觉神往。”南子道:“真的?”公子朝道:“我骗你干什么?”南子听了,沉吟不语。公子朝见了一笑,道:“你是不是对他有兴趣了?”南子道:“我不是跟你说过了么?我虽想见他,无奈他不肯见我。”公子朝道:“你要是真想见他,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南子笑道:“你难道同他有什么交情?”公子朝道:“交情虽然谈不上,但他欠我一笔人情。”南子摇头不信,道:“他怎么会欠你的人情?”公子朝道:“前日他在匡邑东门外被人围困,是我一语替他解围,否则,他吉凶未卜。他难道不是欠我一笔人情?”南子听了,依然不信,道:“休想哄我。孔子同匡人无冤无仇,匡人怎么会同他过不去?”公子朝道:“匡人把他误会为阳虎。”南子道:“原来如此!难道他有几分像阳虎不成?”公子朝道:“说来奇怪,还真有几分相似。”南子听了,不觉失口一笑。公子朝见了,问道:“怎么?阳虎也是经你阅历过的?”南子笑而不答,却道:“既然你以为他欠你一笔人情,那我就听你的好消息了。”公子朝道:“你要等好消息,也不能全靠我,还得靠你自己才成。”南子听了大笑,道:“真是笑话!要靠我自己,还要你帮什么忙?”公子朝道:“卫侯听信弥子瑕的谗言,把孔丘给气走了,你得先叫卫侯把他请回来,我才能帮得上忙。”南子听了一怔,道:“这事你是听谁说的?我怎么不知道?”公子朝听了一笑:“你以为卫侯会把弥子瑕同他说了些什么都一一告诉你?我是听蘧伯玉说的,蘧伯玉的话一向可靠。”南子道:“原来如此。我说他孔丘怎么平白无故离开楚丘去匡邑!”公子朝道:“你要是能把弥子瑕撵走,不愁孔丘不回。”南子道:“孔丘的腿又不长在你身上,你凭什么担保他会回?”公子朝道:“不是我担保,是蘧伯玉担保。”南子听了,略微一怔,道:“这话可是蘧伯玉说的?”公子朝道:“不错。不过,蘧伯玉担心你拿弥子瑕无可奈何。”南子不屑地一笑,道:“笑话!别人拿弥子瑕无可奈何,我要撵走弥子瑕,比捏死梳子上的虱子还容易。”公子朝听了,略一迟疑,道:“一旦撵走了弥子瑕,你我还能这么快活么?”南子道:“你是卫侯自己请来的,他还能对你怎么样?况且,天下的小白脸儿又不止他弥子瑕一个,撵走他弥子瑕,还怕找不着别人顶替他?”公子朝听了,一笑道:“如此便好。”
十二月腊日前夕,空中纷纷扬扬,飘下一场鹅毛大雪。孔丘立在待贤馆正厅外的走廊之上,仰头观赏雪景。春梅自厅内出,笑道:“今日果然是一个好日子。”孔丘道:“此话怎讲?”春梅道:“你今日不是要去见南子么?”孔丘道:“这同下雪有什么关系?”春梅道:“俗话说‘腊日飞雪,两情相悦’,你难道没有听说过?”孔丘听了一笑,道:“休要胡调!南子不止一次请我相见,我要是心中有些那个,还不早就去了。这回她托公子朝来相邀,我欠公子朝一笔人情,所以只好答应了。”春梅道:“南子不仅是个出名的大美人,而且也是个出名的风流种,听说十个男人见了她,九个人都会失魂落魄,我就不信你能例外。”孔丘道:“我怎么就不能是九个人之外的那一个?”春梅道:“因为那一个是阉过的。”春梅说罢,掩口而笑。孔丘听了,也不禁失口大笑。笑过之后,孔丘正色道:“千万不要再说这些疯话,叫弟子听见了成何体统!”春梅道:“你就知道担心什么成不成体统。我倒是担心你去了之后,真的不能脱身,坏了一生的清白!”孔丘听了,道:“我早已想好了一条脱身之计,不然,我又岂敢应南子之请!”春梅道:“原来如此。是条什么妙计?快说给我听听。”孔丘道:“我去了约莫半个时辰之后,你就假装昏厥,一头栽倒在地。子路见了,必然会驾车前去追我速回。”春梅笑道:“我以为是什么妙计,原来不过叫我装死!”
孔丘与春梅在走廊上谈笑之时,子路、颜回、冉求与子贡正立在待贤馆大门口赏雪。冉求道:“俗话说:‘腊日飘雪花,出门坐香车。’果不其然。”颜回道:“此话怎讲?”子贡道:“今晚夫子要去见南子,你难道没有听说?”颜回道:“怎么没听说!不过,夫子去见南子,同这句俗话有什么关系?”冉求笑道:“南子会派自己的车来接夫子,南子的车,难道还不是香车?”颜回道:“原来如此。诸侯夫人的车,当然是要用香薰过的,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子路听了,眉头略皱,道:“说点儿别的好不好?”子贡见了,笑道:“看样子,你是不大愿意夫子去见南子?”子路道:“前几天,大夫王孙贾来看夫子,两人谈起‘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这句俗话,夫子当时不以这话为然,如今却去见南子,难道不是言行不一吗?”颜回道:“‘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的意思是,与其讨好奥神,不如讨好灶神,这同夫子去见南子有什么关系?”子路不耐烦地摇一摇头,道:“同你说不清。”子贡道:“也难怪颜回不明白,王孙贾与夫子都在打隐语。”颜回道:“打什么隐语?”冉求道:“奥神,影射卫侯。灶神,影射南子。奥神的名分虽然在灶神之上,灶神却有实权。”颜回听了,不以为然地道:“我看这都是些捕风捉影的话,未见得是夫子的本意。夫子同意去见南子,一定有他去见的理由,只不过我们当弟子的才智低下,不能理解罢了。”子路听了,冷笑一声,道:“说我们才智低下还差不多,可不能把你自己也算在内。夫子不是说你‘闻一知十’么?要是‘闻一知十’的人还才智低下,我们这些人还不都成了傻瓜?”颜回见子路有些生气,赔笑道:“我只不过是想说,夫子去见南子,未见得有讨好南子的意思。”子路道:“去见南子的人,只有两种意思。一种是去讨好。另一种意思嘛,不说也罢。”子贡笑道:“你也别想得太偏了,我看夫子去见南子,无非也就是打通关节之意。”颜回道:“你的意思是说:夫子希望通过南子而见信于卫侯?”子贡道:“不错。”子路道:“何以见得?”子贡道:“你既然不信,我进去替你问个明白。”颜回听了,慌忙摇手制止道:“千万不可造次,怎么可以拿这样的话去问夫子?”子贡笑道:“你别慌,我也会打隐语。”颜回略一迟疑,道:“既然是打隐语,那就随你去。不过,我可不跟你去,”子贡道:“谁同我一起去?”子路道:“我同你一起去。”子贡问冉求:“你去不去?”冉求笑道:“你两人先走一步,我随后就来。”
孔丘与春梅立走廊上看了一回雪景,觉得有些凉意,正要退回厅中,却见子路与子贡一前一后走了进来。春梅道:“方才看见你两个同颜回、冉求一起出去,怎么不见他两人回来?”子贡道:“他两人还要在门口赏雪,子路与我觉得有些冷了,所以先回。”孔丘道:“我也正觉得寒意袭人,他两人却偏不怕冷。”子路听了,不禁失口一笑,道:“冷虽不怕,却有些怕事。”孔丘不予理会,转身折回厅中,春梅与子路、子贡相继而入。厅子中央一盆炭火烧得正旺,四人围着火盆烘了一回手,孔丘对春梅道:“你去厨房吩咐庖人煮两壶黄酒来散散寒气。”春梅从屏风后退下。孔丘瞟一眼子贡,道:“你好像心绪不宁,难道有什么事情难以决断?”子贡赧颜一笑,道:“夫子明察秋毫,果不其然。”孔丘道:“何妨说出来叫我听一听?”子贡略一迟疑,道:“一个朋友最近得了一块美玉,他问我是珍藏在柜子里好呢,还是找个识货的商人卖掉好?我思量了半天,却拿不定主意怎样回答他。”孔丘听了大笑,道:“这也费思量?当然是卖掉好。我这不也是天天都在等着识货的上门么?你难道还看不出?”子路道:“天天等着识货的上门,是不是也属于‘欲寡过而未能’?”孔丘尚未作答,颜回与冉求推门而入。厅内一阵沉寂,只听得木炭“劈啪”作响。半晌之后,孔丘道:“我知道你们也许不赞同我去见南子,我本来也不想去,否则,还不早就见过了。”子路道:“夫子不想当匏瓜,这我能理解。不过,南子既有淫乱的名声在外,夫子去见她,难道不怕别人说闲话?”孔丘道:“古人云:‘坚乎,磨而不磷;白乎,捏而不淄。’这话你难道没听说过?”子路道:“听倒是听说过。不过,硬到磨都磨不薄,白到染都染不黑,这世上真有这样的事?”颜回道:“怎么没有?夫子难道不正好就是‘磨而不磷,捏而不淄’的例子?”子路听了,沉默不语。春梅恰于此时领两个青衣童子入,吩咐童子把酒壶与酒盏在几上摆好之后,道:“都来喝酒散寒,不要再争。”
当日傍晚,春草园中南子寝室套间之内,南子坐在梳妆台前,卫侯立在南子身后,两名宫女各持一面铜镜分立南子两边。南子发挽玉髻,耳坠金环,对镜左顾右盼,时而取粉扑补粉,时而取眉笔描眉。卫侯见了,不禁失笑,道:“你又不是去见公子朝,如此这般费心!”南子笑道:“说你不解风情,果不其然。公子朝不过是个绣花荷包,想玩的时候,从怀里摸出来,玩够了,再放回去,哪用得着费心打扮去见他!”卫侯道:“我以为你不过是慕孔丘德高望重之名,原来你竟然想打他的主意!”南子嗔道:“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卫侯道:“你不嫌孔丘老?”南子道:“有人未老先衰,有人老而益壮。”卫侯道:“你怎么知道孔丘老而不衰?”南子笑道:“你以为除了你,就没人给我消息?”说罢,又伸头对镜顾盼了一回,道:“取麝香来。”右手边的侍女应声放下铜镜,从妆台上取过一个彩陶小瓶,拔开瓶塞,将瓶递到南子手中。南子用右手接过,在左手手掌上倒出几滴香精来,把瓶递回侍女,两手一搓,先在脖子上一擦,又在嘴边上一抹,最后把手伸进衣领之中,在酥胸上揩了又揩。一名侍女进来禀道:“孔大夫已经在延英阁候见。”南子匆匆起身。卫侯道:“要不要我去陪客?”南子道:“你今天怎么啦?啰啰嗦嗦。你去了,还不成了你见客?”卫侯道:“好!好!我不去。我在这儿等你。”南子道:“你也不用等。我在延英阁见过孔丘之后,还会在留春轩设宴款待他,万一酒兴大发,再去春草池中泡一泡温泉也未可知,什么时候完还不知道。”说罢,向卫侯抛过一个媚眼,腰身一扭,疾步出门。
孔丘峨冠博带,长裾阔袖,垂手立在延英阁客席之上。随着一阵环佩“叮当”之响,一股幽香扑鼻而来。孔丘举目一望,正见南子从屏风后转出。孔丘拱手长揖,南子拱手还礼。寒暄既毕,南子道:“四方诸侯、卿大夫,凡是不齿于同卫君相交结的,也都不齿于同我相识。孔大夫德高望重,盛名远播,今日也肯赏脸,实在令我不胜感激之至。”孔丘道:“孔丘不才,既蒙卫侯以上宾之礼相待,又蒙夫人赐见,实孔丘之幸。”南子笑道:“孔大夫真是会讲笑话。我请孔大夫相见,少说也请了不下三四回了,每回孔大夫都借故推辞,这回如果不是靠公子朝的面子,孔大夫恐怕还是不肯赏脸。”孔丘听了,慌忙拱手道:“前几回夫人相召,孔丘委实不得分身,非敢借故推辞,夫人错怪了。”南子笑道:“如此便好。我不过讲句笑话,孔大夫切莫在意。”孔丘道:“不敢。”南子道:“我这人最不喜欢拘泥礼节,像你我这样分宾主站立,浑身上下不自在,何苦来哉?我已在阁后留春轩备下一席便宴,你我何不就此入席饮酒?”两名侍女从屏风后转出,南子吩咐侍女:“快将孔大夫引到留春轩去!”说罢,向孔丘拱手一笑,率先退下。孔丘不便推辞,只得随着侍女的引领,出了延英阁,顺一条回廊行不十数步,早到留春轩门前。侍女将门拉开,放孔丘进去。孔丘进到门里,四下一望,但见地铺猩红毡毯,壁垂绛红锦帐,四角各立一座青铜犀牛,犀牛背上架一座青瓦火盆,盆中炭火烧得正旺。中央设一方漆黑描金食几,两边各设一个锦绣坐褥。食几四隅各立一青铜丹顶鹤,鹤头顶一只红烛,烛光摇曳生姿,席前若明若暗。南子面门而立,见孔丘进来,口喊一声:“请!”早有两个侍女趋前,侍候孔丘在客席就座。南子自己在主席上坐了,又喊一声:“上席!”不移时,四个侍女捧着青铜托盘,从屏风后转入,将酒浆菜肴布满一席。南子吩咐侍女道:“孔大夫不喜欢俗人打搅,没有我的呼唤,你等不得进来,听明白了?”侍女点头,一一从屏风后退下。南子提起酒壶,先替孔丘斟满一杯,然后给自己也斟满,举杯齐眉,笑道:“请!”孔丘也举杯齐眉,应了一声:“请!”南子仰头倾杯,一饮而尽。孔丘浅尝一口,随即放下酒杯。南子似嗔似笑道:“饮不尽兴,是何道理!”说罢,隔着几案伸过手来,端起孔丘面前的酒杯,递到孔丘嘴边。孔丘见了,慌忙接过酒杯,把杯干了,道:“岂敢不尽兴?无奈酒量不行,万一喝醉了失态,岂不是得罪了!”南子听了大笑,道:“俗话说‘腊日飞雪,两情相悦’,不期正巧应在今日。既是两情相悦,何得罪之有?”孔丘听了,面呈赧颜,道:“孔丘一向只好《诗》《书》雅言,于俗话甚少留意。”南子听了,又放肆一笑,道:“听说孔大夫少时贫贱得很,连放牛牧羊的活都干过,哪能没听见过这句俗话?不过是害臊罢了。”说罢,又提起酒壶,要给孔丘斟酒。孔丘推辞不过,只好让南子斟满。南子放下酒壶,笑道:“‘来而不往非礼也’,这是雅言,不是俗话,孔大夫总该听说过吧?”孔丘道:“这话孔丘岂敢忘!”南子道:“虽然不敢,却还是忘了。”孔丘略微一怔,道:“此话怎讲?”南子道:“我已经给你斟了两回酒,你可给我斟过一回?这难道不是‘来而不往’么?”孔丘听了,不禁一笑,道:“原来如此。夫人不提醒,孔丘还真是忘了。”说罢,提起酒壶,便要给南子斟酒。南子见了大笑,道:“我不过讲句笑话,你何必这么认真?”说罢,便伸过双手来,将孔丘提壶的手腕抓住,孔丘心中一惊,手腕一抖,酒壶倾倒,酒洒席上。南子见了,一边大笑,一边松了手道:“看你紧张的!快起来,别让酒污了衣裳。”孔丘起身离席,南子也跟着起身,行到孔丘跟前,用手在孔丘胸前一摸,道:“衣裳已经湿了,还不快脱下来。”说罢,伸手过来,要解孔丘的腰绦,孔丘慌忙中向后一退,南子假做失手,就势向前一扑,跌倒在孔丘怀中。孔丘正不知所措之时,门外传来侍女的声音道:“孔夫人昏倒在地,不省人事,请孔大夫速回。”南子听了一怔,道:“孔夫人也真是病得巧,早不病,晚不病,偏偏赶在这时候病!”孔丘趁机将南子扶起,道:“天有莫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生病的事由不得人做主。荆妻既病,孔丘不敢久留,不能终席,失礼得很,还盼夫人谅解。”南子略整衣襟,对孔丘道:“除夕之夜,卫君例率执政乘花车绕市一周,以示与民同乐之意。我已经同卫君讲妥,今年除夕,破例请孔大夫随行,盼孔大夫万莫推辞。”孔丘道:“夫人如此盛意,孔丘敢不遵命!”说罢,拱手长揖而退。
孔丘匆匆出了春草园大门,望见子路驾车在门口等候,慌忙登车,遑遑然如漏网之鱼。子路闻到一股女人气息,眉头一皱,道:“夫子怎么一身脂粉气息,难道同南子有了肌肤之亲?”孔丘道:“休要胡说!南子不过在我胸前跌了一跤。”子路听了,发一声冷笑,道:“有这等巧事!南子这一跤,哪不能跌?却偏偏要跌在夫子怀中?”孔丘听了,也发一声冷笑,道:“天下的巧事多了!夫人怎么早不病,晚不病,偏偏赶在这时候病?”子路听了,略微一怔,道:“夫人昏倒,难道是做假?”孔丘不答,却道:“女人都会做假。”子路道:“原来如此。”孔丘道:“天机不可泄露!”子路道:“弟子明白。”说罢,挥手扬鞭,拉车的黑马放开四蹄,踏雪而去。
除夕之夜,卫侯朝服衣冠、南子金玉盛妆,并肩立在一辆敞篷花车之上。花车在仪仗与卫队前呼后拥之下,驰出宫门,往南市方向而去。孔丘峨冠博带,也乘一辆敞篷花车,由子路驾着,尾随其后。楚丘南市广场,灯火通明,人潮涌涌。卫侯与南子的花车缓缓驰入市场,南子在车上左顾右盼,频频挥手,眼波流动,媚态横生。围观的人众欢呼雀跃,争相追逐。等到孔丘的花车驰入市场之时,人群大都随卫侯与南子的车队而去,剩下来的无非是跑不动的老弱病残,一个个只顾摇头叹息,并没有谁扭过头来看孔丘一眼。孔丘见了不悦,对子路道:“这哪是与民同乐,不过是让南子得个搔首弄姿、招摇过市的机会而已!”子路笑而不答。孔丘发一声感叹,道:“人要是能像好色一样好德就好了!”子路道:“夫子因鲁公好色而离开鲁国,如今卫国举国上下好色如此疯狂,夫子难道还能留在卫国不走么?”孔丘道:“丧家之狗,何去何从?”子路道:“上次夫子去陈,司城贞子待夫子十分殷勤,以我之见,何妨再去他家做客?”孔丘不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