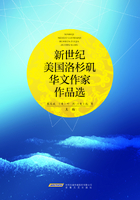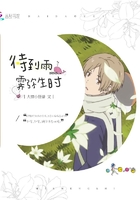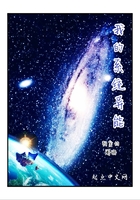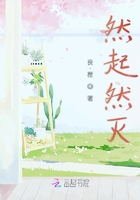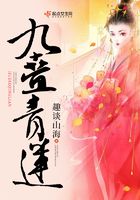时间越过了“大跃进”,越过了“右派”摘帽,越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20年后,不为人知的丁玲,从北大荒、秦城监狱、山西老顶山公社嶂头村,重新回到人们视野中。
白发苍苍,两颊松垂,一个邻家老太太。
老去的不仅仅是容颜和外表,逝去的也岂止是时间和岁月。
有必要复述一下本文先前曾经描绘过的那个丁玲:
她的个性,不单毫无温良恭顺、俯首低迴的传统的中国女儿态,连传统中国男人所擅长的虚与委蛇的心态和行径,也被排斥和蔑视。她原本是不懂得掩饰自己的。长久以来,她谈吐畅快,举止豪放,笑怒随意。她生命中的苦主之一刘白羽,1992年在长篇回忆录《心灵的历程》中,这样描述1937年第一次见丁玲时的印象:“丁玲披了一件黄呢子日本军大衣,她笑得那样爽朗,酣畅,明亮。”这笑声,也会出现在某些头脑简单的人身上,但丁玲不是;丁玲如此,主要是极其自信,对自己的才华和内心极为骄傲,别人从她笑声中接收到的,也是同样的信息。
应该记住这样一个丁玲,就我个人而言,经由阅读存在于心目中的,只有这个丁玲。然而,这个丁玲一去不复返了!
1955—1957年挨整期间,丁玲认过错,却从未低过头。不如说,即使认错的时候,别人也清楚地感觉到她的骄傲,那种与生俱来的她个性中根深蒂固的东西。
1963年,“右派”摘帽工作开展过程中,丁玲从北大荒给她的“死敌”周扬写思想汇报时这样说:
我有一个要求,我希望党根据自一九五八年我到农场以后,五年多来的一贯表现,对过去错误的认识,和对党的态度等,摘掉我的右派帽子,准许我回到革命的队伍里来。……我向党保证:决不重犯错误,我一定全心全意、一心一意、老老实实听党的话,服从领导,做党的驯服工具,为革命,为无产阶级埋头工作,奋斗到底。
多么可怜的措辞和语气!《始末》评论道:“简直是低声下气地哀求了。”收件人周扬读着里面的每一个“党”字,当不难于体察书写者寄寓其中的多层意思。
这是那个傲人的丁玲么?韦君宜说:“从人来说,我对周扬是较有好感的,因为他不摆架子,对待我这样的年轻干部也很亲切,而丁玲则有一点傲气。我对郭小川说过,他说,他也跟我有同感。”(《思痛录》)
因为傲而直,因为直而傲,是丁玲给所有人的印象,也是她几十年行走文坛、闯江湖一贯不改的风貌和个性标志。但是,命运的播弄终于使这个人丢掉了骄傲,同时,也丢掉了直快。
她竟然开始耍起了“心眼儿”!1978年,“四人帮”倒台两年后,为了能回北京,身在僻壤的丁玲深谋细虑,一封又一封地写信给只身去北京“活动”的丈夫陈明,巧为布置。
“不必多找人,但也不躲人,理直气壮些,但少说多听,沉着老练。”(12月10信)
“这些文章(前一封信,她说打算去一趟北大荒,搜集素材,写写王震)还是容易出货,现在要拿货,长篇可以留着慢慢写。你若有文章见报,人家不管你写得好不好,只注意你是‘出’来了。……老说治病,人家就怕麻烦,我不治病,只要去了,就能治病嘛。你有劲头,人家也愿帮忙。我去东北,找王的材料,写王,他为什么不帮忙呢?”(12月16日信)
“我想你走前去看看周伯伯(指周扬,此处是借用子女们对周扬的称呼)也可以。只说你去北京的目的和情况,说我身体还可以。糖尿病有些影响,还不十分重要。将来也还是要见面的。假如我去,也会看他的。反正他也受了‘四人帮’的迫害,就表示一点对他的同情罢。”(12月21日信)
曾经那样孤高、鄙薄权术、自认为不耐在官场虚与委蛇而拚力从高位上抽身的丁玲,而今是这样娴于“政治”、工于心计。没有任何理由指责她什么,年过七旬,流落在外二十年之久,病痛缠身,老境益增,还不得不为找回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日夜焦虑、失眠……这样一个人,这样一种景况,只会让人辛酸、慨叹罢了!
宋之问《渡汉江》说:“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也许,当苍老、衰迈的丁玲,一步步从太行山另一侧向阔别二十余载的北京走来时,是她的故旧以及全中国的文学读者们“不敢问来人”——她,还是那个目光炯炯、英气勃发的女中豪杰吗?
1979年7月18日,丁玲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再版《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所写的《重印前言》,在《人民日报》发表。重新亮相于党报,意义非常。她在里面以极其饱满的热情缅怀和称颂了毛泽东。“文章发表后,张凤珠去友谊宾馆看她,对她这种心情表示难以理解。丁玲笑了笑说:看来这20多年,你政治上进步不大。”(《始末》)
重新回来的丁玲,终于在政治上成熟了——在70多岁的时候。
为回北京而奋斗的那些日子里,丁玲在日记中写道:
忆几十年大好年华,悄然消失,前途茫茫,而又白发苍苍,心高命薄,不觉怆然。惟有鼓起余勇,竭力挣扎。难图伸腰昂首于生前,望得清白于死后,庶几使后辈儿孙少受折磨,有发挥能力的机会,为国为民效劳而已。
此为真实的丁玲,内心的丁玲;字字沉重,睹之令人热泪难禁。
心比天高的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四杰”之一的丁玲,此刻只存下一个念想了——为儿孙计,为亲人计。她将“鼓起余勇”,于瞑目之前挣脱套在脖子上的政治枷锁。
1984年7月25日晚10时,陈明先生得到消息,中共中央书记处已经批准了《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翌日,“在医院中”的丁玲获知此讯,脱口而出:“这下我可以死了!四十年沉冤,这次大白了!”
请注意,她说的是“四十年的沉冤”。在她心中,一生的厄运,并非从1955年算起。
她随即取来录音机,留下这样一段话:
我死了之后,不再会有什么东西留在那里,压在我的身上,压在我的儿女身上,压在我的亲人身上,压在我的熟人我的朋友身上,所以,我可以死了。
痛哉斯言!
一年多以后,1986年3月4日,丁玲在京逝世。距今整整20周年。
她活了82岁。“丁玲”这名字第一次出现,在1927年(短篇小说《梦河》);是年,她23岁。51岁以后,“丁玲”基本停止了文学写作。减去前23年和后31年,在全部82年人生中,作家“丁玲”,只存在了28年。今天,铁凝49岁,王安忆52岁;她们的创作却都正处在蓬蓬勃勃的鼎盛期。
1955年,丁玲留下刚刚开头的长篇残稿《在严寒的日子里》,果真走进了“严寒的日子”;随后,“几十年大好年华,悄然消失”!
铁凝的恩师、丁玲的弟子、《平原烈火》《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将50年前的亲身经历记述下来,书名《昨夜西风凋碧树》。非常恰当的书名,所以我也把它用为本文的题目。
在“丁陈反党集团”案中凋谢的,不仅仅是丁玲这么一个人,这么一个年富力强、才具卓拔的女作家。
徐光耀写道:“他们(批判会上奋起批判丁玲的文坛诸公)往日在旧社会、与国民党作斗争的时候,都是品德高尚,注重名节,从不胡说八道的,如今却顺着大势,作些连自己也未必清明的所谓‘批判’,捕风捉影,胡乱扣人帽子。他们都是有资格名垂后世的,此后,当他们面对后人,要出全集的时候,再重翻这些‘发言稿’,还能找到法子安放这些尴尬吗?”
然而,又必须面对——不仅仅是“他们”,包括作为后人的我们,包括整个中国当代文学,都应该去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