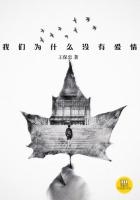清晨的广盛楼后院,寂静无人,仲夏阳光笼在晨雾里,温暖而迷离。后台有几位师兄弟早到,似乎是在对戏,零星飘来几句唱腔。天青只穿一条单裤,赤着上身,坐在小屋前,给自己的厚底靴刷大白。
戏里的靴鞋,大约是与伶人最亲密的物件之一吧。其他行头大都是官中的,伶人轮换穿用,只有角儿们有自己的私房;但是靴鞋,每个伶人都得自备。因为一双靴鞋合不合脚,对戏台上的表现,至关重要,尤其唱武戏的,要在腿脚上见功夫,必须用自己穿熟了的靴鞋。伶人随身带的衣物包袱,都叫“靴包”,里头除了点贴身衣物,主要就是这双靴鞋。
武生的靴鞋,短打用薄底,长靠用厚底。薄底靴倒也罢了,和平时穿的布鞋,差别不多;厚底靴的学问,可就大了去了。这是一双青缎子做的长筒靴,靴底厚达两寸或两寸半,花脸的靴底更是足有三寸厚,穿起来显得整个人高大雄伟,气势非凡。这厚底看似木制,其实是以千层麻纸叠压而成,每双厚底都要历经一年左右的压制,坚韧、结实,侧面刷成雪白,牛皮封底,轧着细密的麻线。这样一双靴子,分量可想而知,外行穿来,抬脚都难,但“厚底功”是伶人熟习的功课,个个都能穿着厚底奔走如飞,在台上翻打扑跌,全不以厚底为碍,反而独有一番英武之美。
天青仔细地用小刷子,给靴底涂着大白,行内管这叫“粉厚底儿”。师父教导,伶人登台,要做到“三白”:护领白、水袖白、靴底白,一身上下,干净整洁,才对得住戏。以往天青唱戏时,这厚底每隔几天就要粉一次,每次登台都是雪白闪亮一尘不染;去年受伤至今,没有再碰过它,上面隐隐地泛了灰黄。靴子和人一样,也都要常练、常用,才有生气啊,搁置了这么久,都不知道要耗费多少心血,才能让它重放光彩。其实,既然不是登台,本也不必去粉它,但是天青在伤了这么久之后,终于可以再用上它,那么,重新粉一粉,似是给它,也给自己一个交代。
全部粉好了,天青放下刷子,拎起靴筒,小心地把脚伸进靴子。左脚还好,右脚伸进时,仿佛走进了一个从没去过的胡同,触脚所及,全都是陌生的感觉。他扎好靴筒上的带子,扶着墙,站起来。右脚的脚底很不舒服地蠕动了一阵,慢慢地,慢慢地踏稳。
他比平时高了两寸半。这是他熟悉的高度,能够施展所长的高度,他喜欢这个高度,习惯这个高度。吸口气,煞紧腰,笔直站在那里,戏台上的感觉依稀回来了。他告别这个感觉,已经整整九个月。曾经一度,都以为自己再也回不到这个感觉了。陈少湖说,二次手术后,五个月才能重新开始练功,天青不敢违背、按照他的嘱咐,老老实实地,一天不差地等到了这一天。
“天青哥!”
声音随着人一起飞过来,是樱草,穿一件月白的短袖小袄,黑裤,抱着一只食盒:“你怎么开始练功了,少湖说可以了吗?”
“他说五个月,就是今天。其实我觉着上个月已经成了,放心吧。”
樱草放下食盒,走过来搀起他的手臂:“真的成?你慢点!”
真的成了。踩着这样的厚底,也稳稳地在院子里走了两圈,虽然脚上依然有些异样,但是越走越熟,越走越有信心。天青跳了两下,落地无声,抬脚轻轻一踢,一点都没有痛,这辈子从没有这样清晰地感觉到,他有腿,完好的腿,自己的腿是自己的腿。晨雾已散,升在半空中的太阳,尽情普照大地,天青觉得全身温暖,一股热流从心里往外地迸发出来,他大吼一声:
“我好了,我全好了!”
樱草摇着他的手,弯弯的嘴角旋出深深梨涡,眼中溢满喜悦的光彩。阳光在她的小圆脸上勾出一道金边,瓷一样光洁的脸颊也微微反射着亮光。天青抑制不住满腔情意,猛地捧起这张小脸,不容分说地,就在这广盛楼空荡荡的院子里,深深吻上她的唇。
“樱草,全亏有你。”
樱草被他紧紧拥在怀中,紧贴着他赤裸的胸膛,那一块块隆起的肌肉,光洁而温热的皮肤,都发散着清晰可闻的男性气息,令她头晕目眩。她羞怯地低了头,轻声问道:
“这就能上台了么?”
“现在可以站堂了。再练两个月吧,就能唱几出自己的戏,难些的呢,大约还得过半年。唱老生戏可以快一点,但是我……还是不想放弃武生。我相信有少湖兄的高明医术,这条腿可以帮我迈回武生行,我会好好操练,把这些日子抽掉的功,都找回来,有朝一日,准定让你重见我的赵云,我的武松,我的陆文龙!”
“不急,我们慢慢等。”樱草的声音,低不可闻,“我等你重新登台亮相,唱好第一出戏,然后双手抱我入洞房。”
天青笑了,明朗的面庞上,带着孩童般的顽皮与纯真。他手臂一紧,又将她拥入怀中,额头抵着她的额头:
“我有点……后悔说了这话!”
时入九月,秋荫正浓,乔双紫家里来了一位客人。
“他檀叔,你可回来了!铭翠呢?”
檀叔名唤李宝檀,是三婶的亲戚,从事皮货生意,半生走南闯北。乔双紫夫妇原有一女,小时候得病夭折了,多年后才得了铭翠这个儿子,爱逾珍宝,一心盼他成才。铭翠少年时候起,就跟着檀叔出门学做生意,专跑东北线路,业务搞得挺兴旺,最近都无暇回家。
“铭翠啊,他……留在锦州了。”檀叔比乔双紫小很多,但是常年出门在外,面貌沧桑,看着十分苍老。他以前回来,都是规矩的商人打扮:瓜皮小帽,缎子长衫、马褂,唯独这次,像个老农民似的,穿着一身短裤褂,系一条布褡包,大热天戴了个遮头盖脸的帽子,肩上扛了个小包袱,整个人风尘仆仆,进门就栽在藤椅里,仿佛累得喘不过气来。
“锦州那边很不太平啊。看报上说,年初时被日本人占了。还有生意可做么?铭翠怎么不跟你一起回来,是不是这小子不听话?他最近身体硬棒不?”三婶一边张罗茶水点心,一边急切地问。
“他挺好的,听话,能干,我年纪大了,这些年全凭他帮手,才做得下来。”檀叔将肩上包袱放在地上,接过三婶递上的茶碗,一头埋在里面。
乔双紫吸了口烟,操着烟锅子,将椅子往前拖了拖:“怎么没一起回来,他檀叔?遇着什么事了?”
“嗯,不太顺利。”檀叔喘了口长气,慢慢地开口,“我和铭翠,还有两个伙计,起初是在沈阳。后来日本人打进去了,我们就想回北平来,但是没走成,在城里困了一个多月。那时候生意已经没法做了,街上乱哄哄的,动不动就杀人,我们整天就关着门躲在屋里头。后来我们寻思着,老这么待下去,迟早是个死,还是得逃出去。我们四个就把东西打点好,找了个时机,分头逃了。”
他自己给自己又添满茶水,不顾热烫,一口喝干。乔双紫夫妇都焦急地盯着他。
“而后我们到了锦州。进城没几天,日本人就来围住了。新年时,把锦州也占了。没法子我们又逃。铭翠那孩子,真能吃苦,东西都是他扛着,一路上护着我。我们没敢走大路,想从小路出去。”
“不是留在锦州了么?”乔双紫问道。
“嗯,留在锦州了。嗯,没逃出去。我们要过女儿河,没有船,好不容易找着一条铁路桥,想从桥上走过去。结果桥上有日本兵的卡子。”
又灌了一碗茶。
“檀哥啊,你快点说啊,到底怎么了,是不是出事了?你们跟鬼子打起来了?”三婶一只手抓着自己胸口。
“我,我不知道怎么说,姐。没打起来。我们一看有卡子,转头就往回走,但是日本兵拿枪指着,喊我们过去。他们把我们的包袱都收了去了,还搜了身,身上稍微值钱一点的东西,都拿走。铭翠不干,想抢回来,我拦着,说千万别动手。我寻思着,我们两个身上什么都没有,总能放了。结果,后来,我才,听人说,鬼子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不走公路走小路的,都,不放过……”他越说越结巴。
乔双紫夫妇都瞪着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他。
“我站在桥边上,一看他们举枪,拉着铭翠就往河里跳,枪响了,打着了我的耳朵,”他除了帽子,露出光秃秃的残耳,“我也顾不上了……河水挺急的,冲得我们往下游漂,我拼死拉住了铭翠,一直没放开他,后来,好远,可算,够着了岸,我拉了铭翠一起上来……姐,姐夫,你们稳着点,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三婶呆坐着,一声不能出,乔双紫紧紧攥着烟锅子:“你说吧,只要他还留着命,怎么都成。”
檀叔停了一会儿,手里哆哆嗦嗦,帽子落在地上。他人也从椅子上出溜下来,跪在乔双紫夫妇面前:
“姐,姐夫……我没能保住铭翠……他中了子弹,在胸前,上岸时,已经……”
乔双紫猛地站起来,三婶仍然呆坐着。檀叔哆嗦着拿过放在地上的包袱,打开:
“我没法带他回来,就埋在……那儿了……我不敢再来见你们,但是想来想去,还是得……我带回了……他的马褂……我对不起你们……”
他捧着打开了的包袱,高举过头。
三婶终于动了,她伸手接过马褂,往胸前一捂,随即整个人瘫倒在地上。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
此事,古难全。
福运并没能眷顾白家所有人。尽管大家忧心祈祷,尽力救治,但三婶终于还是走了,未能留下一句话。
乔双紫像失了魂魄一样,完全成了个木头人。从装裹到出殡,全是白喜祥和天青帮他做主,他自己怔怔的,要他干什么,就干什么,要他怎么说,就怎么说。一向魁梧的身材,现在干瘪下来,两颊颧骨高耸着,满脸黑胡子都连了鬓。
送葬回来,白喜祥拉他到堂屋里,陪他坐着。堂屋桌子上,供着三婶遗像,和气的,喜兴的,笑得满脸麻子都放着光。
足足沉默了一个多时辰,乔双紫终于开口说了话:
“大哥,我要走了。”
白喜祥一愣:“去哪儿?……你,不是要想不开吧?”
“不是。我想了几天了,刚刚定了心盘。我要回东北去,替我儿子和媳妇报仇。”
“怎么,报仇?你赤手空拳的……”
“大哥,”乔双紫抬眼看着白喜祥,“当年你怎么救我的,还不知道么?我想报的仇,准能做得到。”
“那不一样!鬼子有枪!”
乔双紫冷笑一下:
“他有枪,架不住我拼命。我想好了,找个合适机会,顶少杀三个,我就够本,再多杀几个,我就赚到。咱们中国人要是都这么跟他拼命,鬼子早滚蛋了。”
白喜祥手中茶碗颤抖起来:
“你是说,你不回来了?”
“我是抱了必死之志,大哥,你不能拦我。我以前也觉得鬼子离咱们挺远,他们爱在东北闹腾,就闹腾去,那都是当官的该管的事,轮不着咱们操心。可现在不一样了。他们闹得我家破人亡,我一身的血仇!……大哥,我这条命,本也是捡回来的,若没有你,四十年前我已经死了,今天我谢谢你四十年的深恩,以后,你就当没有过我这个弟弟。”
乔双紫站起身,双膝跪地,郑重对着白喜祥磕下头去。
白喜祥泪水纵横,也跪了下来,扶住他臂膀:“双紫!咱们四十年老兄弟,别说这样的话。你是有志气有胆识的好男儿,做哥哥的一直敬重你,如今你这也是要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为国为民,舍生取义,我绝不拦阻于你。什么时候走?我去拿些钱,给你路上用。”
乔双紫拉住他:“不用了,大哥。这辈子,我已经报答不起你这份恩情。我一个人上路,有粥吃粥,没粥喝水,用不了多少,你放心吧。这事儿,你自己知道就成了,别跟孩子们说,免得他们挂心……”
樱草和天青坐在檐廊栏杆下,担忧地听着堂屋里的动静。忽然门开了,乔双紫快步走出来,经过两人身边,猛地站住,盯着他们看。
“三叔……”两人肃然起身。
乔双紫伸手拍拍天青的肩,又摸了摸樱草的头,停了一会儿,说:“樱草,天青,我等不到你们成亲了,对不住。我大哥……拜托你们了。”
说罢,头也不回地冲进东厢房自己屋子,关上了门。
孩子们记忆中的三叔,是个铁金刚一样的汉子。那魁梧高大的身形,粗黑的肤色,下巴上生着长毛的大黑痦子,还有那铮铮闪亮的眼神,看着都教人害怕。同样是穿长衫,他穿起来,如一座雄伟的塔,跟白喜祥穿起来那个文雅的气派,完全不一样。只有在戏台上,他才是那个稳健端凝的好鼓佬,手中一双鼓楗子,声声点点,都是天籁之音。
三叔不是白喜祥的亲弟弟,这大家全都知道,但是三叔到底是怎么变成三叔的,无论是三叔本人,还是白喜祥,都没对这几个孩子说起过。樱草和天青只从乔三叔的寥寥数语里听说,他年轻时候,在牡丹江谋生活,是逃出来的。
“师父,你们怎么了?”
乔三叔离开之后,天青和樱草进了堂屋。樱草忙着为白喜祥投了热面巾,沏上茶,端个小板凳坐在爹爹膝前,给他捶腿;天青也在下首的椅上坐下来,担忧地望着师父。
白喜祥仿佛又苍老了好几岁,动作都迟缓许多。他拿起面巾,擦擦脸,疲倦地说:“你乔三叔……要去投亲戚。”
“他亲戚在哪儿,牡丹江?现在牡丹江让鬼子给占了呀。”
白喜祥望着堂屋外面,东厢房的房门,出了好一会儿神,喃喃道:
“牡丹江……好像都是,上辈子的事了。”
“您年轻时候也去过?”
“是呀。”
白喜祥埋藏了四十年的记忆,缓缓释放出来:
“你们知道,我也是贫寒人家出身,父母亡故得早,打小就自己谋生活。出科之后,走南闯北,到处搭班,因为是大科班出来的,技艺过硬,班社都愿意要。到牡丹江那年,我二十岁,当时那个班主看我性格稳重,要我帮他照看班里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