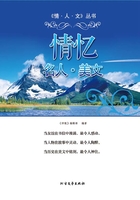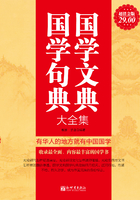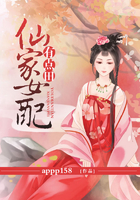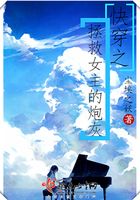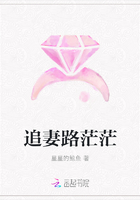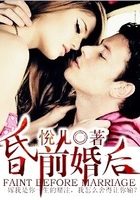曹操《短歌行》赏析
◎王富仁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矜,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沈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讌,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曹操:《短歌行》(其一)
“三百篇之后,曹操的四言诗,最为杰出。”(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册第254页)这个评语,至为精当。但为什么在三百篇之后,四言诗衰落了下去,而到了曹操这里又回光返照,突发异彩,而后又一蹶不振,从此息影于文坛?这个原因,似乎还没有人细谈。现在我谈点未必正确的意见,以贡献于大方之家。
三百篇以四言为主,我们称之为四言诗,以与后来的五言诗、七言诗、长短句(词)和现代的自由诗相区别,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但我认为,《诗经》的四言诗的“诗”和后来的五言、七言诗的“诗”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严格说来,《诗经》中的诗好,并不在于它们是“四言”诗,而在于它们的抒情状物、叙事表意,在于它奠定了中国诗歌发展的基础,形成了中国诗歌意象系统的基础构架,但作为四言之诗,我们读的时候,会感到它的词语的节奏与其表达的情感本身并不十分协调,读起来有些硬,与所抒之缠绵悱恻或欢快愉悦的情绪格调不统一。这个原因何在呢?因为它原本不同于后来我们所说的诗。后来的诗是文人的个人创作,是为读的,不是为唱、为舞的,而单纯为读与同时为唱、为舞是有巨大差别的。读,是以词语的节奏为节奏,唱则是以曲谱的节奏为节奏,它严重地改变了词语本身的节奏,这种区别就是现在的诗与歌词的区别。若歌舞同时,以歌伴舞,其歌的曲谱又要接受舞的限制;舞的节奏是人体形体动作的节奏,与歌的声音的节奏是有分有合的,有些歌的节奏难以用形体动作来表现,而形体动作的节奏也并不都能合于音乐的节拍。这样,用于歌与舞的词就与单纯读的诗有了很大区别。我们知道,《诗经》的“诗”,是诗、歌、舞的综合体,而不是后来我们所说的诗,用现代的话说来,它们实际是舞曲之词。过去我们有一种说法,好像《颂》与《雅》是为舞与乐所撰之词,而《风》则是为诗谱曲,先有诗而后有乐、有舞。这就是元代吴澄所说的:“《国风》乃国中男女道其情思之辞,人心自然之乐也。故先王采以入乐,而被之弦歌。”“《风》因诗而为乐,《雅》、《颂》因乐而为诗,诗之先后与乐不同,其为歌辞一也。”(《〈校定诗经〉序》)我对这个说法有所怀疑。我认为,不论是《颂》、《雅》,还是《风》,在其起源的意义上都是诗、歌、舞的一种综合性行为,如若按照吴澄的说法,好像那时的民间有些像我们现在的诗歌爱好者,一有感触,便写出或读出一首诗来,待到被王的乐官采去,才谱以音乐、被以管弦,用于唱,用于舞。
实际上,这在古代是极难想象的。说的行为本身是不会演化为诗的,因为说较之诗更有明确性,诗在开始时必然是与歌相伴随的行为,及至歌成,其词才作为一种独立的语言形式从歌中独立出来,成为后来的诗,而在人们有了独立的诗的概念之后,才会想到用诗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感触。直至现在,还有很多人一生有很多感触而想不到用诗表达,因为在他没有一个诗的独立概念之前,是不会自然地做出诗来的。农村的诗人很少,但歌手颇多,他们的歌词与他们的歌唱行为是同时产生的,欲歌方有词,无歌便无词。《国风》不但与歌同体,与舞大半也是同体的。只不过《颂》和《雅》的歌、舞都是有组织的行为,而《国风》的歌、舞大半都是即兴的自然性行为。汉族人的“严肃”,是后来的事情,是在礼教制度发达起来之后。只要看一看现在的儿童,就知道任何一个民族的童年时期都是很活泼的。儿童在会做诗以前,就会咿咿呀呀地唱出一些歌来,就会蹦蹦跳跳地跳出一些舞来,他的歌有词,其词有意义,是在后来的事情。在三百篇成书之前的汉族人,也必然与现在的一些少数民族一样,是能歌善舞的,《国风》就是那时歌、舞中的唱词。《国风》的艺术上的一个重要特点的复沓就是与歌舞同体的有力证明,并且更与舞有关。中国后来的诗大都很短小,因为用文字表情意,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言尽意犹在,不受文字长短的太大限制,歌、舞则不同,歌必须有一定的长度,唱了四句就不唱了,你会感到歌才开头,还没有酝酿成一定的情绪。舞就更是这样,一首短诗不成歌,一首短歌不成舞,舞的时间要有更大的长度,才会造成一定的气氛。《国风》当记录为诗的时候,肯定还是以词义为准减少了复沓的次数的,但即使如此,这复沓本身就显示了它与歌,特别是与舞的结合。不过在乐官搜集时,舞与乐难以记录,主要记下词来,然后再重新配曲,用于歌舞,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并不能说《国风》是先有诗而后有乐、舞。
《诗经》之诗是诗与乐、舞的统一体,所以就不能用四言说明它的艺术上的特征,因为它的节奏和韵律不是由它的词语本身所决定的。我在初中上学时用的是《文学》课本,它的第一册的第一课就是《诗经》中的《关雎》,那时是作为诗读,其意境、其描写、其所抒之情当然还是觉得出的,但读起来硬硬的,感觉不到诗本身所抒发的那种缠绵的情思,后来学口琴,在一本口琴曲集中,看到瞿希贤为《关雎》谱的曲子,我就用它来练习吹口琴,口琴虽然没有学会,但我却知道在为这首诗谱上曲子之后,其韵味与它所表现的感情情绪就会非常和谐了,就不会感到硬邦邦的了。音乐改变了词语本身的节奏,所以《诗经》中的诗严格说来不一定就是四言诗的节奏。作为纯粹的诗创作,屈原是我国诗歌史上的第一块丰碑。他的《九歌》也是写来用于歌舞的,但这只说明了他与中国以往传统的连续性,即使这些诗,也是他的个人的创作,只不过他要照顾歌舞的需要,其可读性和个人性开始上升为主导的因素。至于他的《离骚》,则完全是诗的、读的,是个人情感和情绪的表现。屈原的诗就句法而言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十三言,一是六言。十三言实际上是两个六言的连接,中间用一个语气词“兮”连接起来。而这两个六言按照我自然形成的习惯性读法,前三字一组,后两字一组,中间一个字轻轻带过,因而它的主体是一个五言。以《离骚》的首句为例: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兮”是一个语气词,起到连接前后两个六言的作用。去掉它,便成了两个六言句:帝高阳之苗裔,朕皇考曰伯庸。在前句中“之”是一个轻声字,在后句中“曰”是一个轻声字。去掉它们,剩下的是两个五言:帝高阳苗裔,朕皇考伯庸。屈原诗中的六言中间同样以一个“兮”字作连接,去掉它就是一个五言的形式。如《湘夫人》的头两句是“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去掉“兮”字,是两个五言:帝子降北渚,目眇眇愁予。所以,我认为,屈原诗的最基本的形式,实际上是五言的。他不用四言,说明四言诗对表现他的感情情绪是不适用的。十三言的形式是主观抒情性的,那种内心的郁闷随着徐长的语流宣泄流淌;六言的形式在屈原的诗里是叙述、描写性的,作者的感情隐于事件和情景的幕后,词语的节奏不是作者内部情感的表现形式,是便于读也便于唱的。
《诗经》中的诗是诗、歌、舞的综合性行为,但一当诗在这种综合性行为中被独立出来,它也就可以成为一种独立被运用的形式。三百篇被搜集整理之时,也就是中国文人(“士”)这个阶层走向独立的时候,文人的个人独立的创作开始盛行。在思想界有诸子百家,在文学界有屈原及屈原的后学们,同时也自然会有人模仿三百篇的形式做诗,从而流及两汉。但当文人模仿三百篇写诗,其行为与原来的三百篇就有了本质的不同。文人的创作是个体性的行为,他不像原来的三百篇的无名的作者们,是在即时性的行为中进行创作。歌喉一开,舞步一起,歌词伴之,虽然粗糙,但与其情其景,声气相应,多次重复,多次修改,一经定型,便臻佳境。文人离开歌舞,离开群体,独自造词,并且拘于原来四字一句的形式,就不易创作出好诗来了,即使有堪与三百篇中的诗相媲美的个别作品,前有三百篇,也不再为人所重,故四言之诗,三百篇后,顿时衰落。骚体诗外,汉代的乐府诗兴。
乐府诗虽也是由诗官从民间采集而来,但它与《诗经》中的诗已经有了本质的差别。我认为,这个本质的差别就是乐府诗已与舞脱离。从产生三百篇的时代到产生乐府诗的时代,中国的民间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春秋末期到汉的建立,这是一个战争频仍的漫长的时代,秦的短暂统一,又强化了中国的文化的统一意识,它的繁重的徭役直接影响到底层人民的生活。我认为,这个时代,是中华民族迅速“严肃”化的时代,民间的歌舞娱乐之风已远非产生三百篇时的情景,人们对自我生活命运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自我心灵愉悦程度的关注。汉代的统一局面形成之后,儒家的礼乐制度遂成为中国社会的统一的规范,中华民族从此一直“严肃”到现在,产生三百篇的歌舞娱乐的风气也从此与汉族人民无缘。儒家礼乐制度对民间社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在此之前,社会的集体性活动分为平等的两类,一类是严肃之事,一类是娱乐之事;前者如对外的战争、集体性的生产生活活动,后者就是娱乐、喜庆活动了。一个社会成员在前类活动中既行使自己的权利,也尽自己应尽的义务,而在后一类活动中则享受自己最大的自由,像古希腊的酒神节和我国少数民族的泼水节一样,打破一切可以打破的常规,做一次集体的“疯狂”。在这样一个社会的成员,在社会中求生存,也在社会中求欢乐。但自从儒家的礼教制度成为中国社会的基本行为规范,就把所有集体性的行为都变成了严肃的行为,人们在这些行为中都只感到规范的束缚而失去了自由的感觉,因而自由成了个人之事,限制自由成了社会集体性的职责,纯娱乐性的歌舞之事就被严肃的礼乐活动取代了。与此同时,文化教育事业却得到了持续的发展,虽社会动荡,时代变迁,但求学之风仍然日盛,到汉代,文化事业已成规模,社会上读书识字的人多了起来,诗作为一种独立的表达方式也成了他们的一种自觉意识,不在歌舞之时也会想到用诗的形式表达自己的生活感受,有感即发。上述这两种同时出现的文化发展趋向,决定了汉代乐府诗与三百篇的根本差别。汉代乐府诗实际已经不是群体化娱乐活动的产物,因而也与舞脱离了关系。与音乐,还有一定关系,但诗的独立性显然更大了。我认为,只要我们细细体味乐府诗自身的情味,我们就会感到,它们在开始的时候,都是个体人的创作。不但像《孔雀东南飞》这样的长诗必然先有一个人编成全诗的雏形,就是像《战城南》、《有所思》等诗,也都表现着明显的个性特征,题材的独特性、视角的个人化和表现手法的创造性都比三百篇有了显著进步。这到了《古诗十九首》,就成了不易的事实,虽然我们无法确定它们的具体的作者,但它们作为下层文人的自觉创作则已为我们所公认。《古诗十九首》之后,乐府诗体为上层文人所接受,遂成了他们个人的自觉创作,虽还在名目上保留着与音乐的关系,但在实际上已不被作为唱词而创作,正像后来陆游、辛弃疾的词不是为唱而写一样,与乐的关系就不再是一体化的关系,不再是由乐兴词,而是由词及乐。由乐兴词,词随乐出。乐是主要的,由乐的情调决定诗的情感特征;由词及乐,乐为词变,词是主要的,由诗人的感情情绪决定他采用何种音乐形式。前者的词完全是为唱的,后者的词首先是要读的。为唱的词不必斤斤于词语本身意义的丰富和节奏的起伏变化,为读的词则必须充实自己的意义,注意词语的节奏。不懂外文的可以听外国歌,但却不能读外文诗,因为音乐主要是一种声音的艺术,诗才是语言的艺术。在这种情况下,乐府诗就与《诗经》中的诗大相径庭,如果说《诗经》中的诗还不是现在意义上的诗,而乐府诗虽也来自民间,但它同来自上层文人的骚体诗一样,都是现在意义上的诗创作,是一种独立的语言艺术,不再是声音和形体动作艺术的附属物。在诗的形式上,它主要不是四言的,除了一些不规范的因素外,五言是其主要的形式。中国古代的五言诗与乐府诗的关系已经不仅是偶然的巧合,而有了明显的继承关系。
从以上的叙述,我认为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中国古代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创作,从一开始就是以五言为最基本的形式的,只不过那时候还没有形成固定的规范和明确的意识,诗人们还完全自由地使用着对自己合适的形式,因而它必然主要以各种变例的形式存在着,直至五言诗正式形成,它才成了一种自觉的语言规范。为什么一到了诗人的创作,四言的形式就被抛弃而逐渐趋向了五言呢?因为作为“诗”,四言有比五言更大的局限性。钟嵘说:“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邪?”(《〈诗品〉序》)钟嵘这里所说的“五言居文词之要”可谓不易之论。中国的汉字,是单音节的,一字一音,一字一个音节。作为意义的单位,或一字一义,或二字一义,不像西方的文字,一个词可以由多个音节构成,所以一字、二字都构不成音的变化起伏,有时连一个独立的意义也没有,不会成为诗歌语言的基本单位;三字可成句,但仍只有三个音节,像《三字经》,只可表义,难以表情、状物,因为它还无法形成特定的语气,更没有语气的变化。四字句开始带上了一定的语气,但这种语气是不能变化的。每句四字,二字一顿,长短相等,构不成起伏变化,三百篇与不同的乐和舞相结合,通过同义的反复,情景的变化,尚可不致雷同,如若作为写诗的规范,就必然千篇一律,难以适应诗人多变的情绪,更难做细致的描绘。只有到了五字句,汉语言才有了真正的活力,它不但有一个完整的意义,还能造成特定的语气,使同样的五字句可以有不同的意义和情调,从而形成和而不同的诗的整体,在叙事、抒情上也更加“详切”。三字句是死的,不可能有任何变化,它都是单音节词,很多只有用双音节词才能表现的意义它不能表现,读起来一字一顿,没有长短音的差别;四字句是硬的,它把单音节词与双音节词结合在了一起,但所容纳的词性是不全面的,其中多是实词,虚词极难进入四言句,连实词中的形容词和副词也很难挤进,读起来两字一顿,节奏没有变化;五字句就不同了,它不但把单音节词与双音节词结合在了一起,而且一句之中有了长短不同的节奏,把汉语言的所有主要功能(音的、形的、义的)都综合在一个最简单的模式中,所以中国诗歌不格律化则已,一格律化,五言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形式。
那么,曹操的四言诗为什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呢?
我们说四言作为一种诗的形式是带有极大局限性的形式,但却不否认它可以成为一种诗的形式。它的节奏是单一的,语气是缺少变化的,但单一的节奏也是一种节奏,没有变化的语气也是一种语气。中国第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主要是一个抒情诗人。他的求生、求美的意志受到了现实人生的压抑,造成了他的郁闷的情感,这种情感使他用徐长的诗句、造成汩汩流动的气势倾吐出来,因而他没有采取四言诗的形式;屈原除抒情之外,另有叙事、状物(包括他那些丰富的想象),他之后的诗歌创作也不脱叙事、状物、写景、抒情。对于这些目的,正像钟嵘所说,五言才最为“详切”。所有这些诗作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在自己的世界里,不具有完全的主动性。他们或抒发自己的郁闷痛苦的感情,或以同情的态度叙他人之事,或以赞赏的态度写人写物,但都在外在的客观世界面前,透露着被动性的情绪,即使他们的理想,也不具有直接的自我实践的意义。这种心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中国“士”这个阶层自从产生,它就从来没有把自己作为这个世界的主人看待过,事实上,它在中国社会中确也不具有直接的实践力量。他们通过为政治统治者服务而发挥自己的才能,即使贵为公卿大臣,也终是天子的仆从,中国的社会人生是由天子定乾坤,不是他自己的独立意志。更多的知识分子是怀才不遇、郁郁终生、不遂其志,更莫提吞吐宇宙之志,即使有其言词,也难免徒作狂言之嫌,所谓狂放不羁,也只是个人言词的不驯,行为的不拘小节,并非真感到有扭转乾坤的力量。在中国,具有扭转乾坤的力量的,不论在实际上还是在人们的普遍观念中,都只是帝王一人而已。但中国的政治统治者,则以权力临天下,以道德劝人心,不以诗文为事。在他们眼里,诗文是文人之事,即或偶尔为之,也不以私情为目的,毛泽东后来说“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不能不说反映了历史事实的一面。但到了曹操这里,情况就有了不同。曹操本身是一个文人,但他又是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在东汉末年的政治混乱的局面里,汉代封建帝王的权威性动摇了,曹操不论当时有没有自己当皇帝的企图,但他以自己的独立力量收拾旧山河的意识无疑是异常明确的。也就是说,他是把自我作为一个独立的意志主体来看待的,他的这种意识并不空洞,不是故作狂态,不是虚张声势,而是与他的实践意志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不论我们如何评价他的历史作用,但他确实在用自己的力量转动着历史的把柄。我认为,正是他的这种特殊性,使他占有了四言诗。中国历史把真正的四言诗只留给了他一个人。
曹操也写五言诗,并且思想艺术成就也不亚于他同时代的其他人,但真正把他与同时代诗人和中国古代所有杰出的诗人区别开来的并不是他的五言诗,而是他的四言诗。如上所述,四言诗的节奏是单纯的,没有变化的,但正是因为它的节奏的单纯,句式的缺少变化,才使四言诗具有为其他形式的诗所没有的特殊意味。它读起来铿锵有力,绝无缠绵凄恻的情调,透露着诗人的坚定意志和内外如一的质直性质。它的前后语气是一贯的,表现着诗人那不受外在因素影响、不易变动的情感与情绪的特征。它没有抒情诗常有的那种多愁善感的性质,没有叙事写景诗常有的敏感多情的感觉。它无法精描细画,但粗笔浓墨,线条粗犷,如木刻版画,遒劲有力。诗人的心并不温柔,但这正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的性格特征。这类人说不出柔情绵绵的情话,但却也不会可怜巴巴地求人同情、希人怜悯,他是一个独立不倚的人,不悲人也不悯己,所以他的情感是宏大有力的,不狭隘、不逼仄,如临旷野,如观沧海,大气凛然,回肠荡气。
下面我结合他的《短歌行(其一)》具体阐述我对他的四言诗的看法。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现在提起这几句诗,都免不了批评几句曹操的“消极情绪”,但我认为,这恰恰没有从四言诗的独特格调出发来体验这几句诗的真正意义。我敢说,这里的情绪绝不是消极的,而是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少有的敢于面对真实的人生、不回避人生的矛盾并且表现了不屈服于人生的精神气概的好诗句。鲁迅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记念刘和珍君》)曹操这几句诗中便有一种正视的勇气。他直抒胸臆,把自己真实的人生体验质直无伪地表达出来。他不像那些爱面子胜于爱自己的人那样专言自己过去的荣耀,在自己过去过五关、斩六将的经历中沾沾自喜,但他也不是专言自己的委屈,用痛苦的眼泪换取人们的同情,并在这同情中安抚自己受伤的心灵。他直面自己过去的人生,公开承认在过去的体验中,痛苦多于欢乐。回首往事,人生倏忽,转眼之间,已近老境,感到人生像朝露之易逝,去而不返,生命短暂。过往生活的痛苦体验,产生了对人生的忧虑,这忧虑埋于心底,激荡起情感的波澜,慷慨悲壮,无法排遣,只有在酒醉的时候,才能暂时忘掉它。“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这是作者的感情情绪的表现而不是对人的行为的规劝,不是说人生短暂,就应及时行乐,而是说对酒当歌,顿感到生命短暂,忧思难遣。“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里说的是一个事实,而不是一个教导,不是说人就应当沉于酒色,而是说自己的忧思是如此难以排遣,只有在酒醉之时才能暂时忘却。这种人生的感受不正是所有的人都会有的人生感受吗?曹操如此质直地道出这种人生感受,正表现了他的正视的勇气,怎能说是消极的呢?与此同时,这种人生感慨恰恰是那些不满于自己、不满于现实、不满于已有的一切而要追求一个更高远的人生目标的人才会产生,消极的苟活者是不可能敢于面对真实的人生痛苦仍不失豪迈的气概的。在这里,四言诗的形式对它的意义起到了重要的廓定作用。我们为什么不会认为它是教人沉沦于酒色之中、不求上进的颓废主义说教呢?因为我们在读它的时候产生的不是精神萎靡的感觉,而是精神上的豪壮、情绪上的激昂。四言诗的节奏给你打出的是有力的节拍,它不是萎靡无力的,也不是婉曲缠绵的,作者的精神之壮,就在语言的节奏中表现出来,这同时也与下文的内容相呼应。若说这里表达的人生观是消极的。下文的积极性又是从何而生的呢?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沈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在我们解析中国古代诗歌的时候,不能不用中国古代人常用的概念予以概括,这是难免的,也是必要的,但它也同时产生了一个问题,即这类的词语往往在历史的变迁中发生过多次的变化,如何具体感受这些词语遂成了严重的问题,同时它也失去了自身表意的明确性,便如我们在解释曹操的这首诗的时候,就常常用渴望贤才来说明它的意义。但是,招贤纳士是儒家知识分子对封建帝王提出的一个基本要求。在这个要求中,儒家知识分子是把封建帝王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之上的,是封建帝王要实现自己的王政所应当采取的正确措施,被召之贤才是为实现帝王的统治大业服务的,并且因此而被封建帝王所重用,获得自己的人生价值。这是一种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因为帝王的统治大业是属于帝王一人的,“贤才”是辅佐帝王实现帝王的事业,自己的人生价值不是在自己的独立追求中实现的,而是在完成帝王的事业中实现的。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实践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儒家这种招贤纳士的政策有了各种复杂的人生体验,尽管很多人仍然以帝王的求贤若渴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但人们也知道,卸磨杀驴也是这种政策的必然结果。因为帝王是以对自己的用处来确定贤才的标准的,一旦他失去了利用的价值,帝王就会把他从已经得到的地位上踢下来,用更有利于自己的人取而代之,而这些以帝王的重用与否为自己人生价值的表现的儒家知识分子,则必然在帝王的这种“始乱终弃”的行为中感到莫大的痛苦。在这种情况下,用渴望贤才来概括曹操这首诗,就未必能代表人们对它的具体思想和艺术的感受。曹操这首诗所表现的并不能用儒家的招贤纳士的思想来概括。在这里我们首先看一看他所引用的《诗经》中的两首诗: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诗经·郑风·子衿》)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视民不?君子是则是效。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敖!
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乐且湛。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诗经·小雅·鹿鸣》)
这两首诗,诗义都非常单纯,只要不牵强附会地搜寻它们的微言大义,就会感到它们只是表达友爱关系的。《子衿》怀念朋友,说是我很想念你,我没有到你那里去,你也应当来找我呀!对朋友的那种真诚坦白之心,如一泓清水,明澈见底;《鹿鸣》也表达对朋友的感情,说是朋友来我家,我鼓瑟吹笙,用好酒招待。这里的鼓瑟吹笙、设宴款待,都象征着主人见到朋友时的欢乐心情,主客之间是朋友的关系,感情真挚,不是实利关系。曹操在自己的诗里用这两首诗的诗义表达自己的感情,他所表达的也应是人与人之间的友爱,没有理由把它归纳为招贤纳士的实利关系。这是两个范畴的概念。友爱关系是一种感情关系,它不以对方的能力为标准,若是以对方能力的大小为标准作为交友的条件,那就不是友爱,而成了一个势利眼了;招贤纳士是一种实利关系,是以对方的能力和有用无用为标准的,若是以对方与自己的感情关系作为招贤纳士的标准,那就不是招贤纳士,而成了结党营私了。假若我们从上下文的文义理解这段诗的含义,就更不能用招贤纳士这种有明确目的性的语言概括它的意义。上文作者抒发的是人生短暂、去日苦多的感情沟通,这一段就写求友的愿望,顺理成章。当然,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这种求友的愿望也总是和他的事业分不开的。但不论怎样,这里求的是友爱,而不是才能。它之所以能跨越时间和空间与我们的感情相沟通,也正是由于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关系,而不是曹操当时所要实现的政治目的。四言诗的形式即使在这里,也为它的意义远见定了特有的格调,使我们不感到作者是在被动的条件下哀求别人的理解和同情(这在中国古代的抒情诗特别是爱情诗里是屡见不鲜的),它的格调是硬朗的,而不是缠绵的;是直快的,而不是迂曲的。这种解释是比较迂远的。前文讲人生的痛苦,讲对友爱的渴望,那么这里也就是友爱的象征,说人与人之间的友爱之情,犹如明明之月,纯洁明净,令人向往,何时才能得到这种友情呢?想到这种友情的难得,想到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矛盾和斗争,想到人生的痛苦和孤独,忧思之情,由衷而发,绵绵无尽,难以摆脱。由这种忧思,更感到友情之宝贵,所以继而想到朋友之间的相会。有朋自远方来,枉道来访,久别重逢,畅怀而谈,叙旧谈故,两情相契,这是何等的愉快呵!这里所描写的完全是老友见面,欢叙旧情的场面,自由自在,无窒无碍,与帝王垂询政事,谋划国策,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情景。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讌,心念旧恩。
如上所述,我们在上文没有理由一定要用“贤才”代朋友,那么,这一段继续写友情则是显而易见的。“明明如月”是一种象征,在儒家的典籍里,它常常同“德”联系在一起,因而我们在解释这首诗的时候,也根据招贤纳士的观念同贤才之“德”等同起来,显而易见,“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友爱之心,人皆有之,它要求一种依托,要求一个栖息之地。人的爱心无所归依,人的心灵就是孤独而又痛苦的,这几句诗实际上是这种人生体验的象征,是以己度人的结果。作者由自己的孤独体验,进而想到人的普遍的孤独感,想到无所可爱的心灵的寂寥。至此,全诗一转,由个人的抒情,转化为对身外的人生的关注,从而才想到个人的责任。“山不厌高,海不厌深”,一个人的爱心不厌多,能爱更多的人,能被更多的人所爱,使天下之人都能从自己身上得到爱而又被天下人所爱,才是一个如山之高、如海之深的人,是作者所希望成为的人。
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理解最后的“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曹操作为一个政治家,感受到人生的痛苦,生命的短暂,渴望人间的友爱和情感上的沟通,必然不是下层文人常说的个别人之间的友情,也不是下层知识分子常常表达的空洞抽象的政治理想。他把这种友情上升到普遍的人与人的关系上来,上升到自己的政治理想的角度,与自己特殊的政治地位联系起来,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种情感是个人的,但又与他的政治事业结合为一体,成为他政治理想的一部分,二者是水乳交融的,不像“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那样有终隔一层之感,因为它是在不同的地位上对下层老百姓的关心,二者缺乏共同的感情基础,不是从自我的需要生发出来的;也不像“居江湖之远则忧其君”那样有一种牵强感,因为它没有实现这种空洞愿望的现实基础,不是从自我的真实处境中自然产生的思想愿望。曹操的特殊身份使他能够把个人的与政治的系于一体,虽然在实际上是难以实现的,但在感情上却是真实的,在艺术的逻辑上是顺理成章的。“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义相天下,吾与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韩诗外传》卷三)曹操用周公之典,可谓隙合无间。周公和他都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关键作用的人物,用周公的话来说就是“吾与天下亦不轻矣”,曹操正视自己的这种社会地位,不像谦谦君子一样故意把自己说得身轻位卑,这里有他的质直,也有他的独立不倚的精神,但他在这样一个地位上,更容易失去与一般社会成员的友爱关系,把自己孤立于人与人的感情联系之外,所以周公说“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也就是失去人们友好的感情。这里的“士”,可以作为知识分子解,但也可以作为所有国民的代称,所以曹操说“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以周公为榜样,自己爱所有的人,也使整个社会人的爱心有所归。
全诗以个人的孤独体验为本、以对人与人的友爱感情的渴望为主体,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理想。这种政治理想也是人与人的感情关系上的,而不是干部政策上的,所以不能用招贤纳士这种有明显实利性目的的词语来概括它。四言诗这种特定的形式使全诗透露着不琐细、不迂曲、不板滞、不逼仄的特征,所以它尽管抒的是人生的孤独感受和渴望友爱感情的愿望,但基调是豪迈开阔的,精神是悲壮有力的,这与曹操这样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的真实感受有着相互契合的关系,所以,在曹操这里,四言诗获得了成功。可以说,真正意义上的四言诗,是属于曹操一个人的。他的《观沧海》,他的《龟虽寿》,都位于中国古代四言诗之冠,使在歌、舞、诗三位的《诗经》中的四言形式获得了独立的诗的品格。
但是,四言诗到底是局限性太大的一种诗的形式,它更适于言志,而不适用于抒发细腻、委婉的感情,不适于描写和叙述,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真能有独立意志而又有贯彻自己独立意志的可能性的,大概也只有像曹操这样极少的人,并且有其志而又有其才的,大概也只有曹操一人。四言诗在曹操之后几近绝迹,是并不奇怪的事情。但这种四言的形式,后来也在豪放派的词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说句不负责任的话,在中国,写好四言为主体的诗词,几乎是一个人有帝王气概的象征。毛泽东《水调歌头》、《沁园春》就都是以四言为主体的,他的一曲《沁园春·雪》,倾动重庆,让国民党上层社会为之咋舌,让民主人士为之一惊,让当时的左翼阵营感到鼓舞,大概并非捕风捉影的事情。
(发表于《名作欣赏》1995年第3期:四言诗和曹操的《短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