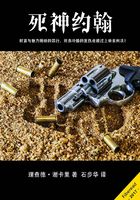星期日,晚上7点30分,一则本地电视新闻吸引了我的注意。
我一般不看地方台的新闻,凑巧调台时那则新闻的画面刺激了我的眼球。画面中出现的是西库镇房倒屋塌后的狼藉景象。笛住过的那座小院,只剩下了半壁残垣,残壁上用白漆画的圆圈中大大的“拆”字分外显眼。那棵老槐树还立在那里,对着那个“拆”字默然不语。画面一转,出现了一座红砖小楼,在周围破砖碎瓦的衬托下,那栋建筑鹤立鸡群,俨然一座孤零零的碉堡。
碉堡已经被重兵包围,十几台铲车、推土机和重型卡车将其围在其中。按照播音员的解释,这是在对西库镇仅存的一家“钉子户”强制拆迁,时间是6月9日晚上10点。碉堡虽然坚固,保卫者却只有夫妻二人。丈夫挥舞着杀猪刀在楼下吼叫,妻子提着汽油桶站在楼顶嘶喊,面对着黑压压的拆迁人员,那夫妻俩仿佛在表演滑稽戏。我在人群中发现了战神,从他被一些人围拢在中心,并专注地倾听他讲话来看,他可能就是这场拆迁战役的总指挥。
战神仍然穿着黑西服,上衣口袋上别着墨镜。在电视镜头中,我看不清他的眼睛,实际上,我从来没见过他的眼睛。只见他和几个官员模样的人商量了几句,突然他把手一挥,十几个迷彩服向那个男人冲过去。迷彩服们手持木棒,人影晃动,木棒挥起落下,那个男人被打倒在地。那个男人仍在挣扎,他叫骂着,但我听不清他在叫骂什么。突然,他甩开了压在身上的四五个迷彩服,呼地站起身来,手中那把一尺多长的杀猪刀噗地刺入了战神的胸膛——战神直挺挺地倒下了,在那一刹那,我看清了战神的眼睛(也可能是我的幻觉),那是一双眼球凸出的环眼,就像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纵目人,在他的环眼纵目中,凝结住的是面对死亡时的惊惧的光——那个男人也愣住了,望着战神的尸体,仿佛在想:这是怎么回事呢?
迷彩服们把放弃了抵抗的男人捆了起来,塞进了一辆警车。另有一些人将战神抬进了事先准备好的救护车。警车和救护车发出不和谐的叫声,飞速地驶离了拆迁现场。
人群中突然发出一声惊呼。
镜头移向楼上的那位妻子,只见她端起汽油桶往头上浇。
人群中响起乱哄哄的喊声。
那位妻子在人们嘈杂的叫喊声里,划着打火机向身上点去。汽油腾的一声燃起,火舌蹿起三四米高。那位妻子挺立着,在火与浓烟中,像一根不倒的火柱。镜头定格在那里,一群迷彩服搬来梯子向楼顶爬去……看罢新闻,我坐在床边久久地盯视窗台上的酢浆草。心形的绿叶虽已闭合,红色的小花开得正艳。在我盯视的时间里,成熟的籽荚爆裂开来,弹出籽粒打在玻璃上发出清晰的响声。这真是一棵神奇的小草,不但能感知太阳的东升西落,还能以爆炸的方式把种子散播出去。可惜,纵使它的爆炸力再强大,它也不可能让它的籽粒在玻璃上扎下根来。这是不会有结果的繁殖,就在这不会有结果的繁殖中,窗台上的这盆酢浆草,展现出了作为酢浆草的天性。玻璃就是玻璃,我们好比玻璃缸里的鱼。看上去我们拥有世界,但我们永远冲不破那层薄薄的把我们囚禁其中的透明的墙壁。
想到这里,我越发地思念岚和笛。
看一眼床头柜上的唐老鸭闹钟,离岚和笛平常回家的时间还有三四个小时。我已不能再等。我要尽快看到她们。
我先去了巴克健身中心,红鼻子头经理说岚开车出去了。我打上一辆出租车,赶到钢琴城。看见我的桑塔纳安静地候在楼下,心里一阵欣喜。我知道,我马上就能见到岚和笛了。
果然,扒着二楼声乐教室的门玻璃,我看见了笛——在声乐教室里教唱歌的只能是笛——笛穿着白色连衣裙,大概空调放得过冷,脖子上围着红色的纱巾。笛腰身挺直地坐在琴凳上,手指灵巧地在琴键上跳动,脸扭向钢琴旁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小女孩唱的是《红蜻蜓》,嗓音清亮甜美,唱得很是动情。声乐教室里有二十几张课桌椅,坐在课桌后面的只有小女孩的母亲。一曲唱罢,小女孩擦去流出的眼泪,笛微笑着为她鼓掌。小女孩的母亲走过来和笛握手,像是表示感谢。笛亲热地和小女孩的母亲说着什么,脸上洋溢着满足与幸福的笑容把那对母女送出教室。
笛一转身看见了我,吃惊地张了张嘴,继而又慌乱地摸了摸胸前的红纱巾。她的脸腾地变得比红丝巾还要红。但是当她开口说话时,她嘴里发出的却是岚的声音。
“你怎么来啦?”岚说,“怎么样,笛够酷的吧?”
“我来看看你们。”我说,“真的呢,笛真的很酷。”
“就是!”岚说,“你还没听笛唱歌呢,真的能迷死你!”
“我就是来听笛唱歌的,”我又问笛,“不会太冒失吧,笛?”
“还有两个学生,”这回是笛的轻声细语,“上完课我给你唱。”
“好的,”我说,“你上你的课,我在外边等。”
一个小男孩沿墙边溜进教室,身后跟着板着脸的父亲。笛冲我微微一笑,轻轻把门关上。
我坐在教室门外的长椅上。琴声响起,小男孩上的是视唱练耳课。
这堂课笛上得很是艰难。小男孩的音准很差,乐感也谈不上,明显是个左嗓子。
一个简单的音,一条并无难度的五线谱,都要反复十几遍。笛教得很是耐心,可小男孩明显缺乏热情,总是心不在焉,对笛给予的鼓励反而充满敌意——他在受罪,他不可能对让他受罪的人抱有好感。
作为听者,我也在受罪。于是,起身在大厅里溜达。我看了会儿玻璃缸里的金鱼,又看了会儿调音师调钢琴,最后坐在沙发上看报纸。估计时间差不多了,沿着那排监狱小号似的琴房回到声乐教室。
小男孩在哭。透过声乐教室的门玻璃往里看,只见那位父亲两手叉腰站在钢琴旁吼,笛半蹲着把小男孩的头搂在怀里。那位父亲指着小男孩骂声不绝,小男孩不停地哭,笛不住地为小男孩擦眼泪。笛也在流泪,好像那位父亲骂的不是小男孩而是她自己。越骂越生气的父亲扬手打了小男孩一巴掌。笛抬起臂肘遮挡,我听见“啪”
的一声响。笛眼泪汪汪地看着被打的手臂,忽然满脸怒容地站了起来——不,不是笛,站起来的是岚——岚伸手揪住了那位父亲的衣领,像拉牲口似的把他拽到了教室外面。
“你怎么能动手打人呢?”我第一次看见横眉立目的岚。
“我打的是我儿子。”那位父亲梗着脖子说。
“打谁也不行,你必须道歉!”岚的脸涨得通红。
“笑话!”那位父亲挣脱岚的手,“没听说过老子教训儿子还得道他妈的什么歉!”
“可你打的是我!”岚的嘴唇在颤抖。
“打你怎么啦?”一些家长闻声跑来看热闹,那位父亲把眼一瞪,“老子花了那么多钱,看你把我儿子教的,老子打的就是你!”
岚的眼中在喷火,两手攥成了拳头。我赶紧推开岚,隔在她和那位父亲中间。
“这位先生,”我微笑着对那位父亲说,“请听我说两句好吗?”
“你是谁?你想说什么?”那位父亲白了我一眼。
“我是这位女教师的男朋友。”我尽量用心平气和的语调说,“我觉得您说得有道理。您作为孩子的父亲,花了那么多钱而我的女朋友没本事或是没尽心把您的孩子教好,所以您认为她该挨打。如果真是这样,您打她一巴掌,她一点都不冤。可我作为这位女教师的男朋友,我认为您花多少钱都是您自愿的,而且我还认为我的女朋友教得非常好,是您的儿子天生就不是学唱歌的料。您尽可以赶着您的鸭子上架,但我的女朋友不能把您的鸭子培养成夜莺那不是她的错。所以您打我的女朋友就是冒犯了我,我现在也非常想揍您一顿。”我微笑地看着那位已经面色苍白的父亲,“咱们下楼去解决吧,别把这么高雅的地方溅得到处都是血!”
那位父亲从教室里揪出小男孩,推开人群向外走。
“咱不在这儿学了,”那位父亲边走边对小男孩说,“爸给你找个音乐学院的教授!”
有人起哄,围观的人随之散去。
“真是个混蛋。”岚说。
“还是个混蛋当中的软蛋。”我说。
走进声乐教室,岚告诉我钢琴城地下室的租赁合同已经谈得差不多了。她计算过了,如果节省着花,资金刚好够用。不过,买车的事得往后放一放。所以,在一段时间内,她还得借用我的那辆桑塔纳。我说桑塔纳你尽管用,我想问笛现在怎么样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正好笛的手机响了,岚于是让位给了笛。
笛接听手机,吸溜着鼻子说了两声好,手机放回挎包,眼泪又扑簌簌掉了下来。
“怎么啦?”我关切地问。
“学生请假,病了,今天不能来上课了。”笛抽搭着说。
“不来就不来呗,那也不至于抹眼泪呀!”我说。
“不是为这个。”笛哽咽道,“你们帮我跟人家打架,就像我的亲人似的,我不知道怎么报答你们才好。”
“嗐!”我笑道,“咱们本来就是亲人嘛!行啦!把眼泪擦干,别让那个混蛋搅了咱们的兴。你那个学生不来,正好咱们唱。看你,满脸泪珠儿,都快成林黛玉了。”
“那你想听什么呢?”笛用纸巾擦干眼泪,“你说个曲子,我给你唱。”
“《题帕三绝》。你现在唱这个,正合适。”
我是跟她开玩笑。没想到,话音刚落,琴声响起。“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闲抛却为谁?”笛凄切切荡悠悠缠绵婉转的歌声,在教室里回旋跌宕。我倚着钢琴的一角,屈肘支颐,静心屏息听她唱。她微微仰着脸看着我,仿佛在向我倾诉衷肠。
“窗前亦有千竿竹,不识香痕渍也无?”唱完最后一句,她呆呆地看着我,任凭泪水一滴滴从眼眶中滚落。
“咱不唱《红楼梦》了,”我的心中也有些酸楚,“还是唱点别的吧。”
“那唱什么呢?你说。”
“唱邓丽君吧。”
“那唱哪一首呢?”
“随便。只要是邓丽君的,我都喜欢。”
笛给我唱了《但愿人长久》,唱了《独上西楼》,唱了《丝丝小雨》。我听入迷了,深深地受到了感动。这是真正女人的声音,是真正女孩的声音。她的声音足以唤醒男人心灵深处蛰伏的那个隐秘的梦,记起在那个隐秘的梦中自己是个男人。通过笛的歌声,我不但真切地意识到了我作为一个男人应当承担的责任,而且我还真切地理解了女人,理解了笛。在笛的歌声里,她寄托了多么强烈的对于爱的渴望啊!
我为笛唱了庞龙的《两只蝴蝶》。
笛为我伴奏,脸上渐渐有了笑容。我唱罢她为我鼓掌。
我问笛是不是也请岚唱一首。笛说:“好啊,我正想请岚唱呢。”岚现身,有些沮丧地看着钢琴说:“莫非轮到我就得清唱吗?我又不会弹琴。”我对岚说:“你和笛试试看,看你们两个人是否能配合一下,一个唱,一个弹琴。”岚瞪我一眼:“难道你忘了?我们俩只有一个身体,不论干什么都只能轮流着来。”我笑着说:“试一试嘛,不试怎么知道不行呢?”
岚笨拙地把手放在琴键上。奇迹真的出现了。只见岚的两只笨拙的手如灵魂附体一般,利索地弹出了上下爬音。“哇噻!”岚盯着那两只自己运动的手大叫起来,“这是我的手吗?我会弹琴了耶!”
“岚,你唱哪首歌?我来给你伴奏。”笛说。
“齐秦的《大约在冬季》吧,这首歌我熟。”
两只手熟练地弹出前奏。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岚唱了起来。
倘若换成别人,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两个女孩的合作。弹琴的是一个,唱歌的是另一个。连我都产生了错觉,以为坐在钢琴前的岚在自弹自唱。岚唱的节奏忽快忽慢,经常自由发挥,俨然二把刀司机驾驶着一辆跑偏的汽车。那两只手或追赶或等待,始终把那辆不按分道线行驶的汽车纳于车道之内。“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音调飘忽,但岚唱得情真意切,“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
岚是唱给我听的,我听出了她的话外音。
我回之以《我心依旧》。虽然只会最后几句,但足以表达我的心意:“有你在我身旁,我全无畏惧,我知道我心与你相依。我们永远携手而行,在我心中你安然无恙,我心属于你。”岚笑着打了我一巴掌,笑道:“胡唱!你只有一颗心,属于我了,那笛怎么办?”还没等我回答,岚眼睛亮亮地说:“树袋熊,咱俩唱刀郎的《爱是你我》
怎么样?”
“行吗?笛。”我问笛。
笛没有回答,但那两只手已经弹出了前奏。
当岚唱到“爱是你的手,把我的伤痛抚摸”时,我感觉我的心在震颤。我和岚一起扯着嗓子喊:“这世界我来了!任凭风暴漩涡!”岚声嘶力竭地吼:“正是你爱的承诺,让我看到了阳光闪烁。爱,拥抱着我!”我俩合唱道:“我能感觉到他的抚摸,就算生活给我无尽的苦痛折磨。”岚热泪盈眶地接着唱道:“我还是觉得幸福更多!”
我泪眼模糊地把“觉得幸福更多”又重复了一遍。我和岚的泪水同时流下,为我俩共同经历的那些“苦痛折磨”,也为“幸福更多”。
“酷毙!”岚抹了一把眼泪,“痛快淋漓!”
“还是听笛唱吧,”我说,“笛,来一个。”
琴声的味道突然一变,笛弹起了《It’sabeautifulday》。我看过莎拉·布莱曼的DVD光盘,知道这首歌。从笛的喉咙里发出了悠扬、迷幻、令人震撼的声音。
她的目光仿佛穿透了墙壁,看见了大海,看见大海尽头一艘缓缓驶来的轮船上升起一缕袅袅青烟。她用英文和意大利文唱,结束时变成了中文:“这是美丽明朗的一天,但却是我的最后一天。”
“唱得好,但歌词不好。”我说,“‘我的最后一天’,听着总感觉不吉利。”
“那我给你换一个吧。”笛微笑着对我说。
笛唱起《Whatawonderfulworld》。我的英文有限,听不懂她唱的是什么。她微笑着看着我唱,像在和我说话,告诉我今天的天气挺好,她的心情也不错。我像是听懂了似的频频点头。我们的目光碰到一起,她没有闪避,脸上也没有羞涩,娓娓唱出我心领神会的亲切话语。
忽然,她用中文大声唱道:
天上彩虹的颜色如此漂亮,
人们的脸庞也是一样。
我看到朋友互相寒暄说,你好吗?
他们真正想说的是,我爱你!
笛的歌声在“Wonderfulworld”的反复吟唱中结束。
我的耳畔“Wonderfulworld”继续回荡不已。我忘记了身在何处,忘记了期待着赞美的笛,完全沉浸在了笛的歌声为我描绘的“Wonderfulworld”里。
我听见有人鼓掌。那是岚。岚在为笛热烈鼓掌。
“听傻了吧?”岚冲我挤了挤眼睛,“我早就说过,听笛唱歌,能迷死你!”
“是啊,”我长长地吸了口这美妙夜晚的空气,“都忘记我是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