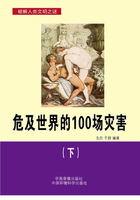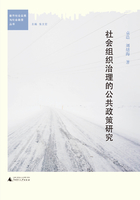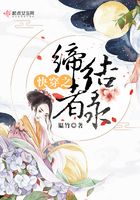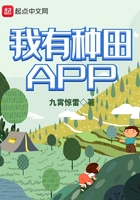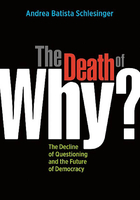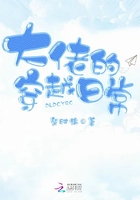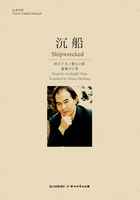出自Les Temps Modernes,no.77,1952,p.1572-1590
1951年,法国的圣诞节因为一桩争议事件而让所有人印象深刻,当时报章杂志和舆论激动沸腾,给节庆日本该有的欢乐气氛添增了不寻常的尖酸辛辣。几个月以来,教会多次通过几位主教之口,表达他们不能苟同“圣诞老人”在许多家庭与商业活动中受到的与日俱增的重视。主教们谴责这是一种令人担忧的“异教化”(paganisation),在耶稣诞生日,将众人的心灵由这个专属天主教的庆典,导向一个没有宗教价值的神话。
这样的攻击在圣诞节前夕更进一步,而新教教会则以较为谨慎,但同样坚定的态度表示他们与天主教教会持同样的看法。
在这之前,报纸上的读者来信以及社论表达了各式各样的意见,但大抵都反对教会的立场,因而显现出这个事件值得玩味之处。最后,事件在12月24日达到了高潮。《法兰西晚报》(France-Soir)在一篇活动报道中如此描述:
在教徒们的孩子面前
圣诞老人在第戎大教堂前庭
被处以火刑
第戎(Dijon),12月24日,《法兰西晚报》
圣诞老人在前一天下午被吊挂在第戎大教堂的栏杆上,并在教堂前庭被公开焚毁。这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处决在数百名教徒的孩子面前进行,并由指控圣诞老人为篡位者和异端邪教的教士所应允。圣诞老人被指责将圣诞节异教化,而且扎根在这个节庆中,像只布谷鸟,逐渐占据愈来愈重要的地位。他最受非议之处,是他还涉入了所有公立学校,尤其是被严格禁止的幼儿园。
星期日下午3点,这位有着白色大胡子的不幸老人,就像许多无辜的人一样,替人们所认为的罪行付出了代价,观众则为处决鼓掌喝彩。火焰燃烧着老人的胡子,他在烟尘中倒地不起。
处决之后,一篇新闻稿公诸世间,主要内容如下:
250名孩子代表教区内所有挺身对抗谎言的基督教家庭,集结在第戎大教堂的大门前,焚毁了圣诞老人。
这不是一项余兴表演,而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动作。圣诞老人成为祭品,以身殉道。事实上,欺瞒哄骗的谎言并不能唤起孩子的宗教情怀,而且无论如何都不是一种教育的方式。那些人居然表示想要以圣诞老人来反对鞭子老爹[2]。
对我们教徒而言,圣诞节应该只是一年一度庆祝救世主诞生的节日。
圣诞老人在第戎大教堂的前庭被处决,引发了民众各种不同的评价,在天主教徒间也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然而,这个过早的表态,可能导致主导者无法预期的后续发展。第戎因为这个事件而分为两个阵营。
第戎的一些人,等待着前一天在大教堂前庭被谋杀的圣诞老人复活。他们认为圣诞老人将于这一天下午6点在市政厅重生。实际上,有份正式的公报宣称,圣诞老人将如同以往每一年,在解放广场召集第戎的孩子们,然后在市政厅的屋顶高处,在聚光灯的照射下对孩子们演说。
第戎的市长及国会议员,也是议事司铎的基尔(Chanoine Kir),在这个棘手的事件中则避免采取任何立场。
同一天,圣诞老人被处决一事成为新闻头条,所有的报纸都评论了这个事件,其中有些甚至以社论来讨论,例如前文所引述的《法兰西晚报》。众所皆知,《法兰西晚报》是法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第戎教士的态度普遍令人鄙夷,以致教会当局似乎都认为暂缓攻击比较好,或至少持一种隐约的保留态度;然而,牧师们在这个问题上却看法各异。这些文章的大部分论调,都是很有分寸又充满感性的:相信圣诞老人的存在是一件美好的事,并不会伤害任何人,孩子们从中得到巨大的满足,成为长大后美好回忆之源,等等。然而事实上,人们并没有回答问题,只是在回避。因为问题并不在于解释圣诞老人讨孩子们欢心的理由,而是必须说明促使成人创造圣诞老人的原因。无论如何,这些极为一致的反应,毫无疑问地显示出公众的意见与教会有分歧。即使事件本身很微小,造成的反响却很大。因为自从“二战”德军占领期以后,法国以无宗教信仰者为主的舆论界与宗教已逐步达成和解,像MRP[3]这样一个宗教色彩鲜明的政党加入政府议会就足以作为证明。同时,传统上反对教权的人也察觉到,他们意外获得了一个的机会:在第戎或者其他地方,他们成了备受威胁的圣诞老人的保护者。然而,圣诞老人却也因此成为不信教的象征。这是何等矛盾!因为在这个事件中,教会仿佛采取了一种渴求诚实与真相的批判精神,而理性主义者反而化身为迷信的捍卫者。这个明显的角色错置暗示了更深层的现实:我们正处于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中,代表了习俗与信仰的快速演变,首先是在法国,但在其他地方可能也如此。在民族学家自己的社会中,很难得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去观察一个仪式,甚至是一种崇拜这般微妙的发展;在当中探寻它的原因,研究它带给宗教生活其他形式的冲击;最后尝试去了解,这些现象涉及了哪些既是心理上也是社会上的集体转变。关于这些现象,拥有许多传统经验的教会乐于赋予它们一个重要价值,使人们不会有错误判断。
*“二战”结束后三年,也就是经济活动回到正轨以来,法国的圣诞节庆祝活动发展到战前未见的规模。当然,受到美国的影响是主因之一。于是我们看到:大型圣诞树竖立在十字路口或交通要道上,夜晚闪烁着灯光;圣诞礼物的包装纸上绘有人物故事;在圣诞节前一星期,迎接圣诞老人的壁炉上展示着圣诞卡;带着铁桶的救世军在广场及街道上募款;大卖场员工乔扮成圣诞老人,倾听着孩子的愿望。这些现象都同时出现了。而不过几年前,这些习俗在那些去美国游玩的法国人看来,还显得幼稚古怪,显现了两种不相容的精神样貌;至于现在,则因被广泛引进且根植于法国,大家早已见怪不怪。对于研究文明的历史学者而言,这是值得深思的一课。
在这个领域,就像在其他领域一样,我们正经历一项大规模的传播经验。这些现象与以往我们根据点火栓、独木舟为例而习于研究的现象,也许并不会非常不同;但要对这些以我们自己的社会为舞台、发生在我们眼下的事进行理性思考,却是最简单也最困难的。最简单,是因为经验的传承是每时每刻且巨细靡遗的;但也是最困难的,因为只有在极为罕见的机会下,我们才能察觉社会转变的极端复杂性,就算是最受限制的转变。同时,也因为我们置身其中,我们很容易给出显而易见的理由,但却与真实原因极为不同。因此,我们有厘清事实的责任。
所以,如果仅以受美国影响来解释法国圣诞庆祝活动的演变,实在太过简单。移植是事实,但这只占其中一小部分原因。我们能很快地列举出其他显而易见的因素:法国有愈来愈多的美国人,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庆祝圣诞节;电影、“文摘”(digests)、美国小说,以及一些主要报纸的报道,都让人更了解美国的风俗;而这些风俗则受到美国来自经济及军事权势声望的推波助澜,甚至连马歇尔计划都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帮助圣诞商品的输入。但以上都还不足以解释这个现象,因为从美国传来的某些习俗,甚至融入了对其起源完全没有意识的大众阶层,例如工人阶级。受到共产主义的影响,他们非常不信任所有美国制造的东西,但他们却与其他人一样,很自然地接纳了这些习俗。因此在单纯的传播理论之外,应该同时讨论一个最早由克娄伯[4]提出的非常重要的传播理论,他称之为刺激性传播(stimulus diffusion):传入的习俗并未被同化,它的角色比较类似催化剂;也就是说,仅仅它的出现,便足以激发原本潜在于社会的类似习俗。我们以一个直接相关的例子来说明:制纸工业的人,受美国同行之邀或参与经贸考察团前往参访,在那里观察到美国人会制作专用的包装纸来包装圣诞礼物,他借用了这个想法,在国内实行,这就是一个传播现象。巴黎的某位家庭主妇,在住宅附近的文具店里购买礼物包装纸,她很中意橱窗陈列的那些款式。她并不了解美国习俗,但这些包装纸能够满足美感上的需求,且传递她的情感。选择了这些纸的同时,她没有(如制造商一样)直接借用他国的风俗习惯,但是这项很快就受到认可的风俗,在她这里激发出一种相同的习俗。
其次,不要忘记,在“二战”以前,法国以及整个欧洲的圣诞节庆祝活动早已愈来愈热闹。这个现象首先与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关,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微妙的原因。如我们所知,即便圣诞节仍存有些许古风,但其本质是个现代节日。例如使用槲寄生来装饰,这并不是(至少不直接是)德鲁伊[5]的遗俗,因为它似乎在中世纪再度流行过。再者,在17世纪某些德文纸本留下记录以前,圣诞树完全未被提及,18世纪时出现在英格兰,19世纪才出现在法国。埃米尔·利特雷[6]似乎不太熟悉它,或者他所知的圣诞树和我们认知的不太一样,他将它定义为“在某些国家,用物品以及给孩子们的糖果和玩具来装饰的杉木或冬青树,让他们以此庆祝节日”(见词条:No?l)。至于分发玩具给小朋友的人,则有不同的称谓:圣诞老人(Père No?l)、圣尼古拉(Saint Nicolas)、圣克劳斯(Santa Claus),这也显示了“圣诞老人”是一个融合各种人物形象的产物,而不是各地保存下来的古老原型。
但是,这样的发展并非凭空而来:它仅仅是将一个古老节庆的片段重新组合,而这个节庆的重要性从未被遗忘。如果对利特雷而言,圣诞树几乎是一个充满异国风情的习俗,那么谢吕埃尔[7]在他的《法国制度、礼仪和习俗的历史字典》(作者坦承,这部字典是改写自圣帕雷关于国家古文物的字典[8])中,却以一个耐人寻味的方式记载:“圣诞节……是直到近期(我特别强调)持续了好几个世纪的家庭欢聚的时机。”然后描写一段18世纪时欢庆圣诞节的场景,那时人们对节日的热衷似乎一点也不亚于我们。因此我们探讨的这个节日活动,在历史上的重要性起伏不定,有过高峰也曾经隐没。美国形式只是较其他形式更为现代而已。
顺道一提,以上的讨论足以显示,若理所当然地以“遗俗”与“残存”来说明此类问题,我们需要对这种过于简单的解释抱持怀疑的态度。如果在史前时期,从来不曾存在树木崇拜(树木崇拜仍于不同的民间习俗中持续),现代欧洲可能不会“发明”圣诞树。如上所述,圣诞树的确是近期的发明,只是这个发明并非无中生有。有些中世纪的习俗已被证实有圣诞树的雏形:例如在圣诞节点燃的树干(在巴黎发展成一种糕点)足以燃烧整夜,圣诞所用的蜡烛尺寸也能持续点燃一整晚;人们会以常春藤、冬青、杉木等各种青翠的枝叶来装饰建筑物(源自罗马农神节,我们稍后将回到这一点);最后,和圣诞节并没有任何关系,《圆桌骑士》(Table Ronde)的故事里也提到一棵挂满彩灯的神奇树木。在这样的背景下,圣诞树像是一个混合诸说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说,将所有的要求集中在一个事物上,直到产生一种解离状态(l'état disjoint):神奇的树木、焰火、不灭的灯,以及不会凋萎的长青植物。反之,就现今的状态而言,圣诞老人是个现代创造物,对他的信仰更是近期的事:人们相信他住在丹麦属地格陵兰岛,搭乘驯鹿拉的雪橇到处旅行(丹麦因此必须创立一个专门邮局,因应来自世界各地儿童的邮件)。有人说,这样的传说会在“二战”时迅速传播,是由于当时美军驻防在冰岛和格陵兰岛的缘故。而传说中出现的驯鹿并非偶然,因为文艺复兴时期的英文文献提及了人们会颁发驯鹿奖杯给那些圣诞庆祝的舞者。这些文献的时间都早于对圣诞老人的信仰,也早于他的传奇形成之前。
这些古老的元素因此与其他被引入的元素融合在一起,酝酿发酵,延续、转化或使旧风俗再生,产生前所未见的形式,可以称之为圣诞节复兴(没有双关语意)。然而,当中没有什么特别新颖之处。那为何圣诞老人会引起如此的情绪,并承载着许多人的敌意?
*
圣诞老人穿着鲜红色的服装,隐喻他是名王者。他的白色胡子、身上的毛皮和靴子、旅行时乘坐的雪橇,都让人想起冬天。他是位老人,在他身上体现了长者的仁慈和权威。所有形象都很明确。但是就宗教类型学的观点而言,他应该被归于哪一类呢?
他不是一个神话人物,因为没有一个神话与他的起源和功能有关;他也不是一位传说人物,因为没有任何野史轶事与他相关。事实上,这位神奇而永恒的人物,永远保持同样形象,负有专属任务且周期性地复返,就像家族的神灵。此外,在一年中的某些时节,他还受到孩子们以文字或祈祷形式的崇拜。他奖赏好小孩,对于不乖的孩子则不予奖励,是某个特定年龄层心目中的神灵(对于圣诞老人的崇信,足以构成这个年龄层的特征)。圣诞老人和真正的神灵唯一不同之处在于,尽管成人鼓励,并用哄骗的手法使孩子相信圣诞老人的存在,但他们自己并不相信。
因此,圣诞老人首先传达的是身份上的区别,一边是小孩子,另一边是青少年与成人。就此而言,它涉及了过渡礼仪(rite de passage)与启蒙仪式(rite d'initiation)这两种范围较广的信仰与习俗,而人类学家在大多数社会中已经从事过相关研究。事实上,在人类群体之内,很少有儿童(有时妇女也是)未被以此种或彼种形式排除于大人的社群之外;他们不了解一些被小心翼翼维护的秘密或信仰,盼望成人们等到适当的时机就会揭露,并借此让他们(年轻的世代)加入成人世代。这些宗教仪式与我们此时研究的主题往往惊人地相似。例如圣诞老人和美国西南部印第安人的卡奇纳[9]之间的相似性,如何不令人感到惊讶呢?这些穿戴着特殊服饰和面具的人物,扮演神灵和祖先;他们定期返回自己的村落,在那里跳舞,惩罚或奖励孩子们;在传统的乔装改扮下,这些孩子认不出自己的父母或亲友。而圣诞老人与其他在现代较不受重视的人物,如啃指妖[10]、鞭子老爹等,肯定属于同一家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同样的教养趋向之下,今日扬弃了这些带着惩罚性质的“卡奇纳”,却让圣诞老人的仁慈性格受到颂扬,而不是如实证和理性思考所推断的那样让他受到同样的批评。就此而言,这当中并不存在教养方式的合理化,因为圣诞老人不比鞭子老爹更“理性”(教会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确切地说,我们看到的是神话被移植了,这一点需要加以说明。
当然,在人类社会中,启蒙仪式和神话具有一个实际作用:它们让年长的人借此使年幼的孩子听话并且顺服。整整一年,我们以圣诞老人为由,提醒我们的孩子,圣诞老人的慷慨与否取决于他们的乖巧程度;而定期分发礼物的特点,则能够将孩子们的要求集中在短时间之内,也就是当他们真的有权利要求礼物时。但这个简单的语句已足以粉碎功利主义的解释。因为,为何孩子有权利?这些权利又为何可以如此专断地强迫成人接受,并使得他们发展出一套复杂且代价不小的神话及仪式,以钳制和约束这些权利?
我们马上可以了解,对圣诞老人的信念不只是成人对小孩的哄骗,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两代之间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交易(transaction)。所以,在整个仪式中,我们用绿色植物如松树、冬青、常春藤、槲寄生等装饰我们的房子。这些物品在今日不需通过某种利益交换便能得到,但在过去,至少在某些地区,是两个阶层人民之间的某种交换:在英格兰,直到18世纪后期,妇女仍会在圣诞节前夕去劝善(a gooding),也就是挨家挨户地募捐,然后将绿色的枝丫作为回报送给捐助者。我们可以在孩子们身上看到同样的交易状态。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向圣尼古拉恳求礼物,孩子有时会乔装成妇女。换言之,妇女、儿童,两者都是尚未启蒙者(non-initiés)。
然而,这个启蒙仪式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面向,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比起上一段文章中提到的功利主义考虑,它其实更深入地阐明了这些仪式的本质。就以我们曾提及的,普韦布洛印第安人(Indiens Pueblo)特有的卡奇纳仪式为例。难道仅只是为了让孩子害怕或尊敬卡奇纳,使孩子乖乖听话,就隐瞒卡奇纳由人类扮演的事吗?是的,可能是,但这仅仅是仪式的次要功能;因为还有另一种解释存在,而起源神话(mythe d'origine)十分清晰地呈现了这种解释。在这个神话里,卡奇纳是早期原住民小孩的亡魂,这些孩子在祖先迁徙时不幸溺毙在河流里。因此卡奇纳既证明了死亡,亦是死后生命存在的见证。但是,当印第安人的祖先终于定居在现今的村庄后,神话指出,卡奇纳每年都会返回此处,并在离开时带走孩童。原住民们因为担心失去后代,于是向卡奇纳承诺,每年都以面具和舞蹈的方式来扮演他们,希望卡奇纳留在冥界。如果儿童被排除在卡奇纳的秘密之外,首先肯定不是为了使他们惶恐害怕。我会很乐意地说是因为相反的理由:这是因为他们就是卡奇纳。他们之所以被排除在哄骗之外,是因为他们代表了现实,而这场骗局便是与现实的妥协。儿童们的位置在他方:不是与面具和生者一起,而是与神灵和死者同行,和死者变成的众神灵一起。而这些死者就是儿童。
我们认为这种解释可以扩展到所有的启蒙仪式,甚至适用所有二分法的社会。“未启蒙者”(non-initiation)并不单纯仅代表被剥夺的状态,只意味无知、错觉或其他的负面含义;启蒙者和未启蒙者,有着正向的关系,这是两个群体之间的互补,一者代表死者,另一者代表生者。甚至在仪式进行中,二者也经常互换角色,不断反复;因为相对而产生观点的互换,就像镜子与镜子相对而立,无止境地重复。如果未启蒙者是死者,他们也同时是至上启蒙者(super-initié);而且,当启蒙者人格化了死者的鬼魂,以吓唬新进者,那么之后的仪式中,这些新进者的任务就是驱逐这些鬼魂,并防止他们回返。不必进一步去思考这些可能使我们离题的议题,只要记住,有关圣诞老人的仪式和信仰是属于启蒙社会学的范围(这是毫无疑问的),它们突显出在儿童和成人的对立背后,存在的是更深层次的、死者和生者之间的对立。
*
在以纯粹共时性(synchronique)对某些仪式和作为其基础的神话内容进行分析之后,我们来到结论的阶段。而一个历时性(diachronique)的分析,也会使我们获得同样的结果。因为普遍来说,宗教史家和民俗学家都认同,圣诞老人的起源可远溯至欢乐教主[11]、疯癫教主[12]、失控教主(准确翻译了英文的 Lord of Misrule)[13]等这些在特定时间内成为圣诞节之王的人物,并且都是罗马时期农神节之王(roi des Saturnales)[14]的继承者。农神节是鬼魂的庆典,也就是那些因暴力死亡或未被妥善掩埋的死者的节日。因此,在贪噬孩子的老农神身后,我们能看见数个对称影像的轮廓:圣诞老人,孩子们心中的善心人;斯堪的纳维亚的尤雷波克(Julebok),从阴间携带礼物给孩子的长角恶魔;圣尼古拉,使孩子们复活并用礼物满足他们;以及最后,卡奇纳,早夭的孩子,不再扮演孩童杀手的角色,而成为惩罚和奖赏的分配者。我想补充一点,如同卡奇纳,农神的古老原型是掌管萌发的神。而如圣克劳斯或圣诞老人这样的现代人物,事实上融合了数位宗教人物:欢乐教主、受到圣尼古拉庇护而扮演主教的孩童,以及圣尼古拉本身;而圣尼古拉的庆典则可以直接溯及与长袜、鞋子和壁炉有关的信仰。欢乐教主的节日是12月25日,圣尼古拉日则是在12月6日,扮演主教的孩童是在圣婴(Saints Innocents)之日选出的,也就是12月28日。斯堪的纳维亚的尤雷波克节庆则是在12月举行。我们可以直接参照贺拉斯提到的自由的12月[15],自18世纪开始,杜·蒂洛特[16]便以此将圣诞节与农神节联系起来。
但是,用死后继续存在的亡灵来解释仍然是不完整的,因为习俗不会无故消失或持续存在。习俗持续时,原因不在于它在历史上的固着性(viscosité),而在于某一功能的持久性。这也是我们的分析所必须揭示的。如果我们在讨论中给了普韦布洛印第安人一个主导地位,那是由于他们的体制和我们的体制间缺乏任何可以想象的历史关系(如果将某些17世纪时来自西班牙的影响除外)。这就表示,关于这些圣诞习俗,我们所面对的并非只是历史残迹,同时也要面对社会生活当中的思想和行为。农神节和中世纪的圣诞庆祝活动,并非这个相对来说难以解释且缺乏意义的仪式的最终论据,但是它们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比较材料,使我们可以厘清循环重现的仪式背后的深层意义。
圣诞节中的非基督教面向,与农神节十分相似,这点并不令人惊讶,因为有很充分的理由认为,教会将耶稣诞生日定于12月25日(而不是3月或1月),是用以取代异教节庆。这些节庆主要在12月17日举行,到了法兰西第一帝国末期,已经延长为七天,也就是一直持续到24日。事实上,从古代一直到中世纪,“12月节庆”都有相同的特征:首先是用绿色植物来装饰建筑;然后是交换礼物,或是给孩子们礼物;还有欢乐的气氛与盛宴;以及最后,富人与穷人、主人和仆人之间的友好往来。
当我们更进一步分析这些事实,会发现两者于某些结构上有令人惊异的相似性。与罗马的农神节一样,中世纪的圣诞节庆也存在着两个相反却交融的特点,就是聚合与共融:阶级和身份之间的区别暂时被消除了,奴隶或仆人坐上主人桌,主人成为他们的家仆;华丽的餐桌上,盛宴开放给所有的人;男男女女互相交换服装。但与此同时,社会划分为两个群体:年轻人自成独立的团体,选择自己的统治者,即青年教主,或者如苏格兰的疯狂教主(abbot of unreason)。而正如这个称号所阐明的,这些年轻人放任自己的不理性,导致对其他人的伤害,在文艺复兴时期,甚至还采取了最极端的形式——亵渎、抢劫、强奸甚至谋杀。圣诞节期间,就像在农神节时,社会根据一套双重节奏运行:加强团结以及激化对立,这两个特点被视为相互关联的相对面。而欢乐教主这位人物就是这两个面向之间的媒介。他甚至受到教会当权者的认可和确立,他的使命便是在一定限度内逾越。欢乐教主,他的功能和他的远房后裔——圣诞老人——的人格和功用之间,有什么关联?
在这里,我们必须仔细分辨历史观点和结构观点的不同。从历史上看,我们已经说过,西欧的圣诞老人以及他对于烟囱和鞋子的偏爱,是来自圣尼古拉节庆,并和三个星期后的圣诞节庆祝活动同化了。这告诉我们,年轻的教主变成了一个老人。但历史和历法上的巧合联结只能说明一部分原因,这样的角色转换应该是更有系统的。一位真实人物变成了神话人物;一位象征与成年人对抗的年轻圣人,变成了熟龄的象征,并传达对年轻人的宽厚;品性恶劣的信徒,现在负责赞扬良好的行为。青少年公然挑衅家长已不复见,取而代之的是家长隐身在假胡子之后,满足孩子的愿望。假想的中介者取代了真实的中间人,并在它改变性质的同时,朝另一个方向运作。
我们不再讨论那些不是必要而且会引起思考混淆的面向。很大的程度上,“青年”这个年龄阶层已经从当代社会消失了(虽然近年来我们目睹了一些重建尝试,但这些尝试的结果如何还言之过早)。一种昔日由三组要角——儿童、青年、成人——参与的仪式,今日变为只涉及成人和孩童两个群体(至少关于圣诞节的部分是如此)。圣诞节的“疯狂”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它的立足点。而它在转变的同时,也慢慢淡薄了:在成人间,圣诞节的疯狂仅仅残存在平安夜的小酒馆里,以及除夕夜的时代广场上。但现在,我们宁可研究一下孩子的角色。
在中世纪,孩子并不会耐心等待他们的玩具自壁炉从天而降。他们会乔装打扮,并成群结队(老法国人因此称他们为“乔装者”[guisarts]),挨家挨户唱歌并献上他们的祝福,以换取水果和蛋糕。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会呼唤亡者。例如在18世纪的苏格兰,他们唱着这首诗歌:
起来吧,好妻子,不要懒惰。
当你在这里时,享用你的面包;
时候就要到了,你就要死了,
到时就不想吃饭也不想要面包。[17]
即使我们没有这个可贵的线索,以及(同样重要的)参与者乔装成神灵或鬼怪的佐证,对于儿童募款行为的研究也能成为线索。我们知道,这些募款行动并不限于圣诞节[18],而是在整个秋天持续进行。那时正是夜暮威胁到白日,逝者纠缠生者之际。这些活动通常始于耶稣诞生日之前几个星期,大多是三个星期前,因此与同样也是乔装打扮来劝募的圣尼古拉节庆——他使死去的儿童复活——建立起联结。它们的特征在秋季一开始的万圣夜劝募(教会后来决定将这个活动移至万圣节前夕)中更是显著。即便在现今的盎格鲁-撒克逊,仍可看到孩子们装扮成幽灵以及骷髅,缠着成年人,除非他们给一些小礼物才得以脱身。随着秋意渐深,从初秋一直到冬至(意味着挽救光明和生命的日子),就宗教仪式上来说,伴随着一个辩证进程,主要的步骤则是:死者复返,带着威胁和迫害的行为,与生者达成共识,用服务和礼物交换,最后生命得到胜利。所以在圣诞节,死者满载礼物离开生者,让他们平静生活,直到来年秋天。值得深思的是,信仰天主教的拉丁国家,直到上个世纪,都还强调圣尼古拉节庆,也就是一种形式较为节制(mesurée)的关系;而盎格鲁-撒克逊人则自然地将它分为两种极端、对立的形式:在万圣夜,孩子们扮演死者,敲诈大人;而在圣诞节,成年人满足儿童,来激发他们的活力。
*
据此,看似矛盾的圣诞节仪式特性得以厘清:在三个月的期间,死者介入生者生活的情形愈来愈显著且迫人。在它们离开前夕,人们庆祝,并给它们最后一个自由表达的机会,或者像英文所忠实传达的那样:让它们闹翻天(to raise hell)。但是在一个充满生者的社会里,只有那些就某种程度来说无法完全融入群体的人,也就是具有异质性(altérité)特质的人,才能化身为死者。而这个异质性,就是至上二元论——死者/生者——的记号。因此,我们并不会讶异于异乡人、奴隶和孩子们成为这个节日的主要受益者。这节日为政治或社会地位低下者与年龄不平者提供相同的判定标准。事实上,有无数的事实证明,平安夜聚餐的真正独特之处便在于给死者提供一餐(尤其在斯堪的那维亚和斯拉夫世界),客人在此时扮演死者的角色,就如同儿童扮演天使的角色,而天使本身,也是死者。因此,圣诞节(No?l)和新年(Nouvel An)(其为同源对偶词)成为交换礼物的节日也就不奇怪了:死者的节庆基本上就是他者的庆典;因为,成为他者,是死亡这件事最先给我们的大略意象。
在此,我们试着对这份研究最初的两个疑问提出解答。为什么“圣诞老人”这个人物会不断传播发展?为什么教会对于这种发展感到担忧?
我们已经看到,圣诞老人是疯狂教主的继承者,同时也是他的对照。这种转换首先是我们与死亡关系改善的迹象;我们不再认为,让死亡周期性地破坏秩序和规律,对于逃离它有所帮助。现在我们和死亡的关系是由一种带点倨傲的善意所主宰:我们可以慷慨大方、主动出击,因为只不过是给它礼物,甚至玩具,也就是一些象征符号而已。但是这种死者与生者间关系的弱化,并没有牺牲了体现这种关系的人物,相反,他发展得更好。如果我们不承认,这种面对死亡的态度以它特有的方式继续存在我们这一代中,这个矛盾便无法解决。此态度也许不是传统对于鬼魂和幽灵的恐惧,而是对于死亡本身以及它在生活中代表的贫乏、冷酷和剥夺感的恐惧。想想我们从圣诞老人那里得到的温柔关爱,想想我们为了维持他在孩子们心中那不可动摇的魅力而必须谨慎小心。因为在我们内心深处,也总是渴望相信一种没有节制的慷慨、一种毫无心机的盛情(即便只有一点可能),相信在这段短短的时间内,一切恐惧、嫉妒和痛苦都会暂时停止。也许不是所有人都完全同意这样的幻想,但当其他人怀抱着这样的希望时,至少让我们有机会在这些年轻灵魂点燃的火焰中得到温暖,这也说明了我们努力的理由。我们相信,若孩子们的玩具来自另一个世界,我们便可以留住我们的小孩。这其实是个秘密活动的托辞,鼓励我们将玩具赠予彼界,好让它们转赠给小孩。通过这种手段,圣诞礼物成为寻求美好生存的真实牺牲品,前提是不要死亡。
萨洛蒙·雷纳克[19]曾在文章中深入分析,古老宗教和现代宗教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异教徒向死者祈祷,而基督教徒为死者祈祷”[20]。毫无疑问,为死者祈祷,与我们每年——而且愈来愈常——对孩子们夹杂着恳求的祈求大不相同:在传统上,孩子是死者的化身,我们希望恳求他们,通过借由相信圣诞老人,帮助我们相信生命。
无论如何,我们把线团理出了头绪,揭开了同一个现实两种不同诠释之间的连续性。教会谴责圣诞老人的信仰其实是现代社会中异教徒最坚强的堡垒以及最活跃的中心之一,这肯定是没错的。剩下的问题只是现代人能否捍卫自己作为异教徒的权利。总而言之,让我们提出最后一点作结:从农神节到圣诞老人的演变之路十分漫长。在这途中,农神节的一个基本特征(也许是最古老的特征)似乎永远失去了。因为弗雷泽[21]已经指出,农神节之王本身就是一个古老原型的继承者。这个原型是,在化身为农神,且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允许从事所有不当的行为之后,隆重地将自己献祭给神灵。而因为第戎焚烧圣诞老人的火刑,使得神话里的主角得以恢复他所有的特征;并且,这个想要灭绝圣诞老人的特殊事件一点也不矛盾,第戎教士只是在几千年之后,完全复原了一个仪式上的形象;在要摧毁它的前提之下,第戎教士反而证明了这个形象的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