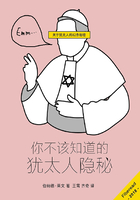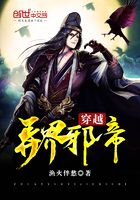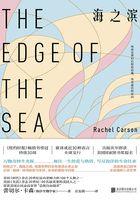江南可采莲
晚唐诗人李商隐有两句诗:“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表明荷花生于暮春枯于暮秋。暮春时节的荷塘冒出荷叶的尖尖角,暮秋时节的荷塘,便是苏轼所形容的“荷尽已无擎雨盖”了。荷花跨春、夏、秋三季,春生秋枯,夏季则是荷花的全盛时期。荷花在许多省市都有,但盛产于号称“江南”的江浙两省。尤其是西湖,“十里荷花”,“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著称于世。从古诗看,江南盛产莲藕,可以上溯到汉乐府诗中的采莲曲《江南》,一直传诵,名闻遐迩。试读: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
鱼戏莲叶间:
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
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不仅表现莲藕的面广量大,而且以五个连动式的“戏”字,重现了一千多年前采莲的规模和采莲人的精神、心态。采莲动作按东、西、南、北次第行动,荷塘的鱼群也便因采莲人的活动而按方位退却嬉戏。人是主动的,鱼是被动的。诗人不说,意在其中。诗从“江南可采莲”开始,以人的劳动和鱼的嬉戏的方位,团团转地结束,令人感到采莲的过程,是一个轻松愉快的过程,是一个人与自然(莲蓬与鱼)和谐的过程。这种“江南可采莲”的劳动,根据历代诗词的描述看,大多由年轻的妇女承担。盛唐诗人王昌龄的《采莲曲》:“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都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便可见当时民风之一斑,采莲女子是要打扮的。今日读之,还不难想见当时妇女采莲的情景和乐趣。
《江南》是一首古代的自由诗,《采莲曲》则是由六朝开始发展、形成,趋向完善的唐代近体格律诗。但从文学史上的影响看,《江南》要超过《采莲曲》。后者从视角的变化和意境的层次看,比较直率,不如《江南》那么曲折,那么多角度地开展诗意。有人嫌它啰嗦,要把四个方位压缩为一句,使《江南》的后五句简化为两句:“鱼戏莲叶间,东北到西南。”这样,简则简矣,却干瘪得太呆板了。要知道“鱼戏莲叶间”是承上启下的警句,叶圣陶先生十分欣赏,曾引入他描写假山池沼的著名散文《苏州园林》中;要是压缩四个方位成为一句,不仅不知鱼儿怎样嬉戏于莲叶之间,更不能显示鱼儿随采莲人的行动而转移方位的细节描写,诗便失去了耐人寻味的艺术魅力。
时至仲夏,是江南可采莲的时候了。当代采莲的方式,当然不会与古代相同,尽管也有诗意,风格也不会与古代相同。只是一想起“江南可采莲”,我便要忆起青年时代的三位老师:胡适、钱玄同和黎锦熙三位先生关于“莲叶何田田”的一次谈笑风生的议论。时间是在一九三六年的夏天,地点是在北平石驸马大街北平师大文学院国文系主任钱玄同先生的办公室。文学院院长黎锦熙先生正在和钱先生商谈《中国大辞典》的编纂方针,并谈到对古汉语词汇如何准确注释的问题。其中就有《江南》一诗的“莲叶何田田”一句正待注解。恰好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之先生有事找黎先生。于是,他们三人就“莲叶何田田”如何注释开始随便谈心。他们都是海内外的知名学者。钱先生是章太炎的大弟子,他认为“田田”一词可能有错。黎先生说:“对‘田田’注释,历来辞书的注释都不准确,带有猜测性。既已习非成是,还是一以贯之,仍照旧注如何?”胡先生说:“《江南》是一首最好的白话诗,‘田田’一词,可能有撰写之误,但也误了一千多年,改也没有可靠根据。”钱先生说:“对于这个词,当年(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在东京太炎先生的国学讲习所里,我曾疑心‘田田’是‘圆圆’之误。太炎先生曾点头说:‘不是“圆圆”,就是“团团”,反正是因形近致误。’”胡先生说:“圆圆也罢,团团也罢,草书是容易被看成‘田田’的。古人好古贪奇,遂以‘田田’为定论。”黎先生接着说:“简体字的‘团’,如果作草书,更易被混为‘田’字。”钱先生说:“习惯成自然。约定俗成,积重难返,就任其‘田田’下去吧。”三人之间,有议论,无争论。我侍立于侧,如游夏之徒,未敢妄参末议。略忆师说,聊作佚闻而已,也算是“江南可采莲”的一则佳话。
(原载《人民日报》一九九三年六月七日)
离弦之箭
——悼念老友李章伯
今年四月二日早晨七点多钟,床头电话铃声阵阵地响了。一听,是台北北投李章伯先生的夫人戴秀丽大嫂打来的。她声音颤抖,断断续续地告诉我:“月华(章伯的别号)昨天突然去世了。”我的耳朵重听,追问两遍,月华的确走了,如闻晴天霹雳,泪水封闭了双眼,嗓门也顿时嘶哑了。其时,正是我的妻子李兴华去世两个半月,尚沉浸在老年失偶的悲痛中,又失去了平生唯一的知己。顿然醒悟:我的心田,既没有了爱情,又没有了友情,是什么无情的魔掌从心田连根拔去了情苗,只剩下血淋淋的一片。我孤零零地面对晨曦,捧读终年八十八岁的老诗人章伯老兄写于一九三五年的一首小诗:
离弦之箭是无法挽回的
我能挽得住你吗
今朝你是决定走了
走了,永不回来
在月光清冷的坟头
为你开一朵向阳花。
但我怎么也读不出声音来,喷涌而下的眼泪,把六十年前的《小雅》诗刊也弄得潮湿了。章伯何曾想到我用他的诗悼念他呢?
章伯是湖南湘乡人,生长于安化。我们是小学、大学同学,抗战后期,又曾一度同事。自日寇投降,台湾光复,他便于一九四六年初去台湾工作,一度担任台北桃园农业学校校长。那是日本人留下的一所破烂不堪的学校,章伯花两年时间加以整顿,办出了特色。其后,他被调任省教育厅任督学,往返台北、台中、台南各地,视察各类学校,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二十多年,为台湾公认的老教育家。章伯为人内向,事业心强,干一件事,总是全身心地扑上去。他的青年时代是以写诗知名的。他到台湾后,为了教育事业,心无二用,竟未与台湾诗坛相联系,连青年时代的诗友路易士以纪弦的笔名开创现代派,他也未加注意。等他知道,纪弦已去了美国。
我和章伯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创办《小雅》诗刊于北平,是华北唯一的大型诗刊,倡导新诗的现代化。纪弦于同年十一月创办《诗志》于苏州,并与徐迟从经济上大力支持戴望舒于同年十月创办《新诗》于上海。于是,我们这三个刊物,鼎足而立,互登广告,互相支援。我们和纪弦会面,是那一年的七月。纪弦到北平接他的母亲和弟妹南下苏州定居。那时,真是一见如故。彼此的眼球活像诗的火种,心也像没有遮拦的原野,是那么赤诚,无话不谈。最难忘的是纪弦当年侃侃而谈,曾坦率地对章伯说:“中国新文学发展到现在,出了不少小说家与诗人,但是多数小说家是书贾培养起来的,而诗人却是自己奋斗出来的。”章伯听了直点头,立即收入《小雅》诗刊一九三六年八月出版的第二期《一得斋诗话》。纪弦的这两句话,即使对照今天海内外的文坛情况,也是符合百分之九十的实际的。当年我和章伯都了解纪弦是胸无城府极其坦率的人。纪弦知道胡适是我和章伯的大学老师,他提起上海和北平在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六年间,曾掀起一场关于“胡适之体”的诗的形式的争论。当时,首先主张推广“胡适之体”的是陈子展先生(晚年任教复旦大学,已故),曾引起一片反对之声。胡适之先生到一九三六年二月五日,亲自出马,写了一篇《谈谈“胡适之体”的诗》的文章。那时,胡先生刚在北平师大讲完“中国禅宗的起来”的学术讲座,因我曾被指定做他的记录,有机会当面对胡先生说:“诗的形式是发展的。先生的诗,也并无一贯固定的形式,而最好的一首,我以为是悼念徐志摩的诗《狮子》,可惜这类形式的诗您写得太少了。”《小雅》诗刊创刊后,我写过一篇反驳陈子展先生的文章,发表在北平的《文化与教育》半月刊上,胡先生看了颇不开心。纪弦从北平话别之后,也寄来一篇短文《诗的形式问题》,章伯把它编发在当年十二月出版的《小雅》诗刊第四期上。纪弦认为关于“胡适之体”的那场争论,“只不过庸人自扰,原不值识者一笑”。“要知道:诗之所以为诗,散文之所以为散文,其真正的区别乃是在于本质——即内容——方面的,而非在于‘诗行’、‘诗节’与夫‘韵脚’的工整与否。”这是纪弦在抗战前夕公开表示的关于诗的内容与形式的观点。
但,仅仅半年,华北局势紧张。卢沟桥一声炮响,揭开了全民抗战的序幕。我是七七事变后半个月,取道津浦铁路,乘长江轮船,经武汉,去长沙的。那时,我在长沙一所农业学校教国文,月入法币一百二十元。由于其时物价尚未波动,生活所需,绰绰有余。因此,凡路过长沙的诗友,我都能招待。章伯离开北平,晚我半个多月,古都已经沦陷。他是从北平到天津后,改乘海轮到上海,然后溯江而上,到达长沙,由我安排在长沙水风井一家中式旅社,食宿包干,每月才十元。章伯是准备去广西教书,暂住长沙,等待聘约的。事有凑巧,不想纪弦领着全家母亲、妻子、弟妹,一行七八人,也于当年十二月顶风冒寒,到了长沙。我只花了有限的几块钱,在一所有名的牛肉馆,为他们全家接风洗尘。次日,他们便乘火车到贵阳去,目的地是昆明。我和章伯对纪弦一家人印象最深的,一是曼士,纪弦的二弟,在北平送别纪弦全家为我们拍照留念的,就是他;二是路珠,纪弦的小妹。我们一直记得她坐在车厢,隔着玻璃,向我和章伯挥手告别的天真形象!几十年来,我一直记得纪弦的二弟曼士和小妹路珠。章伯也常说:中国的文人也真会形容女性,如“秋水伊人”之类,逗人遐想。你看小妹的一双眼,真是明于秋水,不染纤尘。这是当年的闲话。
但自一九三八年初春,和纪弦全家长沙话别后,便半个世纪彼此不知音信。要不是一九八七年台湾当局同意台胞探亲,我又设法和在美国的纪弦取得直接联系,根本就不知道纪弦已如台湾诗人张默所说的是台湾现代派的旗手。由于台湾诗家洛夫与张默的支持,由我主编的《中国新诗鉴赏大辞典》,才得以选入部分台湾主要诗人的诗作,我也才得以对台湾诗坛有一个轮廓性的了解。也由于台湾和香港的诗刊都是同仁集资创办的,更证实了五十年前纪弦说的话:多数小说家是书贾培养起来的,而诗人即是自己奋斗出来的。一点不错,台湾有成就的诗人几乎都是自己奋斗出来的。只是令人遗憾,一九八八年六月,章伯偕夫人来大陆看我,和他谈起纪弦,他虽然在台北四十多年,却与纪弦未见一面,而我则与纪弦小妹路珠同住南京四十年,也彼此没有交往。人寿几何?遭此人为的隔绝!今年元月,我的老伴李兴华不幸去世,章伯闻讣,便打长途电话安慰我,并且计划于春暖花开时节,偕同夫人、女儿(在德国留学多年的音乐家、钢琴家李晚翠)一道来看我。我正期待这么一天的到来,谁知章伯竟于四月一日撒手而去。他到台湾后,虽未从事诗的活动,但也写了不少“解放牌”旧体诗,还写了遍游欧美国家的日记。章伯晚年的旧体诗,多打破传统格律,也就是不拘一格,写所闻所感,指陈时弊,既写得很自然,又写得很老辣。他是学外国文学的,为了消遣晚景,作了一些中诗英译的工作,颇有可读性。他的诗作充沛着生命力,正如他是一个健康老人一样。尤其是《咏史》长诗,蕴含哲理,实一可传之作。他是应该活过百岁的,我曾与他相约,作一场生命的竞赛。哪知人有旦夕祸福,他突然撒手而去。我得知章伯的噩耗,把难于言表的悲痛,凝聚为一首挽联:友好七十年,无话不谈,谊深手足;阴阳几万里,有情难诉,泪洒云天!我还来不及函告在加州的纪弦。纪弦与我同是八十岁的老翁,得知章伯去世,他会联想到他的《火葬》一诗,章伯的确到另一个国度去了。章伯新旧诗很多,一时搜集不齐,我们为他暂编《月华轩诗稿》,将在香港出版,作为赠送亲友的纪念品。章伯!章伯!我愿代表青年时代的诗友纪弦,同声一哭,愿你安息!
一九九三年六月六日于南京
(原载台湾《联合报》一九九三年七月三十日)
新世说五则[1]
烈士只流一滴血吗?
徐州市南郊,有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岿然耸立。六十年代中期淮塔落成之时,某君曾写五绝一首:“塔在如人在,情深似海深。曾将一滴血,赢得万家春。”发表之后,颇为方家激赏,认为四句二联,对仗工稳,情意蕴藉,可慰英灵。但曾几何时,风云突变,大乱十年,小诗蒙难。诗的第三句,被歪曲为恶毒攻击人民解放军,引来反复批斗。一名红卫兵“义正词严”质问道:“红旗是烈士鲜血染红的,难道只流一滴血?”某君有口难辩,只有顺口解释:“我的诗是说解放军的损失最小最小,而取得的胜利最大最大。”不料就此过关。
“何吴余”是“河无鱼”吗?
三年困难期间,某校师生下乡劳动,有三位教师利用休息时间联句。他们一位姓何,是党员,一位姓吴,另一位姓余,均为非党员。他们以联句的方式,集体创作了一首七律,歌颂农村新气象,署笔名“河无鱼”,盖何、吴、余三姓的谐音,取其风趣而已。十年动乱期间,有人张贴大字报,说他们以笔名影射攻击党的领导,连河里鱼都死光了。两位非党员当“牛鬼蛇神”批斗,那位党员则作为“五一六分子”隔离审查。一场批斗,轰动校内外。
难道只红一层皮吗?
某君在六十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到农村劳动,参加拔萝卜。他看见一种叫做腊萝卜的东西,又红又大,十分可爱。当时正提倡“又红又专”,他便即兴赋诗:“红专党所期,劳动奠其基。莫学腊萝卜,只红一层皮。”诗意只是说要红透专深,不要只重外表。哪知“文革”一开始,首先出现批斗这首诗的大字报。说某君写黑诗,讽刺革命派群众,提出质问:“难道他们只红一层皮吗?”
你配称孺子牛吗?
十年动乱中,某君蹲牛棚。白天劳动是拖拉石磙打场秋收。石磙原是牛或驴拉的,因缺少牲口,便由所谓“牛鬼蛇神”代替。某君即兴口占五绝一首:“广场有石磙,往复百千周。我亦团团转,甘为孺子牛。”自鸣得意,害怕忘记,用铅笔写在草纸上,谁知在大解时,那片纸掉在蹲坑旁,为红卫兵拾去。红卫兵看到当天只有某君拉石磙,就笑嘻嘻地说:“你会写诗吗?”某君说:“不会。”红卫兵立即收敛笑容,取出纸头问:“这是谁写的?不是你的笔迹吗?你写了多少交待材料,笔迹一样,还想赖掉吗?”某君说:“那叫什么诗嘛,只是打油!”红卫兵勃然大怒:“混蛋,只有鲁迅才能称孺子牛,你算老几?只兜了几个圈子,就配称孺子牛吗?”某君连声认罪:“不配,不配!”
“两岸猿声啼不住”。
高龄九十五岁的郑逸梅老人,是硕果仅存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其为人也,好学深思,博闻强记,文坛掌故,多耐保存。在国内有“补白大王”之称,在国外有“电脑”之誉。传说其在十年浩劫中,虽年逾古稀,亦在劫难逃。但此老胸怀旷达,生性乐观,批而不臭,斗而不倒,身在批斗台上,目空一切,旁若无人,口中念念有词:“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原载《雨花》编辑部编选《新“世说”选粹》,江苏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关于冯至先生给我的三通信函
冯至先生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一位身体健康、未显老态的长者。他长我七岁,诗龄比我长达七八年,而成就则我无法望其项背。他的逝世,我感到很突然;惊闻噩耗,也就特感哀痛!冯老是二十年代中期崭露头角的抒情诗人,又是海内外的知名学者,对民族、对国家,贡献很大,而又谦光照人。作为诗人,他坚持创新,直到晚年还创造了讽刺“好古之风”的格律诗“新绝句”。他的逝世,确是当代中国诗坛无可弥补的损失。
为了悼念冯老的逝世,特检出近年他给我的三封信,以示沉痛的缅怀。第一封信,是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九日写的。那一个月,他到南京参加全国外国文学研讨会,我曾看望他两次。他的和蔼可亲的形象一直铭刻在我的心目中。我赠给他一部由我主编的《当代抒情诗拔萃》,选有他的“新绝句”,他非常高兴。他听说我正主编第一部《中国新诗鉴赏大辞典》,也深感切合时宜,并欣然承诺为大辞典卷首题辞。他开会返京,便写了这封信,并自选了若干首诗供编辑组参考,显示他的治学谨严,态度也极其谦逊。
第二封信是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写的。其时新诗大辞典已经如期出版。他因为收到较迟,便借龟兔赛跑的寓言,表示他内心的旷达与幽默。大辞典题辞的排列是序齿的。他略长于臧克家同志,由于编辑组的疏忽,把他的题辞排在臧老之后,臧老函嘱第二次印刷要改过来。不久,即在第二次印刷时改正,可是冯老毫不计较。
第三封信是在一九九〇年十月八日写的,因我去信向他祝寿,并希望他继续写诗。他以谦虚的语气,认为写诗上虽未忘怀,却存在“与外界很少接触,因而感觉日趋迟钝”的困惑。这也是冯老晚年的写诗甘苦谈。
总之,冯老的这三封信,对我们后死者,在处世、为人、治学创作上,都有丰富的养料可资吸取。对研究冯老的生平与创作的同志也是极其可贵的第一手资料。
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四日
附志于南京待漏轩
附信:
(一)
奔星同志:
这次到南京开会,得与您晤面,并蒙赠《当代抒情诗拔萃》,深感荣幸。但因时间仓促,未能深谈,不无遗憾,近接到江苏文艺出版社关于新诗鉴赏大辞典的通知,得读您在上面的附言,谨遵命另纸题字数语,不知符合您主编辞典之精神否?并选拙作数首如下:《我是一条小河》、《蛇》、《南方的夜》、《威尼斯》、《深夜又是深山》(可改题名为“深山夜雨”)、《歧路》、《煤矿区》、《皮鼓》、《潭柘寺的千年银杏》、《我和祖国之三》,除最后两首见于一九八五、一九八七的《诗刊》外,均见于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冯至诗选》或《冯至选集》第一卷中。作者往往缺乏自知之明,常有偏见,不足为凭,我还是尊重选者的慧眼。
出版社还寄来一个表格,我不想担任写“赏析”,不填写了。请您替我向出版社表示歉意。
敬祝即将到来的春节愉快。
冯至
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四日
(二)
奔星同志:
三月二十四日来函早已收到。直到五月十日我在外文所开会,才收到这部黄金色封面的大辞典。一来是如今印刷品挂号往往似乌龟爬路,中间要耽搁许多时日;二来是我很少去外文所,这部书也可能在外文所睡了许多天的觉。儿时读龟兔竞走寓言,这次我得到此书,不料龟兔习性,兼而有之。
在你的倡导和努力下,群策群力,广事搜寻,成此巨著,不胜钦佩。诗人的创作,评论家的分析与阐释,互相辉映,相得益彰。当然,入选与否,未必尽如人意,这也难以避免。但我深信,在取舍之间,你是经过仔细斟酌的。总之,我作为新诗爱好者,备有此书,七十年新诗走过的道路,风风雨雨,山山水水,可以说是尽收眼底了。近些年来,你对于新诗的鉴赏研究和资料整理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至于题辞排列先后,不关重要,我毫不在意。
此致
敬礼!
冯至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
(三)
奔星同志:
读九月廿日来信,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非常感谢。一年一度的生日,越来越觉对于我是一种惩罚。一年的岁月又过去了,而工作做得是那样少,徒增愧疚,这真是大大辜负朋友们的期望。诗,我不敢忘记它,无时不想对它有所呈献,无奈近来与外界很少接触,因而感觉日趋迟钝,深深尝到“老”的滋味了。我常读到您关于诗的文章,很钦佩。
此致
敬礼!
冯至
缅怀谢六逸先生
一九九〇年十月八日
一九四三年九月,我因应成都金陵大学之聘,辞去桂林师院广西教育研究所研究员之职。承桂林师院中文系主任张世禄先生设宴饯行,并请吴世昌等教授作陪。其时桂林正处于日寇空袭之下,都认为四川乃天府之国,将是复兴基地,我能先走一步,朋辈特表欢送。
那时,黔桂铁路尚未通车,从桂林到贵阳,要先到金城江再转乘汽车,少则一周,多则半月。我曾托一位老同学、担任贵阳师院总务长的侯子石先生代买去重庆的汽车票。因此,我一到贵阳,他先来看我,对我说:“贵阳师院(今改贵阳师大)中文系主任谢六逸先生在上海就知道你是搞新文学的,曾在北平主编《小雅》诗刊。他说:‘这里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何必舍近求远呢?’”我说:“谢六逸先生是新文学的前辈,我当然要拜访他,只是我的目的地是成都,不能失信于人。”我的老同学就说:“先不忙买票,明天一同去看望谢六逸先生吧。”谁知这是一锤定音。次日下午谢六逸先生设宴为我接风,席间向我一一介绍中文系的中老年教师。其中竟有一位曹未风教授,和先兄吴兰阶是二十年代末在北平师大英文系的同学,握手话旧,倍感亲切。那时他担任贵阳文通书局总编辑,兼贵阳师院教授。交谈之时,忽听有人插话,说他是茅台酒厂的“乘龙快婿”。谢六逸先生举杯祝酒,便说今晚的酒是特级茅台。可惜我生平不善饮,只能抿酒示谢,辜负了主人的深情厚谊。但主人的过分的热情,酒香扑鼻,也不觉陶然欲醉。在一阵阵掌声中,谢六逸先生双手捧送副教授聘书,连声说:“委屈,委屈,半路拦截,失敬失敬。”在醉眼蒙眬中,我竟成了贵阳师院的一名副教授。当时我年方而立,一身西服,面对一批穿长袍马褂的中老年教授,色彩颇不协调。我本拙于交游,只能在感谢之余,请前辈们多多赐教。
为了入境随俗,谢六逸先生安排我休息一周。那时,因暂不开新文学课程,我作为副教授,要担任两门选修课,教务处送来的课表,主要是“杜诗选讲”,还搭配一门“古代文选”。我虽对古典诗文向有兴趣,但在行色匆匆中,都得现炒现卖,边编边讲。“古代文选”从《史记》的本纪、列传讲起,选完篇目,便请助教交印,尚好应付。只是“杜诗选讲”,每周要编四万字左右的讲稿,既有单篇赏析,也有综合评议。迫得夜以继日,笔不停挥,连向一些老教师“拜码头”或讲社交的时间都没有了。穷两个月之力,便编印了一部将近三十万字的《杜少陵绝妙诗笺》,由教务处油印成册,看来尚有气派。当时贵阳师院的几位中老年教授,喜爱宋诗,他们崇敬贵州的先贤,如独山的莫友芝、遵义的郑珍(子尹),都是清末宋诗派诗人。在他们心目中,我这个年轻副教授居然主讲杜诗,并在短期间编成一厚册讲义,未免疑信参半。当时作为系主任的谢六逸先生,却以鼓励为主,见到讲义,总是笑嘻嘻地说我博古通今。但我从不自满,希望他多加指点。他那一贯的学者风度,从不挫伤教师们的积极性。他认为教授们编出的讲义,对于青年学生也是开卷有益的。我的课代表是一位女同学,沉默寡言,要她征求同学意见,总是说没啥意见,讲义内容丰富。但一位教哲学的友人在闲谈中说:我们都是过来人,学生对老师讲课说三道四是正常的。在高等学府讲学,唐诗与宋词历来都有争论。我说:我爱唐诗也喜欢宋词。贵州先贤郑子尹的《巢经巢集》我是比较熟悉的。还是谢六逸先生说得好,最高学府,难得有学术争鸣。抗战时期,萍水相逢,彼此隔阂,难于沟通,也是人之常情。各人讲课,都有讲义,何妨褒贬由人。
谢六逸先生多次与我聊天,都有长者风。他除了鼓励我大胆讲课外,还讲一些三十年代上海文艺界的情况。当年正值鲁迅逝世七周年,我非常赞赏谢六逸先生挽鲁迅的仄韵五律,嵌入“鲁迅先生精神不死”八字,最引人瞩目。但六逸先生十分谦逊。鲁迅先生曾写《教授杂咏》四首,第四首便是讽刺六逸先生的,他毫不介意。当时日寇攻陷桂林,独山吃紧,贵阳震撼,我一个单身汉,便如闲云野鹤,在寒假前夕,北去重庆了。不久,听说谢六逸先生因病谢世,心中十分悲痛。至今整整半个世纪,他开创的贵阳师院中文系,正在大大发展,想他必然含笑于九泉。
(原载《山花》一九九四年第十期)
注释
[1]署名“欧阳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