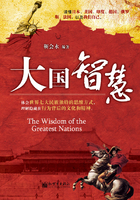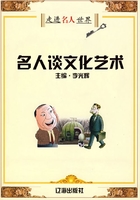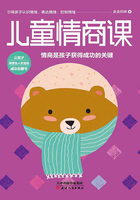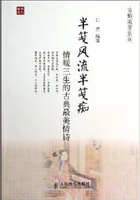如是我母
我三岁丧母,享受过母爱而不自知。母亲去世后,我由祖母抚养,直至国民小学毕业。据祖母回忆说,母亲病危时,示意把我叫到床头,断断续续地对我说:“妈要走了,我只舍不得你。”我说:“我跟妈去,你带我吗?”妈说:“他们要把我埋到土里头的,你不能去。”我说:“我用小锄头把你挖出来。”妈摸着我的头顶,泪水封闭了她的眼睛。但是,我没有流泪,还不懂生离死别之悲痛。不久,妈死了,家里为妈办丧事,我也不懂,仍然到床头去寻妈。祖母说:“妈走了,不能带你去。”我哭了。祖母用几个炮竹哄我,拉扯着我到大门外放响炮。响一下,我蹦一下,笑了。母亲死后,据祖母说,我几乎每夜都在“我要妈”的哭声中,或者睡去,或者惊醒,过了较长时间,习惯了祖母的爱抚,才停止了哭,但祖母仍不敢问我“想妈不”,怕我号啕。
母亲在外祖父家读过书,能看旧小说,也能看报纸,我们乡下有挪威国的传教士,办了一所信义小学,母亲与父亲因为有点知识,都被雇去当教师。据说他们受过洗礼,成了基督教徒。传教士在家乡盖了一座福音堂,占地约一百五十多亩。有一间可容五百人的礼拜堂,有一个可踢足球的操场,一边临大路,靠里盖了几座二层楼房,是教室和宿舍,特别令人瞩目的是一座高耸云霄的哥特式尖顶五层楼房,是外国牧师的高级住宅,闲人是免进的。据说牧师们可以定期登楼目睹天堂。老百姓竟信以为真。
我的故乡是湖南资水下游的山区,老百姓很穷,看见这么一座福音堂,既惊讶其神奇,又羡慕其富丽。资水每年夏天因山洪暴发,到达东坪镇(今天的安化县城)便酿成泽国,人畜死亡,瘟疫流行。传教士便利用这个时候代表上帝,大施仁政,赈济灾荒。凡信教者都可得到救济;一般沿门乞讨的灾民,每天也能分到三餐稀粥。这样传教士颇受好评。老百姓都说“老外国”(挪威国的谐音)做了好事,信教的越来越多。因为信教者到灾荒年头有饭吃,人们便称信教为“吃教”。我的父母因为是乡村的小知识分子,又当上信义小学的教师,比一般“吃教”者高了一个档次。我就是出生于福音堂的。听说教会养了一批奶牛,母亲因缺奶,我便改吃牛奶,直到断奶的时候。传教士们还有从西方带进山区的罐头牛奶,也经常给我吃。我吃过不少,都称我为“牛奶筒”。“牛奶筒”便成了我的乳名,一直被呼叫到十来岁我离乡背井为止。
当然,教会布施的“仁政”是有限度的。母亲一死,父亲也就失业了,全家搬出了福音堂,回到祖传的几间木屋,跟砖瓦结构的西式楼房相比,自有天壤之别。父亲带着我们兄弟回到老屋,如从天堂回归人间,不再“吃教”了。据父亲说,他与母亲“吃教”,并非信仰上帝,不过为了养家糊口。他们倒是受过孔子学说“祭神如神在”的影响,认为上帝也罢,祖宗也罢,都是心理作用。天上既无上帝,人间也无鬼神。如果有,都是心理作用,导致自欺欺人。当时,父亲还不知什么叫“无神论”,但他实际上却是真正的无神论者。母亲死后,他身体不好,而我们兄弟都在外为未来的衣食奔走,不能照顾他,他只好续弦,娶了继室。我们兄弟在感情上都不能接受,但在道义上仍然在父亲去世后照料继母生活,直到她去世之日为止。感情之为物是很奇特的,尽管我对生母毫无印象,回想起来,却是“祭神如神在”,心理上有一个具体的母亲。继母呢,尽管她在我家生活二十多年,却始终建立不起母子之情。父亲保留了生母的一张照片,经过放大,眉眼模糊了。在照片下面,父亲写了四个毛笔字:“今也四十”。母亲逝世于一九一七年,刚满四十。祖母说,我很像妈。所以我至今保存着妈的遗像。我视息人间快八十年了,超过母亲的生年一倍。要是可以代替她的话,我要代替她活够未尽的天年。可惜我记不得妈的音容,妈当然也不认识白发苍苍的小儿子了。即使人有灵魂,也互不相识。今天,常常听说让某人活在心中,其实,谈何容易?但愿天下为人子女者趁父母在世,多多关心他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至于死后活在子女的心中,且不去说它,说也是白说。因此,我的三岁失母之痛,是难以言传的,姑以一绝作结:
浩大天无极,从来喻母恩。
浮云游子恨,不识未归魂!
一九九一年二月十一日于南京师范大学
(原载《我的母亲·新三辑》,香港中国文化馆,一九九二年)
纪弦的天真与直率
最近承台湾著名诗人张默赠送所编台湾现代百家诗选《感月吟风多少事》一册。张默在导言中说:“中国现代诗在台湾的发轫,应以纪弦于一九五二年八月在台北独资创办的《诗志》开其端,……其对新诗运动种子的散播,似乎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接着在次年(一九五三)二月,纪弦又独力创办《现代诗》杂志,立而引起文学界更广泛的注意。从此,‘现代诗’这个名称也就确定了。纪弦借‘现代诗’的号召,……确实给予当时诗坛以极巨大的冲击,……的确培植了不少新人。……一九五六年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代,纪弦借‘现代诗’的号召,于元月十五日在台北成立‘现代派’,加盟者先后共一百零二人,诗坛高手几乎全被网罗,声势不可谓不浩大。‘现代派’的创立,的确把中国新诗运动带到一个空前的蓬勃期。”这是张默追述台湾新诗发展的历史时对诗人纪弦所作的介绍,是我与纪弦隔绝了整整半个世纪后所听到的关于他的确切的信息:这和今年一月第一次收到纪弦从美国来信所述的别情,大体是一致的。
纪弦在三十年代和我有过较为密切的交往。几十年来他写的诗比我多,也比我好,在海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我今天不拟评论他的诗,只想谈谈他之为人。因为“为人”与“为诗”是一致的。了解他之为人就更能了解他之为诗。
纪弦原籍陕西,出生河北,家住北京,青年时期多在扬州、苏州、上海。他填籍贯往往是扬州,有时也说是上海。我却一直认为他是苏州人。因为三十年代他同我交往时,全家住在苏州。他那时写诗、办诗刊,也在苏州。
纪弦留给我的突出印象是“天真”与“直率”。我一见到他,便联想起孟子的话:“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纪弦当然不是“大人”,相反,他的性格同孟子说的另一句话差不多:“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就是说,同官场的“大人先生”打交道,要藐视他们,别被他们那种高不可攀、大模大样的架势所慑服。因此,我把孟子说的话改成了“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这不仅适用于纪弦的青少年时代,从他的来信看,也适用于他的老年时代,他那颗“赤子之心”,也就是天真、直率的心,是终其一生的。正是由于他永葆一颗赤子之心,便对人生对自然经常有新鲜的感觉。这便是他的诗的灵感的来源。
纪弦是他几十年前用过的笔名。他原名路逾。最近来信还说用“纪弦”做笔名的原因。他说:“最初的动机是想胖,因我太瘦了。于是翻字典,找到此二字,觉得尚可,就用了。但用了几十年,至今还是那么瘦,一点也胖不起来,怪哉?”试听!年逾古稀的纪弦,说起用笔名的原因时,口气还是那么天真!五十年前,他是“瘦高条”,我要抬头才能窥见其眉宇。他也许是怕我自惭形秽吧,便解嘲地说,他有一次在上海国际饭店乘电梯,几位欧美人也要向他仰望。言下,嘻嘻一笑,像个天真的孩子,似乎老迈的“东亚病夫”一下子返老还童,有一种民族的自豪感与自尊心,从他身上喷发出来。五十年过去了,他从美国寄来的信,还说经常拿出与我和李章伯的合影看看,并且说:我比章伯“高”,却不如他之“长”。李章伯是三十年和我主编北平《小雅》诗刊的老诗人,现年八十二岁,去年夏天从台湾来大陆探亲,曾合影留念,并寄纪弦一张,他提起“高”与“长”,大概尚未忘记当年欧美人仰望他时所产生的豪情逸兴吧。
在中国,职业文人很少。纪弦可以称为现代中国的职业诗人。他在旅居美国后,在所写《勇者的画像》一诗中直率承认:“因为我的活着,就是为了写诗。”这是他为诗艺而献身的誓词。自然,诗人也不能枵腹写诗。为了生存,纪弦也工作过。如教书、编刊物之类的工作,他也干过,但为时都很短,缺少一贯性或连续性。连续不断,数十年如一日的,只有写诗。他是当之无愧的职业诗人。若问他何时开始写诗,他往往微笑地说:“写诗和初恋是同时开始的。”说得多么天真,多么耐人寻味!仔细想来,他的幽默性的笑谈比直接回答具体的年月更加准确。因为“初恋”是情窦初开的标志,而诗是从抒情开始,并以抒情为本职的。情窦初开之日正是诗兴勃发之时。纪弦写诗正是把握了这个最佳的起点。
纪弦其所以能以“初恋”作为写诗的起点,其秘密在于深入“初恋”而又超越“初恋”,从一定的美感距离回顾“初恋”的情怀,而后诗兴勃发,诗潮汹涌。大概是“初恋”不久,二十刚刚出头吧,纪弦写过一首《脱袜吟》。这是他摆脱格律诗的束缚,试写自由诗的开始。诗分两节:
何其臭的袜子,
何其臭的脚!
这是流浪人的袜子,
这是流浪人的脚。
没有家,
也没有亲人。
家呀!亲人呀!
何其生疏的东西呀!
这首诗于三十年代曾广为传播,但是,贬多于褒。到了八十年代仍为某些论者所讥笑。自然,《脱袜吟》只不过是一首失业青年哀叹生活艰难的小诗,应该如何评论呢?评诗是一项严肃的触及诗人心灵的工作。对于《脱袜吟》进行认真的鉴赏,并予以公允的评价的,据我所知,台湾的诗评家舒兰应是第一人。舒兰指出:“这首诗的好处,在于直率,在于有普遍性。它道出了流浪者的孤伶和四海为家的凄苦生涯。”这是切合诗的内容并令人悦服的诗评。舒兰认为纪弦早期的诗,“接受了法国象征派和美国意象派的影响,从而,创造出个人的独特风格来”。的确,《脱袜吟》是以意象的含蓄和象征的技巧取胜的小诗。其好处,就“在于直率,在于有普遍性”,在于表现了三十年代广大青年为寻求个人出路而流露出来的苦闷心情。意象的亲切、语言的通俗、节奏的自然,取得了深入浅出的艺术效果,最后一节确实道出了流浪者的孤伶和四海为家的凄苦生涯。虽然信手拈来,未免粗俗,却令人觉得直率、亲切、自然,引发情绪的共鸣。不是在寻求出路中碰过无数钉子,不是在流浪的生涯中行过万里路,是写不出这样的诗,也读不懂这样的诗的,《脱袜吟》是纪弦为自己,也为遭际相同的青年,写的一首流浪人之歌。诗的结尾凝聚着何等深沉的感受!奇怪的是,它从三十年代到现在却遭到某些人的嘲弄!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不久,北平沦陷,上海、南京相继变色。纪弦被撵出人们称为“人间的伊甸园”的苏州,携老扶幼,沿江西窜,过九江、武汉,到达长沙。那时,我也刚从北平逃出,在长沙一所中专混饭吃,每月一百二十元。由于物价尚未腾飞,勉可维持几位流亡的亲友。纪弦到长沙,正好李章伯也在长沙,由我安排在一家旅馆,每日三餐,六菜一汤,宿费在内,月仅十元。今天听来,如读上古史,如听天方夜谭,但在抗战初期,却的确如此。纪弦初到长沙,大约是一九三七年冬天。他把家属送往贵阳之后,又折返长沙,说是去武汉讨账,便和李章伯同住一个旅馆。我问纪弦:不远千里而去武汉讨账,究竟可以要回多少钱?他掐指一算,收支相抵,与往返旅费相差无几。我与章伯都不禁哑然失笑,他真是不懂得生活的书生气十足的诗人。
纪弦在长沙逗留的期间,什么都习惯,唯独上厕所成了难题。当时长沙的机关、学校、旅舍的厕所,一般都是蹲坑,不同于江南苏州、无锡一带的红漆马桶。粪坑很深,上架木条。坑深尿多,光可鉴人;捂鼻忍受,顿生窒息之感;否则,便要恶心呕吐。纪弦久居江南,一“久而不闻其臭”的名士派,自然望而生畏,却步难前。此事虽小,却须快速解决。只好由我亮出满口多年不讲的长沙方言,和老板娘商量,把她陪嫁的红漆马桶借来应急。纪弦也真天真,马桶一般藏于门角落,而他却要置于屋中央亮相。我回忆中的纪弦,和他寄来的照片里坐在摇椅上晃荡的纪弦,不仅有年龄上的老少之别,也有风度上的缓急之分,但是,天真烂漫似是一以贯之。
自一九三八年春初在长沙分别后,就不知纪弦的下落。想象他在外寇追逐和生活辗转之中,连《脱袜吟》之类的小诗也写不出来了。可能在“君子固穷”之时,实现了孔子的理想:“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吧,这是半个世纪以来,我对纪弦的一贯怀念与推测,直到八十年代初期,才听说他在台湾,开创了新诗的“现代派”,后来又从所谓“横的联系”,回归所谓“纵的继承”,而所谓“回归传统”了。所遗憾者,全是道路传闻,语焉不详。直到台湾当局同意台胞回大陆探亲之后,我先后会见几批台湾诗人,才知道纪弦真的已从大陆“乘桴浮于海”,在台湾从事新诗运动,并产生了如张默听说的影响。加以又从友人处获悉了纪弦在美国的住址,使我与纪弦之间恢复了联系,从他的亲笔来信中才知道,早在一九七六年年底,他又一次“乘桴浮于海”,到美国定居了。纪弦的来信对我真是“特大喜讯”,提笔写了一首打油诗:“云水深藏梦幻情,五十年间雁一声。休问故家归也未,海涛起伏令人惊。”谁知看完他的信,才知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纪弦还是那么直率。在谈到他在台湾搞新诗运动时,劈头一句便是:“你说我又回归传统了,这话不对,我永远是一个现代主义者,但我是中国的现代主义者,而非英美的或法国的。”好家伙,性格不改当年,年老而童心犹在,实在令人欣慰。我祝愿他健康长寿,利用第二次“乘桴浮于海”,在美洲掀起一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主义新诗的高潮。
(原载《诗神》一九九一年第五期)
忆陈瘦竹先生二三事
陈瘦竹同志离开我们快一年半了。他的形象经常出现于脑海,总觉得他还在亲属中、朋友中,并未辞别这个他曾热爱过的世界。我与他是老朋友,他长我三岁多。我们一同迎接了新中国的诞生。从相识之日起,也已三十多年了。不过,我在三十年代就读过他的不少作品,知道他是创作与理论并重的作家。因为当时我在北平,他在南京,彼此没有见过,便从他的姓名悬想其风采。他既名瘦竹,想来是个子高而潇洒,并具有诗情画意的风采和高风亮节的品德。及至五十年代中期把晤于南京,始觉我的悬想,并不完全符合实际。在品德上他确是高风亮节、敦厚朴实的学者,而在形象上则是中等个儿,稍微偏胖的。至于他青少年时代是否瘦削如竹,则不得而知。当时他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我是南京师院中文系教授,正为本科高年级学生开出新诗专题讲座。一九五六年秋,他邀请我指导南京大学中文系将要毕业的几位爱好新诗的同学撰写毕业论文。为此,我与他畅谈过好多次。在言谈中,我发现他是一位极其严肃认真而又富有事业心的学术带头人。他善于发现人的长处,又善于使用人才。我为他的热情所感动,接受了他的聘请,同意指导三至五人的毕业论文。时间过去三十余年,几位同学的姓名差不多都忘了,只记得一位由我指导抒情诗的研究,而倾向于艾青的学生叫骆运启,其他一些也想不起来了。当年我指导南大几位学生写毕业论文,采取有分有合的方式:凡遇普遍性的问题,就合起来座谈;只有个别性的问题,就分别面谈。不论分与合,我都举一些例子,以示有诗为证,力避空谈胡扯。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关于诗的一些理论问题,都沾了些边,有的还谈得比较深入。我很感谢瘦竹同志给了我一个教学相长的机会。当时的毕业论文的指导,颇与我在八十年代初期指导研究生相仿佛。只因一九五七年的那个不平凡的春天来得突然,党为了整风,发动群众大鸣大放提意见。因会议较多,指导毕业论文的工作,只得由经常性改为断续性;随着反右的深入,断续性就转化为停顿性。师生关系原是亲密无间的,因运动性质的转向而出现了裂痕。我因指导毕业同学骆运启研究艾青,而艾青作为研究对象,又较早被定性为右派,消息传到南京,被指导的其他学生便对我反戈一击,加以艾青的研究者骆运启和我这个指导者还被群众揭发出所谓其他的问题,于是我们三位——艾青、我和骆运启——原本是不相干的,竟然先后被划成了一派——右派。陈瘦竹同志是否受到此事的连累,我从未探听过;至于我与艾青以及运启之间,更无从互通信息,只能从自己推想他们,也会像我一样,到过该去的地方,受过该受的磨难,这是“共性”,当然还有个性就难于一概而论了。所可一概而论者,那就是最可感念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万象更新,拨乱反正,我们都或迟或早获得了改正。我虽不知道艾青和运启(现名骆寒超)的详情,却也先后喜读艾青的《归来的歌》和骆寒超的《艾青论》。到一九九一年八月下旬,“艾青作品国际研讨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我应邀与会,与隔绝近半个世纪的艾青终于握手合影,也见到了骆寒超同志对艾青作进一步研究的论著。所遗憾者,瘦竹同志已作古人,未能共享愉悦之情。好在当年他所选拔的学生骆运启,几经磨难,已成为当代中青年学者,而且还在发展,万里鹏程,未可限量,瘦竹同志有知,当可含笑于九泉了。
瘦竹同志是一九九〇年六月二日去世的。他在所经历的新时期十年,教学与科研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这个十年我与他是经常见面的。我和他都是搞现代文学的,凡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鲁迅研究会、郭沫若研究会以及江苏省鲁迅研究会、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等开会,往往不期而会。北至哈尔滨,南至海南岛,更多的是北京和南京,无不因开会而团聚。我们在饭前饭后,会前会后,随意聊天,毫无主题先行的自由谈,真是谈笑风生,不知老之已至。当然,在谈天的过程中,我也发现他的视力更加衰退了,而听力却特别灵敏,记忆力之强尤其惊人。我每次遇见他,他只见我模糊的身影在前,但只要叫他一声瘦竹同志或陈老,他立即响应,叫出我的名字,热情溢于言表。他这种能以声音辨人的本领,可能只限于亲属和比较熟识的朋友,但我的听力和记忆力却远不如他。特别令人惊奇的是,有一次江苏鲁迅研究会召开年会,请他首先发言,他的讲稿是打印出来了的,但他并不看讲稿,用很自然的语调,论述鲁迅的文学成就与思想发展,连夹注在《鲁迅全集》第某卷某页,他也清楚无误地说出来。他这种惊人的记忆力,恐怕要远远超过司马迁所描述的屈原那样博闻强记的水平。不少听过他讲课的中青年学者或学生告诉我,说陈老讲课向来不看讲稿,丝毫没有“背书”的生硬气,而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非常自然生动。这就可以想见他平时读书用功之勤奋,积累之丰富,才能在讲学和讲演中,收到如此头头是道、如数家珍的效果。这是他的独特的本领,也是他的一种独创的艺术。
更令人钦敬和缅怀的是,瘦竹同志在新时期十年中的成就,特别表现在话剧研究和戏剧理论的探索上。他一去世,我才体悟到:当代的话剧界或戏剧界乃至影视界,理论工作是颇为薄弱的。我们可以屈指数出若干个剧评家和影视评论家,但数不出几个戏剧理论家。我于戏剧创作及其理论是十足加一的门外汉,但阅读一些同志介绍瘦竹同志在戏剧理论方面的成果,不仅很受教益,也极表钦敬。他的代表作是《论悲剧和喜剧》,这是一部论文集,据说是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写的,但其深厚的积累却是从四十年代就开始了的。他对于欧美的悲剧和喜剧理论广收博取,形成他自己的理论体系。全国解放后,由于他认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文艺思想,又对欧美的悲剧理论加以清理,批判其中的不合理部分,更深化和净化了他自己的悲剧理论体系。他通过一系列艰苦的探索表明,悲剧的本质,仍以恩格斯说的“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在实际上不可能实践”的观点最为正确,符合欧美乃至中国的许多悲剧的创作实践。他根据恩格斯的观点,对郭沫若写于四十年代抗日战争中的以《屈原》为代表的一系列悲剧,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和科学的评价。在这一方面,他的夫人沈蔚德教授是他的得力助手和亲密的合作者。他们是无愧于专家的称号的。
至于喜剧理论,陈瘦竹同志也作出了独特的成绩。他立足于我国的喜剧实践,有批判地借鉴西方的喜剧理论,对喜剧的本质和喜剧的类型作了深入的研讨。由于喜剧理论在我国当代戏剧界比悲剧理论更为薄弱,陈瘦竹关于喜剧理论的研究就更为可贵。他认为喜剧的根本特征在于引人发笑。鲁迅曾经指出喜剧是把丑恶的事物(包含人物)撕毁给人看,其效果自然引人发笑。陈瘦竹从笑出发,把喜剧划为若干类型。主要有讽刺喜剧,令读者和观众对人物喷发表示鄙视、蔑视以及憎恨之情的辛辣的笑;有幽默喜剧,令读者和观众对人物发出表示善意的讥讽的笑;还有赞美喜剧,令读者和观众对人物发出钦佩、喜悦的赞叹的笑。诸如此类的喜剧类型,已超越了鲁迅当年对喜剧的界说,是富有启发性和建设性的。
在八十年代初期欧美的比较文学思潮被引进中国,有法国学派、美国学派和苏联学派。陈瘦竹同志以严谨的态度迎接了作为一门显学的比较文学,并且写出了一些比较戏剧的论文。这在戏剧领域,也是开风气之先的。
作为中国戏剧界的前辈,陈瘦竹同志对于来自中青年后学的商榷文章,也是认真思考,热情对待的。例如郭沫若在抗战时期写的《孔雀胆》,演出效果听说是不错的。但该剧在史实上有失真之处,在人物形象上有欠妥之处,在主题思想上有不明确之处。听说周恩来同志当时看过剧本和演出之后,曾经善意地指出:“剧本写得还不错,但史实值得研究,而在当时上演此剧,在意义上是不可能与《屈原》等并论的,但是否上演,请郭老他们自己决定。”(转引自一九八〇年一月十七日《光明日报》张颖《领导,战友,知音》一文)此后,郭老对《孔雀胆》作过修改,并写过一些关于《孔雀胆》的文章。八十年代初期,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郭沫若研究论集》一书,收入了陈瘦竹同志的《论郭沫若的历史剧》一文,对《孔雀胆》作了高度的评价,说剧中的女主人公阿盖公主“是民族团结的象征,忠于爱情的典范,值得我们给予深刻的同情”。对此,有一位中年学者王晓祥写了一篇《〈孔雀胆〉质疑》与陈瘦竹同志商榷的文章。不久,王晓祥又写了一篇《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关于〈孔雀胆〉与〈阿盖公主〉》(均收入王晓祥《“床前明月光”新解》一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十二月第一版)。陈瘦竹同志对王晓祥同志的商榷文章是认真对待的。因此王晓祥在该书《编后絮语》中说:“我非常尊敬陈瘦竹先生。陈先生学贯中西,文通今古,对我有关《孔雀胆》的请教,不以毛糙见责,反而当面给以鼓励,充分显示了一代学者虚怀若谷、奖掖后进的伟岸气度。每一忆此,敬意油然。”这些话是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写的,书是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出版的,瘦竹同志当然没有见到。为了弄清瘦竹同志生前对这一“质疑”的具体表态,我曾函询王晓祥同志,他于今年九月二十三日给了我回信。他说:
陈先生看到第一篇《〈孔雀胆〉质疑》后,通过盛荣同志之口,说我“形而上学”。安徽大学刘元树也对我的观点全盘否定。看到第二篇《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后,陈先生通过他的研究生周安华写来长信:经与陈老讨论,取得一致意见:史剧《孔雀胆》历来毁誉不一,众说纷纭。大作从研究元、明史实出发,通过郭沫若对施蛰存小说《阿褴公主》(奔星按:收入施蛰存历史小说集《将军的头》)和周恩来同志对史剧《孔雀胆》的批评,对两部作品发掘表现同一历史题材作出精细比较,并提出自己富有个性的见解,此实令人钦佩!你对有关史实的把握和分析都是无懈可击的。这是现代戏剧研究必须具备的态度。
王晓祥同志又说:
后来我又写了一篇《〈孔雀胆〉在意义上不能和〈屈原〉等同并论——向陈瘦竹先生请教》一文,发表在《郭沫若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四期上,并寄给了陈老。一九八七年我去南京,陈老对我特别好。他认为:一、过去写文章时,用功不够,看法有些偏颇,并对我的论文给予了肯定;二、他说:施蛰存大自己几岁,对这一流派,过去重视不够,现在提出来很好。
从瘦竹同志对王晓祥的回信与面谈看,他是具有学者风度的:对自己严格要求,对后辈充分鼓励。我把此事提出来,既是发瘦竹同志的潜德之幽光,也是揭示老中青学者之间一次百家争鸣的范例。
瘦竹同志虽然永远诀别了人世,但是,他的道德文章,却如南京的紫金山和秦淮河昭然在目。我不禁想起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的结尾,特略改数字,系于篇末,以示缅怀:
钟山苍苍,秦淮泱泱: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一九九一年十月一日于南京
(原载《新文学史料》一九九二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