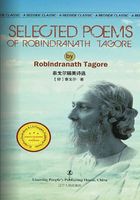一清早,船从普安开出,上午就来到旧城码头。云阳旧城,云门深深,你一道道推敲,门开了,就现出一重重山水故人。
旧城码头,乱石草坡。一下船,就看见两位老人正坐在岸边等船,其中一位还哼唱着山歌——
太阳出来万丈高,
妹妹出来晒花椒。
花椒晒得大揸口,
妹妹晒得汗涔流。
我问:“老辈子,在哪儿学的山歌?”
他说:“在坡坡上干活儿,那些老的在唱,就记得了。”
这唱山歌的老人名叫谭中学,乙酉年出生,今年六十九岁。
“坡坡上总是哦嗬连天的。”旁边的老师傅说,他叫方先云,1953年出生。
我于是坐下来,和他们一起晒太阳、聊天。原来他们在这里等过河船,回对门的宝塔乡。
方先云今天一早来老县城,卖掉了五六十斤油麦菜——“自己种的,一块二一斤。”他倚着空箩筐说,“现在老县城的人都转到高头去了,没钱的人还留在这里。”
而谭师傅今天过来,卖了一些锄草剂,他说:“宝塔乡河边和云阳老县城都淹没了,那些‘双淹’移民迁到江西、湖北、江苏、上海,到处都有。”
我又问:“原先这里是什么样?”
谭师傅指着眼前的江水说:“原先这里是老武装部;那边有一坡梯子上去,两边都是棚棚……”
“我见过的。”我说,“还在棚棚里喝过酒,转眼都是水下的事了。”
“是的。”谭师傅点了支烟,继续说,“对门就是宝塔乡;我们是‘单淹’,土地淹了,房屋没有淹;宝塔乡淹了上百亩的土地。现在好多地都荒起,你想挖就挖;也没有人挖,这里野猪多很了……社员都是麻秧子[94]。”
我又问:“什么是麻秧子?”
“就是最没有用的。”谭师傅笑道。
“现在哪有正经人,”方师傅又说。
而后,我询问过去,谭中学说:“我们老辈子都是湖广填四川的时候过来的,当年八大王张献忠血洗四川,到现在几十朝人了……解放前,宝塔乡有几个地主,像潘祖延、陈茂连,也没吃到什么,还是跟到帮工一起吃,最后减租退押的时候,还是被打了……”
“大跃进的时候,饿死好多人哦!那阵我们还小,把那么多人拉去大办钢铁,也没搞出个名堂。伙食团的人,每顿吃半斤,不做的人吃二两;明里说是半斤,实际伙食团又克扣了……普安死得人烟都没的了。”谭中学师傅如是说。
方师傅又说:“我们宝塔乡小河大队的支部书记姚力先,外号长颈坎儿,伙食团的时候,用棒棒打社员打得不少——社员没吃的,扯点豌豆、胡豆,捉到就打……姚立先后来死了,是老死的。听老人说的,当时的政策严厉得很,当时就有一批万州、云阳来的干部,下放到宝塔乡来挑碗、挑沙,附近有一个碗厂……”
“我十四五岁时候,有一回从猫儿梁下去,去梅子大队催洋芋种,”谭师傅接着说,“之前,他们来我们这里挑红苕秧子,答应给我们一些洋芋种,他们没挑来,让我去挑;我过去梅子、洞鹿那边一看,只有屋,没有人了。”
“灾荒年,我哥和我老头儿去修路,我和我妹在家,伙食团红苕限量,我们吃观音米,那吃不得,是泥巴……伙食团下放他们才回来……”
说到伤心处,谭师傅又唱起山歌,而这一次,是大声唱——
太阳出来云里梭[95],
鸳鸯铺上劝情哥。
劝哥莫去花园耍,
花园二姐要钱多。
我听得高兴,起身给两位师傅点烟,这时,江风吹来阵阵汽笛声。
“气候不同,风来得不同。”谭师傅接着说,“原先清明才断雪,谷雨才断霜,现在冷又冷不过,热又热不过……”
“的确。”我说,“就连我这外乡人也明显感觉到了。”
太阳渐渐升高,过河船来了,谭中学师傅起身叹道:“树老心空,人老颠咚[96],有钱难买少年春。”我点头谨记,并目送着两位师傅乘船离去,回对岸的宝塔乡。
转回身来,我又跟着下船的旅客走上山坡,一起坐在棚棚里歇凉、聊天。这座临江的棚棚我去年来过,主人还在,来往的旅客仍络绎不绝,只是江水更青,坡上的草木更加茂盛。
一位刚下船的老人告诉我,他原先在铁路上工作,老家在龙洞坝上(原来是个乡,现在改为镇了)。坝上、大麦沱整体淹没了。现在和老伴一起搬过来(云阳老县城),住的亲戚的房子,孙子在这边读书,上云硐小学五年级,儿子在外面做工程……从坝上过来十几年了,这里住房不要钱,蔬菜也便宜,就是肉食贵一点,比新县城还要贵……他说完就走进老城,消失在人群中。
一个背着竹筐的中年男子从中坝过来,说道:“来这里卖点面,买点儿东西回去……我们那里是半淹……”
一位白胡子老头告诉我:“家里是农转非,属于三峡库区林区范围……到了六十岁,还要把房子拆了才能买低保,不拆就买不到。”
“我们家在河对门的水磨,属于云阳旧县城。”身边的一个老农民说,“河边的土地淹没了,房子有些拆了,有些没拆,搬迁的移民有七八十户人家,有些后靠,有些搬到了江津。我们是双淹,自己搭个棚棚——也不说是啥子下落,就把你房子拆了……”
我要给他们拍照。旁边的几位农妇赶紧躲开,在一旁笑道:“你是记者,从前来过。”又问:“相片可以马上取出来不?”
我说:“我不是记者,是人民大学的教师。你们给我地址,我回去把相片寄过来。”
旁边人说:“人民大学出来的都是县级以上的干部,你知道不?”
我说:“不知道。”众人一笑。他们中一些人给我留了地址,我小心珍藏,回去一定把照片寄给他们。而后,我又走进旧城。
在一截土路边,见到一个石窟般的小药铺,里面黑黢黢的,百草茂盛。店主冲我微笑,我认出这是从前认识的“赤脚医生”张克炳(1946年出生),尽管身体有些残疾,但总是乐呵呵的。我上前跟他打招呼,他笑着说:“我上次见到你是在高头……”
我问他近况如何。他说:“上面三令五申,下面乱整。我这个药铺不知道被撵了多少回了,在露天坝坝里摆摊都不行……”
谈起从前,张医生又说:“老家在河对门的大沙村,草药是我从前跟叔房一个爷爷学的,考的有证书,60年代就在红狮和云硐交界的地方当大队赤脚医生,后来手续丢失了,现在什么都没得到,还是自己开药铺、采草药。这里有一匹山,小地名叫塘坊沟,山上草药多得很,像蒲公英、夏枯草、益母草、车前草、党参、黄芪、灵芝草都有……”
“那这里不会再赶你走?”我问。
“说不定。”张医生笑道。
而看他门前的货架上摆着一些签签,我随手抽了一张,上写着“顶对唱戏”。我问怎么解,张医生说:“就是唱对台戏,把你人累倒了,戏也不好看。”
我听得倒吸一口凉气,付费之后,匆匆离开。本来我并不想算命,是为了照顾一下兄弟的生意,可即便如此也不该胡乱抽签。这一抽,感觉更累了。
我又走进城口那座阴凉的大棚,刚刚散去的农贸市场,一些老人还坐在那里喝茶、打牌,而其中一位老人孤零零坐在一旁发呆,看他身体瘦弱,目光苦涩却炯炯有神,我于是上前询问,老人家就告诉我——
“我叫陈启付,原先在新津乡小岭一组,是双淹户。原先的土地和河边的六间房子,都淹没了……上面拨的钱,我们实际得不到那么多,没个屋住,生活都有困难。”
“我们那个大队,有一百多亩地,都是坡坡地,皮皮地。现在好地淹完了,栽了树子,什么都没得了。我们总共得了8935块钱的补偿,来回路费都不够,就参加了大移民,迁到了重庆铜梁平滩村三组。到那个地方也不适应,我们两娘母[97]也起不起个房子,又回到老家搭个棚棚。我母亲叫雷明秀,九十多岁了,现在生活困难……我们这些人,说起真是伤心。”老人说到这里,一下哽咽了。
停了一会儿,又继续说道:“乡政府大包干,简单说就是做大生意。做成了,这个钱他却得了,我们群众却得不到——他只给你一点儿。好多群众都不敢说,说了怕被打击报复,我就不怕这个经,你要枪毙就枪毙……我要求曝光:看看我们这里,房子拆了,人民没个落脚处。我要求把那些家伙收了……”
现实无奈,我们又说到过去。陈师傅接着说:“我们祖上是洪武二年湖广填四川的时候迁过来的,到现在住了好多辈人了。原先的字派是:天、地、开、泰,元、贞、启、茂,世、代、齐、昌。祖上都是打鱼,爷爷(陈洪生)、父亲(陈善友,乱了字派的)都是推筏子的,到我这辈才开的机动船……我现在岁数大了,不行了。”
“我们那里是山区,土地薄弱。原先长江鱼多,像肥头儿、白莲、草鱼、黄咕团儿、武昌鱼等等多得很。自从葛洲坝水电站修起,鱼的种类就大大减少了,加上这些年放虾笼、撒丝网,还有烧鱼[98]的太多,鱼都没有了。”
“新津没有大地主。解放初,你稍微好一点儿的,给你打个地主;稍微次点儿的,给你打个佃耕中农;有一点儿的,给你打个自耕中农;我们是贫雇农,什么都没有,解放后,毛主席领导我们,才逐步逐步翻了身……”
“解放前,我父亲给地主做长年,解放后成立互助组,情况一年年改变。我们老的都是在渔船上生活,坡上什么都没得;互助组的时候,才划了一点土地(房子没有分,我们自己搭的棚棚),栽点红苕,点点儿豌豆、胡豆——坡地种不了谷子,只有那么深的土。”陈师傅用手比画着,看上去只有一尺来厚。
“我父亲劳力强,捡了石头挖土地,我妈也挖,家里一共八口人,还是维持不了生活。互助组过后又改成了生产队,在生产队挣公分吃饭,我们打鱼的还要交钱——只能在晚上或抽空时打鱼,一个月要在田里做满27到28天,才能不扣基本口粮。无论是吃菜还是吃草,总得求生活。”
“大办钢铁的时候,好困难,我爸妈都去了洞鹿铁厂,我跟两个姐姐,还有两个弟弟在家……说起这些,我眼泪水往肚子里滚了……我说不出来……”陈师傅再度哽咽,泣不成声。
“看到家里不行了,我大姐才十四五岁,就去铁厂把我妈替回来。二姐看见妈妈就说:‘妈,皂角树那边还有些南瓜节节[99],是我们自己栽的。’我妈就去把它采回来,她看到我们三个娃儿都没得吃,她自己哪里吃得下去……就那样,母亲靠扯野菜、麻根、桐麻皮、苟叶、槐花叶……一点点把我们都带活了。灾荒年,新津口饿死人多得很……”
这时,一声汽笛,船来了,陈启付师傅起程回新津口,我送他上船。一路上,老人含着泪,悲愤地说:“移民款没有到位,安置费、基础设施费都没给,一些移民户口迁过去,人没去……到现在我们两娘母还在公路边搭个棚棚……你一定要替我们反映一下这里的真实情况!”我只有默默点头。
回到大棚里,就看见有位大哥冲我微笑着。这位大哥姓陈,本地人,在外面闯荡多年,如今回乡隐居。而先前我所做的一切,他都看在眼里。之后,他又起身为我做向导,并请我去他家里做客。就这样,老陈领着我再度出发。
走不多远,经过临街的一个简易的棚棚,一位老先生正坐在屋里谈养生之道,门前摆着一个求签算命的小摊,也卖香烛、纸钱。这一次我没再抽签,只是和老陈一起进门拜访。老先生名叫向礼和,云阳人,1946年出生,旁边还坐着他的妻子,几个邻居也没事站在门口闲聊。
“我现在三叉神经受压迫,每天吃两个醋泡蛋,还去广东、浙江那边找来各种药,还是不行。去县医院检查、治疗,医生说我视神经供血不足……”向老师说,我这才注意到老人家身患残疾,一条腿已经截肢。
现实严酷,我还是先询问当地古迹。向老师说:“传说在红狮镇的宝峰寺,那里有个洞子,里面有唐僧去西天取经留下的脚印。在红狮镇老桥桥头,原先有一对石狮子,后来发大水冲跑了,连桥栏杆都冲走了……”而随后,我们又自然谈起往事。
向礼和老师接着说:“我老家就在红狮镇,祖上都是挖泥培土,红狮原先有几个地主,解放后都枪毙了,就剩易茂松一个……我们那时候还小,才几岁,就听到我们父亲说,易茂松是个开明地主,原先在镇上开酒坊。他的家产不大,在别处有些土地,在红狮地很少。政府动员他,他就把土地都分了,财产全交出来,还动员其他地主……后来还给他留了一点儿,在红狮镇的山巅上起了个草屋。易茂松的弟弟逃到台湾去了。他的后人也没有受到影响。还有一个石老二,也是家产不大,后来送去劳改……”
“解放后成立互助组,后来由低级社,到高级社、人民公社,接着就去大办钢铁。那时我才十一岁,就去云阳江峰的康乐铁厂挖煤,当‘内娃儿’,就是钻到煤窑里挖煤,把煤炭运到大路边,再运走;还当通信员送信,从康乐铁厂送到千秋铁厂,有二十多里路,还是在云阳。因为我父亲在康乐铁厂当车间主任,他说自己家人不能不去,就动员我姐姐去,我姐姐去了两天就回来了,因为太艰苦,她不愿意。后来就派我去。在康乐铁厂干了一阵子,1960年又去朝阳水库搞了几个月……灾荒年,说实话,就是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不到半年时间最苦,我十一二岁,一顿就二三两红苕……那一段时期,水磨饿死了些,普安饿死了好多。”
旁边一个叫陈德贵的老人又说:“灾荒年,龚世云的妈妈接近七十岁了,扯了两株莴麻菜吃了,当天晚上就开会批斗,叫她跪到地上,开完会就活活打死了,在天井坝,就是生产队伙食团的三四个人,用棍棒打死的,我亲眼看见的。龚世云我们都认识,他女的叫王云秀。当时他也没什么办法。”
向老师接着说:“1960年,我在朝阳水库干活的时候,就看见有个老头,又冷又饿,赶着个牛车在拉泥巴,因为走得慢些,老头还正在吆喝。支部书记秦登然跑起就抽,用几根竹条绑在一起,一下就把那个老头抽倒在地上,很久都爬不起来……我们很远看到都吓得发抖。你想,他又冷又饿,怎么走得快。”
“我们水磨乡永胜村,陈德华的老头,别人偷了麦把子(在割回来的麦垛中抽一把),怪他,把他弄去开斗争大会,他吓得跳了水。当时你去哪儿找人呐,就在堰塘里瓮[100]死了。”
“还有红狮一队,在山上林场干活的时候,那个地主易永辉,他饿得不行,就扯了把豌豆别在裤腰里,结果掉出来被别人看到了。他本身是个地主,人家就指着他说:‘你看,你要背时[101]!’那天中午,别人在吃饭,他就没回来,在桐子树上吊死了,他是吓死的。直到下午,我们去坡上干活,才看见他在桐子树上挂起的。那是1959年二三月间,那时我们还小……后来土地下放就好些了,尤其是红狮的许知珩调到普安当支部书记以后……”
“那肯定噻。”旁边的老人们说,“许书记上任,当时就提了三个条件:第一,三年不征购粮食。第二,国家要解决好多糖食、麦糊、米糠,给社员救急。第三,要依从他,不得搞虚报浮夸。到1961年3月间,伙食团正式下放,情况才逐步好转。1958年吃伙食团,1959年粮食就开始紧张了,关键是1960年下半年到1961年初饿死人……这件事哪个记不得?”
“也不是毛主席政策撇[102],还是中层、地方,把老百姓整死了的。”向老师总结道,“共产党政策还是好,可惜我现在脚杆断了,没贡献了,要求我退党我就退了……”
我询问究竟,向老师接着说:“我原来在生产队干了一二十年,当过记分员、民兵排长、技术监督员,1971年入的党,后来又当了生产队长、支部书记。”
“1986年4月2号下午,在兴红二队李觉先旁边打石头,当时一共8个人合伙,打石头卖给税务所起房子。那天他们在坡上打,我在下头休息,正说来了来了,三墩石头滚下来,把我压在当中……”
“人都看不到了。”向老师的妻子接着说,“两边石头顶到,中间有一个空,腿压断了,肉掉下来,血都流干了,还是红狮的客车专门把他送到县医院,医生说再晚来十分钟就没命了。在县医院住了一个月,就回来自己上药,医药费付不起,只有自己在家调养……”
“我原来当生产队队长,”向老师又说,“住院之后,红狮公社就开始选举,我回来又去公社开会,去了两回。到1989年10月份整党建党,吐故纳新,公社书记肖元吉就问我:‘老向啊,你啷个搞起[103]?你是愿意退,还是不愿意退?’我说干脆退了算了。他说那你写个申请。我就写了个申请退了。因为当时我脚杆断了,生活成问题,我就给别人画个符、抽个签,他说我不符合党员的形象。还有,公社一共四十几个党员,原先谁死了,组织还送个花圈,之后也不搞这些了。”而正说着,忽然一个熟悉的身影在街对面晃了一下,钻进一个依墙搭建的小木棚里,不一会儿又钻出来,手里拿着一根火钳,朝我们这边望了一眼。
“想起来了,”我说:“那个烧火的,是原来拉二胡、卖中药的吧?我认得他。他怎么了,变化这么大?”
“得了精神病。”老陈说。
“他在煮饭吃。”向老师的妻子说,“叫他搬,他不搬,找他去,他不去,几回都弄不走,后来就疯了。”
“怎么会?”我问。还记得2004年春天,我来云阳旧城拜访过他,在他的药铺里;他的药铺像座吊脚楼,一侧搭在公路边,另一侧悬空,用几根木柱支撑着。里面窗明几净,各种中药、药酒的瓶瓶罐罐摆得整整齐齐,中间还挂着一幅毛主席像……那天我们聊到很晚,后来他还深情款款地拉起二胡,都是歌颂党、歌颂毛主席的乐曲……一晃十年过去了,没想到再次相见,他竟然变成了这样,目光呆滞,蓬头垢面,脸熏得漆黑,痴痴地望着我。
“他认得的人,还有些回忆哎。”老陈说。
“一般人他不说话。”向老师说,“他胡琴拉得好,跟老陈两个扯得来。”
“是的,我们都喜欢拉二胡。”老陈说,“他原先当过兵……”
“前些年,他开的一座石灰窑,被洪水冲跑了……”向老师说,“他的低保,由他哥哥和妹妹经管,每个月拿给他。”
“他那里成了兔子窝了。”老陈又说,“那些兔子又在里面吃,又在里面睡。”
我于是走过去,跟着他一起,又钻进那座烟熏火燎的小木棚;木棚狭小,里面刚够支起一口大铁锅;薪柴正熊熊燃烧,煮着一锅烂糊糊,味道很难闻。
“你还记得我么?”我问。
他点点头。我看见他被烟熏黑的脸上满是汗珠。
他说:“我叫柳德军,柳树的柳,原先当兵,在成都军区高射机枪连……”
“您现在做什么?”我又问。
“没做什么。”他说。
“为什么住在这里?”
“房子拆了。”
“为什么不上去?”
“上去,在哪个凼子?”
“您为什么不搬迁?”
“搬不起。房子没有,又没钱开后门。”
“您就一直住在这里?”
柳德军点点头,我又跟着他过了马路,回到他自己的棚棚里,里面还不如山洞:昏暗黢黑,堆满各种杂物,几十只脏兮兮的兔子在暗中乱窜,一根靠墙的树枝上,还挂着几根电线……柳德军说:“这是电视发射塔,全世界各国都能收到从我这里发出的信号。”
我无话可说,欲哭无泪。而这时老陈走进来,笑道:“走么,到我那儿唱歌去!”
“走么。”柳德军说。我们于是去和向老师一家道别。向老师还递给我一瓶冰镇矿泉水。
顺着大路往前,满城尽是旧楼、土屋和凌乱的土坡。经过一幢旧工房,一位老妇人正从楼梯上下来,眼巴巴地望着我说:“这里住的,都是没有办法的。”
我停下来询问,她就告诉我说:“我叫胡碧伦,身份证、户口本上是1955年出生,实际是1954年,今年六十岁,原先住在硐村乡麦地村,老房子还不窄哎,有两三百平米。我们属于三期移民,房子拆了,黄桷树也砍完了,补的钱加上借的钱买了低保,现在是落零精光[104],在这儿带娃儿上学……”她一边说,我一边记,最后她还说:“谢谢你们的关怀。”我低下头,真正感到汗颜。
再往上走,大树下的土坡上,立着一个坟头,青草间的旧石碑,字迹清晰可见:“美德常齐天地永,家风永伴山河存。”——“九泉安息”。再登上两座土坡,穿过一条小巷,就来到老陈家,一幢独门独院的矮平房,里外两间,家徒四壁,却有一套像样的音响。老陈从里屋拿出两把二胡,二人合奏,像是排练好的一样,上来就是一曲《东方红》——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毛泽东……
然后是《白毛女》——
北风那个吹,
雪花那个飘……
之后又是《洪湖水浪打浪》……我坐在屋里静听,瞬间又回到十年前,同样的乐曲,同样深情款款,神情庄严的柳德军又出现在眼前……而正当我怀念着故园春色,柳德军又唱起一首民歌——
春天的草儿绿幽幽,
春天的水儿不回头,
长江河水不回头,
长江河水永远不回头……
在云阳旧城,这间偏僻的小屋,我们再度相聚。柳德军又说:“毛主席好,规定粮食堆满仓,现在到处一片荒。熟田熟地只栽些树,把旧粮食都吃完了……搬家搬了十几道,没一个固定地方住……”
我正在想,别人都以为他疯了,神经了,而在我这里,他不是好好的么?可他随后的话,又让我默然无语。
“你们晓得不,”柳德军又说,“现在红军长征,完全是从我那儿放出去的。八路军、新四军、世界历史、中国历史、天气预报……都是从我那儿发出去的;美国、德国、意大利、法国、土耳其、伊拉克、西哈努克……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都能收到,都是从我这儿发射的,别人以为是玩具,那不是玩具;你们电视里收到的,都是从我这里发出去的……”
“还是唱歌吧。”老陈笑道。
“哦。”柳德军停了一下,回过神来,又唱道:
王家二姑娘,站在绣楼上,
茶不思来饭不想……
天气晒不过,热呀热不过,
明天又是一个礼拜天,
你我夫妻二人到花园……
那背时的燕子咬人咬不过……
唱到后来,歌词越发听不懂了,但我知道那是他心中的喃喃自语,我的好兄弟柳德军,他已经生活在了另一个世界里了。就这样,暮春时节,在云阳旧城这间清凉小屋里,我和我的两位兄弟,在美妙的乐曲与歌声中,度过了心酸而愉快的一下午。
午后,谢过了老陈,我又匆匆上路,柳德军将我送到码头,一路上我问起他今后的生活,他说:“养兔子,卖给别人,发展……”我不知该说什么。
上船之前,才想起他午饭也没吃。而几次想拿些钱给他又没有勇气,怕落了俗套,反而伤害了兄弟感情,直到船开了又很懊悔……
我不敢回头看他,不敢看他凄凉的生活,温柔凄楚的眼神,而再看一眼云阳旧城,已是满眼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