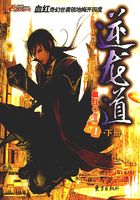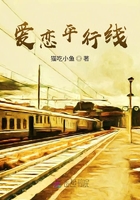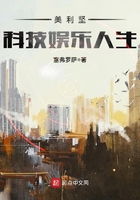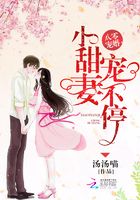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一个眼神、一句招呼语、一声称谓,都成了判断一个人政治地位和处境的晴雨表,多年经验告诉我,早在1966年席卷中华大地的一场风暴发生前,我的地位已发生变化,处境越来越不妙了。平时见面总要跟我打招呼的人遇到我常常把头一扭,视而不见。喜欢到我的办公室翻翻我书架上几本英文企鹅丛书的教师,也逐渐都不露面了。另一个明确的信号是,教研室决定要我开一门英美文学选读课,但开学已久却没有下文,我继续坐在资料室里编书目。这也好,我在书海里漫游,自得其乐,尽管外面战鼓敲得越来越响,莫忘阶级斗争的口号声喊得越来越高。但我不能与世隔绝,偶一抬头,我仿佛看到头顶上悬着一把系在马鬃上的利剑。我是古希腊的达摩克利斯(希腊神话中叙拉古王迪奥尼修斯请他的宠臣达摩克利斯赴宴,在他的座位上方用马鬃拴着一把利剑,使他知道自己随时有生命之虞。)。
阴霾压顶。《海瑞罢官》受到批判,“三家村”被揪了出来。平时喜欢舞文弄墨的人神经都绷得紧紧的。我不写文章,只搞翻译。我自我宽慰地说,我的最大罪名无非是宣扬西方资产阶级思想,谅还不会成为这次文化运动的靶子。
有一天,暴风雨终于爆发了。一张大字报诞生了千百万张大字报。大字报铺天盖地。锋芒所向,从走资派到小爬虫,从反动学术权威到漏网右派,牛鬼蛇神几乎无处不在。朗朗中华霎时变得天昏地暗,成了魑魅魍魉的世界。我自然也不能幸免,有的大字报还在我的名字上打了红叉。但给我戴的仍都是那些旧帽子,算的仍是老账。我自觉心安。
一天上午,革命群众都到兄弟院校去看大字报、取经,校园里出奇的安静。我一个人坐在资料室心不在焉地翻报纸。突然门开了。一个知道我的名字被打了叉仍敢对我挤挤眼睛的年轻教师走了进来,低声说:“没想到你还写诗。”
“我是个俗人,从不写诗。”我说。
“去看看,大礼堂左边靠墙的一张大字报。说你写反动诗。”
“那就奇了。这顶帽子我可不敢戴。”
“开帽店的哪管你戴着合适不合适。先稳着点,小组要讨论你的问题,也许我能知道点什么。”
怕有人发现我们谈话,他匆匆离开资料室。几天以后,年轻教师来还一本书。书里夹着一张字条:“笔记本,遗失后归还,诗歌残句,含沙射影。”看过后,我当然立刻把字条消灭。但我马上恍然大悟。
一年多以前,上海一家出版社计划出一本纪念德国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的诗集,约我为他们译十余首德文诗。对封建统治者的指责,对人民受奴役的怨愤,指的都是19世纪德国现状,同当今的中国风马牛不相关。我接受了这一任务。在人像机器一样昼夜不停运动的日子里,我自然不会有多少自由支配的时间,我的办法是,晚上上床前背一首诗,次日上班,开会也好,或做其他事情也好,一边默诵一边打腹稿。偶然脑子里迸出一两个妙句,恐怕事后遗忘,便随手记在学习的本子里。后来有一天本子失落了。我始终弄不清是否遗失在会议室还是放在办公室桌上突然不翼而飞。又过了几天,系秘书叫我去他办公的地方领东西。他拿出我丢的笔记本,问是不是我的。我把本子拿回来。我做梦也没想到,在遗失的三五天里,我的笔记本已被仔细审查,据说——这是若干年后才知道的——其中某几页还被拍了照,存入我的档案。一顶诗人桂冠——虽然被看作是“反动”的——就这样无形地戴在我头上了。
经过申诉,经过长时间的调查,这件“反动诗”案后来总算澄清了。幸好我还保留着出版社的约稿信、德文版原书以及一极有力的见证——老翻译家孙用(《裴多菲诗集》译者)为我修改译稿后写的一封讨论诗歌翻译的信。不知过了多久,系里的革命领导小组找我去谈话,宣布“反动诗”一事已经解决,但我的问题还没完,我仍要继续劳动(这时我已是牛鬼蛇神劳动大军的一员了),仍要交代反动思想。“诗虽然不是你写的,”一名领导小组成员厉声说,“但你翻译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就没有共鸣吗?”我本想反问,即使我有共鸣,难道1848年的革命思想今天已成为反动思想了吗?但这个问题只是在我脑子里转动了一下,我没有把它说出来。
为我摸情况、通风报信的那位同事早已不在国内了。他是1964年分配到学校来的一位年轻法语教师,热爱文学,曾经野心勃勃想把普鲁斯特的巨著《追忆逝水年华》译成中文。他已译了一部分,常常找我谈论翻译问题。“文革”期间他是逍遥派,后来去南方大串联,认识一个从柬埔寨归国的华侨姑娘,结了婚,70年代中同妻子一起到比利时去探亲,从此再没有回来。我倒想知道他在欧洲是否实现了翻译法国名著的夙愿。
这个一度梦想当翻译家的年轻人恐怕早已把“文革”中的一件小事忘在脑后了。我却不能。而且我至今一想起这件往事,仍怀着对他的感谢之情,如果没有他,不知道这口黑锅我要背多久。
我又想:为“阶级敌人”传递消息要担很大风险,不是很多人能做到的。但当一个人在某次政治运动中已成众矢之的,如果你知道他本来就清白无辜,对他说一句抚慰的话,递一个温存的目光,也许不需要多大勇气吧。可是这对身处危难的人是多么宝贵啊!人们会发现,正义同良心在世上并未泯灭。
往事——回忆孙用
一、第一次听说沙皇时代俄国有个诗人叫普希金,普希金写过一本小说叫《甲必丹的女儿》
我父亲是学俄文的,从我懂事起,他就在哈尔滨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上做事,但是他很少跟我说“老毛子”(当时中国人对俄国人的称呼)那边的事,更从来没有谈过俄国文学。普希金写的那部小说的名字是邻居两个小孩儿告诉我的。当时我十四五岁,混沌无知,但对外部这个陌生世界充满好奇心,很想多知道点什么。我怎么会同毕姓两兄弟成为邻居呢?要把事情说清楚,还得回到20世纪30年代去。1935年春,九一八事变后的第四年,苏联政府把中东铁路单方面卖给伪满洲国,我父亲同铁路高层管理靠俄语吃饭的人全部被解职遣散。我们是满族人,老家在北京(那时候还叫北平),父亲就携家带口迁回北京了。我们住进什刹海北岸一所祖遗的老房子里,这所房子很大,前后三进一共有三十多间屋子。我们家住正院,前院是门房,住着厨子和一家借住的远房亲戚。搬进后院一排北房的是同我父亲一起从哈尔滨铁路上退职的同事,名叫毕慎夫。他比我父亲略小,我叫他叔叔。这位毕叔叔有四个孩子,两姐妹年纪还小,两兄弟大的一个和我同岁,弟弟小我们两岁。开始的时候,我们三个男孩儿并不熟。后来七七事变,北京沦陷,孩子们都辍学在家,只到附近一所小学校补习点英文、数学,就整天一起厮混了。互相借阅各自从家里翻腾出来的小说闲书,彼此说故事,东拉西扯是我们那时候最大的乐趣。偶然看到一两本供青少年阅读的进步刊物,对国家、社会的大事也逐渐了解一二。像鲁迅、巴金、老舍、冰心等这些大作家的名字,大概都是那个时期印在脑子里的。我们家因为有些产业,不愁生计,所以我父亲回北京以后没有再找工作。他在家练书法,看古书,还钻研中医。几年以后,居然通过卫生部门考试,取得中医行医执照。但他的医术显然没有学到家,后来连自己害病也没治好,中年就去世了。邻居毕家原籍山东文登,在北京没有恒产。所以毕叔叔客居北京还必须寻求谋生之道。除了在外面教几节俄语课外,另一条道是做笔耕翻译。我家北房的后窗户正对着他的书房,偶然掀开窗帘一看,总能看到他端坐在书桌后面写东西。我问两个毕家小伙伴,毕叔叔翻译什么,他俩摇摇头。他们父亲的书房,不许孩子进去。但是后来在我的怂恿下,有一天趁父亲外出,两个孩子还是溜进去了。不但进去,还翻看了整整齐齐摆在柜子里的一沓沓稿纸。谜底揭开了。毕叔叔翻译的都是有关铁路管理的规章制度,但是也有几本稿子是例外。那是一部小说——《甲必丹的女儿》。“甲必丹”是什么人?他女儿怎么了?我们自然都一无所知。作者是谁?毕家兄弟只知道是个俄国人,名字也说不清楚。我逼着兄弟俩问问他们父亲,他们却不敢。一问父亲,偷看译稿的事就露馅了。我也不敢问我父亲,这是孩子间的秘密,最好别叫大人知道。最后,我还是托我大表姐把“甲必丹”探听清楚了。我的大表姐因为同继母不和,自少女时代就住在我家,她叫我继母“姑爸爸”,按照满族人称谓,姑姑叫姑爸爸,早已成为傅家的一员,而且家里人只有她能同我那性格有些严峻的父亲搭上话。事情弄清楚了。原来“甲必丹”是一个俄文词的译音,是军队中一个军衔,中文大概是大尉或上尉。后来我学了英语,才知道这是个国际语(英文是captain),很多语言中都有。表姐还为我打听出这部小说的作者,一个19世纪俄国的大诗人,不到四十岁就在决斗中被人打死了。这人叫普希金(表姐当时说的只是俄语发音,肯定不是这三个字)。岁月飞逝,自那以后,我的生活有很多变化。前面说了,当时我只有十四五岁,又过了十几年,我终于读完大学。不但学了一些西方文学,而且靠查字典也能阅读俄语原著了。但是俄文书我读的是屠格涅夫,是契诃夫,普希金的作品一直没有登上我的阅读榜。20世纪中叶,我有幸认识了我国一位老翻译家,没有想到的是,我在他的藏书室里竟和久别的“甲必丹”相遇。《甲必丹的女儿》已经印制成书,扉页上赫然印着我小时候称叔叔的毕慎夫的大名。为把这次邂逅的事说清楚,就需要追述一下我同老翻译家孙用的交往了。
二、认识了孙用,登堂入室,孙用为我修改匈牙利诗歌
我是1942年考入辅仁大学的,但因为总是心有外骛,不肯专心读书,所以岁月蹉跎,直到1950年夏才拿到一纸大学毕业文凭。在跻身高等院校,从事外国留学生汉语教学工作之后,已近而立之年,我决心搞一点文学翻译——以免时日虚度。我有一个在浙江大学求学时代的校友,周文博,当时在《文艺报》当编辑。因工作关系,他认识不少文艺、出版界知名人士。我请他介绍我认识一两位翻译家,传授给我一些翻译技巧。就这样,周文博在某一个假日(时间大约是1953年)带我走进孙用先生的寓所。孙用这个名字,今天国内对老一代文学家感兴趣的人大概都听说过。“文革”期间一度大批特批“裴多菲俱乐部”,裴多菲就是孙用在20世纪30年代初引进中国来的。孙用年轻时家境贫寒,未能升入普通高中,只好在邮局当个小职员。但他自强不息,潜心文学研究,又自修了英文和世界语。他译的第一部作品,裴多菲的长诗《勇敢的小约翰》得到鲁迅先生好评,并蒙鲁迅推荐,上海一家书店于1931年初版。其后,孙用继续翻译了波兰、保加利亚等多部作品,仍然是秉承了鲁迅倡导的译介弱小民族文艺作品的传统。新中国成立以后,冯雪峰邀请他参加《鲁迅全集》编辑工作,1952年迁入北京。除编辑鲁迅作品外,孙用仍不断翻译外国文学。我登门拜访时,孙用住在东城无量大人胡同(现已改名红星胡同)人民文学出版社职工宿舍。论年龄和资历,孙用都是我这种初出茅庐人的长辈,但接待这些年轻的不速之客,他却谦恭和蔼,一点没有架子。谈起话来,好像在叙家常,不断给对方插话和提问的机会。他同我们谈新中国成立前的文坛往事,谈鲁迅作品中的浙江习俗,偶然也谈到旧社会谋生与从事文学活动的艰辛。他说话带有浓重乡音,有时我听不太懂,带我去的好友也是浙江人,就为我翻译。我最初同孙用见面的几年,国内一切欣欣向荣,对这位已年过半百的文学工作者(孙用生于1902年)来说,正是大展宏图的日子。今天反过来查阅一下孙用一生的成就,几部有分量的翻译——如《裴多菲诗选》《密茨凯维奇诗选》和两部域外史诗——都是从50年代中期起陆续完成的。我当时也在译一本反映匈牙利人民解放后新生活的剧本,遇到有关宗教、文化和现实生活的许多问题,孙用先生自然不可能一一解答。他曾表示,翻译现当代作品难度也许更大。文化差异,生活隔阂,有时甚至构成无法逾越的障碍。这方面的困难,我在80年代后转向翻译西方现当代作品时,体会更深。这里就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