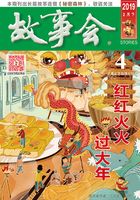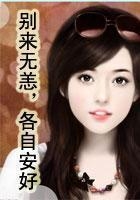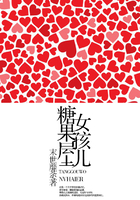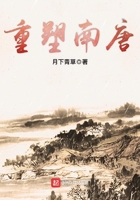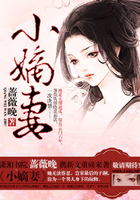人民文学出版社职工宿舍坐落在胡同中间路南,是一座有六七排平房的大院。孙用的寓所在中间一排,坐北朝南,只有两间半房。靠西的一间内室住人,中间和东面半间打通,是孙先生工作和会客的地方。因为他的古今中外藏书非常丰富,所以出版社在他住房的后一排又拨出两间屋子专门供他藏书。最初是为了找一本什么书,他带我去过。我同他熟悉了以后,他就让我自己去他的书室看书,不再陪我了。就是在一次随便翻看他的藏书时,我注意到角落上有一个书架,摆着新中国成立前友人赠他的书刊同他自己早期的译作。我发现了那本我几乎早已忘在脑后的《甲必丹的女儿》就夹在一排旧书里。这已经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了,为了验证我的记忆,写这篇文章前,我又查阅了一下《中国翻译家辞典》(1988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在介绍孙用主要译作的词条内,有下面几行字:[俄]普希金《上尉的女儿》(初版名《甲必丹的女儿》,东南出版社,1944年初版;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1949年重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1959年新版)。我不记得我那时看到的版本是不是东南出版社最早出版的一本,但毕慎夫的名字印在扉页上却是千真万确的事。那文字是:毕慎夫译,孙用校。可惜当时我同孙用先生关系还不那么熟,没有细问。孙用后来是不是抛弃了原译,又另起炉灶重译,我就说不清了。这只能靠有兴趣的人去研究了。
我同孙用先生交往,从初识直到“文革”前一年,延续了十余年之久。见面比较频繁是在1954-1957年,这对我走上翻译道路,影响很大。50年代初期,在我教的外国留学生中,有一个匈牙利派来的学生,名高恩德(Calla Endre),原在国内任大学助教。高恩德精通德语,同我不仅有师生之谊,而且后来成了比较亲密的文友。我翻译匈牙利剧本《战斗的洗礼》(1954年冬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得到他很大帮助。孙用到北京后,在《裴多菲诗四十首》一书基础上,扩大内容,出版了《裴多菲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也得到高恩德大力支持。
1956-1957年,经高恩德推荐,我同他合译了匈牙利著名诗人尤若夫·阿蒂拉(1905-1937)的三十余首短诗。尤若夫是一个工人阶级出身的革命诗人,在匈牙利享有很高声誉,被誉为该国三大诗人之一。我同高恩德首先选定篇目,然后一首一首研读讨论,译出初稿。再交给孙用,请他修改、润色。这本小册子——《尤若夫诗选》195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印了一万册,今天恐怕已经没有什么人知道了。在这本书的《后记》里,孙用对我们三人合作译诗过程,做了简略记述,我当时用的是笔名傅韦。
孙用对我的最后一次帮助是在1964年。这一年,上海一家出版社计划出一本纪念德国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诗选。写信给我,约我翻译二十首德文诗。我译好后送给孙用,请他修改。为此他还给我写过一封长信,探讨诗歌翻译的一些问题。“文革”中,我翻译革命诗被诬为写反动诗,并因此被关进“牛棚”。为了澄清事实,我把出版社给我的约稿信,我的译稿,以及孙用的信,全部交给专案组审查。后来事情虽然澄清,但是我交去的证明材料却没有退还给我。孙用给我的信,他的珍贵手迹,从此遗失,叫我感到心痛。这件事我写进《我戴上了诗人桂冠》,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为了表彰孙用翻译裴多菲诗作,促进匈中文化交流,匈牙利政府于1959年授予孙用劳动勋章,并邀请他去匈牙利访问。根据《中国翻译家辞典》记载,孙用去了一个月,但是我记得很清楚,他只在布达佩斯待了两天,拿到勋章就匆匆回国了。他回来不久,我曾去他家拜访,去拿高恩德托他带回的一件小纪念品。见面时,自然谈了谈他去匈牙利访问、匆匆归来的事。1959年,中国政府已同苏联和东欧国家交恶,大批修正主义,当然不愿意叫一个文化人作为民间使者在域外停留过久。
历史进入了80年代,笼罩在头顶的乌云逐渐散尽,人们又重睹蓝天,我也获得到国外工作的机会。1987年,我应邀去英国一所大学授课,借机游览了欧洲几个国家。我在匈牙利逗留了一周,见到已经阔别近三十年的高恩德和另外一两位朋友,过去他们都来过中国。高恩德陪我参观了布达佩斯市,也去了近郊、远郊几处名胜。在市内一块绿地上,我看到了诗人尤若夫的雕像。不是高立在大理石石基上,而是随随便便坐在低矮台阶上,神态自然,像是置身于阶级兄弟中间,只是诗人眉头紧皱,仿佛正为遭受苦难的人民大众焦灼、忧思。这座雕像非常契合一位无产阶级诗人的气质。我拍了几张照片,可惜我敬爱的导师孙用先生已经在1983年离开人世,我无法把照片送到他手中了。
冯亦代与《译丛》
对于我国读书界,冯亦代这个名字并不陌生。自20世纪30年代起,他在出版界、文化界就非常活跃。曾与戴望舒、郁风等人在香港办文化刊物。1941年去重庆,创办出版社,1943年组建中国业余剧社,茅盾任社长,冯亦代任副社长。抗战胜利后在上海编译出版《美国文学丛书》,翻译了海明威、斯坦贝克等的文学作品。新中国成立后在外文出版社工作多年。同许多文化人遭遇相同,1957年被打入另册,尘封二十余年,直到“四人帮”倒台才翻过身来。冯亦代在年过半百以后,才又重新焕发了青春。
我同冯先生结识纯粹是一个偶然机会。在解冻的日子里,看进口影片是饥渴群众的狂热。电影院虽然还不能公开放映外国影片,但许多文艺机构和团体都纷纷组织专场,内部放映。1979年的某一天,我得到这样一张入场券,到民族宫礼堂去看两部进口片——《音乐之声》和《巴黎圣母院》。我去得较晚,第一部早已开场,我在剧场前边胡乱找个座位坐下。休息期间,发现身旁坐着一位半百老人,精神矍铄,目光睿智,朴素的衣着掩盖不住一身书卷气。四目相对,相互微笑一下算是打过招呼。交谈之后,我才知道这位邻座就是我早已闻名的冯亦代先生。冯先生当时还住在航空署街东里,同我的居所只隔着一条新街口大街,我们可算得上近邻。自此以后,我就成了听风楼(冯亦代对自己书斋的谑称)楼主的座上客。冯先生这时正在筹划出版《现代外国文学译丛》。
《现代外国文学译丛》一二两集以《献给艾米丽的玫瑰》和《在流放地》为书名以32开本于1980年出版。自1981年第三集起才换成16开本,正式冠名《译丛》。
我去冯先生家里又认识了帮助他编辑出书的范、林两位助手和一群青年译者。我在这个小圈子里也凑了个数,提供一些选题。因为当时我还在某一院校担任翻译教学,我的好几个同事和学生都被我拉到冯亦代先生主持的刊物里。
《译丛》聚拢起的一批译者,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而且还都是从未在翻译界露过头角的生手。在通过实践后,这一批人都逐渐成熟,不少人后来都可以独立担当译书的工作了。冯亦代自己动手不多,但他对于译稿审定极严。我几次去听风楼,都看见六七个年轻人围坐在冯的四周,讨论修改稿件。为了改动一个用语,修改一句话,常常各抒己见,争论不休。冯先生已故的夫人安娜,英语造诣很深,有时也参加讨论。许多相持不下的问题,常由安娜拍板定案。在《译丛》的编辑工作中,可敬的冯老夫人也灌注了一份心血。
《译丛》自1980年2月创刊,至1982年初,共出版了六期。其后,广东人民出版社羽翼已丰,便把刊物收回自办,北京原来的编译任务从此就结束了。
粗略统计一下,在冯亦代先生主持出版的六期《译丛》中,介绍了西方现当代名作家数十个。有些名字,像卡夫卡、萨特、里尔克、乔伊斯、艾略特、杜仑马特……可能就是通过这份刊物,才首先在国内流传开;有些西方流派,像荒诞派、黑色幽默……过去人们可能只听说过,也是通过这份期刊,读者才读到实际作品。有一次,我去冯先生家,正碰见王蒙先生同冯先生讨论意识流创作手法。《译丛》刚刚发表的英国女作家伍尔夫的名篇《克尤植物园》和《墙上的斑点》正是伍尔夫用意识流写法描写人物内心流动的代表作。我猜想,王蒙先生是否是因为读了这两篇文章才对意识流感兴趣呢?
严寒虽然过去,但冻土并未融化。在解冻的日子里,有时还吹来一股凛冽寒气。《译丛》大力介绍西方现当代文学,自然也听到一些反对的声音。用冯先生的话说:“早又有人甩过来不少闲言冷语,甚至少数恶言恶语。”(见《译丛》1981年1期《改版的话》。)但冯先生并未因此有所动摇,他坚持办好这本杂志,坚持引进更多的西方现代思想。冯先生是正确的。要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国门就要开得更大一些。古老的中国需要灌注一些新鲜血液。二十年来的实践证明,我们的路子走对了。
附记:此文原系我写的《在解冻的日子里》中一个片段,概述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介绍西方现代文学走过的崎岖道路——初被禁止,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破土而出。我的文稿准备在某一报刊上发表时编辑可能认为禁忌太多,大加删节,不少稍带棱角的话,也被抹去,连文章副标题《一份民办官出的刊物》亦未获刊登。文章发表时(2004年5月25日)我正在伊朗漫游,在Persepolis(波斯波利斯)古波斯王大流士兴建的宫殿废墟上发思古之幽情。
“盛衰如转蓬,兴亡似棋局”,世事变迁如此,令人慨叹!
(2007年6月12日)
狷介一书生——记董乐山
乐山兄走了,中国翻译界失去一位驰骋沙场、卓建功勋的老将,我痛失一位良友。
屈指算来,我同乐山的交谊已有二十七年历史了。1972年春,我所在单位——北京语言学院撤销后宣布并入北京市第二外语学院。同年4月,原在茶淀五七干校劳动的两校员工绝大部分撤回北京,“复课闹革命”。就这样,董乐山和我从分属两校、互不相识的教师成为同校、同系的同事了。第二外语学院校址在北京东郊,我住在市内,乐山的家更远,在西郊皇亭子新华社宿舍。我俩在校内单身教员宿舍各有一个床位,而且恰恰在一间屋子里。但我们从未住过。我们两人见面、交谈不是在办公室就是在下班返城的长途车上。我同乐山当时还都背负着没有了清的“旧账”,仍被剥夺登讲台授课的资格,所以就被一起塞在资料室里。两名无所事事的闲员,相对坐在办公室一隅,一杯清茶,一支纸烟(乐山是在80年代中才因健康原因戒烟的),清谈成为我俩必修的日课。乐山1946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语功底深厚。在抗战前的上海孤岛上就已从事编辑写作,且又参与了当时上海戏剧界的活动,写过不少篇剧评,脑子里逸闻、掌故极多。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参考消息》工作了八年,每天同国外报刊打交道,对天下大事了如指掌。所以同他谈话,我常常有茅塞顿开之感。我同乐山相识后,最佩服他的是两点:一是他读的书多,知识面广;二是他在艰辛的处境中,孜孜不倦做学问、搞翻译的坚韧精神。《第三帝国兴亡史》一书的翻译出版是一个典型例子。
《第三帝国兴亡史》是乐山偶然在新华社图书馆书架上发现的,但翻开一读就不忍释手,“许多过去在报刊上读到过而又语焉不详的历史事件一一重现在眼前,而作者夹叙夹议的评论洞微察毫,令人折服……”(董乐山:《另一种出书难》原语)。这部千余页的巨著从原书被发现,到向出版社推荐,再到最后统一几个译者的译文,总其大成,可以说是他一人的功劳,但直到1973年再版,书上才署了董乐山的名字。他在一篇短文中这样写道:“……出版社让我校订修改。当时出书没有稿费,校订工作足足花一年时间,完全是尽义务……”我在“文革”前后也有相同的遭遇,出书不能或不愿署名,稿费极低或根本没有,甘愿在政治运动中受鞭挞,违心给自己扣上散播封资修思想的帽子,也舍不得丢下笔杆。总想在荒芜的沙漠上,种植几棵青青小草,与人们共享。共同的兴趣和爱好,相似的经历,使我同乐山结识有相见恨晚之感。直到1972年年底,北京语言学院复校,我调离二外,我和乐山几乎朝夕相处,无所不谈。这一时期的频繁来往,不仅加深我们相互了解,而且为以后翻译上的几次合作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