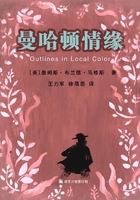在韦之那里聚会的是他的那些艺术家朋友。他们都穿着色彩鲜艳、造型怪异的衣服。他们中的男性都留着长发,他们中有两位女性留着平头。坐在角落里的那一位我从前没有见过。她就是韦之前几天电话里提到过的那一位吧。她的穿着和发型都不激进,但是她显得有点憔悴。
艺术家们正在谈论他们去年底参加的那次画展。
“这个国家没有希望了。”
“记得那个美国人说的吗?他说我们的作品在纽约都会引起轰动。”
“可是那帮老东西不会承认我们。”
“我完全泄气了。”
“我也是。这一个月我连笔都没有摸过。”
“那你摸什么去了?”
一阵不整齐的笑。
“当时我们真应该惹点事出来。”
“把展厅给砸掉。”
“或者把那帮老东西给揍扁了。”
“又要等一年了。”
“明年也不会有好结果。”
“问题根本不是我们不努力。”
“也不是我们没有水平。”
“可是这个国家不会承认我们。”
“就因为我们年轻。”
“年轻就是过错。”
“年轻人没有道德,不结婚就同居。”
又一阵不整齐的笑。
“承认”是关键字。被社会承认其实就是被少数几个有权力却没有个性的个人承认。体制首先将那几个人奴化,然后再赋予他们“承认”的特权,让他们判断正误,评价是非,让他们成为冷漠的“父亲”。这体制有苛刻的原则和光荣的传统。那些敢于冒犯它的原则和传统的人永远也不可能得到它的承认。
我就是这样的冒犯者,因为我思考的是“人”,普遍的人。这个普遍的人困惑地活着,拒绝接受体制强加给他的所有假象。他知道死亡是绝对的真理,他知道体制的“昨天”(传统)和“明天”很值得怀疑。这样体制怎么可能接受我的思考?这样体制又怎么能经受得起我的思考?
我不是体制的奴隶。
1.10
上午在菜场外面的路口出了一起车祸。现场挤满了围观的群众。伤者(也许是死者)已经被抬走了,地面上只留着一摊污血和警察用粉笔做的标记。我停放好自行车,也变成了一个围观者。
我并不想了解事故的经过。我知道,事故的合格见证人只可能是那位已经被抬走的伤者或者死者。我也不想听人们的议论。我越来越恐惧周围的人说话的声音。我深信,口语是这个世界混乱的根源。也许对英语我会宽容一些,因为我刚好能够听懂。而对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日语或者越南语,也许就更能容忍,因为它们对我就好像是噪音,我根本就听不懂。书面语言也同样很成问题,但是它给了我充足的时间,让我可以从容地剔除其中那些明显可能引起混乱的因素。如果说书面语言是缓慢移动的白云,口语则是暴风骤雨。我脆弱的心灵越来越经受不起那种剧烈的风吹雨打。我宁愿永远躲在书面语言的角落,用文字而不是声音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围观者是一种有趣的身份:我在人群中挤来挤去,从不同的角度审视被压扁的自行车、四散的污血、费解的粉笔标记(从那标记可以断定受害者被抬走之前在地上蜷缩成了一团)。更重要的是,围观者可以看到其他的围观者。围观者与围观者之间的关系充满了哲学的意味:对于同一现场,所有围观者看到的是同样的内容吗?对于同一事件,所有围观者会有同样的感受吗?是不是所有的围观者都会像我一样去想象刚才被抬走的是自己?是不是所有的围观者都会像我一样敬畏死亡的生动和荒谬?
我们这个世界充满了意外的事故,但是它并不完全由意外的事故构成。完全由意外的事故构成的世界只存在于我的想象之中(或许将来还会在我的写作之中显现出来)。我有时候相信哲学就是处理意外事故的学问,当然它不会像警察、官僚或者围观者那样去处理。
1.11
阿奇住进了精神病院
白的事故。红的事故。黑的事故。所有的事故。一切都是事故。
“起来吧,阿奇。起来吧。”
表为什么又停了?事故。我明亮的小眼睛也是事故。
“说定了星期五带你去公园的。你不要胡思乱想,阿奇。”
“说定了”是事故。“星期五”是事故。“你”是事故……河水干涸,太阳的仇恨。雪。我没有靴子。我上当了,因为太阳。天哪,不是雪。白羽毛。温暖的白羽毛埋着我。我出了汗。事故。
“阿奇,大家都很喜欢你,阿奇。”
天鹅是怎么死的?是你们。你们是事故。你们举起了屠刀。刑场。社会是刑场。生活是刑场。
“阿奇,说说话吧,大家都来看你了。”
“阿奇,你想吃点什么吗?”
我也想成为刽子手。我首先要将这严严实实的屋子杀了。豹子。
“指导员说他明天来看你。”
指导员是事故。明天是事故。流血染红了白羽毛。星星躲进了乌云里,天要变了。
“阿奇,明天,你听到了吗?”
滚开,考试。我不想再有考试。你们突然出现。你们像一群被驱赶着的羊。牧羊人死了。只有一条孤零零的鞭子还在俯视着世界。你们突然就涌来了。
“阿奇,尽量想那些愉快的事。想想从前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是多么开心,阿奇。”
回忆是欺骗,就像太阳。我不再上当。我也被驱赶着走,甚至连鞭子都没有看见。我的背包里只有一双臭胶鞋和一本教科书。起风了。血腥味的风。刽子手也死了。只有鞭子和教科书不会死。
“阿奇,不要想家。这就是家,我们所有人的家。”
那个盲人应该早就死了。是他说的。他说命运是一场事故。所以我说一切都是。事故是唯一的存在。价值还有什么价值?我永远都会记得你,发现了真理的盲人。
“阿奇。阿奇。阿奇。”
“阿奇。阿奇。”
“阿奇。”
“你们都走吧。”阿奇说,“我累了。”
“躺着也会累吗?”
“声音让我累了。”阿奇说。
“我们不说话了,好吗?”
“你们走吧。”阿奇说,“明天谁也不要来了。”
1.12
刚到办公室,处长就问我是不是已经寄走了要求我在去年底寄出的那一批通知。“早寄走了。”我回答说。
那是关于原计划今年五月召开的全省经济信息交流会的通知。那次通知的内容是:由于种种原因,会议将延期举行。具体日期另行通知。
我记得在起草这份通知之前一个月我们就已经收到了省政府关于取消会议的决定。“为什么不明确地告诉基层单位省政府的决定内容呢?”我问。
“那有点太突然了,”处长微笑着说,“还是写成‘延期举行’比较好。”
“已经拖了这么久了,”我说,“下面那些县市的人可能早就知道了。”
“还是写成‘延期举行’比较好。”处长说,“不要影响了大家的积极性。”
“谁也没有对这种空洞的会议积极过。”我说。在汇总那些上报的虚假信息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下面的各级政府机构对这种会议有多么“积极”。
“你这样说就不对了。”处长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我看你就很积极嘛。”
那一批信还塞在我的抽屉里,我没有也不打算将它们寄走,因为过一段时间,还会有另外的“另行通知”。而哪怕是那另外的“另行通知”也同样可以不寄,因为事情的结果最后大家都会清楚,而且都已经清楚。
这就是我的工作。我为这个体制工作。我在工作中遭受蒙骗,我又用工作去蒙骗别人。受骗是我的“义务”,骗人是我的“责任”。我的拖延甚至“无为”并不会损害我工作的这双层意义。
1.13
进入冬天以来,天气一直非常暖和。今天母亲和外婆坐在一起,又谈起了她们对气候的担心。
“整个地球的气温都在上升。”母亲说,“报纸上天天都在说。”
“是啊,说是北极的冰都融化了。”外婆说,“北极熊都快绝种了。”她也有许多从报纸上看来的信息。
“我们过去还称苏联是北极熊呢。”母亲说。
“也许将来苏联都会从地球上消失呢!”外婆说。
“那怎么可能?!”母亲说。
“如果北极的冰全化了……”外婆说。
母亲想了想,说:“还真有这种可能。”
外婆咳嗽了两声,接着说:“气温这么升上去,地球会不会变成另一个太阳呢?”
“谁知道呢?!”母亲说。
“那会有多热啊。”外婆说。
“那时候我们早就死掉不知多久了。”母亲说。
“我可不想死掉很久之后又被多烧一次。”外婆说。
她们的谈话让我烦躁。“人不可能两次被烧成骨灰。”我在自己的屋里大声嚷道,就好像是在重复赫拉克利特说过的话。
外婆和母亲没有继续说下去了。
我不喜欢日常生活,可是我喜欢记录日常生活。有时候,生活中的细节会被我挪用到自己的写作中去。我应该怎样定义我的写作?它们简约而深奥,读起来让人觉得奇怪又费解,比如前天写的《阿奇住进了精神病院》。我并不是故意将它写得奇怪又费解。它完全是“自然地”呈现在我的大脑之中的。说我的写作是“小说”,一定会引起专家们的不满。我是“业余哲学家”。我的写作对我自己是清晰又完整的。它对应着我心中的灵光或者心中的秘密。它抗拒传统和正统的分类。
1.14
今天办公室的人刚到齐,处长就宣布说:“我们要认真总结一下新年以来的工作了。”大家将椅子搬到了办公室的中间,围坐在一起。处长掏出自己的纸烟盒,给每位抽烟的同事派发香烟。这是办公室开会的时候永不更变的第一道程序。处长将香烟抛得很高,这使办公室的气氛立刻显得非常活跃。在会议进行的过程中,每位抽烟的同事会轮流主持这种派发香烟的仪式,办公室里始终烟雾缭绕。我不抽烟。我憎恶抽烟。烟雾比会议的议题更令我难以忍受。
像平常一样,我尽量坐得离抽烟的同事们远一点。我翻开一张报纸,读起了第三版左下角处那篇介绍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文章。对于经常面临严重饥荒的第三世界国家,这个机构好像是一个救星。但是,联合国底下到底有多少有用的机构?联合国本身又到底有多少用?这些问题很难回答。当国家利益变得不可遏制的时候,联合国的身份不是十分难堪就是非常暧昧。我们曾经在朝鲜战场上与联合国军殊死搏斗,我们后来又因为得到了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席位而得意忘形。混乱的历史与混乱的世界一样,充满了意外,充满了荒诞。
我们是第三世界里的佼佼者。我们将温饱当成基本的人权。我们基本的人权基本上得到了保障。所以,我们可以整天坐在办公室里聊天、喝茶、看报,还不断举行轮流派发香烟的仪式。
从前开会的时候,通常只有处长一个人说话。最近的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最近,同事们的话多了起来。不断高涨的物价让大家的话多了起来。今天刚抽完第一轮烟,坐在我对面的同事就突然情绪激动地说:“现在靠我这么一点工资,连养儿子都养不起。”说着,他将右脚从皮鞋里抽出来,脱掉袜子,很费劲地用右手食指在脚趾缝里捣动了几下,然后用右手拇指将食指上的碎屑弹掉。
大家都看着他的动作,并没有觉得难以接受。
“那你是怎么养的呢?!”处长漫不经心地说。
“广泛发动群众,”坐我对面的同事说,“让亲戚朋友一起来养。”
同事们接着就物价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处长在积极参与讨论的同时又不断提醒大家今天会议的议题是“总结新年以来的工作”。他的提醒远不如他的参与那么有效。他的提醒只能带来短暂的安静,而他的参与总是将对物价的讨论推向高潮。
一开始就跑题的会议一直开到了十二点半钟。机关的食堂已经没有什么好吃的菜了。处长临时决定带全办公室的同事去机关大门对面那家新开的餐馆吃“工作餐”。吃完丰盛的“工作餐”之后,同事们都夸奖处长,说他使我们的“基本人权”得到了保障。
1.15
晚上我又去了韦之那里。他说我的表情告诉他,我等待的信还没有到。
“她可能不会来信了。”
“你伤心吗?”
“我没有办法。”
“没有不散的宴席。”
“这冷酷的陈词滥调。”
“你们最后也许还会见一面。”
“为了正式的分手,我会去见她一面。”
“你觉得这种关系是一场悲剧吗?”
“不知道。”
“生活就像是表演。”
“可是,谁是剧本的作者?”
“没有人知道。”
“也许大多数表演都是即兴的,都没有剧本。”
“你想象过你们最后的见面吗?”
“经常会去想象。”
“也许会出现戏剧性的高潮。”
“什么意思?”
“你懂的。”
“也许什么都不会发生,就像过去所有的见面一样。”
韦之说着,突然低下了头。他好像是想起了他自己生活中的某一次分手。在我的印象中,他在不停地与他的女朋友分手。他的生活好像就是由分手构成的。他会对其中的一次分手有特别的感触吗?
我们的谈话就这样中断了。这时候,我注意到了韦之身后的墙上新挂出来的那块很大的蜡染布。韦之告诉我,那是他不久前去山区旅游的时候买回来的。他说那是一次很浪漫的经历。
1.16
都说哲学是对智慧的爱。而智慧和爱都要求绝对的自由。“专业”是对自由的否定,因为专业将人变成规范的奴隶,教科书的奴隶。因此,真正的哲学只能出自拥有绝对自由的业余哲学家。哲学教授是靠哲学领取工资的人,他也许离智慧不会太远,但是他离对智慧的爱很远,离自由很远。当然,维特根斯坦也当过教授。不过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例外。我也是我们这一代人中的一个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