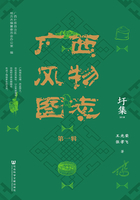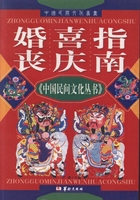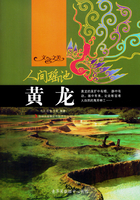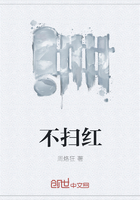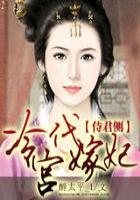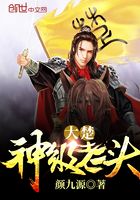如果子孙一时失手将祖父母、父母杀死,同样是大不孝的行为,要受到严厉的处罚。在乾隆中期以前,依照《大清律》的规定,因过失致祖父母、父母死亡的,要被判处“杖一百、流三千里”。而到了乾隆二十八年(1763)则将此类犯罪定为绞立决,较之前的惩罚加重。按照常理推断,一般在子孙卑幼与父母尊长发生争执或者受责打出手反抗时,容易出现过失杀人的现象,而《大清律》的这一规定,无疑是告诫子孙不得对尊长使用自卫权,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绝对顺从。之所以加重处罚,是因为这是关乎忠孝的大问题,过失虽然是无心行为,但子孙对待祖父母、父母应该万分谨慎、尊敬,不应该出现过失行为,就像臣民对君主那样全力尽忠,否则就要受到处罚。
除了以上两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子孙的某些行为被父母尊长视为大逆不道,在无可选择之下,一些无奈的父母往往会走上自尽的道路。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子孙同样会被法律认定为“不孝”犯罪,清朝的法律对此处罚更加固定化和具体化。乾隆三十七年(1772)规定,对这种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逼死父母的不孝子孙处以绞刑;到了乾隆四十五年(1780)又改为斩立决。虽然法律规定极为严苛,但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司法官员会根据情节轻重,给予适当的处罚。《刑案汇览》记载:一个叫汪永昌的人因为敲诈勒索被人控告,他的母亲冯氏得知后对告发者怀恨在心,可又无能为力,眼睁睁地看着儿子身陷牢狱之中,愁苦万分,一时想不开居然投水自尽了。司法官员认为冯氏自行轻生,虽然并没有受到儿子或他人的威逼,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汪永昌被人控告入狱的事情,因此将汪永昌处以流刑。
最后,严格规范子女的守丧行为。父母去世,子女守丧历来是天经地义的行为,清朝法律对此的规定基本承袭《大明律》。如《大清律·礼律》中对隐匿父母丧事的行为规定“匿不举哀者,杖六十,徒一年”,对在丧期内有违礼制,饮酒作乐的“杖八十”,而丧期内脱掉丧服的不孝子则要“杖六十”。同样,对于朝廷官员而言,他们是作为社会的规范和楷模而存在,不仅要遵守上述规定,还要遵守其他的特殊规定。《大清律例》中是这样规定的:如果官员父母去世,应回乡丁忧;隐匿父祖之丧,杖刑一百,且罢职不再录用;丧期没结束就冒哀从仕的,杖刑八十。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皇帝下旨“夺情”起复的官员不必遵守这条规定。
虽然略有改动,但《大清律例》不管是体例还是量刑标准,大部分还是沿袭了《大明律》,没有太大的改动。清朝统治者之所以这样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取得汉族的支持,利用近千年来备受汉族推崇的儒家孝道,结合前代法律,以一种稳妥、渐进的方式让汉族人民承认其政权的合法性,促进执掌大权的少数民族的统治稳定。之后清朝的历代皇帝,虽然结合本身统治需要,对律文条款、审判程序等作过一些调整,但总体上始终未超出“详绎明律,参以国制”的范围。
清朝的法律虽然对“不孝”行为作出了种种约束,但当孝道与法律发生冲突时,也往往以孝屈法,成全孝道,尤其是在血亲复仇方面,统治者从儒家传统道德出发,对复仇的孝子孝女主流都是宽宥的,这是儒家“孝治”原则在司法领域影响力的具体体现。在清王朝,孝与法再一次结合,宣扬孝道,惩治不孝,子孙在严苛的法律规范下,不敢越雷池一步,唯有对父祖尊长尽孝,甚至出现众多愚孝之人。这样一来,对个体家庭而言,子孙卑幼习惯于家长制的权威,家庭自然得以和睦;对清朝政权而言,孝子贤孙也就自觉地习惯于专制主义的统治,皇权自然得以巩固。
五、清朝存留养亲制度的新发展
存留养亲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一项比较人性化的法律制度,它是为了解决被判死刑或者流、徒刑犯人的父母老疾无人侍养问题而设置的。自北魏创制以后,唐宋元明清的各代法典都将其纳入其中,一直到清末修律,才予以废除,这项制度在我国存在了一千四百余年之久。在这一过程中,历朝历代根据自身的统治需要,对存留养亲制度不断地加以修订,唐宋时期已经比较完备,明朝法律设有存留养亲专条,而到了清代,这一制度发展到历史的顶峰,成为一项形式多样且卓有成效的法律制度。
清朝建立之初,基本继承了明律存留养亲专条的内容。《大清律例·名例律》规定:“凡犯死罪非常赦所不原者,而祖父母(包括高、曾祖父母)、父母老(七十以上)疾应侍(或老或疾),家无以次成丁(十六以上)者,开具所犯罪名奏闻,取自上裁(由皇上裁决)。若犯徒、流者,止杖一百,余罪收赎,存留养亲。军犯准此。”清律把存留养亲分为两种情况,即犯死罪和犯徒、流罪。犯死罪的人,律文明确规定“非常赦所不原者”才能存留养亲;犯徒、流罪的人,律文虽然没有作出限制,但与犯死罪一样,也只有“非常赦所不原者”才能留养。
什么是“非常赦所不原”呢?清律是这样规定的:“凡犯十恶,杀人,盗系官财物,及强盗,盗窃,放火,发冢,受枉法、不枉法赃,诈伪,犯奸,略人(掠夺人口),略卖(劫掠贩卖),和诱人口;若奸党,及谗言左使杀人,故出入人罪(法官故意裁判错误的罪行);若知情故纵听行,藏匿,引送,说事过钱之类应实犯(有心故犯),虽会赦并不原宥。其过误犯罪(过失杀人,失火及误毁、遗失官物之类),及因人连累致罪,若官吏有犯公罪(因公事而无心误犯),其赦书临时定罪名特免,及减降从轻者(降死从流,流从徒,徒从杖之类),不在此限。”
从条文中可以看出,清初承袭明律对“常赦所不原”的界定范围十分宽泛,几乎涵盖了所有刑法规定的重罪,远比唐律严苛。由于存留养亲条件过于苛刻,符合条件的犯人很少,导致这一制度在清初很少见于具体实践,形同虚设。直到康熙时期,随着封建统治的日益巩固,清王朝逐渐放宽了存留养亲的限制,并在处理个案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例文与成案。
对“十恶”之罪的放宽。“十恶”历来被认为是对封建统治危害最大的犯罪,十恶不赦是封建法律一以贯之的原则。按照清律,犯有“十恶”之罪的人不准留养,但清朝的例文对此有所放宽。例如杀伯叔父母、姑、兄、姊,叫做恶逆,是“十恶”之一,清律规定,对这种犯人,定案时要依律办事,不许申请留养。如果案情实在值得怜悯,要由皇帝下旨判决死缓,等两次秋审之后,官员查明情况属实,就允许办理存留养亲。清代的秋审一年举行一次,也就是两年以后才可办理留养,虽然耗时较长,但比之前不准留养的规定还是有所放宽。
但是有清一代对“十恶”中的前三甲谋反、谋大逆、谋叛,不准留养的规定还是非常严格。《刑案汇览》记载,一个叫阿小贵的爷爷犯了谋逆罪,按律阿小贵也在流放之列,但当时他年仅3岁,离不开母亲,他的母亲身为儿媳不在流放之列。于是官府决定将阿小贵交给他的母亲抚养,等到年满16岁之后再予以流放。谁知等到阿小贵长大成丁,他的母亲已经瘫痪在床,生活无法自理,地方官员向刑部申请阿小贵可否留养。刑部回复说:“阿小贵是叛逆的后代,为十恶不赦之罪,非常赦所原,不许留养,立即将其发配。”可见,清朝统治者处置严重危害统治的罪行十分严酷,所有的规定都是为了稳定政权而服务。
对杀人犯罪的放宽。杀人犯罪,清律规定是“常赦所不原”,不允许存留养亲,但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清代形成了这样的定例:凡是斗殴命案,在查证时,就要将凶犯有无祖父母、父母老疾以及该犯是否为独生子的状况调查清楚,一并上报,定案时,就可依据这些判断是否可以留养。如果审案的时候,罪犯不具备留养条件,但当定案时,父祖已是老疾或者兄弟子侄死亡的,仍然允许存留养亲。斗殴杀人是指两相殴斗时,致使一方死亡的犯罪。根据清律,只要符合条件斗殴杀人是可以存留养亲的。
除了斗殴杀人以外,清律还将杀人犯罪中罪情较轻的如误杀、戏杀、过失杀、擅杀等,也列入了存留养亲之列。误杀,是指一时差错,失手致人死亡;戏杀,本来没有杀人动机,但在动手过程中将人杀死,如拳脚过重致人死亡;过失杀,是因为“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到”而出现的意外杀人状况;擅杀,是指被杀者原本就是罪人,如抓获小偷,不送官府,而是擅自将其处死。这几种杀人犯都属于案情较轻的,只要犯人情有可原,一般都可以准许存留养亲。
而情节较严重的如谋杀和故意杀人犯罪,原则上讲不在留养之列,但乾隆五年(1740)制定的一项条例:“凡犯罪有兄弟俱拟正法者,存留一人养亲,仍照律奏闻,请旨定夺。”就打破了这一原则,自此之后,只要符合上述例文规定,即使兄弟所犯的是谋杀、故杀之罪,也有一人可被准许留养。《刑案汇览》中就记载了相关案例:沈现顺、沈现宇两兄弟杀死一家两口,沈现顺作为首犯,按律该处斩;沈现宇是从犯,按律判处绞刑。但他们的父母只有这两个儿子,依照清律的规定,可以存留一人养亲,于是官府上奏请旨,是否可以准许被判绞刑的沈现宇存留养亲。案件的结果是,官府遵照皇帝旨意,将沈现宇依例枷号(强制罪犯戴枷于监狱外或官府衙门前示众,以示羞辱)两个月,杖一百之后,准其存留养亲。
对孀妇独子犯罪的放宽。“孀妇独子”在《乾隆十一年之定例》中首次被纳入可申请适用存留养亲的范围,这是清代存留养亲制度的一大创新。这一例文规定,如果犯人的父亲已经去世,其母守节长达二十年及以上,犯人又没有别的兄弟,就可以申请存留养亲。封建统治者大肆宣扬“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鼓励妇女从一而终,这样社会上就出现了一大批守节的寡妇,为照顾她们的晚年生活,统治者才特意制定了这种条例。
一般情况下,得以留养的犯人,其父母至少有一方或老或疾,但在孀妇独子的情况下,其母是否老疾,都可以不必考虑,只要符合上述条例就可留养,比一般条件要宽,但如果其母中途改嫁,就被视为失节,不能作为存留养亲的依据。《刑案汇览》中有这样一则案例:陕西张自得犯罪被判处绞刑,他以“孀妇独子”为由申请留养。但经过官府调查,他的母亲燕氏,曾经嫁过三个丈夫,虽然最后一任丈夫去世已经超过二十年,也只有张自得这一个儿子,但她并非从一守节,于是便没有准许张自得存留养亲的请求。可见,孀妇独子犯罪能否留养,关键在于其寡母是否从一而终的守节。
对于诬告罪的放宽。清代对于诬告罪的处罚,遵循“诬告反坐”的原则,即诬告他人犯某罪,就以某罪来惩罚诬告人。在存留养亲的问题上,理论上也是如此,被诬告罪名准许留养的,诬告人就可以留养;被诬告罪名不许留养的,诬告人就不可以留养。但清律有这样一条规定:“诬告拟流加徒之犯,除被诬罪名应准留养者仍照定例遵行外,如诬告人谋、故杀及为强盗等罪,以致被诬良民久淹狱底,身受刑讯,荡家破产,迨审明反坐者,依律发问,不准留养。”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条例文,以谋杀、故杀及强盗罪诬告他人,如果诬告人被抓,即使被诬罪名原本是不许留养的,但被他诬告之人未受刑讯逼供、未被长期关押、也未倾家荡产,诬告人仍可申请留养。这条例文的重点在于被诬告之人“淹狱、受刑、荡家破产”的严重程度,如果情节严重,依律诬告人就不可申请留养;但如果被诬告之人没有受到太大伤害,情节较轻,那对诬告者就可以法外施仁,准许其存留养亲。
清代法律放宽了对存留养亲制度的种种限制,使之由前代的一纸空文变为切实可行的法律制度,但也在原有的执行条件之上又有所补充。(1)杀人犯奏请留养的,必须先查明被杀者是否为独子,其祖父母、父母是否无人奉养。如果被杀之人是家中独子且素日孝顺,只要尊亲无人奉养,不管老疾与否,杀人者都不准留养;但如果被杀之人一向对父母不孝或者常年游荡在外,杀人犯还是有机会留养的。(2)申请存留养亲的犯人要素日守孝道且只准留养一次。犯人自身平时是否遵循孝道,对留与不留有重要影响。此外,清律还有规定,若留养之后又犯有流、徒等罪行,一概不准再次留养,这主要是考虑到若一再准许留养,将使国法失去效力,凶恶无所恶。(3)得以减死留养的犯人,必须先枷责两个月、责打四十大板,并要根据其家庭经济状况,给予死者家属一定的银两以作赡养之用,这表明清代统治者已经注意到对被害人亲属进行经济上的补偿。
存留养亲制度,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情、理、法完美结合的产物,清代统治者将存留养亲制度发展到了完备阶段,更加强调和体现中国传统的孝道伦理和法律思想。这一制度的存在,体现了封建法律人性化的一面,既使老疾尊长得到亲人的奉养,可以安享天伦,也使罪犯得到亲情的感化和改造,为统治者博得“仁君”的美名,争取到更多的民心。儒家孝道文化更加深入人心,在维护家庭稳定和社会和谐的同时,也巩固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