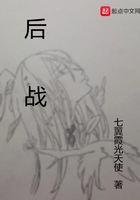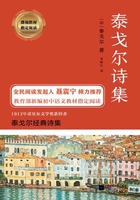伯延村来了两个陌生庄客。一位是短衣打扮,一位穿了长袍马褂。村里老汉们对这二人侧目而视,几个小孩围了他们看稀罕。
他二人牵着马匹来到徐家庄园门前,暗暗打量着眼前这座豪华气派的宅院。但见朱红色的大门上挂着镀金的门环,上面雕刻着精致的拧丝花纹;透过高高的围墙可以看到树木掩映下的楼阁一角,飞檐画栋,古色古香,华丽而大气。
他二人回来走动,不时偷往大院内看。门子张彬打开门走出来,问道:“你俩是干什么的?”
短衣人道:“啊!我想找人,请问这家主人贵姓?”
张彬皱着眉头,蓦然警觉,不耐烦问道:“你找谁呀?”
长马褂人顺大门看到一位老者正练太极,心想他肯定就是徐老太爷,咳嗽了一声道:“我们找徐老爷子有点儿小事。”
张彬凝视着他道:“你们认识我家老太爷?”
短衣人点着头道:“认识、认识,我父亲和徐老爷子是同行。”
张彬感觉神态有点失礼,便收拢眼光,看着来者道:“啊,你家父也是做药材生意的?”
短衣人点点头,拱手道:“是,做生意路过武安,顺路过来看看老爷子。”
张彬欣然答道:“你俩等等,我往里通报一下。”
短衣人和长马褂人点点头,默等着。
徐兴厚听张彬说有人来找他,停住手,收回脚,往后捋捋几根凌乱了的长发道:“让他俩进院说话。”
短衣人和长马褂人把马拴在墙上的拴马圈上。来到院里,短衣人停了脚步,定眼望了一会儿徐兴厚,笑着上前两步,搀扶住他的胳膊道:“老前辈,您老记不得我了?”
徐兴厚上下打量一下来者,皱起眉头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满眼茫然,摇了摇头。
管家世福一看有客人,急忙走过来,静静看着他们,问道:“请问你们是哪里人?”
短衣人不敢与他目光对视,转开了视线望着徐兴厚,哈哈一笑道:“我家父和徐老太爷是世交。”
徐兴厚听他说他父亲和自己是世交,拍拍自己的脑子就是想不起来。
世福冷冷注视着短衣人,微感不悦,说道:“请问你家老爷子是哪位?”
短衣人望着徐兴厚,想了想道:“我不说老爷子一会儿也能想起来的。我家父以前也是在东北做药材生意。”
徐兴厚一听是在东北认识的药材朋友,心想不管咋说吧,来者便是客,边往上房走边道:“世福,让粉儿上茶。让我再好好想想。”
世福不放心地看他一眼,带路向上房走去。
短衣人赶紧上前一步,搀扶着徐兴厚的胳膊,并肩而行。他扭脸看着这一道道大院,不禁脚步缓了下来。打量这所院落的格局,心里盘算,地方够宽敞,风水也不错,拱手道:“老爷子,您家院子盖得不错嘛?这房子严密得很,围墙极高,不怕贼来。”
徐兴厚微笑着点点头,说道:“这是我家逆子年前盖的。”
走进上屋,进门见客厅中安放着两把紫檀木交椅,交椅后背正墙上镶嵌着“五福捧寿”壁幅,煞是气派。
主客客气后落坐,徐兴厚叫粉儿拿来旱烟,又吩咐世福装果盘,泡好盖碗茶招待客人。
短衣人和长马褂人连声道:“不客气,不客气。”坐下来,他们双肘自然而然地搭在扶手上,非常舒服。短衣人低头细细赏鉴,工料两精,惊道:“这好像不是本地货色?这要值不少银子吧?”
徐兴厚捻须道:“贤侄真是识货的行家!一眼就识透了。这堂木器是我儿从南方运过来的,这是紫檀木。”想了想,来者乃是外地人,对他们的来历还不大清楚,说多了怕是不好。徐兴厚打定了这个主意,灵机一动,顿时将笑收起,平静地道:“至于值多少银子我也不大清楚。”
长马褂人看对方说话之间有了戒心,再问多了怕是没有什么好处,此处不可久留,示眼短衣人直奔主题为妙。短衣人明白他的意思,看看身边站着的佣人,再扭头看看徐兴厚,拱手道:“我有些生意上的事,想要单独跟老前辈您请教一下。您老人家是否能给晚辈这个机会?”
徐兴厚看他俩没有恶意,便道:“世福、粉儿,你们去院里把那几盆菊花儿浇浇水。”
世福没动地儿。
徐兴厚摆摆手道:“去吧,把花儿浇浇去。”
粉儿拽拽世福的大袍,世福很不放心地向外走去。
短衣人望着佣人离去,骤然变了脸色,低声道:“老爷子,我们是从天津来的,我们过来的意思,是希望您马上叫您的儿子徐敬修撤掉天津铺子,咱两来无事,如他不撤掉天津铺子……”
长马褂人接口道:“我们日本人会要他死得很难堪!”
“啊!你是日本人?”
长马褂人“唰”地摘下假头套,掏出腰间的匕首,用舌头舔舔刀刃,拉起徐兴厚头上一缕白发,轻轻割下放到手心,轻轻一吹,头发散落了一地。
徐兴厚吃了一惊,吓得浑身打战。
短衣人笑笑道:“老爷子,您家这座大院盖得可是很有讲究啊,这可是比着当今万岁爷的皇宫建筑的!这事儿您想想,如果让当今万岁爷知道了,后果您是知道的吧?哈哈哈……”
徐兴厚“啊”了一声,只觉得眼前发黑,天昏地旋,晕倒在太师椅上。
他们对话不到半个时辰,短衣人便带着长马褂人不慌不忙地走出上房。走到世福跟前,短衣人弯下腰道:“这菊花长得不错嘛。”
世福瞪他一眼,没有言语,放下手中的水瓢向上房走去。
长马褂人看世福起身,拉拉短衣人的后襟,起身匆匆走出徐家庄园。
世福走进上房吓了一惊,只见徐老太爷歪着头、双眼紧闭地瘫坐在太师椅上。
世福忙走上前喊道:“老太爷,您咋了?您哪儿不舒服?”
粉儿看世福进屋没有出来,便紧跟着也走进上房。世福看着情况不对劲,轻喊道:“老太爷、老太爷,您喝口水。粉儿,快点给老太爷倒水。”
徐兴厚慢慢睁开双眼,轻轻喊了两声:“敬儿、敬儿……”又闭上眼睛。
世福吓得大喊道:“粉儿快去,快去叫郎中!”粉儿吓得拔腿哭着向外跑去。
徐敬修、穆四妮、二春他们一身疲惫返回了伯延村。刚进徐家巷,两匹快马兜头从他们身边擦身飞奔北去。
徐敬修吃惊躲闪开,不耐烦地说道:“嘿嘿,你们看看这两个人,在村里还骑这么快,碰撞着孩子咋办?”
二春望了一眼骑马人的背影,不由得皱起了眉头,自言道:“这个人的背影咋这么眼熟?”
穆四妮扫了他二人一眼,撇撇嘴,道:“别是从咱家出来的吧?”
徐敬修扭着头望着远去的骑马人,哈哈一笑道:“那可是说不定啊。”
说话间,粉儿哭哭啼啼跑了出大门。
徐敬修看到粉儿哭着从家里跑出来,感觉事情不妙,急忙翻身下马,大喊道:“粉儿!你不好好伺候老太爷,跑出来干什么?”
粉儿一看徐敬修他们回来了,哭得更厉害了,哽咽道:“您们快去上房吧,老太爷晕过去了!”
“啊……”众人听后都瞪大了眼,诧异地看着粉儿。
徐敬修诧异了一瞬,蓦然反应过来,丢掉马缰绳撒腿向大院跑去。
看着奄奄一息的父亲,徐敬修的心刀割般疼痛,颤抖着双唇泪流满面。双手握住父亲抖动的手,哽咽道:“爹,爹,这是咋了?您睁开眼看看儿吧!儿回来了。”
好半天,徐兴厚才勉强睁开双眼,迷糊中看着徐敬修,又看看穆四妮,鼓起最后力气道:“儿呀……速把天津的生意撤回……你要当心日本人……”话没说完,脑袋一沉,身子一软,去世了。
徐敬修听后一愣,见父亲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肝肠寸断惨叫一声“爹——爹啊——”赶紧跪伏在地上。顿时,哭声叫声一片:“爹——爷爷——老太爷……”
哭着哭着,徐敬修突然止了哭声,大喊道:“世福!你过来!”他的脸上写着惊愕与不解,瞪眼厉声道,“世福!今天谁来过咱家?”
世福低着头嗫嚅道:“刚才有两个天津口音的人来过。其中一位说他父亲和老太爷是世交,要跟老太爷单独说会儿话,老太爷看他没有恶意,就吩咐我和粉儿去院里浇花了。待那人走后,我回到屋内老太爷就晕过去了。”
徐敬修双眼眯缝,狠声道:“天津口音,难道是他?”
“是谁?马继宗?”穆四妮吃惊地望着徐敬修。
徐敬修含着眼泪重重地点了点头。
穆四妮瞪着大眼望着徐敬修,脸色煞是难看。
二春攥紧拳头,怒声道:“我说刚才看那人的背影那么熟悉,那个人是秦有福!”
“日本人?爹为什么会说日本人,难道秦有福带着的那个人,是日本人?”徐敬修自言自语,细琢磨了一下,不由得吃了一惊。他想起芸香说的一句话来:马继宗跟着日本人出去了,他的事我没有过问过……徐敬修狠狠说道:“龟孙子!”
一阵旋风刮过,村头杨树林的枝叶纷纷掉落,尘土飞扬着席卷了伯延村,整个村落陷入天昏地暗。
徐家庄园那扇宽大而沉重的大门敞开着,通往各个四合院的甬道门扇都打开了。一眼望过去,便是灵堂中那个斗大的“奠”字,左右高悬着挽联。挽联下,祭奠的供桌摆着菜肴果品等祭物,桌上“长明灯”忽明忽暗,两旁的香烛“噗噗”冒烟流泪,徐兴厚的灵柩置于供桌之后。
灵堂的布置肃穆庄重,白茫茫的烛光让整个厅堂显得饱和而压抑。
夜里,灵堂的白蜡烛静静地流着泪,灵柩两旁的杆草上跪着身服重孝,腰间系着白麻长绦,额前挽着白色绸带的徐敬修、穆四妮、徐敬文、徐敬云、徐大光、徐大任、徐赵氏、徐白氏、徐利平、宋运青、李长水等人。家丁和佣人们也都身挂孝衫忙碌着穿梭在院中。
突然,一支飞镖冲着徐敬修的头呼啸而来,穆四妮手疾眼快飞身接住飞镖。朝远处望去,看见一条黑影从屋顶一闪而过。
徐敬修和大伙儿还没有明白过来怎么回事,只见一道白光飞身而起。灵堂前跪着的人都吓呆了,一个个目瞪口呆,半天才惊呼起来,道:“啊!是太太!太太飞走了,太太飞走了!”
徐敬文等人都吃惊地回头看着徐敬修。
徐大任惊恐地指着夜空,道:“爹,我娘飞走了!我娘她飞走了!”
大院内所有的人都用吃惊的眼睛望着徐敬修。
徐大个子跑过来,惊慌地指着房顶道:“老爷、老爷,那白影可是太太?”
徐大光近前一步,正欲说话,徐敬修挥手制止了他。慢慢地站起来,淡淡的说道:“哪能是太太呢?我刚叫太太回屋休息去了,大家不要惊慌,该干吗就去干吗去!”家丁和用人们都相觑一眼,没再敢言语,低头各干其事去了。只有二春心里明白那就是太太穆四妮,他望了徐敬修一眼,低头干活儿去了。
徐大光回头扫了徐大任一眼,用疑惑眼光看着父亲。
徐敬修视而不见,先跪下来,用强硬的口气道:“还不都跪下!”
徐大任颤声问道:“爹,我、我娘她是不是会武功?”
徐大光也瞪着吃惊的眼睛看着父亲。
徐敬修挠着头,悠悠道:“不会吧!也可能会一点儿?我也说不清。”
徐大任闻言一惊,指着房上道:“爹,我娘这是会一点儿武功吗?”
徐敬修望着父亲的棺椁发呆,半晌才沉声道:“大光,你在这儿坐着不要动,大任,跟我过来。”
徐大光道:“爹,你们要去干吗?”
徐敬修没有回答,径自朝正房走去。
徐大任愣了一下紧跟上来。正房内,徐敬修从床上的柜子后面,费劲地双手拿出一条长布兜。徐大任凑在父亲耳边低声问道:“爹,这是什么?”
徐敬修低声道:“这是你娘的九环刀。”
徐大任手一抖,目光看向父亲,学着父亲常用的口头禅道:“我的老天爷呀,我咋不知道我娘还有大刀呀!”
徐敬修嘴角噙笑,看儿子一眼道:“你不知道的还多着呢。”
走到大门口,身后的徐大个小跑过来道:“老爷,二少爷,您抬的啥?来,让我替您们扛着。”说着就要伸手去拿。
徐敬修用身子一挡,道:“不用了,我出去办点事去,看好家啊!小心那黑衣人和那白衣人再回来。”
徐大个子凝视着他,忙点点头道:“对、对、对,别让他们再回来,我要看好咱的家。”
徐家父子抬着九环大刀向村西南方向走去。定眼望去,但见西坡地乱石岗上,一黑衣蒙面人仗枪卓然而立,冷然道:“明天我让你们家一葬两人!”
穆四妮一指黑衣人,大声喝道:“你是何人!竟敢擅闯我府,你我有何恩怨?”话音未落,就听黑衣人道,“费话少说,看枪!”
穆四妮怒道:“大胆贼子,今天我就让你晓得本奶奶我的厉害!”双袖一挥,袖影之中撒出漫天的芒影,犹如暴风骤雨般地疾打出去。黑衣人大喊道:“想用暗器伤我?没门儿!”话音未落,低头一看,右肩处的衣襟已然撕开,血迹隐约可见,里面露出一道深深的刀痕。伤处顿传出阵阵剧痛,黑衣人的神志却是很清醒,厉喝一声:“看枪!”长枪化作一道寒光,直取穆四妮的喉咙。就在这千钧一发时,徐敬修暴喝道:“给你大刀!”
“来得正好!”只见穆四妮飞燕般的身形急向空中旋去,闪电般地从地上拾起她的九环大刀,又腾空翻越,传出一阵“当啷啷”兵刃交接声。
黑衣人手持九曲枪,枪头如蛇形,顶尖锋利,两侧的薄刃寒光逼人,搭、缠、圈刺向对方。
穆四妮手中九环大刀通体浑厚,刀锋犀利,背部的九个大环银光闪闪,劈、刺、砍化作一大片寒芒光弧,滚滚向前迎上。大刀倏地一振,破空剌出;刀势凌厉,犹如闪电惊虹。黑衣人连接对方数十招,已招架不住,心中不禁大骇。他“噔、噔、噔”后退几步,以枪拄地,胸前衣衫破碎,面色一阵苍白;发髻蓬乱,腰间血迹隐约,身形摇摇欲晃,“噗”的一声,枪落尘埃,仰首望向长空,目中黯然无神,缓缓长叹一声,哑声道:“你杀死我吧!”
徐大任大喊道:“娘,把他的面纱解下,看他是何人!”
穆四妮走过去挥刀挑去黑衣人脸上的黑布,喊道:“闫罗峰!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来到武安地界,真是欺人太甚!我有意放过你,而你不知悔改!”
闫罗峰手捂腰间,面色苍白,凄然说道:“今天又落入你的手中,天公灭我,要杀要刮随你!”
穆四妮皱眉紧盯着他的脸,颤音道:“你弟弟横行霸道,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欺人太甚。我哥哥为民除害,你们将我哥哥活活打死。今晚,我要为我的哥哥和我的父亲讨个公道!”说着举起大刀跃身上前,要置闫罗峰于死地。
就在这时,只听徐敬修大声哀求道:“夫人啊!我求求你,放下心中的恩怨,不要再伤人命了!闫罗峰,请你扪心自问,谁对谁错,我相信你能从中找出答案,也希望你能从恩怨之中走出来,找回你自己。得饶人处且饶人吧!”
闫罗峰听后心头一振,看了徐敬修一眼。
穆四妮听着徐敬修发自内心的表白,蓦地心软了,于是,她虚晃一刀,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
闫罗峰一看穆四妮有意放他一马,迅速退爬几步,提枪逃离现场,飞向黑处逃之夭夭。
徐大任急喊道:“娘,看!他跑了,他跑了。”
徐敬修看着闫罗峰逃走,急步走过来道:“伤着你没有?”
穆四妮痛苦地摇摇头,冷冷说道:“老爷,我说那晚杀了他吧,你说不要再伤及无辜了,看看这是不是放虎归山?我糊涂的老爷呀,你心软,可他不会心软的。”
徐敬修心痛不安地仔细打量着自己的女人,摇摇头道:“你把他杀了,改天他的儿女再来找咱报仇,你说这冤冤相报何时了呀?”
穆四妮听后闭目摇摇头。
徐敬修看着她憔悴不堪的面容,拍拍她的肩膀。
穆四妮话未出口泪先流,急急擦去眼泪,埋怨的话已到嘴边,硬生生吞了回去,摇摇头长叹口气。
徐敬修把她鬓边的碎发拢了拢,道:“啥也别说了,回家。”
徐大任用疑问的眼神看过去,问道:“娘,您武功那么高强?我咋没有听您和爹说过?他是谁?他与咱有什么恩怨?他为什么会来害咱?”
穆四妮半仰脸,看着头顶的夜空,含泪带着惋惜道:“就是因为他家,你舅舅和外公才离开咱们的。”
徐大任呆愣住,脸色骤青,默默地跟在母亲身后。好一会儿,他才急走两步,狠狠地说道:“娘,既然是他害死我舅舅和外公,您刚才还不一刀将他杀死。留下他的狗命作甚?”他看看父母都没有言语,转开话题道,“娘,我想听听你们过去发生的事。”
穆四妮脑中一片混乱,直视着前方,沉默了会儿,道:“三天三夜也讲不完。”
徐大任半搂半搀着母亲的胳膊,道:“娘,看您从家里飞出来时,吓我一跳。娘,您啥时候学的武功?您咋还能飞起来啊?您用的那叫啥功夫?”
徐敬修一直在旁观察着儿子,品味儿子发现他的母亲是武林高手之后的心理动态。他背手快步走到家门口时,干咳两声,回过头道:“你娘那轻功可是功夫秘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