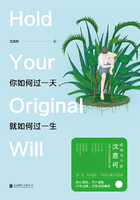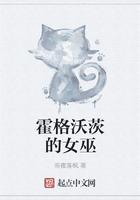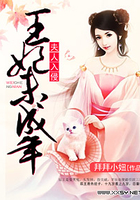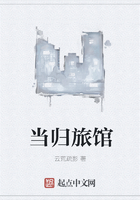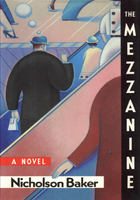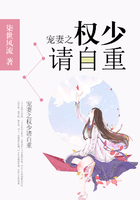我有时能听到水声,有时又听不到。这在于梦境的真实与否。时间过于久远的场景,有时就没法分清是梦境还是现实,两者混在一起,像半瓶糨糊倒入流沙。水声有时出现在通往密山渡的路上。红色的风化山岩上流下来的泉水汩汩作响,时间是春天或者夏天,甚至是冬天,总之阳光刺眼,空气灼人。亚热带气候中,季节的特征并不是特别明显。那时候是1984年,我正跟着爷爷步行去密山渡,赶赴三叔公嫁女的喜宴。密山渡是爷爷出生的村子,位于广西平乐。
而此时,2008年春天,我身处广西东兰,天色已暗。我要去采访一位从北京来此地教书的老师,做完这次采访,我就要去北京了。北京有时候像梦境。我仍能记起第一次到北京时的情景。火车在市郊的铁轨上疾驰时,我甚至怀疑北京在此前是否存在,是不是一座只在观念中存在的城市。小时候,和同一条巷子里的小朋友曾有约定,2000年,迎接21世纪的那一年,一起去北京玩。21世纪遥远得和科幻世界差不多。1992年,北京申办奥运会的时候,我在一张纸条上写下:我希望2000年到北京看奥运会。2000年,我应该上大学了。要看奥运会,最好考上北京的大学。2000年到来的时候,北京既没有举办奥运会,我也没有考上北京的大学,也没有跟巷子里的小朋友一起去北京。
我住进了江边的一家旅馆。旅馆后边就是黑黝黝的山脊。躺在床上,看着那些山,我又听到了水声。我想起了爷爷。东兰大概是爷爷工作过的离家乡最远的地方。他在这里的邮局工作过一段时间。爷爷曾考上大学,但作为家里的老大,他没去上学,留在了家乡——广西平乐。那已经是20世纪30年代的事情了。
我从未问过爷爷是否心甘情愿留在家乡,当我想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已经去世多年。我们家就住在县城中学旧址的墙根边。爷爷曾经指着门前那些老房子的窗户,告诉我哪里是食堂,哪里是教室,哪里是厕所。通往厕所的木质天桥横跨巷子。
酷暑时节,爷爷会在家门口倒上一大盆凉水,我看着那些水慢慢变成水蒸气,消失在阳光下。太阳远远地从金子岭落下去了,望着那些山,我会想,山那边会是什么地方呢?我会离开这里,到山的那边去吗?
看着那些逐渐隐入夜幕的山峦,我睡着了。睡姿不好,早上起床时脖子有些疼。退了房,我登上了从东兰县城开往隘洞的车。
客车在东兰雨后的崎岖山路上快速盘绕,每一次猛烈的拐弯都让人感觉车子将会飞身坠入山谷。一位上了年纪的村妇不停地向着窗外呕吐,司机大声地和回乡的青年们用壮语聊天。颠簸的客车在一条小河边上停了下来,前方已没了可供一辆车行驶的车道,乘客们都下了车,并卸下大袋的化肥、饲料以及各种杂物。
“萧老师昨天才坐我的车回来。”女售票员在得知我是来这里找萧望野之后,指着河对岸的校舍说。
寒冬过后的料峭空气中,这所乡村小学里巨大的木棉树还未开花。正值午休时间,我在树下坐了一个小时后,一位女子从学校唯一的教师宿舍楼里走出来。一个学生告诉我,那就是萧老师。
她一头短发,矮个子,看上去白皙而柔弱。跟我握手之后,她拒绝了我观看她教学现场的请求。“现在还不成熟,我不想让别人看。”
各个教室里传出的声音汇集在校园里,萧望野所在的教室传出的声音显得很欢快,而其他的一些教室,则可以听到老师用近乎嘶吼的声音在讲课。
临近黄昏,萧望野随着寄宿的学生进到学校食堂里。由于中午忘记拿饭盒到食堂蒸饭,她只能从几个学生那里分得一些米饭。除了米饭,食堂里只有一大锅水煮的青菜,每份四毛钱。一些学生只是吃着米饭。以前是两毛钱,现在涨价了,有的学生吃不起。
晚饭结束后,学生们围着萧望野问着一些什么。一个学生说,以前的这个时候,萧老师会吹笛子,听到笛子声,他就会去阅览室。
阅览室里堆着杂物。这个周末,学校要拆掉一幢不合格的旧教学楼,须要占用这里的空间。书整齐地摆放在木质的螺旋形书架上,以画册居多,一本叫《七谷》的小画册上署有这所小学四十位学生的名字。这是萧望野和学生一起做的书。
从阅览室内的一本相册里可以看到,螺旋形的书架上点着一圈蜡烛,学生围坐一旁。萧望野会先敲击扬琴,让学生安静下来,蜡烛吹灭后,她带着学生沿着螺旋形的书架走进去,开始他们每天的课外阅读。这是让他们获得安宁的途径。
锁着门的阅览室外,学生们在打篮球。萧望野偶尔也会出手投几次篮,更多的时间,她坐在木棉树下,被几个孩子从各个方向搂抱着,轻松地聊天。
萧望野住在教师宿舍的一楼,窗户玻璃早就掉了,她用了一只簸箕来遮挡。屋子对面,有一个空置的房间,从山外至此的人会被校长安排在这里留宿。
几年前,从北京第一次来这里进行教育交流的萧望野就住在那个房间里。
“活动进行了一个多月吧,学生们很高兴。我要走的那天早上,五点钟,孩子们拿着火把和食物站在窗外。他们很伤心,哭着问我,老师你什么时候回来?”萧望野觉得这样的回忆有些肉麻,她不愿意继续说。
她感觉到她和这些山里孩子有缘分,于是,在回到北京之后,她重返此地。
她写于2004年12月13日的日记,对这次重返有过描述。她抱着女儿光之奴,搭乘火车、汽车和船,来到这里。“坐在船的甲板上,风有些大,可是干净的阳光、山峦、河流、低飞的鸟,我想这就是我要去的地方了。”
萧望野认为这与“幻想”“诗性”“浪漫”毫无关联,她只是选择了一种自己愿意的生活。
自己愿意的生活?我有时候会想,什么是自己愿意的生活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只是想着能去北京就好了。北京,离广西的这些山那么远,足够远就好。而此时,我是在采访一个从北京来到广西山里的老师。
早上,天空湛蓝,阳光充足。萧望野没有课程安排,备完课后,她往山上走去。往上走,就是她的书稿《那美》中所说的叫“那美”的地方。
山路上落满黄褐色的枯叶,村里的猪、牛、马、鸡在上面或跑或走,发出一阵断裂的声响。在刚过去的这个异常寒冷的冬天里,山上的许多树木在冰雪中倒下,然后被村民拖回家后截成木段置放成堆。在一堆木头的附近,一座黄土砌成的房子凋敝不堪,房门上的锁头已经锈迹斑斑。
四年前,她就在这里给孩子们上课。
在这个环望皆山的村子里,有好几个这样的教学点,以方便山里的孩子上学。这个教学点有三十多个学生,由一位五十多岁的每月领八十元工资的代课老师上课。教室里有两块黑板,一、二年级学生坐在教室两边,一半人听课,一半人做作业。冬天里山风穿房而过,孩子们几乎整个冬天都挂着鼻涕,老师有时候得停下来,让孩子们集体擤完鼻涕才能上课。
我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南方周末》有一个栏目叫《百姓茶坊》。有一天上晚自习的时候,我在这个栏目里看到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乡下代课老师去外地开会,吃午饭的时候,他没有跟其他老师去餐馆,而是找了个水龙头,就着自来水吃自己带的馍馍。我的眼泪哗哗地流了出来。我想到了自己听闻过的一些故事,就用信笺写了下来,买了个信封,我看了看栏目编辑的名字,写下“徐列编辑(收)”,就把信寄了出去。
如今,我成为了《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徐列是《南方人物周刊》的主编,我的新老板。
在正式入职《南方人物周刊》之前,我来过东兰的这所学校,采访德国人卢安克。
实际上,我见到萧望野的同时,也见到了卢安克。这是让我感到有些尴尬的时刻。卢安克化解了这样的尴尬。他把自己的房间让出来给我住,就像半年前那样。
半年前的那次采访,卢安克并不希望自己被报道,但我觉得,他在这里做的事情应该被世人所知道,介绍我来采访卢安克的朋友们也如此认为。报道发出去之后,卢安克生气了。此次见到他,他的笑容让我觉得心安了一些。但心里真正放下,是几年之后,他在电视镜头前接受了柴静的采访。
多年以后,很多人会问我:“在你采访过的人当中,给你印象最深的有哪些?”我列出的名单中,有卢安克。
我第一次见到卢安克的时候,他正走在青黄错落的稻田间。阴天,午后的浑浊阳光漫过山梁上的茂密树林,洒在他留有泥渍的宽大T恤上。这个穿着廉价迷彩裤,蹬着劣质塑料凉鞋,钥匙用白色尼龙绳串在腰间的瘦弱德国人,从背后看去,仿佛是赶圩归来的农民。
卢安克走了三个小时的崎岖山路,到乡里能上网的地方下载了一个程序,再步行回学校。学校的电脑出了问题,他希望能快点解决。
小学没有通网线。卢安克问过电信部门,回答是——要有五个以上的用户申请,他们才会把网线拉过来。在这里,凑齐五户人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电脑在卢安克的摆弄之下恢复了正常。下午已过,黄昏来临,宁谧的山村里升起白色的炊烟。
卢安克到校门口的小卖部买了一小袋花生米,回到宿舍炒熟了,再煮上一小锅饭,这是他的晚餐。餐桌上方,有不少苍蝇嗡嗡盘旋。在同一间屋子里,同宿舍的几位老师喝着乡民自酿的糯米酒,盘子里是油腻的五花肉。
卢安克不吃肉不喝酒,口渴了,直接把嘴往水龙头边一凑。“这里的自来水比商店里卖的纯净水还好喝。”
吃晚饭时,夜色渐浓的窗外有一群孩子在打篮球,嬉闹声和叫喊声混杂着,四散开去。孩子中有三个卢安克以前的学生,去年小学毕业后进入初中,由于表现非常“糟糕”,这个学期被拒收了。
这三个孩子告诉过卢安克,他们不喜欢被人讨厌。“但别人对他们的看法已经定下来了”。他希望人们对这三个孩子的看法能够改变。
他更希望世界上的很多事情能够通过教育得到改变。从1997年起,他在中国广西的大山里已经待了十年,辗转多处山村,坚持做他的教育研究。
因为不喜欢甚至害怕露面,他拒绝了无数次采访要求,但他的模糊形象还是通过媒体的只言片语得到了广泛传播,“活雷锋”“白求恩”“感动中国人物”……无数顶“帽子”飘落到他的头上,可他并不喜欢。
2006年,卢安克再次被媒体推上话题浪尖,他希望加入中国国籍而未获批准的事被炒得沸沸扬扬……签证到期的卢安克在争议还没结束时便离开广西,回到德国。八个月之后,他返回中国,再次来到这个山村。
萧望野此时也来到了这里。
“我来到这里的时候,那位老师很高兴,觉得终于有人来帮他了。”那位老师是山上的代课老师。萧望野感到有些为难,她希望用自己的方法教授孩子一些东西,而不是帮孩子们应付中国偏远山村里同样具有的考试压力。
半年后,这个教学点解散了,代课老师失去了每月八十元的工作,回家继续种田。空置的黄土瓦房被萧望野改造成了幼儿园,她的女儿和村里的孩子们就读于此。
她居住的房子中,老鼠随意跑动,虱子、跳蚤、臭虫轻易便可寄居在人的身体上。上厕所时,蚊子和苍蝇成群,大便后,需用废弃的竹篓条来清洁。“在潮湿、阴冷的晚上,痛会浸入你的四肢,最后进到你的心里”。
当女儿的脚上长出很痒的疱,当绿毛在房间的各个角落里隐秘生长,当在漆黑的夜里找不到归路时,人的耐性会受到考验,“对自己充满疑惑,害怕留下来,也害怕离去”。
在那美的日子,萧望野患上了风湿病。“这样的天气,得好好晒晒太阳。”萧望野坐在村民老牙家用竹子搭成的晒台上。
十分钟前,老牙在山道上遇见萧望野,邀请她去家里吃午饭。在我和萧望野行走的山道上,每个经过的人都认识萧望野,每个人都会提出这样的邀请。
“这里潮湿,很多人都有风湿病,上了年纪的人几乎都有。”老牙边张罗饭菜边说。
在萧望野的眼中,并非所有的事情都如此糟糕,在那美住下来后,她欣喜于获得了充沛的时间来阅读、冥思、祈祷和反省,还可以打水、劈柴、烧火、煮饭,关心小鸡的冷暖。
她觉得最重要的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教育理想开展教育活动——这被她认为是极其迫切的事情。
透过山上那间紧锁的土房门缝,还能看到一些残迹。那里摆放着破烂的桌椅,有远方来的朋友曾建议她换些新的桌椅,但她拒绝了。
“这些桌椅还保留着孩子们的父辈成长的生命痕迹,但是,很多人感觉不到这些,我们的教育是有问题的,除了有物质的感觉以外,还应有灵性的感觉。”
下午三点,当萧望野从那美山上下来的时候,学校里的学生和老师已开始把桌椅从那座即将拆除的教学楼里移出来,搬到学校附近的好几个村民家。学生们将分散到这些村民家临时上课。
萧望野和几个老师、学生将书架拆了下来,她希望这个书架能够被重新布置,那是她对学生进行“灵性教育”的一部分。她在《那美》一书中写道:“书中谈论的是灵性教育,而不是在谈宗教教育。灵性是人的一种区别于其‘它’的特性。无论你是不是一个宗教信仰者,你都是一个灵性的生命。”
在萧望野看来,人有身体和心灵,而精神是看不到的,心灵像一面镜子,去反射精神的光。“反射得明亮的时候,我们把这种状态叫灵性。”
很遗憾,萧望野没能让我亲眼观看她是怎么进行灵性教育的。她只是告诉我说,我们要对色彩、音乐、语言、文字、文化……有一种精神范围的研究,这样它们才会真正有生命,在我们的生活中活起来。
“比如,我们不会在教小孩画画时,让小孩在一个框框里填颜色,那是强迫小孩服从于一种标准。像鹦鹉和猴子那样模仿别人的课程,不能带来精神力。”
萧望野还举了“水”的例子。在认识“水”字时,应先和孩子们在大自然中感受“水”;接着用毛笔蘸上有“水”的特点的不同颜色来表达感受;在地上画一个包涵着平衡、和谐、循环、川流不息、“你在我中,我在你中”的“水”的图形,然后,让小孩模仿和感受老师的节奏,在这个图形上走动,那么,平衡、和谐、循环、川流不息的“水”的特质,就会被小孩的身、心、灵所感受到。
阳光下,孩子们来回搬着桌椅,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那美读幼儿园时便接受了萧望野的“灵性教育”。她很关注这些孩子,希望看到一个结果。
我问萧望野:“你强调老师对学生的作用,而你不可能一直带着学生读完初中、高中、大学,当你离开他们时,效果有多大?你在山里待这么久又有多大的意义?”
并不是我一个人有这样的疑问。
一位朋友在给她的信中问:“如果你想全身心地投入于那美的事业,我可以理解。可是,你在信里说,学校那边的情况并不好。那,你未来怎么办呢?继续带着孩子在大山里游荡?……有时候,想到你的生活,我在心里会觉得悲哀——对,是悲哀。我看到晏阳初(民国时期的著名教育家)当年在定县的努力。他当年做的事情,灰飞烟灭,除了一些记忆之外。”
萧望野在回信中这样写道:“学校的确面临危机,现在只剩下五个小孩。我趁春节他们外出打工的父母回家时去家访。结果,他们只关心我吃饱了没有。我认为他们需要的却不是他们认为他们需要的……我的未来?我是不清楚的,但我是清醒的。我妈妈以前经常为我设想,不过,我的人生却比她想的有意思多了。目前,我还继续和之奴在大山里生活,而非流荡。晏阳初所做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永恒地存在着。这些,是整个世界发展的酵素……寒冷在两天以前过去了,短短的两日阳光,我房门外的白梨花开了。春天总是要开花,在真理中总是有希望。”
学校的周围种着许多青菜,天气回暖,青菜开始开花。青菜的花朵意味着,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山村里将没有青菜可吃。
“那时,村里人就上山挖野菜吃。”萧望野提到她吃鱼腥草的一次经历,“我贫血,而鱼腥草是凉血的,一吃就晕了过去。”
在那美住的那两年,每到春天来临,她自己翻土、种菜。朋友听说了她的生活,寄了一本《瓦尔登湖》给她。梭罗说:“从今以后,别再过你应该过的人生,去过你想过的人生吧。”
两年前,幼儿园的人数越来越少,萧望野不得不结束在那美山上的生活,随着她的学生到山脚的小学里去了。
已是星期五的傍晚,当教室里的桌椅都处置好之后,萧望野和一些回家的孩子往山里走去,她要去看一个叫韦云会的十一岁学生。
山间的田野满是正在开花和即将开花的青菜,而韦云会家缺少篱笆的菜地里,青菜已被村里觅食的鸡啄食殆尽。韦云会的家在半山腰一处裂痕累累、似乎行将倒塌的黄土房里。村里没有多少人在乎这家人的处境,长期的贫穷已经让他们神情麻木。
韦云会的家门前,堆着数百块大石头。他的父亲在过去一年里,独力将这些每块上百斤重的石头从河边挑上来。他想给孩子们建一所更坚实的房子。而他在两个月前一次醉酒行路时,从山上摔了下去,再没有回来。
天色已暗,刚从学校回家的韦云会正在山里找寻他家的两头牛。他没有名字的傻姐姐站在门口看着萧望野,笑着,她喜欢萧老师的到来。
牛没找到,失望而归的韦云会快速地生火、切菜、煮饭。他是这个家庭唯一的劳动力。他的傻姐姐和常年有病的母亲需要他照顾,他只有十一岁,能力实在有限,他弟弟已在一个月前被送到别人家抚养。
萧望野认识这家人是因为韦云会的傻姐姐。她去乡里赶街时,经常在村口看到这个头发蓬乱、任何季节都光着脚丫的傻女孩对她笑。“我很好奇,有一次就跟着这个女孩子回家,才知道韦云会在我们学校读书。”
萧望野将几张照片送给韦云会和他的姐姐,这是她去年来他们家时拍的,照片上有韦云会的弟弟,那个时候,他的弟弟还未送人。
韦云会的邻居看到萧望野来了,请她到家里住。“他们家连床都没有多余的,怎么住啊?”邻居说。
其实,也就是在当天,学校里的人才送给韦云会家一张床。刚过去的那个寒冬,他们家得有人睡地上那块破木板。此时,韦云会的妈妈用脚将木板踩断,准备扔到煮饭的火堆里烧了。
那天晚上,萧望野留在了这个家里,抱着那个全身脏兮兮的女孩,在满天繁星的夜晚里睡去。
第二天早上,大家准备去找走丢的牛。萧望野唤醒韦云会的时候,这个十一岁的孩子说他累了,须要再休息一会儿才能去找牛。萧望野的手感觉到孩子的体温很高,在她的执意要求之下,韦云会到村里的卫生所就诊,超过四十摄氏度的体温需要两大瓶药水才能降下来。
我和萧望野带着打完吊针的韦云会回家,路过河边的石桥时,韦云会的傻姐姐正对她笑。萧望野叫女孩回家去拿肥皂,女孩照做了。过了一阵,她拿着肥皂从山路上下来,回到了河边。“别看她傻,她内心其实什么都知道,她需要有人跟她做朋友,关心她。”
我坐在河边。几米之外,萧望野站在小河中间裸露的石头上,弯下腰去,用肥皂和山涧流淌下来的清水,细细地洗净了女孩结满污垢的头发,晌午的阳光从蓝色的天幕投下,让河流、小桥、房屋、树木以及这些场景中的人,变得温暖而有光泽。
给女孩洗完头之后,下午移向尾声,日头已经西斜。回到学校时,一个姓潘的八岁小女孩已经等候多时,她是来请萧望野到她家吃晚饭的。
萧望野已经一天没吃东西没喝水了。这是她斋戒的第一天,只能在天亮前和天黑后进食与饮水。她说这并不是因为她笃信某种宗教,而是相信这些宗教倡导的体验。“斋戒是体验放弃,你体验过什么是放弃吗?”萧望野问我。
在潘家的门前,可以看到西面向晚的山峦开始收敛光芒。萧望野看了看表,“时间还没到,七点钟才能去吃饭。”
潘家的火熏腊肉真是好吃,我和老潘就着这些美味喝下了很大一碗糯米酒。萧望野坐在旁边,只吃青菜。
“都认不出是你了。”潘家一位穿着土布衣服的老人对萧望野说。她为萧望野这个学期的新发型感到新奇,因为年前还梳着一条又长又粗大辫子的萧望野,如今是一头短发。
萧望野的解释是,上学期结束的时候,她缺少去南宁的路费,于是在乡里的集市上卖掉了她的辫子。此地有收辫子的习惯。“每次我去赶集时都有人问我辫子卖不卖。”萧望野这条好辫子卖了一百多块,她获得了去南宁的路费。
这个村子里延续着一些传统。萧望野曾对山村里农妇编织的土布感兴趣,她的一群热心于此的山外朋友还成立了一个土布社。萧望野曾穿上请本地人帮她做的布鞋赶街,她觉得那样真好看。
但没有多少人认为这些土布是重要的。这里的年轻人只存留着对自己文化的少许记忆,他们的父母甚至反对萧望野请本地老师教小孩唱壮语歌谣。他们说:“萧老师,你真伟大,来这里教我们小孩讲普通话。可是壮话不好听,没有用。”
萧望野对他们说:“如果你在外面打工,受了委屈,生了病,你是不是想回到这里?这是你的家。如果有一天,这里的房子是汉人的房子,语言是汉族的语言,衣服是汉族的衣服,那时候,你连回家的感觉也没有了。”
萧望野已经很久没回北京了,在来东兰之前,她曾在北京待了十几年。她回想起和那些诗人、画家、导演、音乐人谈论“什么是有意义的人生”的日子。
“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年轻人举办诗歌朗诵会,还会不会有诗人站出来,要求在场的人在聆听朗诵时,抱以一种虔诚的态度。诗歌会结束后,是否还有破自行车在吱嘎吱嘎地伴随着细碎的月光行走。”
有一次回北京,一位老朋友给她唱了一首歌,有几句歌词令她印象深刻:“我是一个要中途下车的人,你们不要觉得诧异,我们只是共同搭乘火车的人。你们认为我没有到达终点,这,就是我要下车的地方。”
北京的朋友问她,别人说你女儿像个乡下小孩,你如何让她以前生活的北京接受她?
萧望野觉得自己和女儿在北京的时候就是边缘人,一位朋友曾请她到学校工作,并免费让她的女儿在这个豪华的国际幼儿园上学。在圣诞节的表演中,所有的女孩都穿上一千多块钱的天鹅裙,萧望野只给女儿买了一条健美裤。
“如果所有的创造都可以通过钱、现代技术来达到,好无聊。之奴是乡下小孩,就意味着她的生活是通过她‘自己’和‘自然环境’来实现的。”
“中国的教育真的需要大家勇敢一点。”萧望野说,“不要过多考虑自己的利益。要大家一起呼喊,要有信念。我们在这里做教育研究,外面的人会被吸引,很多人也会有为中国教育做些事情的愿望,但很多人没能长期坚持下去,这只能说,他们的愿望不够强烈。”
萧望野在学校那棵木棉树下讲这番话时,树丫顶上的夜空,清晰得可以看清每一个星座。她曾对山外的人说,这里能看见整条银河。他们说,这怎么可能呢?
她曾经是学校的“叛逃者”。
萧望野上小学的时间是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家乡四川宜宾的小学里,她的学习成绩很好,还乐于学雷锋,但当她真把时间用来学雷锋的时候,老师却到家里告诉她的妈妈,你的小孩不好好学习,把心思花在和学习无关的事情上。
萧望野感到疑惑,而且,疑惑快速增长。读到小学三年级时,她固执地认为,自己应该离开学校了。
她不想成为某种她并不认同的教育目标的实现者。“学校把我当成动物和工具,在利用我,有不纯洁的动机,就好像一个人对我说‘你跟我合作,我们来欺骗这个社会,我给你糖吃’,而我决定不吃这些糖。”
这个小学生做了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退学。
萧望野多次用一个关于睡觉的隐喻来分析教育的好坏——在课堂上想睡觉的小孩,希望精神的世界得到保护,如果这个时候老师把孩子唤醒,这个孩子又适应了这个老师的话,这样的小孩在他的一生当中都醒不过来。而当时坚持要睡觉的小孩在他成年之后却会醒过来。“像我这样,想睡,却被唤醒,但又适应不了的孩子就会有非常强烈的和社会做斗争的力量,我就是这样的孩子。”
十几岁时,萧望野离开家乡,去往北京,在圆明园画家村里与艺术家探讨艺术,并思考人类。这个喜欢雷诺阿、凡·高、塞尚、高更的女孩开始从事关于乡村的工作,也就有了后来从北京到广西的教育研究活动。
在那美和山村里的孩子一起度过幼儿园生活之后,萧望野的孩子光之奴去某所农民工子弟学校读小学。
“光之奴”这个名字会让人感到奇怪,萧望野解释,意思是“光明的仆人”。光之奴在学校里被同学开玩笑称作“光头”,萧望野对孩子说,这没什么,每个人都会有外号,不叫你“光屁股”就行了。在她看来,家长的幽默与超然也能够让孩子幽默与超然。
“那里的学费很便宜,孩子也很高兴。”孩子具体在哪里读书,她不愿意说,她并不乐意过多地谈论个人生活:她以及和孩子有关的人,包括孩子的父亲。
“之奴其实可以去非常好的学校,不少人邀请我去深圳办学校,我的孩子会受到所谓的很好的教育,但那都不是真实的。真实的是我现在的生活;真实的是内在的力量和信心,对精神世界的信任;真实的是我是什么样的人,这会给我的孩子带来真正的成长,也会给我带来真正的快乐。”
未来,萧望野说她也许会继续待在这里,也可能去往他乡,决定这些的,她觉得是命运。
晚上九点,萧望野走过布满星光的木棉树,按时回屋休息了。周遭静谧至极,山村里大多数人都已睡去。白天,他们都会说:“萧老师是一个好老师,学生喜欢她,我们也喜欢她。”然而几乎没人真正了解,这个老师究竟要做什么。
对于卢安克,大家也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那次离开中国前,他和学生拍摄了一部全由乡间孩子真人演出的“电视剧”。
卢安克自己创作了充满魔幻色彩的剧本。在剧情中,孩子们从“魔法世界”进入“技术世界”,最后“解放世界”。
卢安克的同胞哥哥卢安思是摄影师,在收到弟弟求助的电邮后,正在泰国工作的他来到中国的大山里,并从当地电视台借来设备,协助弟弟拍这部“电视剧”。
孩子们刚开始对剧本不感兴趣,他们最希望做的,是像香港武打片那样表演武功。卢安克不喜欢香港片的暴力,但为激起孩子们的兴趣,他还是设计了一些武打镜头。
拍电视剧的过程并不轻松,学生不认真,道具很容易被破坏。“电视剧”拍完之后,卢安克和哥哥并不满意最后的成片。但孩子们看了片子之后很惊奇,并为自己当初的不认真感到后悔。
卢安克觉得学生会从中获益,“重要的是,这些孩子应该多进行文化创造活动,只有创造才能获得力量”。
发掘人的创造能力,正是卢安克教育研究的重要部分。“我做事情的大方向是和华德福教育一样,但是具体做法不同。”
华德福教育是由德国教育家鲁道夫·施泰纳创立的一种教育体系,强调从头、心、手整体出发,培养和谐完整的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贝娄甚至说过,如果他有一个学龄孩子,一定送他去华德福学校学习。
卢安克和哥哥卢安思是一对双胞胎,两人小时候性格孤僻,不愿意和人接触。周围的环境对兄弟俩并不包容,许多孩子看不起他们,他们为此而自卑。
为了两个孩子,他们的父亲放弃了收入优厚的工程师工作,到一所华德福学校当老师,然后用华德福的方法教育儿子,使他们受益。
十几年前,卢安克来到中国留学。
他选择农村作为他研究教育的基地,他认为,农村孩子可借助的力量较少,从他们身上更能看到教育的实际作用。另外,亲近自然的孩子比在钢筋水泥森林里生活的孩子更有想象力。
在东南大学无法获得接触农村的机会时,他转学到了广西农学院。
在山村的小学里,喜欢戏水的学生想建一个游泳池。卢安克就让学生自己去考察,然后一起设计游泳池。
等到动工的时候,许多家长来帮忙,这么一来,学生什么也不敢做了。
“这里的大人认为不可能和小孩在一起工作”。卢安克觉得这样失去了做这件事情的意义,便不让家长继续参加。大人走了,孩子自己来做剩下的工作。这样的情形才是卢安克希望看到的。
“我们是为了做,而不是为了有结果。”卢安克说。
东兰县一所中学的老师韦天钰参与了这个游泳池的修建,他为卢安克对孩子动手能力的要求感叹不已。“我们是想着怎么快点做好,他是想着孩子的感受。”
刚刚过去的暑假里,卢安克住到了深山里学生的家中。这段宁静的日子里,他翻译了施泰纳的一些教育理论著作。卢安克已经写作和翻译了许多关于华德福教育的书。他把这些文字放到了自己的网站上,供人免费下载。
卢安克并不认为自己有多大力量。“我讲课时,学生随意打闹,似乎没有意识到我的存在。”他甚至为此感到困扰。
卢安克兄妹四人,只有弟弟生活在德国。弟弟的工作是策划和组织大型晚会,他是全家挣钱最多的人。
哥哥卢安思是绿色和平组织的成员,他并不参加所有绿色和平的活动,按卢安克的话来说——“只有那些会被特警抓起来的”,他才参加。
2003年年初,卢安克收到了哥哥的一封电子邮件:“1月24日,我在英国南安普顿登上了绿色和平组织的‘彩虹勇士号’。我的工作,除了像其他人一样要攀爬到船上表示对战争的抗议之外,还担负着现场摄像任务。我们直接把船开往南安普顿的马奇伍德军港去。准备攻打伊拉克的美国和英国军队正从这个港口运送武器前往波斯湾,其中有军用直升机、卡车和坦克……”
“这件事情很危险,但也没有伊拉克人活得那么危险。”卢安克支持哥哥。
卢安克的妹妹在非洲,受聘于纳米比亚的一所幼儿园,领着一份并不高的工资。
卢安克最想念的是自己的父母。
在德国汉堡,清晨,卢安克的父亲会按时起床,吃完老伴做好的早餐,听一段古典音乐,吹上一会儿黑管。在教堂里,卢安克的父母会和别人谈起在中国的儿子。
从前,卢安克的父母对孩子也有一些传统的期望,就像大部分家长一样,希望卢安克能有好的收入,有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有自己的房子和自己的家,生活在美好舒适的环境中不用受苦。
“幸好有一天他们发现,‘为了满足他们的愿望’,‘为了实现社会保险’等目标,会让我失去理想。在发现我活在世界上不是为了把个人生活安排得更好时,他们就放弃了对我的所有期望。这给了我自由,使我能做一些我认为在世界上需要有人做的事。”卢安克说。
之前,卢安克还在另外一个山村时,村民们曾请他去求政府拨款帮他们建桥。“他们以为我是个重要人物,只要我说句话,政府就会满足我的愿望。不过,我是走路的,政府官员是坐空调车的,我怎么去找他们?过了几年,倒是政府的人来请我帮他们找钱,但是我也不懂得怎么找,只好拿自己的稿费给他们。”
村民几乎已忘了他是一个外国人,他们像对待村里人一样,和他打招呼、聊天、开玩笑。
在小学里,学生见到卢安克,经常一起扑到他身上。每到周末或是假期,冷清的校园会让卢安克感到不安,他会住到学生家里去。刚过去的暑假,他只在学校里住了一个晚上。
“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家,我也需要家。我的家(学校)比较大,我的孩子(学生)比较多。他们的父母外出打工,多年不回家,他们也需要一个可以暂时替代他们父母的人,他们那么靠近我,就是因为没有父母可以靠近。”
很多人觉得山村生活很苦,但卢安克却觉得舒服。头一年,卢安克回到德国,吃东西拉肚子,很久才适应过来。他已不习惯家乡的生活。
大城市的生活对卢安克似乎诱惑不大。“大城市一方面是花费太贵,在德国一个月要花相当于几千块人民币的钱,而我在这每个月花不到一百块。另一方面是不自由,不能尽情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
卢安克不是个愿意袒露内心的人,他敏感而腼腆,声音柔和舒缓,对人充满善意。“我从来没见过他发脾气。”山村里的一位朋友这样说。只有在讲述他感兴趣的事情,比如他的教育心得时,他才会滔滔不绝。他认为天地间存在着“真理”,这种“真理”类似老子的“道”,他最感兴趣的是研究能够通向“真理”的教育。
卢安克要求自己教书不领工资,一个原因就是希望自由。“我只做我自己感兴趣的事,拿工资的人是不自由的。”
他曾经拿过工资。他在汉堡美术学院读书时,学的是工业设计专业,但他发现这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做工业设计方面的工作需要很多时间来表现自己,向别人证明自己的能力。他说他“做不了这样的事情”。
2004年,卢安思来广西看卢安克,卢安克送哥哥到南丹去坐车。在半夜返回山村时,卢安克乘坐的农用车突然轮子脱落,车身从几十米的山坡翻滚而下,在只差两米就要掉入红水河时,被一棵巨树挡住。
卢安克和司机从变形的车身里爬出来,发现另一个朋友不见了,他们在暗黑的河边摸索了很久,最后在车底发现了他,朋友的脖子卡在车轮下,已经没气了。
走了很长的山路,他们才找到一处透着灯光的屋子。司机去寻求支援,把卢安克留在屋里。不知情的主人请卢安克进屋看电视,他一动不动,脚上的一道大伤口正不断流血,他告诉主人,自己不看电视,他的朋友刚才死了……
这次车祸让卢安克的脊柱压缩了三厘米。
2006年,卢安克注册的德国鲁道夫·施泰纳教育友好协会驻中国办事处执照到期,他的中国居留证也到期了。为方便留在中国做研究,他打算加入中国国籍。根据有关规定,他的申请没有获得批准。原因包括“要有中国籍配偶”“需在国家一级单位工作四年以上”,等等。
一些媒体为卢安克打抱不平,但一向心平气和的卢安克认为这事没那么严重,“不符合条件,没被批准很正常。我只想试一试,不行就算了。”
2007年4月开始,卢安克获得了中国共青团国际志愿者的身份,成了广西唯一的国际志愿者。
一个德国人在广西的贫困山区里待了十年,他会一直待下去,从青年、中年直至老年吗?
卢安克说他以前不会考虑未来,现在也不会。但他显然不想离开中国广西的这个小山村。“我喜欢这里的孩子,还有我的研究,离开这个地方就等于没我自己了。”卢安克低声说。
他还是会怀念德国。“那是另一个世界,是我的另一条生命。”
他曾是德国一家帆船俱乐部的成员,到现在已有十几年没碰过帆船了,那时他还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来中国前,他把自己的那艘帆船卖掉了。
卢安克曾冒出一个想法,希望能做2008年北京奥运会帆船项目的志愿者。他当过教练,和帆船世界冠军比赛过,但一想到记者会汹涌而来时,他又担心了。
“志愿者的事……还是算了吧。”也许,平静的生活才更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