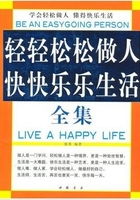两位石灰商和他们的陪伴者走进阿贝·波特森小姐的领地,他们的陪伴者(他隔着柜台间的半截门,用一种自家人的口气介绍了他们和他们冒充的行当)向这位小姐提了个颇有形象性的要求,请她在“雅座”里给生上“一小点儿火”。阿贝小姐一向是乐于对合法的当局表示支持的,便吩咐鲍布·格里贝利侍候这几位先生到那个僻静的去处,立即生火掌灯。光着两只胳臂的鲍布接到使命,便点个纸捻子在前面引路,迅速地完成了任务,于是当他们刚一跨进它那好客的门槛,“雅座”似乎是从黑沉沉的睡眠中一跃而苏醒过来,温暖地拥抱着他们。
“他们这儿的热雪利酒挺不错呢。”探长先生说,向他们介绍一点当地风味。“也许你们二位也喜欢来它一瓶?”
回答是:当然。鲍布·格里贝利从探长先生那儿接到指示,便欣然离去,那心情是从他对法律威严的崇敬中相应产生的。
“可以确定,”探长先生说,“我们从他得到报告的这个人,”用他的大拇指朝肩后伸伸,表示说的是赖德胡德,“过去一段时间里,在你们的石灰驳船的事情上,给另外那个人散布过恶言,所以人家都躲着那个人。我不是谈他这样做有什么意义或是能证明什么,但这是确定的事实。我是从我的一位女性熟人那里最初听说的,”他又把大拇指往肩后一伸,含糊地指阿贝小姐,“她离这儿不远,就在那边。”
那么探长先生对他们今晚的来访,并不觉得怎么突如其来啰?莱特伍德暗示地问他。
“那么,您明白,”探长先生说,“这是一个要采取行动的问题。而如果你不知道该如何行动,行动便毫无用处。你还是稳住别动好。关于这件石灰的事情,我当然认为很可能是这两个人当中哪一个干的;我一直有这种想法。但是我还是不得不伺机而动,而我一直不曾有幸得到个有利的机会。我们从他得到报告的这个人却抢了先,并且,如果不遇到阻碍,他会加劲儿干下去、抢上个头一名的。那个抢到第二名的人也可能很得点儿好处,我不说谁可以或者谁不可以争取一下那个位置。我反正尽我的责任,不管怎么,尽我所知,尽我所能吧。”
“作为一个石灰商,我说——”尤金开始说。
“在这一点上没人比您更有发言权了,是吗?”探长先生说。
“希望如此,”尤金说,“在我以前,我父亲是个石灰商,在他以前,我祖父也是——事实上,我们家几代人都是埋在石灰里,一直埋到头顶心的——我要求说一句,如果这批遗失的石灰能够找回来,而同时不把它跟这笔石灰生意(我像看重我的生命一样看重它)当中的某位著名人物的某个年轻女眷牵涉进去,那么,我认为对于从旁协助的人们,也就是说,对于烧石灰的人们,可能是个更加可以接受的做法。”
“我也认为,”莱特伍德哈哈一笑,把他的朋友推向一边,说,“顶好能够如此。”
“只要方便,先生们,定会这么办的,”探长先生冷静地说道,“就我来说,是毫无意思给那方面造成任何不幸的。的确,我也为那方面感到难过。”
“那方面还有个男孩子吧,”尤金指出,“他还在吗?”
“不在了,”探长先生说,“他不干这一行了。对他另有安排了。”
“那就剩下她一个人了?”尤金问。
“就剩下,”探长先生说,“她一个人了。”
鲍布又出现了,手执一只热气腾腾的酒罐,他打断了他们的谈话。但是,虽然那酒罐正喷出一股浓香来,它的内容却还没有获得“六脚夫”在这类重大场合下,凭它高超的绝招儿,所要使之具有的那种美妙滋味。鲍布左手拿着一只前述那种形式的尖帽子形铁酒壶,把罐子里的酒全都倒进这只壶里去,又把它的尖头深深插进炉火里,让它在那儿呆上几分钟,趁这时间他消失,然后又出现,带来三只亮晶晶的玻璃杯。他把杯子放在桌上,弯腰向火,意识到自己所负责任之重大,凝神注视着袅袅上升的蒸气,那态度实堪嘉奖,在这操作过程的一个特定瞬间,他停止注视,一把抓起铁酒壶,灵巧地一转,让它发出一声轻轻的咝咝的响声。然后便把那内容重又注入酒罐中;他把三只光亮的酒杯轮番在酒罐喷出的热气上烘一烘;这才一一斟满它们,然后,便凭良心静待他的这几位同类对他的称赞。
他们称赞了他(是在探长先生说了“为石灰生意干杯!”这个适时的祝酒词之后),于是鲍布退场,去向柜台间里的阿贝小姐报告客人对他的表扬。这里不妨悄悄地承认:他不在场时,房门是紧关着的,似乎没有丝毫理由需要煞费苦心去维持这个关于石灰的虚构故事。只是因为探长先生认为这故事编得异常令人满意,而且充满着神秘意味,所以他的两位客人便谁也不去提出异议。
这时窗外传来两下叩击声。探长先生匆忙再喝下一杯酒,给自己增加些御寒力,脚下无声地溜达着走出门去,脸上还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好像是走出去看看天色,或者是观察一下气候似的。
“这变得有点儿可怕了呢,莫蒂默,”尤金低声说,“我不喜欢这个。”
“我也不喜欢,”莱特伍德说,“我们去不去呢?”
“既来之,则安之。你必须搞个水落石出,而我不愿离开你。再说,那个孤单的黑头发的女孩子让我念念不忘。我们只不过是上次看过她一眼,可是我今天晚上总好像是看见她坐在火盆边等着的样子。当你想到那个女孩子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她既有点儿像个奸细,又有点儿像个扒手呢?”
“颇有点儿觉得,”莱特伍德回答,“你呢?”
“很有这个感觉。”
他们的陪伴者又溜达着走了回来,向他们报告情况。他的报告除去各种石灰灯火的光影之后,大意是:老头儿划船出去了,大约是按老规矩去河上守望了,刚才涨潮时他应该回来的;不知道因为什么错过了,那么,按他通常夜晚活动的习惯来看,在下次涨潮前不能指望他会回来,要不就是在一个小时左右之后;她的女儿,透过窗子看去,好像在急切地盼望着他,因为晚饭虽还没烧,却摆好在桌子上,随时可以下锅的;下次涨潮大约在半夜一点钟,现在才刚刚十点;除了监视和等待之外别无他事可做;当探长先生做现在这个报告的时候,那位告密者正在进行监视,但是两颗脑袋总比一颗强(尤其当第二颗是探长先生的脑袋的时候);因此这位报告者打算也去参加监视。并且,鉴于在这样一个寒风凛冽的夜晚,还不时地要下一阵冰雹,去趴在一只拖上岸来的船下边,业余爱好者未免会感到无聊的,因此报告人在结束时建议,两位先生最好是,哪怕暂时,留在目前所在的地方,这里没有风雨,而且暖和。
他们无意反对这个建议,但是他们希望知道,一旦需要时,去哪儿和监视者们会合。与其相信口头的描述——这样很可能出错——尤金(他今天心头的个人烦恼事来得比平时少些)情愿跟探长先生走一趟,看清地点再回来。
在倾斜的河岸边,在堤道上又黏又滑的石块中间——不是“六脚夫”所在的那条特殊的堤道,那里有一处专门供船停靠的小码头,而是另一条堤道,比那里再远一点,和被告者的住处,那老旧的风磨房距离很近——有几条船,其中有些是系泊的,已经开始漂在水里了;另外一些是拖上来摆在潮水达不到的地方的。尤金的伙等候父亲伴钻进后边这些船当中的一只底下,就隐没不见了。当尤金看清了它和其他船相关的位置,并且确定他不会找不到它之后,便转过眼去望着那房子,人家已经告诉他,那孤单的黑头发的女孩子就在那间房子里,正坐在火盆前。
他可以看见火光透过窗户在闪亮。也许是这火光吸引了他,要他走上前去看一看吧。也许他出来正就是怀着这个目的。河岸的这一带杂草丛生,走近这间房子并不困难,脚下也不会有任何响声:只须爬上一块大约三四英尺凹凸不平、相当坚硬的泥地,再踏在杂草上走近窗下就行了。他就这样到达了窗下。
除了炉火之外,她没有其他光亮。那盏没有点燃的灯放在桌子上。她席地而坐,眼望着火盆,一只手托着腮。她脸上有一种隐约的光亮或闪烁,他最初把这当做摇曳不定的火光;然而,再看一眼,他看出她在哭泣。随着火光的时明时灭,他面前呈现出一幅凄凉孤独的景象。
这是一扇只有四块玻璃的小窗户,没挂窗帘;他选择这扇窗子,因为旁边的一扇大窗是挂上窗帘的。他从窗子里看见了这个房间,看见了墙上那些轮番被风掀起又缩回的关于溺死者的告示。他只对这些告示稍稍地一瞥,却长时间地、目不转睛地望着她。她的身影构成一幅色彩浓郁的画面,尽管凄凉而孤独;她面色棕红,头发闪着光,坐在时明时灭的火光前哭泣。
她突然立起身来。他非常安静地立在窗外,因此确有把握不是自己惊动了她,所以,只是从窗口向后移了移,站在窗旁墙壁的阴影里。她打开房门,惊慌地说道:“爸爸,是你叫我吗?”又叫一声:“爸爸!”倾听了一会,又叫道:“爸爸!我好像听见你刚才叫过我两声!”
没有反应。等她返回到门口了,他跳过河岸,在泥泞中,从靠近那隐藏的地方走过,向莫蒂默·莱特伍德走回去。他对莫蒂默述说了他所看见的这女孩的情况,也说到这情景是怎样一点不假地变得非常可怕。
“如果真正的犯人像我一样做贼心虚的话,”尤金说,“他的日子一定非常不好过。”
“这是神秘感的影响。”莱特伍德提出他的看法。
“把我搞得又像是地窖里的盖伊·福克斯盖伊·福克斯,1605年一次天主教密谋案件中的主犯,他藏在地窖里,想把主教炸死。从前每逢11月5日,英国有焚烧此人肖像的风俗。又像是个钻进地下室的贼,”尤金说,“给我再喝点那玩意儿。”
莱特伍德给他又斟了些那玩意儿,但是它已经冷了,喝来已索然无味。
“呸,”尤金把酒吐在炉灰上说,“一股子河水味道。”
“你对这条河里的水味那么熟悉吗?”
“我今天晚上好像很熟悉,我觉得我似乎半截身子淹在河里,灌了半加仑水进去了。”
“这是地点的影响。”莱特伍德提出他的看法。
“你今天晚上学问大得很嘛,你跟你的这些影响都很有学问嘛。”尤金回答他,“我们在这儿还要待多久?”
“你想还要待多久?”
“要由我选择,我说只待一分钟,”尤金回答说,“这‘快乐的六脚夫’并不是我所知道的顶快乐的家伙。不过我想,我们最好还是留下,等到半夜的时候,他们把我们跟另外那些可疑的人物一齐赶出门去的时候再走。”
说着他便把火拨燃,坐在火炉的一边。钟敲十一点,他假装很有耐心地保持着安静。然而渐渐地,他的一条腿在动弹了,接着另一条也在动弹,接着一只胳臂在动弹,接着另一只胳臂在动弹,接着是下巴颏儿动弹,接着是背脊动弹,接着是额头动弹,接着是头发动弹,接着是鼻子动弹;接着他便伸长身子斜靠在两把椅子上,哼哼唧唧;接着便一下子跳了起来。
“这地方尽是些看不见的、魔鬼一样在动的小虫子。我浑身上下又是痒痒又是痛。我好像在精神上犯了最卑劣的盗窃罪,执法如山的迈密登迈密登,希腊神话中跟随阿契里斯去特洛伊作战的塞萨利人,在英语中作为盲目执行他人命令的人的代称。们正在跟踪追捕我呢。”
“我也是一样地糟糕。”莱特伍德说着坐起身来面对着他,头发乱蓬蓬的,他已做过几个奇妙的动作,在此过程中,脑袋一直处于全身的最低位置。“这种心神不定在我是早就开始了。整个你出去的时间,我就好像格列佛遇到利利普特人利利普特人,英国作家斯威夫特著《格列佛游记》里“小人国”中的小人。对他开火一样。”
“这样不行呀,莫蒂默。我们必须出去透透气;我们必须去跟我们那位朋友和老兄赖德胡德待在一起。咱俩定个合同吧,这样我们就精神镇定了。下一回(为了求得我们心头的平静),咱们不去捉罪犯,而是自己来犯罪吧。你保证同意?”
“当然!”
“说话算数!让蒂平斯当心点。她的性命危在旦夕了。”
莫蒂默打铃叫人来算账,鲍布过来跟他办理这项事务。这时尤金以他那漫不经心的态度胡扯着,问鲍布是否愿意在石灰生意里找个位置?
“多谢,先生,不要,先生,”鲍布说,“我在这儿的位置挺好,先生。”
“假如哪天你改变了主意,”尤金回答说,“到我场里来,你随时都可以在石灰窑上找到个空缺的。”
“多谢,先生。”鲍布说。
“这位是我的同伙,”尤金说,“他管账,还管发薪水。我这位同伙的格言从来是:活儿干得好,工钱不会少。”
“真是一句好格言,先生们。”鲍布说,一边收下小费,用他的右手朝下按着他的脑袋,鞠了一个躬,那姿势和他用抽酒器从啤酒桶里抽出一杯啤酒来的姿势非常相像。
“尤金啊,”又只剩下他俩的时候,莫蒂默非常开心地笑起来,喊他一声说,“你怎么能够这么滑稽呢?”
“我就是个滑稽脾气,”尤金说,“我就是个滑稽人。天下无事不滑稽。走吧!”
莫蒂默·莱特伍德心头掠过一个想法:在方才这半小时左右的时间里,在他的朋友身上发生了某种变化,说它是强烈地表现了他朋友身上所有一切最不受拘束、最漫不经心、最满不在乎的东西,也许是最为恰当的说法。他对他是十分熟悉的,而他这时却在他身上发现了某种新出现的、过分的、暂时还是令人困惑不解的东西。这种想法在他心中一闪即逝;但是过后他又曾回想起它来。
“她就坐在那儿,你瞧。”尤金说。他们站在堤岸下,堤岸在狂风中呼啸作响,好像要被撕裂一样。“那就是她的火盆的亮光。”
“让我去窗口上悄悄望一眼。”莫蒂默说。
“不行,别去!”尤金抓住他的手臂,“顶好别去看她出丑吧。到我们诚实的朋友那儿去。”
他引他来到监视岗哨上,两人都蹲下身子,爬进船下边。这地方和呼啸的狂风与毫无遮掩的黑夜相比,倒是个比事先想象的更好的栖身之所。
“探长先生在家吗?”尤金低声问道。
“我在这儿,先生。”
“我们那位额头上出汗的朋友是不是在那一头?很好。有什么情况?”
“他女儿出来过,以为她听见他的叫声了,要不这就是个信号,通知他躲开。很可能是这样呢。”
“还可能是唱大英帝国的国歌呢,”尤金喃喃说,“但是它又不是呀。莫蒂默!”
“在这儿!”(他在探长先生的另一边)
“现在有两项盗窃罪了,还有一项捏造罪!”
尤金这些话显示出他的情绪非常低沉,后来便没有再出声了。
在很长的时间里,他们都没有出声。到涨潮的时候了,河水离他们比早先更近了,河面上的喧闹声比以前更多了,他们也更多地在倾听着。倾听船上蒸汽明轮的转动声,铁链条的叮当声,辘轳的吱嘎声,有节奏的划桨声和过路船只的甲板上狗的凶猛狂吠声,它们似乎嗅出了他们这几个躲着的人。夜色并不是那么黑暗,除了来往滑过的桅杆上和船头上的灯光之外,他们还能辨别出灯光下那影影绰绰的庞然大物;时而会有一只鬼似的驳船;张着又长又黑的帆,仿佛伸出一只手臂在威胁人,突然在他们的面前出现,又驶过去,消失在黑暗中。在他们监视的这段时间里,附近的河水老是被远处的某种冲击搅动得起伏不停,他们往往会把水中这些溅泼声和击打声,当做是他们躲在这儿等候的那只船靠岸来了,要不是那位非常熟悉这条河的告密者待在他的地方一动不动,他们几次三番都已经跳出来了。
在他们的下风处,许许多多市区教堂的钟声都随风飘失了,但那些上风处的钟声却告诉他们,现在是一点——两点——三点。没有这个帮助,他们将只有靠河岸上越来越宽的那条黑黑的水迹所记录的潮水退落情况,和一英尺一英尺地从河水中露出来的铺石的堤道,才能知道夜色消退了多少。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鬼鬼祟祟变得愈来愈没有必要了。仿佛是那个人得到了风声,知道有人在对付他,或者干脆已经逃跑了。他的行动可能是早有预谋,好为他赢得十二个小时的时间,使他不致落进他们的手里。那位花费了自己额头上的汗水的诚实人变得不安起来,颇含辛酸地抱怨说,人家动辄就会欺骗他——欺骗他这个凭劳动吃饭的正派人!
他们这个藏身处是选择好既能监视河面,又能监视那所房子的。自从那女孩以为她听见父亲叫她以后,再没有人出入过。没有人可以出入而不被发现。
“可是,五点钟天就亮了,”探长先生说,“到那时候我们就会被人家看见。”
“听我说,”赖德胡德说,“你们觉着怎么样?他可能溜来溜去划了几个钟头了,只是硬挺住在两三座桥中间来回划,不回家来。”
“那你又怎么想法呢?”探长先生不在意地、但却也是不表赞同地说。
“他可能现在还在那儿来回划着呢。”
“那你又怎么想的呢?”探长先生说。
“我的船就停在堤道旁边那堆船中间。”
“那你对你的船又怎么想法呢?”探长先生说。
“要是我划船出去到处看看怎么样?我知道他的路数,也知道他可能蹲在哪些他喜欢蹲的角落里。我知道在潮水的这段时间他习惯待在哪里,另一段时间他又待在哪里。我不是跟他合伙的吗?你们谁也别露面。你们谁也别挪动。我不要人帮忙就能划出去;要是人家瞧见我,我反正一天到晚在这儿的。”
“你这个主意还不算太坏,”探长先生想了一想之后说,“试试吧。”
“等一会儿。咱们先商量好。要是我找你们,我就划到‘六脚夫’附近,给你们打个呼哨。”
“我尊贵而勇敢的朋友的海事知识当然不是我所能加以挑剔的,但是假如我可以擅自向他提个建议的话,”尤金极其慎重地插进来说,“很可能,打呼哨会令人感到神秘,并且招致怀疑吧。我相信,我尊贵而勇敢的朋友将会原谅我这个局外人提出一个我认为是为了我们国家和这座房子的利益所必须提出的意见。”
“这是那另一位先生呢,还是莱特伍德律师?”赖德胡德问道。因为他们是俯着身子或是躺下说话的,互相看不见面孔。
“作为对我尊贵而勇敢的朋友的问题的回答,”尤金说,他是仰面朝天躺着的,用帽子遮着脸,他认为这种姿态最能表现出是在进行监视,“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回答(因为这和为公众服务毫无相悖之处),刚才的口音是那另一位先生的口音。”
“你们的眼力够好的吧,是吗,先生?你们的眼力都够好的吧,是吗?”那告密者问道。
都很好。
“那么要是我划到‘六脚夫’下面,往那儿一停,就没必要打呼哨了。你们会看出,那儿有个什么黑点子或者其他的东西。你们就知道是我了,你们就沿那条堤道走过来。都懂了?”
“都懂了。”
“那就开船了!”
顶着从侧面吹来的刺骨寒风,他马上就摇摇晃晃地跨进了小船;一会儿工夫,他已经离岸了,正沿着他们所在的这边河岸向上游缓缓划去。
尤金用肘支撑着身体跟着他向黑暗中望去。“但愿我尊贵而勇敢的朋友的那只船,”他重新躺下,用帽子盖住脸,喃喃自语地说,“能够慈悲得翻个底朝天,让他淹死掉!——莫蒂默。”
“我尊贵的朋友。”
“三件盗窃罪,两件捏造罪,还有一件夜半谋杀罪。”
但是,尽管良心上压着这些沉重的负担,尤金在事情最后出现的这点小变化的影响下,有些儿快活起来了。他的两个同伴也是如此。最重要的是发生了变化。心头的悬虑似乎有了一个新的希望,似乎刚才又从头开始。又有了点东西好让他们寻求了。他们三个人便都更加留意地守望着,因而也感到这个地点和这个时间所给予人的难受的影响已比较不那么沉重了。
一个多小时已经过去,他们甚至在打盹了,这时三个人当中的一个——都说是自己,都说他自己没有打盹——发现赖德胡德划着船在约定的地点出现了。他们一跃而起,从隐蔽处走出来,向他走去。当他看见他们走过来,便把船靠着堤道停住;于是他们站在堤道上就可以跟他低声交谈,沉沉入睡的“六个快乐的脚夫”那庞大的阴影正笼罩住他们。
“我真搞不清是怎么回事了!”他说,眼睛瞪着他们。
“搞清什么事?你看见他了吗?”
“没有。”
“那你到底看见什么了?”莱特伍德问。因为他非常奇特地瞪着眼睛在瞧他们。
“我看见他的船了。”
“不是空船吧?”
“不,是空船。还有呢——船在顺水漂着。还有呢——一只桨不见了。还有呢——另一只桨卡在桨撑子上折得只剩一小节儿了。还有呢——船让潮水冲进两排驳船缝缝里卡牢了,还有呢——他这回又走运了,他要没走运那才叫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