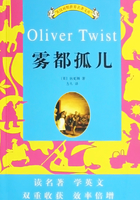我们的支教活动即将结束了,每个人都得到了渡口中学师生们的好评。临走前一天晚上,我买了一只花篮去看望朱鹃,她房间里的灯是黑的,我心想她可能外出了,就在楼梯口的台阶上枯坐,一直等到将近12点,她房间里的灯突然亮了,原来她其实一直在家呀。我上去敲门,门开了,她好像刚刚睡醒,穿着睡衣。我走过去将她揽进怀里,把头埋在她的肩膀上哭了。朱鹃也泣不成声。我们就这样在泪水中疯狂地做完了这辈子的最后一次爱。完事后,她问我吃饭了没有,我说吃过了。她说她还没有吃,让我陪她吃最后一顿晚餐。我坐在台灯下看书,她在厨房切菜,不知什么时候她走了进来,将一截血淋淋的指头放在了我的书页上……
我在惊慌中一把将书掀在地上,推开朱鹃,逃出了那间房子,在漆黑的大街上狂奔了数百米。我不敢回头,不敢回忆,更不敢回来。
可是现在我回来了。
我将头埋在浴缸里,憋得快要窒息时才猛地冒出水面,水花四溅,打湿了缸边的纸鞋。我赤身裸体地爬起来,望着雾气蒙蒙的镜子,我知道,我在那里面,可是我无法看见我。
肚子又剧烈地疼了起来,将近三点钟我才迷迷糊糊地入睡。疼痛迫使我将原来的计划做了些调整,我没有下楼去吃东西,也没有心情和力气给朱鹃打电话,我想还是先把这该死的病治好后再和她联系吧。
与十年前相比,樊城的变化是惊人的。早上走在街上,我觉得自己完全置身于一座陌生的城市,我甚至搞不清楚渡口中学在哪个方位,一想到我要见的人也许是一个陌生人也说不定,心里面就七上八下起来。我就近去了街边的一家职工医院,挂号,看医生。医生轻描淡写地询问了一下我的病情,当他听说我怀疑自己乱吃东西也许肠胃坏了时,就很肯定地说道:那就是了。他给我开了些消炎药。我取了药,出来站在街边望了一会儿人群,又端详了半天手里的药片,随后去小卖店买了瓶矿泉水把药喝了,打算回宾馆休息。在来樊城的路上,我曾通过原渡口中学的教导主任陈建国打听到了朱鹃的住宅电话,这家伙当时居然没有听出我是谁来,后来解释了半天他才恍然大悟,连声答应帮忙查查。我坐回到车里,从包里面找出电话簿,心怀忐忑地拨通了陈建国给我的那个号码。没人接。等我回到宾馆躺在床上时,手机响了。我问是谁?她反问我是谁。我心里一紧,“是我,张望,”我尽量平静地回答道。
“张望,张望是谁?”女人问,语气漠然。
“那么,你不是朱鹃?”我失望地说道,“我想找朱鹃说话。”
“朱鹃?”对方有些警觉,顿了一下,问道,“刚才,你说你叫……张望?你找朱鹃干吗?”
我解释道,“嗯,是的,我叫张望,是她的一个多年没有联系的朋友……”。未等我把话讲完,对方说了句“朱鹃不在”,挂断了电话。
我回味着电话里那个女人的声音,听上去似乎比朱鹃的当年声音要粗一些,还有些沙哑,尽管我们已经十年不见,但再怎么说,朱鹃的声音也不至于会变成这样陌生吧?肯定不是她,那么,她怎么会在朱鹃家里呢?难道她是朱鹃的亲戚或保姆么?但听口气好像都不像,那么,她是谁呢?
我从陈建国那里得知,朱鹃有过婚史,但婚后不久就离了。目前是单身,有个孩子,她早已不在农行上班了,现在自己开了家体育用品公司,去年夏天渡口中学还在她的公司买过几个篮球架和一些乒乓球牌呢。我有些后悔当时在电话里没有询问一下朱鹃公司所在的具体位置,这会儿再打电话问陈建国,他若知道我已经身在樊城,一定会被他缠上的,陈建国喜欢生性豪爽,爱交朋友,也好酒,当年我在渡口中学支教时,就经常被他拽到家里陪他喝几盅。为了不节外生枝,我只好作罢。
我让餐厅服务员送了点吃的来房间。肚子还是疼,没什么胃口,连烟也不想抽,我强迫自己吃了几口,但很快就吐了出来。莫非真的病了么?我担心发生这样的事情,但不详的预感却越来越强烈。我迷迷糊糊地躺在床上,带着对十年前的那场爱情的丝丝缕缕的记忆进入了梦乡。
醒来已是晚上了。银狐酒店位于繁华的闹市去,我的房间毗邻一座超市,对面是一家夜总会,霓虹灯闪烁,把花花绿绿的光斑投射在我的窗纱上,使黯淡的卧室墙面显得扑朔迷离。
我揉揉眼睛,抓起床头柜上的电话,又往朱鹃家拨了一次。还是那个女人接的,但这次她没有立马挂断,我听见她喊了声,“朱鹃,你的!”,接着是一阵叮叮当当、窸窸窣窣的响动,一个女人拉长腔调:
“喂——”
“朱鹃吗?我是张望,”我直了直身子,左手捂住小腹,低声下气地说道。
“张望?哦,你怎么来了?你不是死了吗?又超生成人了?难道人世间还有值得你念念不忘的什么吗?”朱鹃口气并不惊讶,也听不出任何激动的情绪,倒是充满了嘲讽的意味。若是放在以前,我肯定要暴跳起来的,但此刻,无论她怎么挖苦打击我,我都不会还嘴。谁让我当年抛弃人家,现在又来找她呢?
我不吭气。她好像气消了些,“说吧,你来找我干吗?”
“现在能见面吗?”我轻声问道。
“你在哪儿?”她迟疑片刻,问道。
我报了位置,补充道,“你说个地方,我开车过去。”
朱鹃犹豫片刻,说道,“那就八点钟吧。在人民广场左手边的那家‘星星索’酒吧碰面。你还没吃吧,要不,你先吃点东西?要不,你来我家吃,我做了‘夫妻肺片’,可是你当年爱吃的菜。”
我说不饿。我知道她在故意气我呢。不过,当年她做的“夫妻肺片”味道实在是好极了,但我记得她自己是不大爱吃的,只挑里面的花生米吃,难道她现在喜欢吃了么?
放下电话后,我暗自庆幸好事多磨。此前,我最担心的是怕找不到朱鹃,或者,找到了,她却出于怨恨不愿见我。现在我放心了,她不仅乐意见面,而且听口气好像还挺关心我呢。想到这里,我赶紧起来,强忍着肚腹之痛,梳洗,换上干净体面的衣衫,走了出来。
我先行到达酒吧,找了张相对隐蔽的台位坐了下来,点了杯冰咖啡,要了盘薯条,边吃边等朱鹃。我设想了见面后的种种情形,但又被自己一一否决,十年过去,我发现我对就要见面的这个女人完全丧失了把握能力,我甚至怀疑,等会儿她出现时我会不会真的认不出她来了。如果是那样,该有多么难堪啊。我紧张地在脑海搜索着她的音容笑貌,说服自己打起精神来,准备迎接即将迎面驶来的这辆时光之车。
三
时间过得真慢啊,吧台那边的那只黑色石英钟好象没有走动。疼痛、燥热,加上紧张,使我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水。不断有人出入于酒吧大门,那边有人在弹琴,很业余,琴声过后,又有人唱起了歌,依然很业余。可惜我身体不适,不然我倒有兴致过去弹奏一曲的,正好可以转移我此刻的无聊、虚弱和空虚。正这样想着,突然感觉有只手隔着真皮挡板在挠我头发梢,我扭身抬头,看见一个女人模糊的剪影,光线太暗了,我只好站了起来,“是你吧?”我没头没脑地这样咕哝了一句,觉得口气有些生分,便补充道:
“你好,朱鹃!”
“我能不好吗?”朱鹃穿了条绛灰色的毛尼裙,上身是件白色的V型领口毛衣,一条蓝色围巾随意搭在肩膀上,还是从前那种齐耳短发,但发梢烫了卷儿。她看上去很精神,气色也不赖,只见她随意拢了拢裙摆,在对面椅子上坐下,垂下眼睑看了看桌面上简单的杯盘,问道,“你打算就用一包薯条打发自己啊?也不准备给你的老情人点点什么开胃的东西,献献殷勤吗?”
我被她率性的口吻惹笑了,也松了口气,便将竖立在桌子中间的食品牌朝她面前一推,问道,“你想吃点什么?自己点。”
“开玩笑的,我吃过了。为了陪你,我就来杯‘哈根达斯’吧,”朱鹃拿起那块塑料牌,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各种酒水的名称和价钱,“先说好,今天我请客,等会儿买单时你别和我争。喂,你不想来两瓶啤酒么?”没等我回答,她就替我要了两瓶“太阳”啤酒。
“你气色不怎么好,很不好啊,”她看着我的眼睛,关切地问道,“没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吧?”
“还好。”我鼻子一酸,唉,老情人终归是老情人。我赶紧起身,借故去了趟洗手间,我用凉水浇了把脸,看见镜子里的那个人满脸倦怠,脸色呈暗灰色,没有一点生气。
回到座位上后,我脱下休闲西服,将高领衫的袖子捋了捋。朱鹃在抽烟,面前放了包女式“茶花”,我伸手拿过来抽出一根,放在鼻子前嗅了嗅,有些薄荷味。“不来支吗?”朱鹃笑道,“你还不至于把烟都戒掉了吧?”她来的时候看见桌子上的烟缸里是干净的,可能以为我真把烟戒了。我说没有戒啊,“今天的确是有些不舒服。”
面前的这个女人与我记忆中的朱鹃从外表上看是有很大差别的,这个女人成熟,自信,像洪水退下去以后的滩涂,少了些棱角,多了点圆润。她今年应该有三十出头了吧,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些。
“是不是觉得我老了啊,”朱鹃见我在端详她,就叹了口气,端起杯子碰了碰我的酒瓶,说道,“来,让我们为往事干杯!”
我喝了口酒,继续考虑着怎样打破沉闷的气氛,把话题引向那些神秘的来信。转念又想,才见面就说信的事,可能仓促了一些吧?我犹豫不决,肚子疼得更厉害了,放在桌沿上的手臂都微微颤抖起来。“我昨晚就到樊城了,”为了分散精力,我东扯西拉地说道,“樊城变化很大,我都快认不出来了。你这些年过得怎么样?”
“呵,你不是都看见了嘛,我很好啊,不好还会来见你?”朱鹃往后仰了仰身子,用右手捂住嘴巴打了个哈欠,然后双臂搁在桌面上,只见她十指交叉互相搅动,突然松开,用左手的大拇指呵食指拧了拧右手的无名指,使劲一扯,半截指头掉落在了桌布上。
我被眼前的这一幕吓呆了,浑身颤抖,差点叫出声来。朱鹃瞟了我一眼,没有理睬我的慌乱,只见她镇定自若地将那半截指头重新戴到了右手上,十指又恢复了先前的完好无缺。“这截指头是硅胶做的,再也没有痛感,可以随便用刀砍的,”她诡异地笑着,这样的笑容使我记忆中的那个女孩又像鬼魅般浮现了出来。
我大气不出地缩在角落里,留心着她的一举一动,刹那间,产生出一种自投罗网的绝望感,我想到当年落荒而逃的情景,不禁有些羞愧,羞愧中又夹杂着一丝恐惧,因为毕竟才刚刚见面,朱鹃就开始以这种方式来报复我了,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更恐怖的事情在等候着我呢?我背上沁出了一层冷汗,毛孔发紧,手脚冰凉。
朱鹃一直在留意着我表情的变化,她摁灭烟蒂,走到我身边,问我哪儿不舒服。我指了指下面,“肚子,”我说,“唉,我也说不清楚,反正是很难受,胃胀气……”。“我看看,”朱鹃做了个让我平躺下去的手势,“不知所踪、不知所往的疼,甚至不知所在的痛,是最可怕的,我体验过的。躺下吧,让我看看,说不定可以帮你找出准确具体的位置呢。”她一语双关地说道。
我见周围没有什么人走动,就移动了一下屁股,朝外面挪了挪身子,半躺下来,腿伸在座椅子外面。一只光滑柔顺的手就这样无所顾忌地伸进了我的衬衫里,并将我的皮带往下扯了半寸。
“是小腹吧,最好解掉皮带,方便我检查,”她像医生似地很在行地吩咐道。我有些难为情,虽然我们曾经肌肤相亲,但那毕竟那是十年前的事了。
见我自己不动手,朱鹃就“嗤啦”一下,一把拉开我的皮带扣,笑道,“又不是没见过的,还以为你是谁啊。”她伸张着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从我胸口逐渐按下去,每按一下,就问我一声“疼不疼?”我就“哎哟”一声,随着她越来越用力,我的叫声越来越大了。“这么欢快干吗?又不在做……嘘,小声点,不要让别人误会了,以为我在虐待你呢,”她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整个手掌用力挤压着我的腹部,边按边问,“这里?这里?”“都疼,”我冷汗直冒地嘟囔着。
折腾了半晌,最后,朱鹃的指头停在了我右腹下方,她使劲按了一下,接着马上松手,再按,再松手,连续试探了几次后,她问有什么感觉,我说,你一松手就非常痛。
“那就是了,”朱鹃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吩咐我起来穿衣服,“马上去医院,很有可能是急性阑尾炎。”
“你能确定?”我束了皮带,扯着衬衫下摆,拿起包,招呼服务员过来买单。
“我们打个赌吧,如果是阑尾炎,你能赌什么?”朱鹃推开我的手,递了张一百元的钞票给服务生,“说啊,你赌得起什么呢?”
我说,“如果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那就一言为定,”她伸手和我握了握,我才想到见面后我们还一直没有握过手呢。
朱鹃说对了,果然是急性阑尾炎。再晚一点,阑尾一旦穿孔引起腹膜炎,你这条命可就丢了,医生说道。朱鹃在一旁得意地笑着。当晚,我就被推进了手术室。朱鹃替我在“家属”栏中签了字,并垫付了住院费。在完全麻醉之前,我清晰地记得朱鹃在病床边不断安慰我说,“这是小手术,不用怕,等你出来又生龙活虎了。你记住我们的赌注就是了,想想你该赌什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