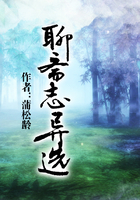要寄东西也行,给我寄个小闹钟来;如果没通行证,连张车票都不好买;父亲重病,他也没能多留下几天;凡是吃的,想尽办法从上海带过去。
当初,上海青年看了描绘新疆风情的纪录片,听了鼓动人心的宣传动员,怀着美好的想象奔赴到那遥远的地方;同样,也有新疆当地的人后来看了《霓虹灯下的哨兵》之类的电影,于是问起上海青年:“你们上海真的有电影上那么漂亮吗?如果上海有那么好,你们干吗要报名来这里?”
要回答这个问题,恐怕就要了解年轻人那份躁动的情怀,要了解特定时代人们对政治任务的义不容辞;另一方面,这又何尝不是萦绕在上海青年心头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远离上海,来到边疆?什么时候,才能够重新回到故乡呢?”
她们又哭又闹,她坐在一边不吭气
就像当年新疆对他们的召唤一样,不觉间光阴似水流过,家乡上海对他们内心的召唤也愈发地强烈起来,压抑已久的思乡之情日益浮上了心头。
还是在上海青年到来的头两年,程均友这个当连长的,每天晚上都会到这个班坐坐,那个班坐坐,了解了解情况,看看想家了没有。问他们:“想不想家呀?”回答:“不想!”再问他们:“想不想家里人?”还是干脆地回答:“不想!”但是程均友和他们朝夕相处,天天都在观察他们,他很清楚,咋能不想家,你想想,小孩子才出来,从上海到这戈壁滩,你说他能不想家,那是哄鬼。
笔者找到了至今还留在开都河畔21团的徐佩君,她抹了一下干涩的眼睛说:“确实,都不能想,一想就掉泪。说个不好听的话,那个时候晚上唱歌……以前有个电影叫《星星之火》,里面那个小真子,童工嘛,就是这样唱的,‘盼星星,盼月亮,左盼右盼盼亲娘……’”
34团的余加安也说:“对呀,唱得最多的就是那个沪剧《星星之火》。到晚上,乖乖,那些姑娘就是唱这种悲歌呀,一边哭,一边唱—‘妈妈呀……’整个曲调那么凄婉,在夜晚很勾人感情的。”
那时候写信到家里,家里再回过来,信光在路上往返就将近一个月。每次一批信送来,接到家信的时候,一个连队,哭声起伏。有些男的本来接到信不哭,听见那边女的一唱一哭,也勾起来了。那么男的怎么发泄?就敲东西,瞎喊。“砰砰砰”,拍门、敲碗、敲盆,啊……啊……,就那样瞎喊。
鱼珊玲对此不大以为然,在她看来,哭闹没有什么意思。所以旁边别的人苦闷得闹啊、哭啊、吵啊,她却不吵也不闹。她觉得,他们好像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没有经过像自己来之前那样反复的折腾。
鱼姗玲确实算是折腾得够厉害的,本来还要再考大学,马上就能去香港和父母团圆,过上舒服的日子,结果一番厉害的“折腾”之后,她选择去遥远的西部边疆。父母连发十二封电报,母亲专程回上海劝说,都没能把她拉过来,最后她还是坚持了自己支边的选择。所以她的思想准备应该是比较充足了,她不会再去跟家里人叫苦,不会再怎么表现出伤心。当宿舍里她们在哭、在闹的时候,鱼姗玲就坐在一边不吭气。
不管心情怎么样,也都得接受现实了。那么接下来,大家在一起共同的事情就是想上海的家,想上海的生活。可想而知,大家一说起上海往往会眉飞色舞,仿佛又回到了上海的南京路、淮海路、延安路、黄浦江外滩,对眼前匮乏的生活就暂时淡忘了。
应当说,有一条是大家共通的,一般他们给家里写信都是报喜不报忧,并不说在这里怎么艰苦,都是写“我在这里一切很好,我现在积极要求进步”,或者“我申请入团了”,就这一类的话。也不是怕检查,就是觉得相隔那么远,想叫家里人放心。而家里的来信内容也是这样,不管他们生病也好,有什么困难也好,都不跟远方支边的人说,都会写“你在那里要好好工作,要积极争取进步”之类的。
有的人可能从来不写信向家里要什么吃的、用的东西,但是有一样恐怕都是要过的,那就是粮票。为什么要粮票?实在吃不饱。所以要爹妈想办法给寄上两三斤全国通用粮票,在新疆也能买吃的。但家里也很紧哪。
当然,不向家里要东西的人至少是出于两种情况,一是不想再给父母增添负担;还有一个,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每个礼拜各班都有一次生活会。开会讲什么?主要检讨资产阶级思想。这叫自觉革命,让你自己讲出来。比如自己检讨说,我上次给家里写了信,问家里要了什么东西。只要是写信要了东西,都要如实说出来,那时候的人就这么傻,甚至还要说得更严重些。
余加安的家里曾经写信跟他说:“你已经工作了,给你寄块手表吧。”其实要寄的表也是旧表修好的。他赶紧回信说:“千万不要寄手表。要寄也可以,给我寄个小闹钟来。”为什么?小闹钟才几块钱一个,不算资产阶级思想,可以用它看看时间,好掌握学习和工作。如果戴上手表,那就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问题了。说句老实话,当时全连也只有连长、指导员才可能戴手表,一个小老百姓戴什么表呀。
两个月不吃不喝买张火车票
从1968年开始,“文革”中冲锋陷阵的红卫兵小将,变成了上山下乡大潮的主力。与这新一拨热血青年形成对照的是,在新疆支边的大哥大姐已经由单纯转向了务实。他们开始经营起自己的小日子,那时候探家就成了改善生活的一种机会,也可以说是一年到头最大的期盼。
当初是作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作为解放军的一部分动员他们去的,类似于征兵的性质。所以说好了享受一些部队的待遇,比如头三年实行供给制,吃穿公家管,没工资。三年以后根据工作表现,评定工资,工资分一级二级。而且说了,满三年就分期分批可以回上海探亲。当时这些都写在征招的简章里。
史美云记得,临去的时候,动员的干部讲好了,你们去三年就可以回来。倒是也没有明确讲是可以回家,还是可以探亲,大家好像都没有去多想它。不少人想当然地理解为,就像当兵三年服役期满可以回家一样。可后来却不是这么回事了,三年到了,也没再提起让你回家。后来终于说有探亲假,但是要等着轮,一个连一次只能走一个。
在“文革”开始以后,生产半停顿了,上面第一次讲有探亲假,一个连一两个名额,大家都争着抢着。安康他们连有两三百个上海人,就抢这一两个名额。最后抢不到怎么办?这时候,正好造反的都跑到他们那里去了,一闹,趁着乱,干脆也不管名额了,胆子大的就自己跑回去探家了。
但是在那个年代,出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有一阵子红卫兵全国大串联畅通无阻以外,其他人,特别是兵团人要想离开一个地方外出,绝不是轻而易举的。据王祖炯所知,上海支边青年自从到了新疆的团场以后,不管是哪个师的都没有工作证,个人没有户口本,没有身份证件,那时候也不兴身份证。一般正式单位至少有个工作证可以代表身份,但他们属于半军事化,根本没有工作证。作为团场职工,一直到他们几十年后离开新疆的那一天,从来都没有工作证。所以一出去,除了穿的一身“兵团黄”,没有什么能够证明身份的东西。
那么探亲的时候怎么办?他们既然算是部队性质,至少是半军事化,批了探亲假以后,出去的话要发“通行证”,没有通行证连车票也不好买。具体来讲,当过兵的都知道,探亲要逐级批准,发一张纸,铅印盖上,折叠起来,正面上的字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通行证”。没有照片,填上名字、年龄、单位、探亲缘由、时间起止。这张通行证到期自行作废。
每个人都会清晰记得那些与探亲有关的情节。等到供给制的三年一过,评工资,大部分人一个月工资是二十九块六毛八,当上排长的,一个月是三十一块零八分。差不多两个月的工资不吃不喝可以买一张火车票,来回一趟就相当于四个月不吃不喝。谁能攒得了更多的钱呢,也就是攒够火车票钱,一张硬座是五十四块一毛,只要批了探亲假,许多人手头的钱能买张火车票就跑回去了。
说起来探亲确实不易,为了准备探亲,就要省吃俭用尽量把钱攒起来,后来,像余加安和李小女夫妇两人这样,工资算高的,余加安已经提干,是二级,一个月三十三块九毛二;李小女是先进,也是这个标准,其他许多人都是二十九块六毛八。
后来的那些年,除了吃饭、养孩子,也就是养家糊口之外,剩下来积攒的钱,就铺到铁路上了。一旦男女青年在团场结婚,探亲假不再给报销路费,而路费是那时候制约人们出行的重要因素。回趟上海一个人来回就要一百零几块,那还只是坐火车的钱。他们大部分在南疆,都是先到吐鲁番的大河沿去坐火车,去的路上几天还要住宿,要乘汽车,碰得巧了,搭上过路车,或者逃了票,碰得不巧还得花钱。到了上海,总要再多花点儿。所以,三四年好不容易攒下的钱一下子全都铺到路上了。
一个人哪能来那么多钱?大家的感情好到什么程度,在这上面就反映出来了。比如有要回家探亲的,大家有多少钱都凑给他,他回来了以后再说。等到下次他回家的时候,大家再把钱都凑给他。当然钱给谁,谁也要帮大家带东西。
除了探亲假以外,家里有特别重要的事,先请假,批假了才能回去,时间一到马上就要回来。安康的父亲病重,他回去了,一到日子必须返回,家里问他:“你不能再续假吗?”他说:“不行,一超假可不是小问题,而且就不给报销路费了。”来回一趟不能报销的话,半年工资没了。怎么办,只好走。
探亲假批多少天就是多少天,包括路上乘车转车的时间都算好了,到时候就要回来销假,不销假的不能报销。因为这个,安康父亲重病叫他多留几天他也没留。他走了之后不久,父亲去世了。这种情况不稀奇,很多人父母生病,都没有办法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