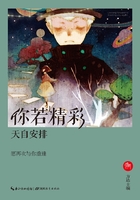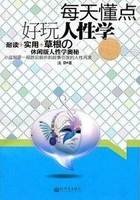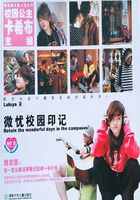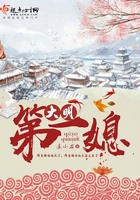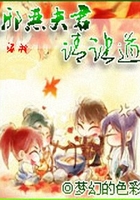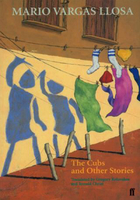普希金的腹部里面留着骨头的碎片,内脏受伤很重。在这种情形之下,医治的第一要义,——就是要使得病人的内脏完全休息,并用鸦片来制止它的运动。可是那位外科御医却根据不可解的理由,命令为病人灌肠。结果当然是非常可怕的。普希金的两只眼睛露出凶恶的光芒,就像它们要从眼眶里面跳出来似的,满脸都是冷汗,两只手也变得冰冷。虽然他竭力想抑制自己,但还是高声叫喊起来,使得大家都为主震骇。那个被吓坏了的当差就去告诉丹扎斯,说普希金吩咐他把写字台上的小抽斗拿给他,然后就退出去,而在这只抽斗里面正放着手枪。丹扎斯赶忙跑到普希金面前去,想夺他的手枪,而他已经把手枪藏到被单下面去了。普希金承认他想自杀,因为这种痛苦实在难受。
清晨时分,痛楚稍减,普希金又恢复原来的样子。他直到临死之前既没有呻吟一声,也没有号叫一声表示自己的痛苦。
普希金住宅的门前挤满了人。熟识的和不熟识的都挤在门口,不断地探问:“普希金怎么样啦?他好了一点儿吗?是不是还有希望呢?”
大群的人阻塞了普希金住宅前的那条街道,以致无法能挤到他的门前。但在这群人当中,却没有一个来自上流社会的人。
普希金每小时都在衰弱下去。死亡逐渐逼近了,他自己也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朋友们都对他说:
“我们都抱着希望,你也用不着灰心。”
普希金回答道:
“不,这个世界上没有我活的地方。我一定会死的,显然地,并且应该这样。”
正月二十九日(新历二月十日)近午,普希金要了一面镜子,照了一下,挥了一下手。脉搏低落下去,一会儿就完全消失。两只手也开始僵冷起来。突然间他又张开眼睛,要人家把用糖渍过的杨梅拿给他。当拿给他的时候,他又清楚地说道:
“叫我的妻子来,让她喂我吃。”
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就两膝跪在普希金的枕边,把小调羹递到他的嘴边,又把自己的面孔挨近他的额角。他轻轻地抚着她的头说道:
“呶,呶,没有什么,谢天谢地,一切都好!”
此后,普希金就开始坠入昏迷的状态了。医生兼作家的达利[1]时时刻刻都守在他的身边,普希金非常爱他。垂危的普希金,好几次把手伸给他,握着手说道:
“呶,把我抬起来。我们一同去,更高,更高,——呶,我们一同去!”
当他苏醒过来的时候他又说道:
“我做了一个梦,就好像我跟你一齐沿着这些书和书架爬上去,爬到高处去,——因此我的头都发昏了。”
有几次他注视着达利,问道:
“你是谁?你?”
“是我,你的朋友。”
“为什么我不能认识你。”
他不讲话了,闭上眼睛,又在寻找达利的手,拖着他的手说道:
“呶,我们一同去,请,我们一同去!”
普希金开始垂死的挣扎。他要人家把他的身子翻到右边去。达利和丹扎斯仔细地抬着他的两腋,把枕头摆到他的背后面。突然间,他好像醒来的样子,迅速张开眼睛,面孔更加明亮起来,他说道:
“完结啦,生命!”
达利没有听清楚他的话就回答道:
“是的,弄完啦。我们已经把你翻转过来。”
普希金又清楚地重复了一句:
“生命完结啦!”
他的呼吸愈来愈慢,只剩最后的一息。生命从此长逝。在场的朋友,永世都不能忘记的,就是普希金死时面孔上所流露出来的那种伟大的幸福的安详。
【注释】
[1]达利(1801—1872),作家兼语言学家,编有《俄国谚语辞典》(1861—1862)及《俄语大辞典》(1863—1866)。
十二、葬礼
在莫伊卡河边上,就是普希金逝世的那所房子的门前,发生了一种在当时是完全异常的情况。所有那些想向普希金的遗体致敬的人,就像潮水涌涨一样不断地增加起来。据目击当时情况的人说,到普希金的灵前来吊唁的,有三万至五万人之多。车辆从城市的各方面向莫伊卡驶过来。雇车的时候只要对车夫说一声“到普希金家去”就行了。
在普希金的灵柩旁,并没有上层显贵们的踪迹。挤向灵前的,都是些大学生、自由职业者、下层官员、商人和新兴的急进民主阶层而后来被称为“平民阶层”的“庶民”。在普希金的葬礼中,这个阶层最初出现于社会活动的舞台,并且觉得自己是一种社会力量。
普希金最后的几年,无论在社会方面、精神方面、文化方面、文学方面和家庭方面,都是生活在一个可怕的孤独的圈子里。“一个人孤独地活着吧!”他对自己这样辛酸地说道。但他却没有觉察,就是在他遭受折磨以至于死的那个圈子之外,他有着成千上万的热情恳挚的朋友。
死使得所有的人感觉到普希金的伟大的无法补偿的价值。他们高声地、坚决地、不用空话而用他们自己的一切行动表示出:
“普希金是我们的!”
就在这时,莱蒙托夫这位差不多还不大知名的诗人所写的一首愤激的诗:《诗人之死》出现了——这是篇火一般的诗的宣言。它异常迅速地被传抄和流行着,所有的人都重复背诵着他的诗句:
你们,站在宝座周围的这贪婪的一群,
全是自由、天才与光荣的刽子手!
你们躲藏在法律的荫庇之下,
在你们面前,法庭和真理——都得静默闭口!
但是,你们这些荒淫的宠臣呀,有着上帝的法庭,
有着威严的审判官,他正在等候,
他不能用钱贿赂,
他预先见到了一切思想与行为。
那时你们的毁谤是枉然无用:
它不能再帮助你们,
你们也不能用你们的污血,
去把诗人的正义之血洗清!
社会愤慨的激发,也使得沙皇尼古拉吃惊和感到害怕。他起先对普希金的死是冷淡漠视的,并且还完全认可了丹特斯的行为。可是自下而上的这种压力,使得沙皇了解到,问题不只在于涉及一个低微的“作家”,一个他的宫廷里的小官宫廷近侍,而是一个被全国广大民众所高高敬仰的人物。
尼古拉不得不改变了他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假装着说他非常重视普希金的死,认为这是国家的一个莫大的损失。丹特斯被贬为士兵,因为他隶属外国国籍,就把他驱逐出境,至于赫克伦公使由于沙皇的请求,也由荷兰政府将他从公使任上撤调回国。
另一方面,尼古拉又急忙地阻住一切足以成为社会激烈愤慨情绪所要表达的道路。严令各报对普希金的死,“保持应有的温和与适切的态度”。有一家报纸因为上面写着“我们诗坛的太阳殒落了”,“他是死在他伟大行程的中途”等语而遭到处分。普希金住宅邻近的房子,都安置了步哨,在他的住宅的大门口和住宅里面,都有暗探来往徘徊着。
在移灵的前夜,正月三十日至三十一日夜间,人群散去之后,普希金的住宅里只剩下他的几位近友;这时候宪兵团参谋部长杜别尔特将军带着宪兵前来。他们并不把灵柩移到第二天要举行奠礼的圣伊萨阿克大教堂去,而移到马厩教堂,在举行奠礼的这一天,教堂入口处都布满了警察,只允许那些被邀请参加的人进去。祭奠完毕之后,就把灵柩放到教堂的地下室里去了。
二月二日至三日的夜间,有一部灵车和两辆马车开到教堂门口。一辆马车里面坐着宪兵长官,另一辆马车里面坐着普希金的朋友亚历山大·屠格涅夫,他是奉命把普希金的遗体护送到普斯科夫省,距离米哈伊洛夫斯克村不远的圣山镇修道院去安葬的。他们把棺柩装上灵车,就急速地驶出城去。普斯科夫省的省长预先接到皇上的命令。当棺柩经过时,“禁止一切特殊表示,一切迎接,总而言之,禁止一切仪式即是”。
这个特别的葬礼行列,日夜兼程地在雪地里飞驰前进;就好像罪犯们,想急忙秘密地了结掉自己所作的勾当一样。
在一处驿站上,一位过路的教授夫人看见这些鬼鬼祟祟的宪兵们,在督促车夫赶快为一辆盖着藁草的车子换马,在这辆车子上就放着一个用草席裹着的棺材。她就问一位在旁边守望的人,这是怎么一回事。
“天晓得这是怎么一回事。听说,一个什么姓普希金的人被打死了,他们就把他包在藁草和席子里沿着驿站飞奔——愿上帝宽恕我,就像他是一头死狗一样。”
尼古拉统治的沙皇俄罗斯就这样在二月六日(公历十八日)的黎明时埋葬了这一位最伟大的俄国诗人。
自从普希金逝世以来,已是一百多年了。杀害他的沙皇专制政体已经崩溃,而一些人劳苦和受难,另一些人不劳而获却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的那种社会制度,也已经崩溃了。人民对于普希金的敬爱是与年俱增。他对于一切的人都是必要而又无限珍贵的。大家之所以需要他与珍爱他,就是因为他有写诗的天才,他的不屈不挠的反抗性,他对于真理的不知疲倦的追求,他用来灌注生活的那种欢乐与美丽,他的深刻的人性与文化,他的语言的无比的音乐性,和他的文字的崇高的明朗性与朴素性。
普希金曾经幻想过的那条通到他纪念碑前的人民的路径,已经变成了宽阔坚实的康庄大道。他的著作被印成千百万册,并且立刻为群众所吸收,好像瀚海里的干沙在吸收水分一样。一切的人都知道他。他的作品被译成苏联境内许多在过去最为落后的民族的文字。普希金的预言实现了:
我的名声将传遍整个伟大的俄罗斯,
它现存的一切语言,都会讲着我的名字,
无论是骄傲的斯拉夫人的子孙,是芬兰人,
甚至现在还是野蛮的通古斯人,和草原
上的朋友卡尔梅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