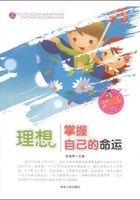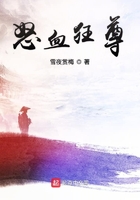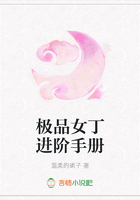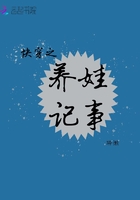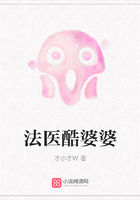为了提高理论水平和文化修养,我还连续一学期听了陶军教授为住在昙华林的青年教师开设的哲学课。大约是61年,陶教务长每个星期从桂子山到昙华林钟楼一楼的一个小教室来讲一次哲学课,他不需要课本和讲稿,只是带一些卡片;卡片上有讲授提纲,他经常结合国际政治形势、中国和世界社会经济与教育等方面的实际情况,用通俗明快的语言把深刻的哲学理论讲得那么明白、好懂,比我们自己硬着头皮死啃哲学著作收获大多了。也正是那几年,我多次听到关于南下的军代表陶军用英语在武汉大学演讲,使那些老教授深深震惊的不同版本的故事。经过比较,最正确、可信的版本是马敏、汪文汉两位教授主编的《百年校史》(1903——2003年)(华中师大出版社,2003年)第233页所记述的故事:那是1950年冬天,身穿军装、刚过而立之年的陶军,应邀在武汉大学大礼堂给武汉大学和私立华中大学的专家教授作报告。他用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声情并茂地讲解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打动了大多数听众。但是也有人从台下递上来一张用英文写的纸条,上面写道:“你陶军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写纸条的人根本看不起这位衣着土气的“军代表”,想当众出共产党的洋相。陶军沉着地讲完一部分后,举起那张纸条向全场宣布:“我刚才收到一张用英文写的纸条,为了回答他的问题,下面的报告我改用英语进行。”在场的教授没有想到:这位土里土气的“军代表”,竟然能用地道的英语流利地作报告,不禁对他肃然起敬,大家这才知道共产党里确实有人才。当陶军以一种嘲讽的口吻指出纸条上有两个单词的字母写错了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多少年过去了,这个有趣的故事却被一代代华师校友通过口头往下流传。1987年4月9日陶军同志不幸病逝,我们都怀着沉痛的心情去参加了追悼会,那一天我看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部、湖北省教育厅、本省和外地很多高校都给陶军教授送了花圈,或发来了唁电。著名哲学家、武汉大学校长陶德麟教授在花圈上的落款是“后学陶德麟敬挽”。这些都表明:陶军教授在我国教育界,特别是在湖北省高等教育领域有着很高的声望和深远的影响。
1962年秋季,中文系1959级的学生已经升到四年级,按学校的安排,要到武汉市和外地去进行教育实习,我带领的一个实习组到黄石二中,经过一个半月日日夜夜的辛勤劳动,我们胜利完成了语文教学和班主任实习任务,于10月下旬返回华师。中文系副系主任王庆生对我说,经与总支书记张洪、系主任方步瀛商量,要我在从事现代汉语教学的同时,兼任系教学秘书。过了几天,陶军教务长从桂子山来到昙华林分部,在一个小会议室听取中文系汇报。王庆生在汇报中文系教学工作前先对陶教务长说:刘兴策带实习生到黄石市进行教育实习刚回来,系领导商量要他兼任系教学秘书工作。陶教务长望着我点了点头,微笑着说:“好哇,走马上任嘛。”听到陶教务长平易近人的话,我暗暗地想,一定要努力做好教学秘书工作。
那几年为了更好地在教学中加强“三基”训练,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我们系每个年级在一学期中通常要召开两次年级教师会;在开年级教师会议前,由教学秘书先分别召开各个年级与小班学习委员和学生代表会,听取同学们对本年级任课教师教学的意见和建议,并将意见进行整理后在各年级教师会议上向任课老师转达(包括优点和不足之处),以便于各年级专业课和公共课老师一起,交流教学经验,并有针对性地商讨如何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对于任教的老教师,同学们最喜欢听高庆赐、石声淮、方步瀛等老教授的课。高老师是北京人,青年时代在北京大学研究院师从罗常培先生攻读语音学,在语音学方面造诣很深,他对词汇学、语法学、修辞学也很熟悉;加上他备课认真,在下课休息时间询问学生对讲课的意见和要求,这样他讲起课来针对性更强,能做到得心应手,运用自如。无论是讲现代汉语,还是古代汉语,他都用纯正的普通话授课。他还擅长于边讲课边把讲授要点快速而规范地写在黑板上,使学生十分喜欢。从1953年到1955年,高先生任华师副教务长,还担任了华师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他以身作则,带头参加文娱体育活动,家住华中村的他周末常到昙华林分部体育馆楼上去参加舞会,既锻炼了身体,又常与青年教师和大学生交谈,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他到校本部开会或上课,也常常由家里步行十几里到桂子山去。他曾在《华中师院》上发表了题为《为了生活得更美好》的文章,号召大家积极锻炼身体,增强体质,他对生活的热爱之情,在潜移默化中感染着学生。
石声淮老师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几年中,为了帮助青年教师过好基础关,还为古典文学教研室青年教师和外校来华师进修的教师开设了《中国古代散文选讲》课,我也去听过好几次。他对古代散文十分熟悉,在中文系资料室给我们讲课时,许多作品能成段地、顺畅地背出来,令青年教师敬佩不已。他不仅认真教书,也时常教育我们要怎样做人,怎样当好老师。他在为本科生讲古典文学的大课堂,在为青年教师讲古代散文的小课堂,乃至在家里与青年教师和学生交谈都讲到不要当“白面书生”。他并不反对师生适当地参加体力劳动,但他担心大学生离开校园接连几个月去大炼钢铁或从事别的体力劳动,对“书”太“生”(生疏)了,将来怎么去传道、授业、解惑?怎能担当起教师的责任?所以他多次提出要多读书,对重要的书要“熟”读。现在回想起来,石老师常用谈笑的方式规劝青年师生改变对“书”生疏的状况,与外国文学教授胡雪先生那几年所说的“一锄头挖不出莎士比亚”,都是话语不多而情深意长,其实他们都是希望学校能保持正常的教学秩序,表现了老年教授对于青年一代的关心和对人民教育事业的责任感。石声淮先生还有一个特点,无论是在课余休息时间与青年师生聊天,还是在家里与来访者交谈,他都能平等待人,决不摆老教授的架子。也是上世纪60年代初,有一天有几个青年教师去他家看望,他当时刚清洗了假牙还没有戴上去,便一边开门,一边指着自己的嘴巴说:我现在成了“无齿之徒”,逗得几个青年人都笑起来了。有的青年教师是第一次登门拜访,本来有些拘谨,但见石老师这么平易、随和,拘谨之态顿时荡然无存。还有一次,我偶尔与石老师谈到普通话与方言问题,石老师立即讲了他家里的趣事。他曾对子女说:“在长沙,我是你们的爷(yá);在武汉,你们是我的伢(yá)。”石老师是长沙人,长沙话称父亲为“爷”,读作yá,保留了中古音的读法;但石老师的子女都是在武汉出生和长大的,都会说武汉话,武汉方言把小孩儿叫做“伢”(yá),与长沙话的“爷”恰好同音(至少是十分近似)。石先生讲的这件趣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给研究生讲《汉语方言学》时,还用了这个例子。我觉得几乎每次与石先生交谈,都会受到启示和教益。还有我们的系主任方步瀛教授,多年来给中文系学生讲元明清文学都深受欢迎,我们邀请学习委员和学生代表开会时,不少学生都说方老师对元明清文学十分熟悉,引用诗词、散文从来不看讲义,总是能流畅地背出来,而且讲课富有激情,有声有色,声情并茂;即使他浓重的江西方言同学们不一定都听得懂,也都喜欢听他的课。我在任教学秘书时常与方主任一起开会,与方先生较熟悉,在与中文系教工团支部书记商量后(我曾兼任中文系教工团支部宣传委员和副书记),请方主任给我们上了一次团课。他在团课中着重讲了自己读书与写作的做法和体会,他总结的两条重要经验和体会是:文章以顿悟为重,学问以积累为功。这两句话我一辈子都记得,永远不会忘记。
三
1966年初,按校系党政领导的安排,我和中文系部分教工一起,跟1963级学生到蕲春搞“四清”。到1966年5月底,搞“四清”的教工又奉命回到华师参加文化大革命。那时中文系已搬到了桂子山校本部,我也就住在桂子山。1967年底我爱人快要生孩子,她在汉口一所中学教语文,为了便于她产假期满后上班,学校总务部门同意我们退还桂子山的房子,搬到离汉口较近的昙华林分部住(那时原昙华林分部的房子几乎都划拨给湖北中医学院,只有两小栋不到十家长住昙华林的华师老师仍在昙华林分部)。我的儿子和姑娘都是我家住在昙华林分部时出生的,为了照料孙子、孙女,我母亲也来到昙华林分部,与我们住在一起,这更能说明我和我们家祖孙三代与昙华林是多么有缘分。
从1967年底到1982年的十几年中我长住昙华林,对它的了解自然也就更多了。回想1948年14岁的我随父母从南京回武汉时,只知道昙华林这条小街上有一所小学;读大学后才知道,在昙华林街北侧东头,还有一所办得不错的中学,它在武汉解放前叫湖北省立一中,武汉解放后改名为武汉市第十四中学。20世纪30年代,省立一中背靠一座小山,修建了一大批校舍后,还有大操场和大片的空地。1938年初,这里曾先后成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和第三厅的驻地。郭沫若在他的抗日战争回忆录《洪波曲》第四章第三节“昙华林”中有这样一段记述:“昙华林在武昌城内的西北隅,在文华大学(其实那时“文华大学”已改名为“华中大学”——引用者注)的对面。地方很宽大,房屋很大,但建筑都很旧”。“政治部刚成立的时候,这儿曾作过本部。要经过一条很窄而长的背街才能到达,那条背街只能够勉强通过一部小汽车。大员们嫌交通不便,不久便乔迁了。于是这样大的一个地盘便留给了我们。场面真够大,大到尽可以在里面办一座综合大学。”(《郭沫若选集》第二卷第14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也是在我上了大学以后,才逐渐知道在昙华林街不仅有一所武汉知名的中学,更有一所历史悠久的著名的大学。早在1903年,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就在昙华林原文华学院的基础上建立了文华大学,后来更名为华中大学;到20世纪30年代,它已发展为事业蒸蒸日上的教会大学了。1951年私立华中大学与南下的中原大学教育学院合并,建成公立华中大学,1952年,又根据教育部的指令与中华大学、湖北省教育学院等校合并,到1953年建成华中高等师范学校。经过几次院系调整,东西南北的几所经历不同、风格不同的大学组建成的华中师院,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崭新气象,学校领导优势互补,团结合作,教师队伍迅速壮大,人才荟萃,学校各项工作顺利推进,很快地华中师院就成了中南地区规模最大、实力领先的师范大学,并成为教育部直属的全国六所重点师范大学之一。
从1967年底开始,我的家多年住在与湖北医院只有一墙之隔的昙华林分部12栋(这一栋住5家,都是华师老师,其中4家是中文系教师)。中文系在1965年又搬到了桂子山,我上课、开会、做社会工作,得经常到桂子山校本部。为了让我1968年出生的儿子与1973年出生的女儿从小就受到优质教育,我从1972到1982年十年间,得送儿女上华师幼儿园和附小,并接他们回家;除星期日以外,经常得奔波于桂子山和昙华林之间。但做好教书育人工作和让儿女健康成长对自己和家庭来说都是重要的事情,作为父母不管多忙多累,也是责无旁贷。
似乎是1979年的一个星期天,湖北人民出版社的袁晓眉编辑来到昙华林12栋,他本来是找中文系副系主任哈经雄的,想请华师中文系老师编写一套“语文新四书”。早就住在12栋的哈经雄却又忙得很,他考虑到我曾任教学秘书数年,与教师的交往较多,便请我来抓这件事。袁晓眉与哈经雄和我一起商量编写《古文精华》、《古今诗粹》、《语文知识千问》和《优秀作文评点》四本书的有关问题,一致认为必须请熟读四书五经的“活字典”石声淮老师任总主编,请研究成果丰富的语言学科主要带头人邢福义老师任副总主编,并邀请各相关专业的学科带头人或骨干教师参加编写,由我负责组织编写队伍和联络工作。在得到石、邢两位教授的赞同和支持后,大家齐心协力,在预定时间保质保量地胜利完成了编写任务。上个世纪80年代初,这套新四书刚问世,首先在中文系作者和领导中引起热烈的反响,因为这是华师中文系建立30年来,由各相关专业教师共同编写并公开出版的第一套丛书,这套书也受到省内外广大读者的热诚欢迎。1983年和1985年,这四本书先后被评为中南地区优秀教育读物一等奖,1986年,“语文新四书”又在北京被评为全国优秀畅销书。这套书虽然是以普及语文知识、培养语文能力为主要目的的普及读物,但它展现了华师中文系教师对广大读者认真负责的精神和扎实的业务能力,也为教育的春天增添了一些春色。
《庄子·知北游》说:“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我在中文系读本科的前3年,作单身老师住颜母室(楼)的7年,成家后住在原昙华林校园内15年,回顾在昙华林25年的生活,仿佛都发生在昨天一样。在回忆和思索这15年往事的过程中,我不知不觉地萌发了下面两点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