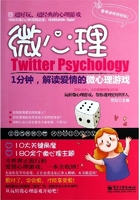睡了有两个时辰,外边就有了动静。想起今天要祭祖,祁敛翻了个身,坐起身来。出来的时候,二爷爷已经坐在正堂里了,看见他眼睛都笑弯了。
爷俩正吃着,突然门嘭的一声被踹开,两个五六岁的娃娃抓起石块就往饭桌上扔。
祁敛脸色一沉,袖子一甩,石块便被反弹了回去。
饶是两个小孩撒丫子就跑,还是被打在了屁股上。
这下可好,哇的一声齐齐哭起来,不一会,门外就围了一圈的人。
两个孩子的爷爷一脸愤怒地站在门前,直直盯着祁敛,“干什么一回来就打小娃娃?”
阿三憋不住气,“是他们……”
才刚说了三字,就被祁敛一记眼风给挡了回去。
果然那边老者暴怒,“这哪有你个浆人插话的地!老二哥,你这孙子就这么教的?”
“您甭往我爷爷身上扯,”祁敛走到门边,“两个小娃娃不懂事,我帮着教训一下。”
“他们爷娘俱在,哪轮得到你来教训?”
祁敛冷哼一声,“当年我不小心撞到了您,您不也是反手就一巴掌吗?”
“你!”老者一时语塞。
这时二爷爷突然开口了,“小刀,怎么跟长辈说话的!”
祁敛垂头往后退了一步。
二爷爷单脚跳着上前来,几乎要贴到那老者脸上,“一大早堵到我门口,老六,你是对我这老疯子有意见吗?若是不满,请老翁爷来出面,我拿刀的时候,你小子还光屁股呢!”
许是因为跳了那几下,二爷爷背后原本被包的结结实实的刀身就露了缝出来,鲜热的红如燃烧的火。
老六脸上憋得通红,后退两步,“老二哥言重了,小弟不敢。”
这时又出来几人劝和,说都是一家人,今天又是祭祖,切不可因一点小事伤了和气。
人群一时就散了。
二爷爷扶着门框,转身看祁敛,“小刀,你要记住,你姓祁,这辈子都改不了。”
祁敛目光望向门外的黑洞,好一会才点了点头。
一路驾着马车下炁崖,往齿挪峰山脚下而去。
此时山脚下已聚满了人,黑压压一片人头。
但再仔细看,便见人群排列有序。妇女们站在山脚,从老至幼排满了一整片空地,而男丁们则顺着没入云端的石梯依次向上。
祁敛有心帮二爷爷,却也不得不干看着。
祭祖历来除了襁褓中的婴儿,均不得借助外力登顶,即使是卧病在床,也要凝聚所有的心力上去,哪怕下山就死呢。
二爷爷就这样单脚一级一级地往上跳。
祁敛到了自己所在的位置,祁远才这次倒是出人意料,规规矩矩地站在祁敛身后,脸上表情意味不明,不知又在打什么鬼主意。
祁敛转过身去,不再看他。
不多时,老翁爷等族中长老一一登顶。
巳时正,祭祀开始。
只听老翁爷苍老却满是威严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年华如驶,倏又三春。念我老祖,祁氏先人。儿孙皆临,报本情殷……韶光流易,旧典宜遵。兄友弟恭,不可乱序;长幼一族,不可二心。谨记使命,刀祭螭吻。不扰世事,净我本魂……伏惟、尚飨!”
气氛极为肃穆,除了耳边的风声,百千人竟连呼吸声都听不到。
紧跟着便是三叩首,叩首后,家祭也便结束了。
众男丁缓缓向上,穿过浮云到达吻天洞台上。
很快,五大家族的男丁都已到了,按长幼之序排着,从正上看,就像是一圈圈荡出去的波纹。
正中的吻天洞口上出现了一个浮在半空的石板,石板三丈见方。说不清它从哪来的,每到祭祖时,便会从吻天洞中浮上来,找不到任何牵引支撑的东西,就那么凭空浮着。
第一轮公祭是五大家族的老翁爷。
因白家擅占卜,可上窥天命下探吉凶,一直以来都站在最中间,而不知哪一次祭祀开始,陆家就站最里边了。
只见陆家的老翁爷瘦瘦高高,站得笔挺,花白的头发整齐地束起,一身灰白袍子在风中猎猎作响,似有千军万马之势。
他左边是祁家老翁爷,右边是白家老翁爷。
这白家老翁爷头发披散着,遮住了半张脸,身材佝偻,似是已老到了极致。但偶尔从散发后透出的目光,却锐利地让人不敢逼视。
他右边是程家,程家老翁爷黑发黑须,看上去不过四十来岁。
其实他的真实年龄比紧挨着的白家老翁爷小不了几步,只见他脸色绷着,似是这世上就没有什么值得开心的事。
祁家老翁爷左边是贺家老翁爷。
这贺家老翁爷在或威严、或神秘、或严肃的众位老翁爷中最是不同,人矮矮胖胖的,脸上一直带着微微的笑,让人如春风拂面。
五人齐声喝唱祝文,祁敛只顾着打量台上的老翁爷们,回过神时,祭文已到了末尾。
“今祭我祖、化引真人,开天辟地,赐我洪恩。万物长荣,五族同心。伏惟、尚飨!”
接下来登台的是中代首祭,祁敛将目光放在了祁木桓身上。
大概有四五年没见过祁木桓了,他似乎更瘦了,衣袍穿在身上晃晃当当的,似是一阵风都能给吹跑。
脸色苍白中带着不自然的潮红,表情似都在努力维持。
祁敛心头一惊,瞧这光景,祁木桓只怕撑不到下一次祭祖了。
而此时祭台上最惹眼的是陆家,因为位置是空的。
传闻陆家这位首祭十多年前突然就消失了,生死不明。
最后登台的是新代首祭,相比对中代首祭,很明显众人对这些天赋异禀的年轻人更感兴趣。
因是小辈登台,底下的气氛也松动了一些,能听到有人在小声的交头接耳。
“瞧,那个就是白家的阿渔!”
“开天辟地第一个女首祭,不知道庐山真面目是什么!”
“嘿,我是不知道她庐山真面目是什么,但肯定不是什么美人。白家的女人都阴森得很,脸上花花绿绿的。看美人还是陆家的姑娘,一个赛一个的美!”
“对对,那个阿檀当真是天仙下凡!除了陆家,程家的姑娘也不错!”
祁敛望向台上,三年前的祭祀他没有上来,对那个被传为神话一样的阿渔并未见过。按说,祭祀是不允许女人上来的,而白家不止让女人上来了,还是作为新一辈的首祭。
说起来那阿渔也当真是了不得,年仅十六岁就成了红背刀,甚至破了祁木崖十七岁成为红背刀的记录。
所以一度有人猜测,祁木崖死后,螭吻珠到了阿渔的身上。
但祁敛知道,不是。
那这个女子的天赋就有些吓人了。
此时看过去,只见那“阿渔”头上戴着白纱,将脸遮得严严实实,盘起的发髻上只插着一支簪子,坠着一尾小青鱼。
小青鱼随着她的动作微微晃动,似是荡开了一圈圈涟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