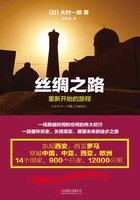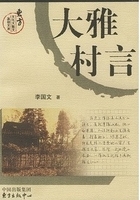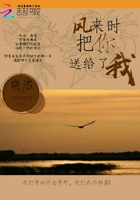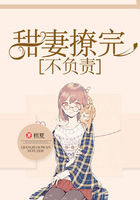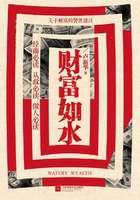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有这样的情形,你会很高兴在这场男人的吹牛大会中输掉。死亡意识仅有的几种慰藉之一便是,总是——几乎总是——有人比你更倒霉。不仅仅是R,还有我们共同的朋友G。长期以来,他是死亡恐惧项目的金牌持有者,因为他四岁就已经被死亡闹铃[10]唤醒(四岁!你这个混蛋!)。这件事情对他影响至深,以至于他的童年一直在永恒的虚无和可怖的无限中度过。长大后,他依旧比我更惧死亡,因而也容易陷入更深的抑郁。判定重度抑郁症发作有九大基本标准(从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消极情绪到周期性想到死亡和周期性的自杀意志,并伴有失眠、觉得生活无意义等症状)。两个星期内满足五条就可以确诊为抑郁。而早在十年前,G就在九条都满足后不得不去住院了。他告诉我这件事时没有任何竞争的锋芒(我早就不和他竞争了),不过话音里带着一丝讨厌的扬扬得意。
每个恐惧死亡的人都需要有个倒霉鬼榜样,以求暂时的安慰。我有G,G有拉赫玛尼诺夫——一个既恐惧死亡,又恐惧死后复活的人,一个比其他任何人更多地将末日审判[11]渗入音乐的作曲家,一个会在放映《弗兰肯斯坦》开场的墓地一幕时语无伦次地逃出电影院的观众。拉赫玛尼诺夫不愿意谈论死亡才会让他的朋友感到吃惊。其中,一件代表性的事情是:1915年,他去拜访诗人玛丽埃塔·沙吉娘和她母亲。起初,他请她母亲用纸牌给他算命,(当然)希望能知道他还能活多久。之后他坐了下来,和诗人开始谈论死亡:那天他选了阿尔志跋绥夫的一篇短篇小说。在他手边有一碗咸开心果。拉赫玛尼诺夫吃了一口,谈论死亡,然后挪动椅子好离碗更近些,然后又吃了一口,接着再谈论死亡。突然,他停了下来,大笑道:“吃了开心果,让我的恐惧都消失了。你们知道它上哪儿去了?”诗人和她母亲都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可是,当拉赫玛尼诺夫要去莫斯科时,她们给他一整袋开心果让他路上吃,“好治愈他对死亡的恐惧”。
如果让我和G扮演俄罗斯作曲家,我会让他与肖斯塔科维奇——一位更伟大的作曲家,一位同样伟大的沉思死亡的人——匹配。“我们应该更多地思考死亡,”他说,“更习惯于考虑死亡。我们不能让对死亡的恐惧出其不意地冒出来。我们必须让自己熟悉这种恐惧,一个办法就是将它写下来。我并不认为思考和书写死亡只是老人的特征。我认为,如果一个人越早思考死亡,他就会越少犯愚蠢的错误。”
他还说:“恐惧死亡,也许是最强烈的一种情感。我有时候想,没有比这更深沉的情感了。”这些观点并没有公开表达过。肖斯塔科维奇知道,死亡——除非是英雄般的殉道——并不合乎苏维埃艺术的主题,这种主题“和在客人面前用袖子擦鼻子差不多”。他不能让末日审判在乐谱中发光。他得让音乐藏而不露。但是渐渐地,这位谨慎的作曲家鼓足勇气,拿衣袖擦了擦鼻孔,尤其在他的室内乐中。他最后一批作品往往包含对死亡的悠长、缓慢而沉思的祈祷。有一次,他给贝多芬四重奏组的小提琴家这样一个建议:在演奏《第十五弦乐四重奏》第一乐章时,“要让苍蝇倒毙在半空中”。
当朋友R在《荒岛唱片》中谈到死亡时,警察缴了他的霰弹枪。当我这么做了,我则收到了一堆形形色色的信,信中说,假如我懂得内省、诚心笃信宗教、上教堂祷告,等等等等,我的恐惧症便可不治而愈。这是一碗神学的咸开心果。这些给我写信的人并非全然以恩人自居——有的善感,有的严厉——但看他们的意思,似乎这一解决方法对我来说很新鲜。好像我是某个丛林部落的成员(就算是,我也不能没有自己的一套宗教仪式和信仰啊),而不是一个在基督教即将从我们国家消亡的时刻出来说这些话的人,部分原因在于众多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已有一个多世纪不信教了。
这一世纪几乎与我能追溯的我们的家族史一样久远。我默认成了我们家的档案管理员。在离我此刻写作的地方几码远的一只浅斗抽屉里装着全部文件资料:出生、结婚、死亡证明,遗嘱和遗嘱认证,专业证书、介绍信和推荐书,护照、配给卡、身份证(还有法国身份证);剪贴簿、笔记本和纪念品。这里有我父亲写的诙谐歌曲的原稿(唱这些歌要身着晚礼服,倚在钢琴旁,他在学校的同事或战友为他作慵懒的夜总会式的伴奏)、他签过字的账单、剧院节目单以及填了一半的板球得分卡。这里有我母亲的主妇笔记本、她的圣诞卡清单以及股票债券表。这里有他们之间来往的电报和战时无线电报(但是没有信函)。这里有他们两个儿子的学校成绩单和发育记录卡、他们颁奖日的活动安排表、游泳和运动证书——我看到自己1955年的跳远冠军和足球赛季军的证书,还有我哥哥和迪翁·夏勒搭档获得的手推车比赛亚军证书——以及我早已忘记的成绩证明,譬如,我小学某个学期的全勤证明。这里还有我外公的几枚一战勋章——充分证明他于1916年至1917年在法国服役,那是一段他从不愿提起的时光。
这个浅斗抽屉大得足够装下整个家庭的相册。盒子上有父亲手写的“我们”“两个儿子”和“古董”的标签。照片中,爸爸穿着教师长袍,或皇家空军制服,或戴着褐色领带,或者穿着远足短裤和白色板球服,总是手拿香烟或嘴叼烟斗。在这些照片中,妈妈穿着自家做的时尚衣服,或者身着不甚暴露的两件式泳衣,或穿着共济会晚宴用的豪华套装。这里面有那位法国助手,大概是他拍摄了马克西姆:狗,也就是后来帮忙将我父母的骨灰撒在法国西海岸的那位助手。在这些照片里,我和哥哥还处于尚有一头金发的年轻时光,在为一系列自家做的针织衫做模特,旁边是狗、沙滩球和儿童三轮车;这是我们在同一辆三轮车两旁的照片;这是我们随意拍的拼贴照,后来我们将它们装上硬纸框,取名为“雀巢儿童乐园纪念,1950年于奥林匹亚”。
这里也有外公的照片记录,一本红色的布面相册,名为“沿途风景”,这本相册是他1913年8月在科尔温湾买的。它记载了1912年到1917年的时光,此后,他似乎放下了相机。这是伯特和他的兄弟珀西,这是伯特和他的未婚妻内尔,然后这是他们婚礼上的照片:1914年8月4日,一战爆发的那天。这张,在那些褪成棕黑色的无法辨认的亲戚和老友照片中,居然被损坏了:照片上是一位穿着白衬衫的女人,她坐在折叠帆布躺椅上,下面标着日期1915年9月。日期旁的铅笔字迹——是名字?还是地点?——基本被擦除了。这个女人的脸被恶毒地连撕带抠,直到只能看到下巴和粗硬的像维他麦一样的头发。我很纳闷这是谁干的,为什么,对谁?
少年时代,我也有过一段时间爱摄影,有过一个简单的暗房:塑料显影池、橘黄色暗房灯和接触式晒印框。这段狂热期的某一天,我对一份杂志上的一则广告深感兴趣,那是一款廉价而神奇的产品,广告里保证它能把我那简陋的黑白照转换成色彩丰富、栩栩如生的彩照。我不记得我在邮购之前是否问过父母,也记不清当打了保票的一套工具原来只是一把小刷子和一些能粘在相纸上的彩色长条状颜料时,我有没有感到失望。但当时我立马干了起来,把我们家这些图像记录变得更生动,假如不是更真实的话。这张是爸爸穿着亮黄色灯芯绒裤子和绿毛衣,背景是黑白色的庭院;外公穿着同一种绿色的裤子,外婆穿着淡一点的绿色的衬衫。他们三人的手和脸都诡异地泛着潮红。
我哥哥质疑记忆的根本真实性,而我质疑我们渲染记忆的方式。我们都有自己的廉价邮购颜料盒以及喜欢的色调。因此,在前面几页我说我记得外婆“娇小而圆通”,而当我问起我哥,他拿出他的画刷,提出相反的意见,说她是“矮小而专横”。他的心灵相册里比我的装着更多1950年代早期祖孙三代赴伦迪岛出游的珍贵照片。对外婆来说,那基本上是她唯一一次离开不列颠陆块;对外公而言,这是他自1917年从法国回来后的第一次出行。那天,大海波涛汹涌,外婆不幸晕船。当我们到达伦迪岛时,却被告知因风浪太大不能下船。对此,我的记忆已经褪成棕黑色了,而我哥哥的却仍旧色彩鲜艳。他描绘外婆如何在甲板下度过整段旅程,如何呕吐到一个又一个塑料杯中。当时,外公拉下他的鸭舌帽,盖住眉毛,不厌其烦地接着每个吐得满满的杯子。他并没有把这些杯子扔掉,而是把它们放到架子上排成一列,好像故意要让她难堪。我认为,这一段是哥哥最中意的童年记忆。
是娇小还是矮小,是圆通还是专横?我们使用的不同形容词反映了对几近忘却的情感的零碎记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更喜欢外婆,或者为什么她更喜欢我。难道是我惧怕外公的专制(虽然他从未打过我),并且觉得他男性榜样比父亲的更粗粝?我喜欢外婆仅仅是因为她是女性?我们家族女性可真少见啊。虽然我和哥哥与外婆相处了二十年,我们却很难忆起她说过的话。我哥哥唯一能提供的两个例子,都发生在她激怒母亲的情况下,所以此时她说的话也许更多的是提供一种愉快的感觉而非内在的含义。第一个例子发生在冬夜,当时母亲坐在火炉旁取暖。外婆提醒道:“别坐得太近了,小心毁了你的腿。”第二个例子发生在几乎整整一代人之后。我哥哥的女儿C,当年大概才两岁,接过一块蛋糕但没有道谢。“说ta[12],亲爱的。”她的曾外祖母提醒道——闻此,“我们母亲对这种粗俗用词怒不可遏”。
这样的记忆碎片能更多地展现外婆、母亲或者我哥哥的性情吗?它们是否表明了某人的专断?我意识到,我自己关于外婆“圆通”的证据其实并不存在;但是,就这本身而言,也许是存在的。我搜肠刮肚,但怎么也想不起自己小时候喜爱的这个女人的只言片语;能记起的也许只有一句间接的话。外婆去世很久以后,妈妈跟我讲了一句外婆的格言。“她常说:‘世上如果没有坏女人,就不会有坏男人。’”外婆对夏娃之罪的确认就这样被不无鄙夷地转述给了我。
我在清理父母亲住的小屋时,发现了一小堆1930年代至1980年代的明信片。它们都是从国外寄来的;英国国内寄来的那些明信片,无论赠言多么风趣,在过去某个时候都已被扔掉了。这是我父亲1930年代写给他母亲的明信片(在寒冷的布鲁塞尔给您温暖的问候;到奥地利给您打电话!);我父亲从德国寄给在法国的母亲——那时只是他的女朋友?还是未婚妻?——(不知我从英格兰写给你的信你是不是都收到了。收到了吗?)父亲写给家中两个小儿子的(希望你们能听话,收听板球锦标赛广播),宣布他给我搞了些邮票,给哥哥弄了些火柴盒。(火柴盒我倒忘了,只记得哥哥收集橘皮书。)然后是我和哥哥充满少年戏谑意味的明信片。这是我从法国写给他的:“假期以五大教堂完美爆炸开始。明天打算一把火烧掉卢瓦尔城堡。”他在尚佩里给我写的,当时父亲带着他在那儿作学期旅行:“我们安全抵达。除了那些火腿三明治,我们对这趟旅程还算满意。”
我无法确定最早的那几张明信片是什么时候写的,邮票——连同邮戳——已用蒸气取了下来,无疑是给我收集的。不过我发现父亲在写给他母亲的明信片中用了不同的落款:从“伦纳德”,“你永远的,伦纳德”,直至“爱你的,伦纳德”,甚至“爱你吻你,伦纳德”。在给我母亲的明信片中,他用了“皮普”,“你的皮普”,“永远的,皮普”,“爱意浓浓,皮普”和“我的至爱,皮普”:从遥不可及的求爱期开始,直至我来到这世上,情爱日渐炽热,称呼在渐渐变化。我持续关注父亲更换名字的过程。他的教名是阿尔伯特·伦纳德,父母亲和兄弟姐妹称他为伦纳德。等他做了校长之后,阿尔伯特取代了伦纳德,在师生公共休息室他一直被称为“阿尔比”或“阿尔比老弟”,长达四十年之久——不过这可能是源于他名字的首字母缩写,A.L.B.——偶尔又以阿森纳防守后卫沃利·巴恩斯之名被戏称为“沃利”。我母亲并不喜欢这些教名(毫无疑问也不喜欢“沃利”),于是决定叫他“皮普”。此名取自《远大前程》?但他不是菲利普·皮利普,当然她也不是埃斯特拉。在战时,父亲所属的皇家空军驻扎在印度,此时他名字又变了。我有他的两支蘸水笔,当地一名工匠在笔杆上手绘了一幅图像。一轮血红色的太阳悬在光塔清真寺的上方,正缓缓下落,我父亲的名字也在太阳下方:“里奇·巴恩斯,1944年,阿拉哈巴德。”那里奇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又去往了何方?翌年,父亲回到英国,也变回了皮普。他身上的确有一丝孩子气,但是,随着他年龄增至六十、七十、八十,这个名字就越来越不合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