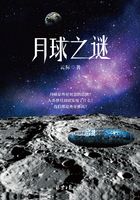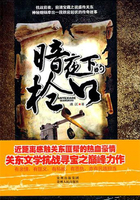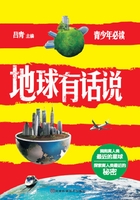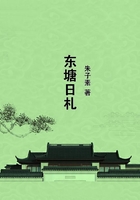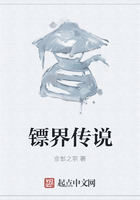——田耳
(自序)
一贯跟别人扯,写小说是不小心,写了,得以发表,再写,再发表,一路纵有波折,硬着头皮挺过来,慢慢地,直到成为职业的写作者。听同行自述生平,也一再重复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写作经历。这样的话,说多了,自己也信。
忽然有一天,一次聚餐,某小学女同学跟我说,毕业纪念册上,她给我留下一行字:祝你成为一名作家!我深深记得有这事,但不知为什么,很多时候,我宁愿忘记。我以为她也早已淡忘,这只是若不经意的细节。那是一九八九年,她十三岁,我一样大小。那年月我觉得世界很大,我们很小,毕业走散,应该就是天各一方。她的毕业纪念册,我这么写: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古诗上扒下来的,以为是很好的句子,回头一想,分明没有吃透句意就贴送他人。读初中跟那女同学是邻班,时常见着面,便有些尴尬,就像去火车站送人,先前已郑重告别,没想到站后却误了点,还得一同返回。而她,祝我成为作家,一语成谶似的,预言了很久很久以后的事。
当然,她祝我当作家,也有前因。小学时我们那班,恰好是作文教改实验班,还起个名叫“童话引路”,该写作文时全写童话。记得当时还闹了不小影响,四年级有一个学期几乎没法正常上课,班主任上公开课,接受电视台采访,我们怀着荣幸的心情予以配合,争抢回答问题的机会。小学毕业之前,全班四十五人,有近九成在公开刊物上发表过童话或作文,有的作文杂志给我们班同学开专辑,一发一溜。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热至烫手,想当作家的人路上随便抓,一抓一把。但当时我写作文并不冒头,记得班上作文写得最好的是两位女生,姓熊,姓黄。班内搞起小作家协会,正副会长好几人,我混上副秘书长。在老师看来,我好歹也算第二梯队人选。我以为她们必将成为作家,而我也希望向她们靠近。后有“神笔马良”之父洪汛涛莅临我班指导工作,摸出一支钢笔,说是神笔。班主任指派,由姓熊女生接收。彼时,在我看来,不啻是一场仪式,宣告她已光荣地成为一名作家。那一刻,我的心里,酸甜苦辣咸,羡慕嫉妒恨。
还在读小学,我就以为所读班级是有专业方向,老师一心要扶植、培养一帮作家。我以为,即使毕业,也有一帮同学内心已揣定当作家的志向,表面上不管如何地不露痕迹,其实这志向已如信仰一般牢固。我们正向着作家这一身份发动集团冲锋,若干年后,再保守地估计,那几位种子选手,总是拦不住。我想象着,若干年后,我们一同以写作吃饭。我以为将来必是这样,从不曾怀疑。想当一名作家,这愿望于我而言来得太早,十岁就有,十多岁已变得坚固。这是很可怕的事,想得多了,纵然只发表三两篇童话作文,我便在一种幻觉中认定自己已是作家。那年月,文青比现在想着靠唱歌一夜成名的愣头青还多,我区别于他们,他们是想当作家,而我知道自己日后就是作家,毫无道理,却毋庸置疑。这种幻觉,使我在任何状况下都不以为然。读书成绩飞流直下,离大学越来越远,没关系,作家不是大学教得出来的;读大专时给校刊投稿未被采用,没关系,校刊的编辑往往肉眼凡胎;毕业后有好几年不名分文,躲家里蹭老,被人嘲笑,没关系,心里默念高尔基《海燕》里的名言: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因这幻觉,身无分文的那几年,我并不觉得苦。现在有记者找我谈谈人生经历,暗示我不妨走一走励志路线,虽然我也予以配合。访谈和小说一样,何尝不是按着一种预设的方向瞎编乱造,一逞嘴瘾?事实上,我能成为作家,不是靠努力,励不了谁的志,现在作家这身份本就跟“励志”两字毫不搭界,整体上沦为不合时宜的人。我是靠一种幻觉的力量,心中总盼着奇迹发生,得以写作至今。我不知道心底向往奇迹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有就是有,隐隐约约,让人时而兴奋,体内产生一阵阵莫名的悸动。朋友老说我一根筋,我将自己干过的事罗列起来,爬梳一番,仔细分析研判,一根筋的情况显然是有。我被幻觉牵引想当作家,幸好幻觉成真,要不然就是神经病。当年,我以为会一同当上作家的小学同学,各有各的经历,都不再与写作有丝缕瓜葛。我不知道他们为何抛开好好的作家不当,去干那些古怪职业,比如老师、医生和领导。反正,只有我一个一条胡同走到黑,竟还看到亮光。所以,那女同学唯独祝我成为作家,估计也了解了我这人一根筋。
不管怎么说,成为作家,于我个人而言,是生命里小小的奇迹,是将文学视作信仰后的一次“应验”。就像乡贤沈从文所说,我怎么创造生活,生活怎么创造我!与生活发生互动的关系,这应是很少人能体验到的美妙。
然后,按照要求,将收入本书的几个中篇做些自我的阐释。我不知道怎样阐释算是博尔赫斯式,什么是昆德拉式的或者李浩式的,我还是愿意信马由缰地说一说,也许这能算我自己式的。收入本书的四篇小说分别为《独证菩提》《友情客串》《掰月亮砸人》和《人记》。我长中短篇都写,长篇自行成书,短篇结一本书就已用完,手头还有二三十个中篇,此前结集成书的仅三分之一左右。剩下二十来篇未结集的中篇里头,挑出这四篇,若要给它们找一个关键词串联在一起,我宁愿使用“奇迹”二字,尽管这是含义宽泛、非常任性的大词。
《独证菩提》原名《一朵花开的时间》,写鲁智深。他的一生,我以花开作比。鲁智深一个浑人,把他喻为一朵花,当时还自鸣得意,时隔多年想想,总觉有些不妥。这小说,是我自作珍爱、自鸣得意的篇什之一。在一篇创作谈中我说到,作者本人对作品的把握,总有那么点阴差阳错,同是自己创作的小说,发表以后,就各自有了命运,有的命好,有的无声无息。说这话时,我头脑想到的正是《一个人张灯结彩》和《独证菩提》。我一度认为这一篇和《湿生活》是自己迄今最好的两个中篇,但只是个人的想法而已,这篇小说几乎没有任何反馈意见。随着写作经验的积累,我知道写反映当下生活的小说,若可以百分制考量,那么写历史题材或者经典重构的,字面上无论如何漂亮,文本结构上无论如何繁复精巧,也只能打八十分到顶。但我还是私爱这一篇,我对我笔下的作品有一套泾渭分明的判断,好或坏,不太好或不太坏,都在脑海里一一摆明。但这对别人未必有用,就像郑庄公寤生惊了老娘,老娘不喜欢这“寤生”,只爱他弟弟。这样的爱与憎,当然没太多道理好讲。而我对《独证菩提》的喜好,是不是也掺杂了太多个人情绪?首先,《水浒传》是我重读最多的小说,各种版本尽量搜全,包括把高冲汉写成武功第一的“古本水浒传”。我还记得,童年时在老家乡村,大家围炉夜话,故事讲来讲去,《水浒传》始终是话题的终结者,没有哪部小说的魅力可与它抗衡。读得多了,最喜爱的人物始终是鲁智深,却不明白他为何叫花和尚。他实在是,呃,一点都不花的。心有困惑,即是动力,围绕“花和尚”三个字,虚构诸多细节,以期与原小说互为印证。我的私爱在于,我写出了信仰的状态。信仰之物也许从未出现,但却不妨碍信仰之境的终身伴随。到最后,写到鲁智深六合寺坐化,我设想着他“听潮而圆,见信而寂”,随着钱江潮消逝于海天之间。鲁智深坐葫芦漂于水上,眼见诸多曼妙画面,有朋友认为是人死之时的幻觉。我表示认同。人总是天生害怕,回避死亡,忽有一天,奇怪地,忽然正儿八经考虑自己如何面对死亡,应如何修炼那一刻的心境和态度。这恰是人之异于动物的几微之差。终于明白有些事无可逃避,对奇迹的期盼才显如此重要。
《掰月亮砸人》大概要算我迄今为止,将故事写得最复杂的一个中篇,有些文友看得头皮发麻,没能撑到底。这故事看似玄虚,却有原型,一直流传在我老家都罗寨。说是解放前,当叫花子的韩宗玉曾去辰溪煤矿做工,因坍塌事故困于井下,两个月后竟奇迹般生还。我记得当时说起这事,后辈有人就怀疑,宗玉叫花子是不是在矿井下面生吃人肉,得以保命。这样的怀疑一下子打开我想象的空间,有些人信有奇迹,另一些人却怀疑事事必有因果法则。这一信一疑的出入,本就不可调和,是为生活中诸多烦恼的缘起。但我做了夸大处理,成人间剧烈的冲突,写到最后,变成一个少年的成人礼。我自己喜欢这个变形的过程,这个环环相扣的故事,到最后被我敞开,少年怀揣着情窦初开的悸动,步入尔虞我诈、险象环生的成人世界。我知道,即使成年以后,偶尔心情大好,脚底下不经意踩出一溜跑跳步,一旦意识到,马上停住,环顾四周,怕别人看见。我们为何将跑跳步视为失态,将麻木不仁视为得体?我们都是这样的人。
《人记》本想影射一名时常现于屏幕,喜好扮成大师模样的作家,没想发表以后无人看出。可能,现在的小说已经日益缺少暗通款曲的玩法,简单粗暴成为必然途径。既然无人看出,这一篇我自己多说,又有何益?只想说说,《人记》中的“人记”这概念,没有出处,完全杜撰出来,是受汪曾祺《异秉》一篇的影响。我知道,每个人都暗自怀有期待,天降大任于己,体内定然藏有不凡禀赋,会通过一次奇特的、仪式般的行径,突然开启,转眼间,自身就变得光芒万丈。韩瘤子和十一哥这样的土匪,也有这样的自命不凡,杀人越货,也仿佛是天意颐指,不得不为。所以十一哥对韩瘤子死亡的求证,不需任何理据,只为自我开释。有些人愿意被“奇迹”牵引,心生信力;有的人自以为与奇迹同在,其实什么也不肯信。
《友情客串》,富家女子苏小颖有“救风尘”的情结,而她的穷闺蜜葛双并不买账。为了弥合彼此之间的距离,苏小颖有了友情客串、当一把妓女的冲动。在葛双看来,苏小颖的一切行径都是纡尊降贵,居高临下,这也是彼此真正的间距。既然苏小颖有心客串,葛双也乐得将计就计,一切都在她的算计中,毛大德将替换郑来庆,使得苏小颖的“客串”变成一次真正的卖身。于是有了粉哥豺狗子阴差阳错的“救风尘”之举。在我们生存的当下,很多人拿着钱兑换感情;苏小颖对郑来庆明明心存好感,却要将这好感“象征性”地兑换成钱。这个中篇人物众多,唯有苏小颖,是相信奇迹存在的。苏小颖飞蛾扑火般想去拯救他人,最终达成心愿,同时竟还保全了自身。这在葛双、毛大德、马桑、豺狗子构成的边缘社会里,无疑就是一场奇迹,只是,这是一种苦涩的奇迹,在苏小颖的视线之外,有了太多辛酸的铺垫。犹如我们抗争生活这无物之阵,纵有胜利,常是惨胜;纵有奇迹出现,人也不再敢于相信。
当然,这样的自我阐释,有太大的随意,如果以“奇迹”两字统摄串联,我如是说,你给我换一个词,也许我照样洋洋洒洒地说一通。这正是我吃饭的本事,似是而非本就是小说家的惯技。只是,对写下的小说进行一番自我阐释,心情总不免古怪,往往也是遵嘱而为。我宁愿自己总结得不准确,甚至让人不知所云,以印证读者本人的客观公允。小说家就是这样一种矛盾动物,要让人信,同时又要让人在信中生疑,疑窦中又生成更彻底的信。前一个“信”只能算是小说家的本事,最后一个“信”才见着能力高下。
如果我这小序能有导读作用,你翻开书连带小说一并看了,也许说,你这人,从小敢当自己是作家,一俟写出来,也就这么些玩意!我以何对焉?只好说,呃,你毕竟还看了。这年月看小说的还没有写的多,你能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看一看,鄙人已是感激不尽!
马尔克斯说,小说里头,时常抛出一些细节,犹如往地上扔西瓜皮,等着看评论家踩上去。我知道,这是他写作时巨大的快感。鄙人不才,也有相似的经历。在访谈中,我曾说过,写小说以来,年年给沈从文烧纸,求得庇佑。没想这样的细节,更能引人注目,以后每次访谈,对方常常要扯出这事,要我再次发挥。也有的问我到底信不信,我只好说,这是自我认信,越是信它,越能平添一股力量,何乐不为?一烧十几年,现在若不坚持,心里会发毛,怕来年写不出东西。这样的话,我瞎说说,别人随意听听,爱信不信。但我确实暗自地问:你真的不敢不烧,害怕才思枯竭?既然有此一问,某一年我真就没给沈老烧纸。事实是,那一年东西照样写,小说照样发,除了我本人,谁又知道我当年有没有去沈从文墓地烧纸?谁又真正在乎?不去给沈老烧纸,我也很容易找出别的招数代替,比如找一找当年算准我要当作家的女同学,请她再算一算,今年鄙人文运如何。不要指责我不够严肃。在我们生存于斯的,一切难以具名、一切难以指称的奇葩时代,即便要厘清何为严肃,也并不容易。
小说家言,当不得真。我敢不去烧纸,是认定沈从文是小说家里罕有的好人,他不会跟我计较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但那一年,心底确实战战兢兢,随时想着,要是情况稍有不对,一连半月写不出一个字,赶紧去沈老坟头多烧几刀,求得宽恕。走夜路多了会撞上鬼,我们写小说的,虚构为业,杜撰谋生,时不时也该把自己绕进去,大概才算职业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