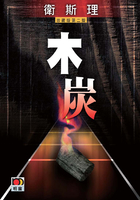敖德斯尔 著
斯琴高娃 译
敖德斯尔
蒙古族,1924年生于赤峰巴林右旗。1948年开始蒙汉双语文学艺术创作活动,出版有长篇小说、中篇小说、散文、文艺理论以及话剧、歌剧、电影文学剧本等多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共三十本,蒙、汉文共计八百余万字。
斯琴高娃
蒙古族,1933年生于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中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作家协会理事。从小爱好文学,与丈夫共同创作了《骑兵之歌》等长、中、短篇小说,蒙译汉作品有《新春曲》《老车夫》《含泪的笑声》《风,在草原上吹过》等,其中《小钢苏和》《骑兵之歌》等多次获奖。
杏花开了,又谢了。
一朵粉红色的花落在我的袖口上,乍一看那形态、那颜色似熟悉,又像是个模糊的痕迹。这朵花,忽然在我人生长河中泛起一连串回忆的涟漪。往事如烟,已飘散去不少。那荷包的颜色已记不清了,可绣荷包的人,却异常清晰地从我心底浮现出来。
那是个我家乡的牧民常常掖在腰带上的烟荷包。记得我的那个烟荷包上绣着一朵盛开的桂丽森花[1],花绣得并不精致,但是她拿自己的心绣的。可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对它渐渐疏远、淡忘,不知什么时候,我却把它丢了,当然把她也忘了。现在,这偶然落在身上的一朵花,把一连串时而喜悦时而忧伤的首尾不相衔的岁月连接起来了。
我管她叫桂丽森嫂。她比我大三岁,年轻的时候,她很秀气,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她一双打动人心的黑眼睛和嘴角一对深深的酒窝。但她和一般漂亮女人不同,在她那清秀的容貌中有一种粗犷、热烈,近乎刚强的力量,这就是她的个性。
桂丽森嫂嫁到我们浩特[2]达赉哥家的时候,我是个十分淘气的十五六岁的孩子。那次热闹非凡的婚礼,眼花缭乱的宾客,头上蒙着红头巾的新媳妇,激起了我多么大的好奇心啊!后来,犍牛一般结实的达赉哥在去草原牧民称为母亲的额吉渚尔盐池拉盐的路上,突然得急病死了。噩耗传来的那天晚上,达赉哥的母亲和桂丽森嫂的哭声,揪人心肺,连我都感到了撕扯般的痛楚。
达赉哥留下了两个女孩,大的三岁,小的才一岁。
后来,听浩特里的人们说,达赉哥去世一周年后,桂丽森嫂的娘家人曾来接她回去,可她终因扔不下孤身一人的婆婆而留了下来。
就这样,她情愿用她那纤弱的身板支撑起一个有老有小的毡包,刚过二十岁就开始了人类生活中最难熬的寡妇生涯。
游牧民族的生活条件是很苦的,如果没了男人,就意味着苦上加苦,那看不到尽头的凄苦日子,渡不完的难关,干不完的繁重劳动,必须每时每刻都要付出不屈不挠的努力才行。没有经历过这种生活的人想象不出它的凄苦和磨难有多么深重。我看见她从早到晚马不停蹄地干活儿,心里很可怜她,我也常常看见她门前的马桩上拴着各种各样的马,可是从来没看见过有人帮她干活儿。
开始,尽管生活的担子那么沉重,却还没有很快就把桂丽森嫂那年轻、充满活力的双肩压弯,也没有能压抑住她活泼开朗的天性。每当春暖花开,或秋风吹拂的季节,全浩特的人每天都听见桂丽森嫂那圆润而悲哀的歌声。她是我们那一带最有名的歌手,无论谁家嫁姑娘娶媳妇都缺不了她。
那时的我,正处在朦朦胧胧寻找爱的阶段。开头,我只是喜欢听她的歌声。那歌声,有时能唤起我的莫名的冲动和莫名的烦恼,有时又带给我青春时代的芬芳和无尽的遐想。后来不知是什么时候,我开始怀着一种说不清的情感去关注她的生活了。每当我拖着套马杆放牧的时候,或者早晚牵着马去河边饮马的时候,我的目光总是有意无意地向浩特东头的一顶篱笆围墙的蒙古包望去。那时候,桂丽森嫂头上的红头巾,就像熄不灭的一团火一样,起早贪黑,不停地飞蹿在绿色的草地、静静的河流和尘土飞扬的畜群中间。
我每天都想看见她,想和她说话,把心中对她的喜爱,用眼睛表达给她。可是她总是忙碌着,没空注意到我。我偶尔进她家蒙古包的时候,她总是在篱笆小院里里外外团团转着,伺候着她的几头犹如儿女一样的羊羔和牛犊。有时饭菜都凉了,也顾不得进来吃喝。她那年老多病的婆婆总是坐在图力嘎[3]西边那张沾满粪土的牛皮上,不是哄孩子,就是闭眼念玛尼经[4],从来不出门,也不说话。
秋分以后的一个天高云淡的下午,阳光照彻了金色大地,清凉的秋风吹拂着河岸上的芦苇。我饮完马群回来的路上,远远地望见一个小小的红点,在一辆拉青草的牛车旁忽隐忽现。啊!那不是可怜的桂丽森嫂一个人在那里拉草吗?这时,我似乎闻到了开放在草原上的野菊的芳香。我立刻调转马头,向那个野百合一般的小小的红点驰去。
桂丽森嫂把牛车停在晒干的草垛旁,刚刚装完一车草,正在满头大汗地拽着捆绳,想把装得高高的草捆得更结实些。我来到牛车旁,先把马绊在离草垛较远的地方,去帮她拽紧捆绳,拴得结结实实。
“到底是男子汉有力气呀!”
桂丽森嫂拿腰带的一头擦着红通通的脸,笑着说。她那好看的大眼睛,在强烈的阳光下眯成了一条缝,一排洁白的牙齿闪闪发光。
我见她打了那么多青草,心里很佩服,又有点心疼,不由自主地拿自己的前襟,向她扇着风,说:“桂丽森嫂,你真能干!一个妇道人家打了这么多草,又是一个人装车,一个人拉,也够辛苦的啦。”
“唉!有啥办法呢,”她亲切地瞟了我一眼,继续擦着汗,低下头说,“养活一家老小真不容易呀!”
看着她那被风吹日晒而变得越来越粗糙的脸和满身尘土草屑,我心里好难受。这时,在心灵深处隐藏了很久的、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强烈的感情涌上了心头。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一下猛扑过去,不顾一切地、紧紧地抱住了她。
“别……别这样……”她轻轻地推着我,带点羞愧的目光移向别处。紧接着,一种轻微的踌躇闪过她的脸。这时,她那俊秀脸上的一对深深的酒窝,显得更好看了。亮晶晶的大眼睛,忽闪忽闪地左右看了之后,把宽宽的前额贴在我的脸上。
我顿时心情紧张而又有点迷惘,一种无法抑制的冲动使我更紧地抱住了她,疯狂地亲吻她那烧得红通通脸蛋的时候,她紧张地呼吸着,把眼一闭,伸出双臂搂住了我的脖子。
……
从那次以后,我的整个心思都飞进了桂丽森嫂的毡包,有事没事总爱往她家跑,当然有时也帮帮她的忙,更多的时候都是因为需要她。
大约过了几个月,在一个寒风刺骨的夜晚,我来到桂丽森嫂家。那四面透风的破毡包里那么冷,就跟外面差不多。可是,她把自己结婚时候穿来的唯一的好皮袄盖在她婆婆和小女儿身上,自己却蜷曲着单薄的身子,冻得浑身发抖。她钻进我那冬天下夜的马倌穿的宽大的皮袄里,紧紧地抱着我,告诉我:“我怀孕啦。”
“啊!那……那怎么办?”我慌了。
“到时候就生呗,有啥别的办法。”她没有一点抱怨的语气,那么平静而坦然。
“又多了一张嘴,这对你来说,是个多大的负担啊!”毫无思想准备的我感到意外。我语无伦次地叨咕着,想着她本来就累得喘不过气来的生活将又增加新的负担,心里真有些过意不去。
桂丽森嫂似乎觉察到了我沉重的心情,沉默了好一阵,说:“没什么,哪个女人不生孩子!老佛爷让我受着,我就得受着,你别替我操心了,天不早啦,睡一会儿吧。”
大约又过了两个月时间,我参军离开了家乡。临走前的一个傍晚,我在河边饮马的时候,头上戴着红头巾、身穿深蓝色长袍的桂丽森嫂挑着水桶,迈着飞快的步子向河边走来。我已经意识到桂丽森嫂这几天时刻都在注视着我。临别时应该和她打个招呼,也算是告别吧。所以尽管我的马早已喝足了水,但我仍在磨蹭着、等待着。她来到河边放下水桶和扁担,掏出一个拳头大的小包,塞进我手里,问:“啥时候走?”
“后天。”
“啥时候回来?”
“不知道。”
我打开小包一看,是个绣着杏花的烟荷包,里面还装着一袋旱烟。我知道,蒙古族妇女往往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深情。我用颤抖的手捧着它,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滋味儿。
“这两天我心里难受,老是睡不好……”她看着那烟荷包说,“羊油灯下,连针尖都看不见,绣得挺难看,可是我……”突然间,她的眼圈红了,两滴亮晶晶的泪水顺着她的脸滚下来。
我僵立着,不知所措,同时又感到羞愧难当。对着这样一个女人,这样一颗真心,我只觉得胸口被什么冲击着,猛烈疾跳,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借着枣红马的阴影,把双手放在她肩上,轻轻地抚摸着。
她抬起头:“祝你平安!”
然后她挑起水桶,脚步沉重地离去,去得踉踉跄跄,很不稳当。
我手里握着那烟荷包,伫立了很久很久。
革命的狂风暴雨的年代,对一个刚刚远离家乡和亲人的骑兵战士来说,烟荷包寄托着思念家乡和亲人的感情。我把这绣花的烟荷包珍藏在日夜不离身的子弹袋里,单独执行任务或一个人站岗放哨的时候,常常拿出来看一看,摸一摸,思绪会飘回故乡,回到她的身边。
如果不是经过了那么漫长而坎坷的岁月,后来当了干部,娶妻生子,有了一个温暖的家庭,我也许会永远保留着那个绣着美丽的杏花的、绣着深厚感情的烟荷包。但是我终究把它给丢失了。我一再升迁,并且总是调动,工作一直很繁忙,说不清从什么时候,那烟荷包和绣它的人终于从我生活里彻底消失了。
过了好多年之后,我第一次回老家探亲。回到故乡,冷不丁儿想起了桂丽森嫂,于是想去看看她,不管怎样,过去还有过那么一段。
当我打听到那微微歪斜的、换成柳条围墙的蒙古包就是她家后,不知为什么,却又有点局促不安。在包前停立了一会儿,还是鼓足勇气,轻轻地叫了一声:“看狗。”
从蒙古包里走出一个穿戴破旧的妇女。看见我,站住了。最初的一刹那,我怀疑自己找错了人家!站在我眼前的这个中年妇女,无论从肤色、体形、服装到气质,哪方面都找不到一点当年那吸引过我的桂丽森嫂的影子。
她掩饰着激动,扯动着僵在嘴角的微笑,语无伦次地说:“哟!是丹毕……快进来,快进来。听说你回家来啦……啥时候回来的?”
是她!还是原来那清亮的嗓音。可是那一对好看的酒窝已经拉长了,变成了两道深深的沟纹。
“一走就是十多年,老不回家来。”她边看狗,边把我领进蒙古包里。
“坐!北边坐!你还是原样,比过去白了,也胖了。”
她渐渐恢复了平静。我的到来,使她憔悴的脸顿时容光焕发。她热情地忙碌着,为我熬茶。
我看着包门口站成一排、衣衫褴褛的孩子,问:“这么多孩子,都是你的吗?”
她点点头,把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儿拉到自己身边,亲昵地抚摸着他灰扑扑的脑袋,意味深长地笑:“你看,我这儿子多帅!你还记得吧?……他是你走的第二年春天生的。”
我怎么不记得呢?我仔细端详着长相仍有熟悉之处的那个男孩,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情在涌动。
她拿出几块奶豆腐,分给每个孩子一块,孩子们一哄而散。
“这孩子多像你呀!我给他起名叫阿木古郎[5],祝福他阿爸不管走到哪儿,遇到什么事儿都能平安无事。这不是,你平平安安地回来啦!”
我愧疚地低声说:“我……我已经成家了,还有两个孩子。”
她温和地抬起头,看着我说:“我听说啦!男人们都是这样。”
她的话虽然平静、温和,却像针一样扎得我心里疼灼起来。
在她出去拿烧火的干牛粪的工夫,我才敢抬起头仔细看看她的家:包内空空荡荡,一贫如洗。除了日常生活离不开的一些锅碗瓢盆之类杂物外,只有几件单衣和皮衣整齐地叠在哈那[6]底下,连个毡褥子都没有,那贫困是显而易见的。草原上的寡妇真的太苦了!
桂丽森嫂给我盛了一碗没放奶子的黑茶,脸上带着不好意思的神色,难为情地说:“你看,我这个日子过得,客人来了,盛的跟白开水差不多的黑茶,唉!”
“有多少牲畜?”
“一头乳牛,今年没下犊,还有五六只山羊,在我娘家的羊群里。原来的那匹老毛驴早就死啦。”说着,她伸手搂住一个两岁左右的小姑娘,擦掉她的鼻涕,亲了又亲,高兴地说:
“以后他们长大了,我就不困难了!我的孩子要养活阿妈,是不是?”她还是那么温和低笑着,继续亲着孩子说,“现在,我包里的孩子越来越多,圈里的牲畜越来越少。一个女人养活十来口人,真不容易呀!我的大女儿在她舅舅家帮忙,二女儿在牧主家看孩子。”她点燃了我给她的一支香烟,望着缭绕的烟雾说,“我也心疼她们,小小年纪……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得些报酬吗?”我怕她听不懂,解释说,“就是给点什么不?”
“哪有!就给饭吃,有时给一件旧衣服什么的。不过,少两个人吃饭,这对我来说,减轻不少负担啦。”
她没有悲伤,没有怨恨,没有不满,总是带着宽慰的微笑,时而回忆昨天的噩梦,时而叙述今天的苦难。我从她那单调而平缓的声音中感到潜藏着的深深的寂寞和哀凉。我的眼前突然闪现出那拴在她家马桩上的各种各样的马。这些年来,她就这样艰难地生活着。作为一个健康的年轻女人,只是为了过一个正常人最起码的生活,付出了多么艰巨的、超乎常人多少倍的努力啊!而我们这些男人……我感到无地自容。
我默默地凝视着她那增加了许多皱纹、同三十多岁的妇女一点不相称的脸,不知该说什么好了。我显得有些局促不安,只觉得自己对她和那个穿破烂衣服的小男孩欠下了还不清的债,犯下了赎不完的罪。
当我离开她家的时候,她倒像做了一件对不起我的事似的,一再难为情地说:“我没有想到你今天来看我,没有一点准备,没法好好招待你啦。”说着,从那已经看不清原色的黑柜子里掏出了一块不知保存了多长时间的干奶豆腐,硬往我大衣口袋里塞,“拿去给你的孩子们尝尝吧。”
那个真诚的热情,使任何人都不能拒绝。这时,我才遗憾地想起,来的时候给桂丽森嫂和她的孩子们什么东西都没带,哪怕是一包点心,或者一条香烟呢,唉!
我终于没有说出一句自责的话,就向桂丽森嫂告辞了。我觉得,比起她所付出的,无论说什么都是卑微的。
又过了许多年,到了“文革”期间。我被打成“走资派”,进了“牛棚”。
有一天,我从“牛棚”门缝看见有几个穿蒙古袍、戴红袖章的人在单位革委会办公室门口吵吵嚷嚷,跟工宣队头头辩论着什么。我隐约听到一个大嗓门在喊:“你们为什么不解放干部?为什么不落实‘5·22批示[7]’?”
接着,那几个穿蒙古袍的来到门口,嘭的一声踢开门,一个穿长筒马靴的高个儿小伙子喊了一声:“谁是丹毕?”
“是我!”我老老实实地站起来。觉得这帮外调的又要逼我揭发什么人吧。
那小伙子伸着手走过来,出乎意料地握住我的手说:“我是从我家乡来的,叫阿木古郎,是桂丽森的儿子。”
“噢……你小的时候……我见过你。”我注视着对方充满青春活力的面孔,想起了他母亲说过的那句话:这孩子多像你呀!
小伙子紧紧握着我的手,故意大声说:“你家乡的贫下中牧都说,你出身成分好,没有政治历史问题!你们单位的造反派反复去外调了好几回,什么都没捞着。”接着他压低声音说:“我阿妈告诉我,到城里一定要找到叔叔,看看他身体怎么样?”他略微一顿,问,“你……受伤了没有?”
“受了一些,可现在好啦。”
“那好,多保重!”说完,他从手提包里拿出一瓶黄油放在小桌上走了。
“谢谢你……阿妈,谢谢家乡的乡亲们!”我用颤抖的声音说着,深深地点头跟他告别,我目送着他,不由得眼睛湿润了。
在那些蒙受冤屈的凄苦日子里,第一次有人说这样令人全身热烘烘的话,这些犹如一团火的话,是怎样温暖了一颗备受凌辱的心啊!并且一直到从“牛棚”出来,这团火每日每时都燃烧在我的心里,使我有了勇气和信心,不再感到凄惨无助,不再感到永无出头之日。这时候,我想得最多的是桂丽森嫂,同时又猛然想起了她送给我的绣杏花的烟荷包。从“牛棚”出来后的头一件事,就是找那个荷包,可是翻遍了所有可能放的地方,也没有找到,我感到很遗憾!
又过了几年,有一天中午突然来了一位陌生的漂亮姑娘找我。她是桂丽森嫂最小的女儿,长得跟她母亲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如今她考上了内蒙古大学,是经过这里去呼和浩特。她给我带来了一件羊皮背心,说她母亲已经去世了。这是她临死前让女儿带给我的一点心意。
我用颤抖的双手捧着桂丽森嫂亲手缝的羊皮背心,思绪万千,不由得又想起那个不知什么时候丢弃的绣杏花的烟荷包……
1992年1月
注释
[1]桂丽森花:蒙文音译,杏花。
[2]浩特:蒙文音译,一户牧人家。
[3]图力嘎:蒙文音译,烧火的铁架。
[4]玛尼经:藏经的一种。
[5]阿木古郎:蒙文音译,平安。
[6]哈那:蒙古包毡壁的木质支架。
[7]5·22批示:指1969年5月22日毛主席关于内蒙古所谓挖“内人党”扩大化的批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