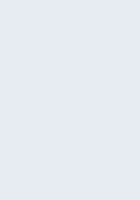淳化元年(990年),苏州吴县人范墉,病故于徐州节度掌书记任上。
范墉生前娶有两房妻室,共生五子。正室夫人陈氏生有四子,长子夭折。次子范仲温,三子范仲滋(后来进士及第,但未入仕便病故),四子夭折。
范墉之妾谢氏,生有一子,名范仲淹,此时方满两岁。
昨日,是范墉七七忌日。
今日午后,陈氏夫人端坐在前堂,吩咐侍女招谢氏前来。
谢氏正躲在自己的房里暗自悲伤,老爷说走就走了,不曾留下只言片语。老爷在时,夫人就对她冷眉冷眼的,如今老爷不在了,还能容得下她母子么?她看着怀里儿子熟睡的脸庞,心里一阵酸楚。
“谢姨娘,夫人叫你去前堂。”侍女在门外直着嗓子喊。
谢氏抹了眼泪,把儿子轻轻放到床上,盖上被子。她悲哀地想,真是人走茶凉,老爷七七刚过,范家仆人对她的称呼与说话的方式都变了。
她就着盆里的冷水洗了把脸,对着镜子梳了发髻。她不想让陈氏看到她的悲伤,或者是狼狈,她换了身干净衣衫来到前堂。
陈氏一双饱含怨毒的眼睛紧盯着谢氏,她忌恨眼前这个女人,虽然生的儿子也有两岁了,可她依然面目姣好明妍,身段窈窕丰盈。老爷在时,她虽妒而不敢言,如今老爷死了,看你还能靠谁!
谢氏上前施礼,陈氏半天不语,只盯着她看,让她心里发怵。她不知道等待她的是什么,但她心里明镜似的,她母子二人的命运就握在陈氏手中。
陈氏从衣袖里抽出帕子,揩了揩那不曾流泪的眼睛,哽咽道:“妹妹,你说咱姐俩怎么就如此命苦?老爷说走就走了,一句半句的热心话都不曾留下,咱孤儿寡母的,这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
这句话正中谢氏的心坎,她热泪长流,哭倒在地。
谢氏正哭得伤心,耳边却响起陈氏冷冷的声音:“我说妹妹,你也别哭了。老爷走了,你就是哭倒长城也哭不回老爷来。”
谢氏停了哭泣,脑子里嗡嗡地响,一片混乱。
陈氏又道:“我看妹妹还年轻,模样儿又周正,不如趁早寻一家好人家嫁了,也好把孩子拉扯大。”
谢氏抬起一双泪眼,惊恐地望着陈氏:“我是范家媳妇,老爷走了,我理当守节,如何能再嫁?”
陈氏心里冷笑:你倒是贞节得很!这个家可是我跟着老爷一手积攒起来的,岂能容你母子俩坐享其成!口中却抽泣道:“老爷这一生官小位卑,又不曾利用官职搜刮钱财,也无大宗的遗产留下。你也看见了,就这么一点家当,与其大家在一起饿死,不如妹妹带着仲淹另择良家,求条活路,也好让孩子长大成人。”
谢氏哭泣着摇头。
陈氏道:“妹妹,你不想自己,也该替孩子着想不是?”
想到孩子,谢氏哭得更伤心了。
陈氏厌烦地皱了皱眉头,却依然耐着性子细细说道:“妹妹,不是姐姐心狠,实在是家道不好。前儿我娘家嫂嫂来看我,说有个淄州长山人,去年没了妻子,正想续弦。我叫嫂嫂托媒人去打听,原来这人还是个县令,也还忠厚老实,虽然前妻留下两个儿子,你过门了就是正室夫人了,仲淹跟着你也不会吃亏受苦。”
谢氏听陈氏把话说到这一步,便停止了哭泣。老爷刚过七七忌日,她就为自己找好了人家,可见她要赶走自己的决心是何等的坚决。再哭,再求,也无济于事。
陈氏见她不哭了,满脸堆笑:“妹妹,有道是,择日不如撞日。那长山人过几日便要赴澧州安乡(今湖南省安乡县)上任了,你今日就过去,再随他一起赴任,岂不好?”
谢氏站起身,心绪茫然。她不知该说什么,是道谢?还是道恨?二者都不合适。既是要离开这个家,还在乎是今天、是明天?还管它是吉日、是凶日?此刻,或者往后,她心里只有一个牵挂,那就是她的儿子,她的小仲淹。
她回到自己的房间,儿子早醒了,见了她,一头扑进她怀里,仰着稚嫩的脸连声唤道:“娘,娘。”
她捧着儿子的脸,含泪道:“娘在这儿呢!”
陈氏的侍女在门外道:“朱家的轿子来了,在门外候着呢!夫人吩咐了,你可以带走自己的随身衣物,还有仲淹少爷的随身衣物。”
她听懂了言外之意,除了自己和儿子的随身衣物,她不能带走这里的一针一线。但她拿定了主意,她可以不要任何贵重的东西,却一定要带走那张琴。
谢氏背着包袱,牵着儿子的小手出门时,有一个中年女子已等候在轿子旁边。她没有回头,因为她知道不会有人来送她,这样或许更好,她也好,儿子也罢,从此与范家再无瓜葛。
陈氏的话不假,淄州长山人朱文翰果然忠厚老实,娶了谢氏进门,以正室相待,并将谢氏两岁的儿子仲淹改名为朱说,带往澧州安乡任上,视同己出。
谢夫人眼里没有眼泪,她平静地讲述着,似在说一个年代久远的与自己毫不相干的故事。
朱说坐在母亲身边,如老僧入定。他的思绪似乎凝固了,又似乎在某个不为人知的地方游弋,让人琢磨不定。
谢夫人见儿子痴痴呆呆的,心里涌起一股难以言明的愧疚。她凝视着儿子那张轮廓分明的脸,微蹙的眉头,深邃的眼睛,还有挺直的鼻梁,这张脸太像他的生身父亲了。
谢夫人不知是该庆幸,还是该担忧。在这张青春的脸上,作为母亲,她看到了儿子过早的成熟与刚毅,还有几分她不愿看到的,却真真切切地刻在儿子额头上悲天悯人的忧愁。
“夫人,少爷,喝口水罢。”不知何时,香草送了两碗茶进来,轻轻唤道。
朱说如梦初醒,他起身离开座椅,跪倒在母亲脚边:“娘,孩儿今年已有二十二岁,本应娶妻生子,侍奉双亲。无奈孩儿心怀天下,仍需继续求学,不能孝敬于母亲膝前,请饶恕孩儿的不孝之罪!”
谢夫人心悸地问:“你,你要去哪里求学?”
朱说没有回答,而是转向香草。他依然跪在地上,拉了香草的衣袖,流泪道:“香草姐姐,请你好好照顾我娘,我娘这一辈子不易。我以十年为期,十年以后,我一定来接我娘,也报答你的恩情!”说毕,起身回到自己的住处,收拾衣物书籍。
不知何时,朱诚站在他身后,小声问:“你真的要走么?真的要离开朱家?”
朱说没料到,朱诚会来问这个问题。他盯着他的脸,心里猜测着:他是来取笑我,还是来挽留我?但他在朱诚眼里看到的是坦诚。
朱说笑道:“我要去求学。”说出这句话的同时,他已经解开了与朱谆朱诚两兄弟的怨结。
朱诚低头道:“方才,我与谆哥听到了你跟娘的谈话。谆哥不好意思来,叫我来请你留下,不要离开朱家。”
朱说点点头:“谢谢你们的好意!走,我是一定要走的,但我也必定会回来接我娘。十年之内,还请你们好生看待我娘。”
“说儿。”谢夫人在门边唤道,朱诚见了,忙退了出去。
“娘!”朱说迎上去,扶母亲进屋,见母亲手中捧着一件物事,正欲询问。
谢夫人走至桌边,把手中捧的东西轻轻地放在桌上,取下外面的黑色布套,一张乌木古琴出现在朱说眼前。
他惊叫一声:“琴!”
谢夫人抚摸着古琴:“这是我当年从范家带出来的唯一的东西。当时,大太太已经吩咐下人传话给我,不准带走范家的一针一线。我不明白她为什么又让我带走这张古琴,如今想来,她或许是想把你父亲最喜欢最珍爱的古琴留给你罢。她的心,还是善良的。或许范家的家境是真的不好,是为娘错怪她了。”
朱说抬手轻轻触动琴弦,说不出心里的滋味。
谢夫人又把琴衣套上,边系带子边说:“这张古琴,你带在身边,你是范家之后,却是朱家养大的。你的天性像极了你的生父,认定了的事情,必定会坚持到底。你要离开朱家,娘不拦你。但你也要记住,为民也好,为官也罢,最要紧的是先要做个顶天立地的人。你的生父、养父都是这样的人。”
朱说道:“孩儿谨记娘的教诲!孩儿也会记住养父的养育之恩,教导之德!娘!孩儿走了,十年之后,必来迎接娘亲,侍奉于膝下!”说毕,担了琴剑书囊,头也不回地出了朱家大门。
朱说走至村口,忍不住回头张望,见母亲依然倚在门前那株桂花下,单薄的身影,显得那样的无助而孤独。霎时,两行热泪夺眶而出,他负气出走,心里并不知该往何方而去。
前路茫茫,朱说孑然而行,思绪混乱。一只鸟儿鸣叫着掠过他的头顶,飞进前面的山林。
他蓦然想起,醴泉寺方丈曾经说过,自景德年间起,朝中执宰大臣不下十人,其性格不一,人品各异。内中最受人称道的当数李迪了,此人学识渊博,且公正严明,疾恶如仇。
李迪是濮州鄄城(今山东鄄城县)人,自幼聪慧,博闻强记,胆识过人。青年时,曾揣着自己的文章去拜见当时的名士柳开。柳开读了他的文章后,非常惊讶,对他说:“读君之文,须沐浴始敢见。”(宋代邵伯温《邵氏闻见录》)
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三十五岁的李迪举进士第一,钦点状元。入仕后,曾在多处任地方官,两度任宰相,因性格耿直、刚正不阿而得罪当权奸臣,多次遭贬谪。如今正通判兖州,以右司谏知郓州。
朱说一路走一路想,当年,李迪能去见柳开,今天,我为何不能去见李迪?我虽没有好文章作为进见之礼,但若能请他指一条读书之路,也不枉了我这次负气出走。
他为自己这一想法兴奋不已,振作精神,整理了琴剑书囊,往郓州而去。
李迪接见了远道而来的朱说。
当年,他在朝中任宰相时,门庭若市,慕名找他的人络绎不绝。而今身遭贬谪,门庭冷落,居然有人求见,心里不免有几分诧异。
他眼前的朱说,虽衣着简朴,却干净利索;虽身材清瘦,却不减英武之气。那张轮廓分明的脸上,一双漆黑的眸子,透着睿智和刚毅。
李迪暗暗称奇,心想:此人万万不可小觑了!
朱说见李迪温文尔雅,和蔼可亲,便将自己的身世与想读书的愿望一一相告。
李迪思索片刻,盯着朱说眼睛问:“有朝一日,你若金榜题名,将何以为官?”
朱说挺直背脊,双目炯炯,不紧不慢道:“有朝一日,小生若能金榜题名,入仕做官,应清正廉明,奉公守法。以天下为己任,置国计民生为首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好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李迪拍案而起,连声赞叹。兴奋开心之余,忙唤家人快快准备酒菜,他要与朱说一醉方休。
席间,李迪侃侃而谈,向朱说介绍了一所读书的好去处。
大宋朝的政府机构设施,从朝廷到地方,是相当紧密而繁复的,而能供求学者读书的地方,除了朝廷设立的国子监,民间没有一所正规的学堂。
国子监是宋朝的最高学府,又称为国子学,七品以上的朝廷官员子弟,方可入国子学读书。可见,国子学是达官贵人的学堂,民间百姓的子弟望尘莫及。而国子学的学生,大多都徒有其名,并无真才实学。
民间的有志之士子,若想步入仕途,取得一官半职,便要有丰富的学识,才能通过科举考试。于是,民间便有了私人设立的聚徒讲授的场所。
南都应天府,秦时设置为睢阳县,唐时为宋州。宋太祖曾为归德军(即宋州)节度使,登基后定都宋州,国号为宋。
至真宗景德三年,宋真宗感念太祖皇帝“应天顺时”创建大宋,便将宋州改为“应天府”。
早在五代的后晋时期,儒生杨悫在归德军赵直将军的扶持下聚众讲学,赵直将军为其建书舍数间,称为南都书舍。因为南都书舍在睢阳县,人们又称之为睢阳书舍。
有位叫戚同文的,出身于儒学世家,幼时父母双亡,随祖母一起寄养于祖母的娘家。在当地,戚同文虔心侍奉祖母,以孝闻名。祖母故去时,戚同文日夜悲泣,数日不食,乡邻颇为感动。
南都书舍初办之时,戚同文投学而来,杨悫听了戚同文的身世,见其求学心诚,便收留了他。天资聪颖的戚同文,刻苦向学,长期衣不解带,仅仅一年工夫,竟熟读五经,深得杨悫的器重,并将妹妹许配给他为妻。
时值后晋末年,天下混乱,赵直劝戚同文入仕途,造福于天下。戚同文立志不去做官,却希望天下统一,因此取名为同文。其为人忠厚纯朴,乐善好施,不蓄钱财,不建居室,主张“人生以行义为贵,不必积蓄钱财”。
杨悫死后,由戚同文继续主持办学。
赵直将军非常器重戚同文,病重之时,将家事托付于他,礼遇有加,并帮其扩建书舍,广收学子。慕名的求学者,不远千里而来。
大宋立国初,开科举之考,南都书舍百余名应考的学子中,竟有五十六人进士及第,南都书舍从此名扬天下。
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应天府首富曹诚,仰慕戚同文先生的“纯质尚信义”,筹巨资重建南都书舍,增学舍150余间,收集上千卷名著,广收学子,并请戚同文的孙子戚舜宾主管书舍,一时盛况空前。
应天府尹将这一盛况上奏朝廷,真宗皇帝听了欣喜不已。
太祖皇帝建立大宋以后,天下复归一统。从太祖皇帝到真宗皇帝,都注重文治,所以当真宗皇帝听说应天府学风蔚然,欣喜之余,赐名南都书舍为“应天府书院”。
朱说听了李迪的介绍,兴奋不已:“李大人,且不说皇帝为学府赐名,单是那戚同文先生贫贱不屈、刻苦向学和主张‘人生以行义为贵,不必积蓄钱财’,就让学生倍加仰慕与尊敬。”
李迪道:“你既有心向学,不如去应天府书院。书院的老师都是来自天南地北的饱学之士,他们的藏书更是聚史上之名家经典,多达千余册。”
朱说起身施礼:“多谢李大人指点!学生就去应天府书院求学。”又道:“学生从家里跑出来,并非真心憎恨朱氏兄弟。虽是一时性起,实则是想继续求学,也想自立门户。常言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养父对我的养育之恩、教导之德,我铭记在心,永生不忘!”
辞别李迪,朱说昼行夜宿,几经周折,终于进了应天府书院,这一年,是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
一晃四年过去了,在应天府书院的读书生涯里,朱说的刻苦,比之在长山醴泉寺,有过之而无不及。常人读书,常以头悬梁、锥刺股来激励自己。而朱说,以先贤戚同文当年读书“累年不解带”为楷模,昼夜苦读。寒冷的冬天,夜晚读书疲倦不堪,他就以冷水洗面来提神,确实太累了,就和衣倒在床上眯缝一会儿,从不曾脱衣睡个囫囵觉。
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正月,宋真宗率文武百官到亳州太清宫拜谒老子,加封老子“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随即,又往应天府赵家祖庙——圣祖殿拜祭。
这日,真宗的御辇刚至圣祖殿前,便听人惊呼:“有‘天书’降于皇帝的车驾之上!”
众人抬头看时,果见庙宇上方,霞光普照,一朵黄云冉冉而降。霎时,百官跪地朝贺,山呼万岁,震天动地。
自大宋在景德元年(1004年)跟辽国签订“澶渊之盟”以来,边境再无战事,宋朝境内风调雨顺,物埠民安,这一派安稳祥和之气,常常使宋真宗庆幸与辽国的讲和。而资政殿学士王钦若私下里奏说:寇准主持的与辽国签订的“澶渊之盟”,表面上是议和,实质上是“城下之盟”。
王钦若一番话把事情的性质完全颠覆,“城下之盟”是敌人兵临城下之时,被迫与敌国签订的休战条约,是以丧权辱国为代价的。
真宗不知王钦若说的这番话,其实是因为对刚直不阿的寇准的嫉妒。这种妒贤嫉能的奸佞行为未能引起他的注意,反而对所谓的“城下之盟”耿耿于怀。
真宗想:作为太祖太宗皇帝的子孙与继任者,应该是大宋帝国的圣明天子,岂能容忍这样一个平和清静的太平盛世,是出自与辽国签订的“城下之盟”?若真如此,大宋皇帝的颜面何在?但将如何补救呢?
王钦若便怂恿真宗“封禅”。
封禅,是祭祀天地的大典,是圣德之事,若不是明德之君的祭祀,天地是不能接受的。
真宗不辨是非,而是满腹疑虑:“封禅,乃圣德之君所为,不是随便哪个皇帝就能做的,要有天瑞昭示,朕方可封禅。”
王钦若不假思索道:“没有天瑞昭示,就不能人力为之么?古人不是也借造化神妙弄出河《图》洛《书》以教化天下?”
真宗听了,恍然开悟,这便有了“天降祥瑞”以示天下太平,皇帝是圣明之君,便有了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耗资巨大的泰山“封禅”。
今日在应天府圣祖殿,又有祥瑞降临,岂不是天大的荣耀!真宗皇帝大喜之余,立即下诏,升应天府为南京。对应天府境内以及出巡以来所经过的各县州实行特赦,并恩准在“重熙颁庆楼”大宴臣民三日。
一连几日,应天府热闹非凡,陌上杨柳飞花,城内流光溢彩。街上,香车宝马,行人如织,都争着去看皇帝是什么样子,也赶着去品尝御赐的美酒佳肴,真是一片太平盛世的繁华景象。
书院里的学子也不例外,这日都早早起床,梳洗干净,穿戴整齐,去瞻仰天子圣颜,唯有朱说不为所动,读书如故。
平日里几位要好的同学非常奇怪:“朱说,你还不快换身干净衣裳?大家都要走了。”
“何事?”
一位同学夺了他手中的书卷:“咦!天下竟有你这样的人!是不是读书读痴了?”
朱说不解:“读书如何能读痴?读书只会去愚昧、长见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顺手抢回自己的书。
“可天下人莫不想瞻仰天子圣颜。这次皇帝巡游应天府,实乃千载难逢的机会,难道你不想去?”
朱说依旧坐回到桌前,翻开书,不紧不慢的:“天子真容,日后再见也不迟。”
“哟!你好大的口气!日后再见也不迟。”那位同学撇撇嘴,学着朱说的腔调。
另一位同学问:“你当真不去?”
“当真不去!我现在发奋读书,将来金榜题名时,皇帝自会在金銮殿上召见于我。”
大伙儿心里嘀咕了一声“狂妄”,便不再理睬朱说,一同出了书院,往街上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