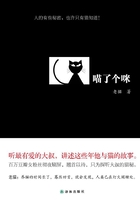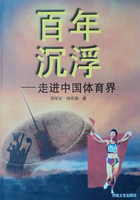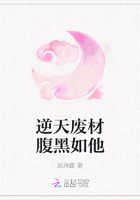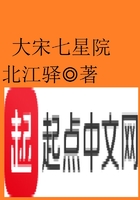重读《红旗歌谣》:试看“全民合一文化”
这本无人再读的“诗选”应当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它恐怕是人类有史以来最精选的诗选,可以在世界纪录大全中占一位置。1958年春,毛泽东指示“搜集民歌”,仿照古代盛世采风以观民情。不奇怪,马上出现了一个“全党办文艺,全民办文艺的新局面”。全国几亿工农兵,几个月中写了上亿首诗。党委要宣传部层层上报这个“大跃进”成果作为“献礼”,最后由郭沫若与周扬选出两百多首,集为《红旗歌谣》一书,应当是近一百万首诗中精选一首。
这些诗艺术上如何?“全部封建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的文艺成就,和可能达到的艺术高峰比起来,都是‘一览众山小’。”
且住。此类愚行,在中国当代多矣,不值一提,更不值得为之写一篇“重读”。只消看任何一本当代文学史,提起这场公案都有一长串“虽然”、“但是”的辩证法。比起当代中国一个接一个惊天动地的运动,这场“新民歌运动”至少有个好处:挺文雅的,没有捣毁东西打死人。最坏的后果,据一本权威性的当代文学史说,只是“得不偿失,造成精力、物力和时间上的严重浪费”,形成“对文艺生产力的破坏”。写诗能计什么得失?大干大忙还能不让人借个理由休息?笔墨纸张算多少“物力”?至于“文艺生产力”,原不比麻雀的繁殖再生能力差。
如此而已,这场“运动”真是个无伤大雅的笑话。所以《红旗歌谣》主编之一周扬,在1978年20年后重印此书时,另加一跋,依然赞美有加,并有妙语云:“虽然带有浪漫的夸张的色彩,但也正由此反映了当时历史的真实。”所谓“反映论”,如此一用,倒是歪打正着。周扬写到此,做了个鬼脸,我希望。
如果本文只是以官修文学史作为论辩对象,任务就过于简单了。实际上最近几年出版的当代文学史,都把《红旗歌谣》说成不值得一提,尽可能三言两语迅速打发,或是闪烁其词烟云模糊过去,让笑话留在笑话的平面上。而本文则想花上一点篇幅,来证明《红旗歌谣》意义极为重大,它把中国文学与文化史长期存在的一个基本的困惑点,突然推到了极限。从这本诗集入手,或许我们能解开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死结,即雅与俗的关系。
歌谣,是所谓“口头文学”的一种。“口头文学”这词自我矛盾,文学是书面的。《说文解字》:“文、错画也,象交文。”合集众字成篇章,谓文。西语literature源自拉丁文literalis(字)。《牛津词典》解为“书面作品集合”。
当然,我们可以把“口头文学”这个词组看作让步修饰,就像“绢花”、“面人”。但这词在文学史上依然造成混乱。它似是指原来形态的口头语言艺术表演,但很多时候又是指这种表演的书面记录转写。转写不可能“完全忠实”。口头言语与文字有多大差别,口头语言艺术与“口头文学”就有多大差别。
书面与口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表意方式。口头语言艺术是一种多中介传达,许多语气、手势、场面等“副语言”(paralinguistic)因素同时进入表意,它本质上是不能重复的,每次表演,都创造了一个新文本。既然不重复,也就难以存留,难以检验查核,它的意义权力小,它的文化责任就轻。简单地说,既是过耳即逝,瞎说胡唱也没多大关系。
书面文本大不相同,它的最基本特征是可重复性——可以保存,可以重新阅读,重新抄录或重新出版。因此,它必须比较严格地尊崇社会规范。文化责任给书面文本带来意义权力,不识字小民也知敬惜字纸。
口头“文本”虽然能用师徒传授记忆方式代代相传,但传授不可靠(变异可能太大),渊源也不可考。因此口头文本是不具有历史性的文本,它的存在是即刻的、此时的、非积累的。它基本上处于文学史之外。
无责任、无权力、无历史的口头语言艺术实际上是在中国主流文化之下的亚文化表意方式。作为亚文化的潜流,它倒也得其所哉,与主流文化两相安。主流文化一般说不把自己的规范强加于口头艺术,而是让它作为“化外之文”存在。中国文化的延续,靠的是会读会写控制着书面表意的“知之”的君子,不识字小人只消“使由之”即可。君子小人之分,也就是书面口头之分。“礼不下庶人”,也就是文不下庶人。《论语》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必“文”。
优戏,说讲,历史上一直有记载而无记录。歌谣因为短,一直有少量记录,却是风俗志、谶纬、野史等其他文本的附笔。《诗经》中某些篇什保留不少口语痕迹,先秦之后,中国文化的书面偏重已经确立,“书同文”严重削弱了语音影响文字的能力。汉乐府诗,说是口头歌谣的记录,实际上口语成分已相当弱。11世纪之前的中国书面文化,基本上是均质的。“口头文学”留在口头,与书面文化很少关联。
宋元时期中国文化起了重大变化,中国出现了相当规模的俗文学。俗文学从一开始就处于一系列两难之境中:俗文学不是口头文学,也不是口头文学的书面化,而只是假定在模拟口头文学。俗文学是书面的,却不是书面主流文化的一部分,而是亚文化文本的书面化。可是亚文化文本一旦书面化之后,它就失去了亚文化文本的许多特点或特权。
自敦煌文献发现后,文学史家都认为佛教变文是宋元俗文学的先导,但两者之间的联系始终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说明。变文很少有文学意味,其中带情节故事的篇章,完全没有后来宋代“平话”的叙述学特征。中国的口述艺术不是变文刺激出来的,而是古已有之。佛教的讲经与授徒,只是提供了一个先例:口头表述也可拥有意义权力;变文则提供了另一个先例:口头文本可以书面化。因此,由变文刺激而产生的新的文学现象,不是口头文学,而是俗文学。
俗文学在文化地位上的暧昧地位,可由其“用途”见于一斑。“话本”不知是给说话人用笔记,还是供读者阅读的小说,很可能两者兼用。但是两种用途大不一样,前者是口述表演者的器具,不能说是文学。早期平话小说均用粗浅文言写成,越发展,口语成分却越多。如果说白话俗文学来自口头文学,无法解释这种变化。
书面的俗文学是给谁读的,这问题到现代更令人困惑。五四运动初期起,许多文学家就提倡研究俗文学。北大歌谣研究会成立于1920年,沈兼士、周作人为首,顾颉刚、钟敬文等人又于1927年成立了中山大学民俗学会,五四新文化重要人物几乎全卷入民俗研究。《歌谣》杂志广告征求民谣的真正“原本”,目的是作为资料供专家研究。50年代,民间文学界反反复复批判的,就是五四文学界这种“科学态度”,而坚持要求民间文学应是“供劳动人民阅读”。供老百姓阅读,则寓教于乐,此为俗文学;供文化专家研究,求其真,才是“采风”,就必须力求接近口头文学。这两者,内容似乎相同,却是完全不同的文类。其实就五四而言,对真正“原生态”亚文化的容忍度可能还不如明清。西谛(郑振铎)1926年重印道光八年(1828)出版的吴歌集《白雪遗音选》,其跋文说:“我们现在不能印全书……原书中猥亵的情歌,我们没有勇气去印。”注意他用的词“我们”,这是号称大无畏的五四一代人的态度。如此谨慎,这种对亚文化的态度,到50年代仍不免挨批。
回到俗文学的兴起。佛教唯心哲学对中国思想的冲击,促成理学兴起;佛教俗讲方式,推动了俗文学形成。这两者同时出现并非偶然,它是中国文化走向明显分层的一个重大转型,也是儒家伦理向社会下层延伸,礼教的重点从“君子”转向“小人”。这种礼教俗化,我在另一篇文章中详细论述过,是中国文化在明清走向衰竭的主要原因之一。
俗文学在文本等级上处于极低地位,但却没有口头文学的自由度。口头表述因为无存留可能,可以免受社会规范和意识形态过强的压力。俗文学用书面文本方式流传,其代价就是不得不对文化规范表示尊崇。而且,处于最底层的俗文学为了在中国文化的书面文类阶梯中取得一个地位,哪怕是最低的地位,都不得不对主流文化规范格外崇敬。
俗文学出现,主流文化规范就必须往社会下层延伸,限制并控制亚文化。主流文化现在允许亚文化有书面表达权,俗文学也必须因其道德教化功能而被容忍。
此种文本间关系,元末明初文人领袖杨维桢曾在给文言小说集《说郛》写的序言中做了一个说明:
是五经郛众说也。说不要诸圣经,徒劳搜旁采,朝记千事,暮博万物,其于仲尼之道何如也。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约则要诸道已。
周敦颐提出“文以载道”论时,没有想把小说之类包括在内。北宋时俗文学尚在萌芽。杨维桢把“文以载道”论扩展到中国文化中新出现的书面文本分层格局上:五经为城,众说为郛(外城),众说必须让出中心地位,并且礼崇中心,无法“要诸道”的文本,则拦在城郛墙之外,形成城-郛-郊的格局。不奇怪,杨维桢对俗文学极为推崇,多次著文赞扬俗文学的道德热忱。这就是为什么“齐东野人”的不入流之语,可以为“博雅君子所不弃”,因为它们“要诸圣经”,接受主流文化规范。
对杨维桢很尊敬的朱元璋,看来同意《说郛序》。他对亚文化非常严酷,却明白规定:“凡乐人扮做杂剧戏文……其神仙道扮及羲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另一个著名道德家皇帝康熙则把杨维桢的城郛比喻变成实际控制方式:“凡唱秧歌妇女……尽行驱逐回籍,毋令潜居京城。”“京师内城,不许开设戏馆,永行禁止。城外戏馆,如有恶棍借端生事,该司坊实查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