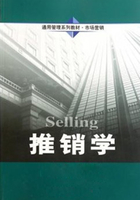湖水有涨有落,但有没有规律,周期到底多长,谁也不知道,然而许多人照例是要假装知道的[641]。通常来说,冬天水位高,夏天水位低,不过跟天气的潮湿或干燥没有关系。我能记得和我在那里生活的时候相比,它的水位什么时候低了一两英尺,什么时候又高了至少五英尺。岸边有片伸入湖里的狭长沙地,淹没它的湖水特别深,大概是在1824年吧,我曾在那上面帮忙煮熟一锅杂烩汤[642],那地方离如今的湖岸有六杆地的距离呢,然而二十五年来,在上面煮汤已经成了不可能的事情;也有相反的情况,早些年树林里有个偏僻的湖湾,我常常划船去那里捕鱼,那地方离他们唯一知道的岸线足足有十五杆,很久以前就已变成草地,每当我把这件事说给朋友听,他们总是显得难以置信。但过去两年来,湖水持续上涨,如今是1852年的夏天[643],水位比我在那边生活时高了五英尺,或者说又像三十年前那么高,人们又可以在那片草地上捕鱼啦。湖面因之向外扩展了六七英尺,然而从周围的山丘流入的水量是微不足道的,所以这种漫溢肯定是跟地下水位的上涨有关。就在这年夏天,瓦尔登湖的水位又开始下降。无论是否有周期,这种涨落最让人称奇的是,它需要许多年才能完成一个轮回。我已经观察到一次上涨和两次下落,估计在今后十二到十五年,湖水会再次降低到我所了解的最低的地方。往东一英里是弗林特湖[644],它的水位偶尔会受到流入量和流出量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其他几个小湖却跟瓦尔登湖差不多,最近它们的水位和后者同时涨到了最高点。据我观察,白湖的情况也是如此。
瓦尔登湖这种相隔多年的涨落至少起到这样的作用:湖水在高位维持一年或以上,虽然给沿湖走动带来不便,却浸死了自上次水退后生长出来的灌木和乔木,刚松、白桦、赤杨、白杨和其他树木再次卧倒,于是湖岸又是一片整洁;所以瓦尔登湖不同于许多湖或者每日都有潮汐的江海,当水位最低时,岸边是最为干净的。在紧挨着我的木屋的湖边,曾经有一排十五英尺高的刚松被湖水浸死,像有人从下面撬似地扑倒在地,它们的侵略也就这样戛然而止;从这些树的大小可以看出来上次湖水涨到这么高是多少年以前的事情。瓦尔登湖借由这种涨落实现了对湖岸的控制,湖岸就这样被剃了胡须,树木虽然长在那里,却保不住它们的地盘。这些地方是瓦尔登湖的嘴唇,嘴唇上面没有胡须。它时不时会舔舔自己的吻部。当湖水处于高位,赤杨、柳树和枫树会冒出长达几英尺的根须,离地面三四英尺的树干四周长满了这些红色的树根,以此来维持它们的生命;我还发现湖边的高丛蓝莓[645]通常是不结果的,但在湖水上涨时,它们的枝头却会挂满果实。
沿岸的石头铺得很整齐,这让有些人感到很困惑。我的同乡全都听过那个传说[646],那个镇上的老人说他们在年轻时便已有所耳闻的故事,据说古代的印第安人在这里的山上举行庆祝大会,现在的瓦尔登湖有多深,当时那座山就有多高;那个故事说印第安人做了许多亵渎神明的坏事(不过人们常常把莫须有的罪名安到印第安人头上,这当然也是信口开河的污蔑),所以就在大会进行期间,那座山摇晃起来,突然下沉,只有一个叫做瓦尔登的老太婆得以逃生,湖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的。在人们的想象中,从山上摇落的石头变成了如今的湖岸。反正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从前这里并没有湖,而现在有了一个;这个印第安故事和我前面提到那个古代居民[647]的说法完全是不矛盾的,那人清楚地记得,最初他拿着探测棒来到这里,看到薄雾从草地上升起,手里那根榛木棍子坚定地指向下方,于是他决定在这里挖一口井。至于湖边的石头,许多人还是认为它们不太可能是从周边的山上滚下来的;但我发现在这些山丘上,同类的碎石头特别多,乃至铁路公司[648]不得不在临湖而过的铁路两边砌好石墙,还有就是湖岸最陡峭的地方石头也最多;所以很不幸,这对我而言已经不再是个秘密。我发现这是冰川的作用[649]。这湖的名字如果不是源于英国的某个地方,比如说萨福隆瓦尔登[650],那么它原本的名字大概是叫石墙湖吧[651]。
瓦尔登湖对我来说是现成的水井。湖水每年有四个月是冰凉的,而且永远是那么纯净,反正康科德镇找不到比它更好的水。冬天时,湖水因为暴露在空气里,所以和不直接接触空气的泉水和井水相比,它更为冰凉。在1846年3月5日下午五点,我提了一桶湖水放在屋里,翌日中午再去测量,发现水温只有42度,比镇上刚汲上来的最冷井水还要低一度,而在此期间,由于阳光照耀着屋顶,室温最高曾达到65度或者70度。当天沸泉[652]的水温是45度[653],这也是那天我测量过的最高水温;不过据我所知,如果不混合浅表那层静止的水,沸泉的水在夏天是最凉的[654]。除此以外,瓦尔登湖在夏天时也不像其他受到阳光照射的水体那么热。每到天气最热的日子,我通常会放一桶水在地窖里,夜里那桶水就冷却了,而且隔日能保持整天都很冰凉;不过我有时也会用附近的泉水[655]。湖水就算放一个礼拜,尝起来依然跟刚打上来的差不多,而且没有水泵的味道。夏天时,人们要是到湖边搭帐篷住一个星期,只要在帐篷下方挖个几英尺的地窖,放一桶湖水进去,便完全不需要奢侈的冰块。
有人曾在瓦尔登湖里捕到一条重达七磅的狗鱼,其实还有条更重的,迅猛地拖走了整卷钓丝,钓鱼的人没看到他,但猜肯定有八磅那么重。此外也有人捕到鲈鱼和鲇鱼,有些体重超过两磅,以及闪光鱼、黑斑须雅罗鱼[656]或者小眼须雅罗鱼(Leuciscus Pulchellus) [657] ,少数的太阳鱼和几条鳗鱼 [658] ,其中一条鳗鱼有四磅重,我说得这么精确,是因为通常越重的鱼越出名,而除了这几条,我还没听说有人在这里抓到其他鳗鱼。另外,我依稀记得湖里有些小鱼,五英寸长,两侧是银色的,背部是绿色的,有点像闪光鱼;我提到这种鱼,是想把事实和传说结合起来。不管怎么说,这个湖的鱼并不是很丰富。狗鱼虽然不算很多,但已经是它的主要鱼类。有一次[659],我曾看到至少有三种狗鱼躺在湖面的冰层上,其中一种很瘦长,钢灰色的,与河里捕到的狗鱼差不多;一种是亮金色的,反射出绿色的光芒,在水里特别深的地方,这是湖里最常见的一种;另外那种是金色的,形状和第二种相同,但两侧有些细小的深棕色或者黑色圆点,中间混杂着个别淡淡的血红色斑点,看上去特别像鳟鱼[660]。这种鱼的专名不应该是reticulatus[661],而应该叫guttatus[662]。这些鱼的肉特别密实,所以实际重量比看上去要大很多。和生活在河里以及其他大多数湖里的鱼类相比,瓦尔登湖里的所有鱼类,包括闪光鱼、鲇鱼、鲈鱼,都要干净和漂亮得多,鱼肉也紧密得多,因为这里的湖水更加纯洁,他们和别的鱼有很明显的区别。也许很多鱼类学家可以用他们培养出新的品种来。湖里也有发挥清洁作用的青蛙和乌龟,以及少数贝类;麝鼠和水貂也在湖边留下了足迹,偶尔也会有路过的拟鳄龟[663]来访。有时候,当我在早晨把小船推到湖里,我会惊动一只在船底躲了整个晚上的大拟鳄龟。野鸭和大雁在春秋两季经常来,白腹的燕子(Hirundo bicolor) [664] 贴着湖飞过,翠鸟 [665] 从巢里疾冲而出,斑腹矶鹬(Totanus Macularius) [666] 整个夏天“大摇大摆”地在铺满石子的湖边行走。我曾有几次惊动了在横亘于水面之上的白松枝头栖息着的鱼鹰;但我怀疑海鸥[667]是否曾亵渎这个地方,尽管费尔黑文湖[668]有很多。潜鸟每年最多只来一次。这些就是目前在瓦尔登湖出没的主要动物。
要是在风平浪静的时候乘船,你可以看到在东岸的沙滩附近,在那水深八到十英尺的湖底,以及湖底的其他部分,有几个直径十来英尺、高一英尺的圆堆,那些圆堆由比鸡蛋还小的石子组成,周围全是沙子。起初你会疑心是不是印第安人出于某些目的,有意把它们摆在结冰的湖面上,在冰层融化以后,它们沉到了水底;但这些圆石堆太过齐整,有些年代显然很近,所以不可能是这么回事。它们与在河里发现的圆石堆是相同的;但由于这里既没有胭脂鱼[669],也没有七鳃鳗[670],所以我不知道它们是哪种鱼的杰作。也许是黑斑须雅罗鱼的老巢吧。这些石堆给湖底平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湖岸特别不规则,所以看上去不会很单调。我闭上双眼也能看见,西岸镶嵌着几个很深的湖湾,北岸很开阔,美丽的南岸像个扇贝,有许多伸入湖面的岬角彼此交叠,让人想到中间隐藏着未经探索的隈隩。从群山环绕的小湖中央望去,周边的树林真是最好不过的背景,显得出奇的美丽;因为倒映着树影的湖水充当了最美的前景,除此以外,曲折的岸线也让树林拥有了最自然和悦目的边界。湖边的森林是浑然天成、完美无瑕的,不曾有斧头砍伐出一片空地,不曾有锄头开垦出一片农田。那些树木在湖面上有宽敞的舒展空间,每棵树都将最有活力的枝桠朝那个方向伸出去。大自然编织了天然的包边,沿岸低矮的灌木和高大的乔木层次非常分明。那里几乎见不到人工的痕迹。浪花冲刷着湖岸,千载以来始终如此。
湖泊是大地上最美丽、最生动的景物。它是大地的眼睛;凝望着湖水的人可以测量自身天性的深浅。沿岸濒水而生的树木是它的修长睫毛,而周围郁郁葱葱的群山和悬崖则是它浓厚的眉毛。
我曾在九月某个平静的午后,伫立于湖东光洁的沙滩上,当时有片薄雾模糊了对岸的景象,而我终于明白了何谓“波平如镜”。如果你头朝下从胯间望出去[671],瓦尔登湖像是一根最精美的蜘蛛丝,悬挂于山谷之间,在远处松林的映衬下闪闪发光,隔开了两个天空。你会以为你能够浑身不沾一滴水地从湖底走到对面的山丘去,而且在其上飞翔的燕子可以栖息在湖面上。实际上,燕子有时候会冲到那根线下面去,因为他们看错了,上当了。如果由东往西望湖,你必须用双手遮住眼睛,除了挡住真实的阳光以外,还得挡住湖面反射的阳光,因为它们同样耀眼;若是仔细地观察夹在两个太阳之间的湖面,它看上去确实像镜面般平静,只是湖面上有许多隔开同等距离的水黾[672],它们的动作让阳光下的湖面荡起了优美得难以想象的细纹,整理羽毛的野鸭也会打破这份宁静,或者正如我前面说过的,燕子飞得太低,碰到了湖水。也有可能是远处有条鱼在空中划出一道三四英尺长的弧线,它出现时有一道亮光,扎进水里时又是一道亮光;有时候,这两道亮光连成了完整的弧线;湖面上有时候也会漂浮着许多蓟草[673]的冠毛,那些鱼要是一头扎到那上面,湖面就会再次泛起波澜。湖水就像已经冷却然而尚未凝固的玻璃溶液,里面的些许杂草就像玻璃里的气泡般纯净而美丽。你往往还能观察到更加平静和幽深的水域,仿佛有张无形的蜘蛛网将它和其他水域隔开,或者是湖居的仙女在其周围打下了栅栏。从山顶俯视,你能看见几乎到处都有鱼跳出来;有条狗鱼或者闪光鱼虽然只是捕食湖面上的一只虫子,却很明显地打破了整个湖的安宁。于是这个简单的事实,这桩水族界的谋杀案,就如此被精美得让人称奇的波纹公之于众了;从远处的观察点,我看到那波纹不停地向外荡漾,直径足足有六七杆那么长。你甚至还能看见有一只豉甲(Gyrinus)[674]不停地在光滑的湖面上行进了四分之一英里,因为它们轻轻地犁开了湖水,弄出一片由两根线条包围着的明显波纹;但水黾从湖面走过时却几乎没有留下肉眼可见的痕迹。每逢湖面波浪翻涌,水黾和豉甲就消失了;但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这些虫子显然离开了它们的港湾,勇敢地从岸边向湖心蹦去,直到占满了整个湖面。在天气晴朗的秋日午后,于温暖的阳光中像这样坐在山顶的树桩上,静静地俯视着湖面,仔细观看许多圆圈在原本倒映了天空与树木的隐形湖面上无休无止地荡漾着,真是让人感到心旷神怡。那些波纹并没有扰动巨大的湖面,而是随即慢慢地平息消退下去,就像花瓶里装了水,瓶子里的水会颤动着,然而很快又回归平静。无论是从水底跃出的鱼,还是掉落湖面的昆虫,都激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波纹,那些线条看上去很美丽,看上去仿佛不断涌出的泉水,仿佛湖水是活的,而这就是其脉搏的跳动,是其胸膛的起伏。谁也分不清这到底是欢乐的振荡,还是痛苦的颤栗。瓦尔登湖的景色是多么的祥和啊!那些人类的杰作又像在春天般闪闪发光[675]。在这午后时分,所有的树叶、枝条、石块和蜘蛛网宛如披上了春天的晨露,都散发着星星点点的光芒。船桨或虫子的每一个动作都产生了一道亮光;当船桨落下时,那回声是多么的动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