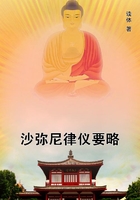点的那首曲子仍旧没有放出来。刘冬有点急,小过没表现在脸面上。好像每次都这样,胡丽君早热热闹闹地玩去了,刘冬在一旁倒替她拿捏着一把汗。场子已经热了起来,开始有点怯的人现在都酝酿出了感觉,选了自己拿手的给了DJ,有几个连礼貌也顾不上了,插了人家的队,把自己的歌不知羞耻地排在前面。刘冬遍一遍地听着别人唱歌,民族的、流行的、英文的、美声的,甚至还有当下小年轻们最时尚的RAP,听着有声有色热闹非凡,台下起哄的叫好声一片。场子里是随舞的人群,男男女女,搂搂抱抱,影影绰绰,便是从来在一起早晚相处着的,待在一起的时间比家里人还多的同事们,这会儿,在暗暗的有些暧昧光影的舞场里,也分不清谁是谁来了。刘冬仍旧用眼睛找着了胡丽君,她一直跳舞来着,三寸高的尖头皮鞋,一袭雪白的大摆裙,束胸卡腰的紧身上衣,早不时兴了的装束,慢三慢四,悠闲地敷衍着请她随舞的男性。这曲将尽,一个旋转,再一个旋转,轻轻地过来,被那行政处的男同事旋到刘冬坐的位置上来,刘冬看见胡丽君莞尔一笑,在蓝幽幽的光影下,闪出一口森白的牙齿。
刘冬给她递了一叠餐巾纸,胡丽君站着,用手摆了摆汗,仍旧笑嘻嘻地,问了刘冬一句:“你怎么一直坐着?不去跳个舞?”刘冬还没搭上腔,那首曲子已经铿铿锵锵蛇一样地蹿出来,胡丽君还没歇稳,猛听着那起头的音调,攥了那叠纸巾,急急地从刘冬坐的桌旁拿了一杯可乐灌下一口,忙匆匆地跑到台上。开了重音效果,把原音全部抹掉,胡丽君背对着荧屏,把提词儿的屏幕当成了华彩的背景,摆了一个身姿,右手的兰花指也翘出了形状,冲出口的是一句《苏三起解》,高八度的音,假声盘旋得惟妙惟肖,又花又亮,冲到嘎调的时候,台下看的人都以为她的嗓子要上不去了,要破了,结果一个回转,慢慢下得峰来,柳暗花明又一村,怨艾的一个苏三就兜头兜脸地出来了。
台下一片叫好声。
多是男的。刘冬睃了周围一圈,和前几次胡丽君上台K歌一样,单位里那几个爱起哄的男人叫得最欢。这会儿全场的中心是胡丽君,嗓子亮到极高处,有点炫耀地飞扬:……来生变犬马,我也当报还……音调拖得很长,似有无限的底气,身形也做到足处,手指随着长音拖开去,随着颤音开始抖开了,一段西皮流水,漫成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浪涛,漾得无边无际。一个女人紧挨着刘冬的身边,冷笑地说一句:“就她出得了风头,瞧她那德性,真不枉了这名,真真一个狐狸精。”讲这话的是财务处的林月芹。旁边的人附和着笑了,开心地,有点促狭地,同善共济地,把一帮男同事的起哄叫好声也埋了进去。刘冬暗暗地喝了声彩,她在心里感慨地说:“这谁还敢接着唱了呢?胡丽君的这副嗓子,生生地一点白也不留给人家了。”她不得不服胡丽君,便是运的假嗓,也不是一朝一夕能练就的,最重要的还在于天生,还在于天生的能把握舞台。刘冬想林月芹的妒忌是有道理的。
刘冬是个好女人。在结婚以前,刘冬应该说是个好女孩。好的含义是什么呢?大约是平常,大约是普通,身世,经历,没有一点波澜壮阔,平平淡淡地就这样顺顺溜溜地下来了。高中毕业考了普通的大专,大专毕业进了现在的公司,工作了十好几年,一个不痛不痒部门里一个不痛不痒的副职。生活上呢?就更稀松平常,也是谈过两场恋爱的,不多,就两场,处的两个男朋友,也是母亲知根知底的同事介绍的,开头的那个处不来,说不上为什么,就两下里都没了来往的兴致,后一个呢,就有了些缘分,便再接再厉,进行了这场持续已久的婚姻。孩子是婚后一年生的,婆婆妈妈各带一段,拉扯着儿子也上小学了。好像在刘冬的日子里,太阳每天都是一样的,她的人,就像她的衣着,从来就没有招摇过的,扔到街上,转一个角,就在人海里淹进去了,再也寻不到踪迹。同事呢,因为她的从来不逞强,倒也颇结人缘,尤其是女人,好像是老中青三代通吃的,跟谁都合得来,说拉帮结派也好,说弄小集体也好,她走到哪里,也从没形单影只过的。不久之前,她听过一个段子:女人最应该得到的评价是漂亮,如果不漂亮,就应该夸她有气质,如果既不漂亮也无气质,就应该夸她可爱,如果既不漂亮也无气质又不可爱,就该称她聪明,如果既不漂亮也无气质又不可爱还不聪明,那就该说她善良了。刘冬当时是怔了一下的,她知道好的含义是什么了,呆了半晌,心里的落寞一层一层地往上涌来,漫过了喉头,闯过了鼻腔,涌到了眼睛里,竟汇成了一股酸楚的眼泪来,喷薄而出,汹涌而下。
那个时候,他们一家四口还住在厂区宿舍里,十六平米的房间,一张大的双人床靠东墙摆着,一张小点的单人床就靠着南墙,很结实的木架子床,床头还钉着铁包皮,凹陷的钢印里打着一串数字,是有着“公家”标志的东西,不知怎么就来到他们家了?打小的记忆里它就是存在的,那是刘冬唯一的空间。弟弟比她还可怜,知事的时候,和父母分床而睡,只能在晚间快要熄灯的时候,在屋里再也挤不下的空间里搭起一张行军床,蹦蹦跳跳地在上面还耍过把戏。
父亲总是木讷的,沉闷不语,唯一的爱好就是烧点菜肴,在那种物资匮乏的年代里,一碟小鱼干,一坨牛肉块,也能烧出翻新的花样来,汩汩的香味漫过了整个五六家共用的大厨房,惹得一宿舍的人都来羡慕她家锅碗瓢盆里的丰盛。母亲却是严厉的,似乎很少有过笑容,人的性格属于硬的那种,刘冬姐弟几乎没在母亲身上体会过课本里所有有关对母爱赞颂的温柔温暖的词汇。那会儿也兴烫发了,一色的发式,圆的长的宽的三角的,各式的脑袋上顶着一样大卷的鸡窝,母亲也还是不排斥的,还抹了头油护着卷发,塑料齿的梳子梳一层,油也跟着掉一层,黑乎乎的油渍把一柄粉绿的梳子也弄得脏兮兮的。母亲也穿高跟鞋了,中粗的跟,现在想来,那种鞋跟是多么粗粝,硬邦邦的,哚哚哚地响,离了几百米外也能知道母亲回来了,可是不知为什么,总觉得透着一种说不出的小心。
刘冬在晚晌做完了作业,也会和院子里的玩伴一起玩。她好像一直是当不r什么主角的,成绩一般,体育一般,音乐美术写作,跳绳踢毽耍猴皮筋,没哪一样是出众的,小孩子能耀武扬威的领域里,她也实在没什么出彩的地方,什么都是稀松平常的,顺眉顺眼地,巴结着别人。一直是有朋友的,是的,一直有,可就是那种巴结,像母亲蹬着粗粝高跟鞋的脚,虽然哚哚哚的有声有色,却是透着无以名状的小心。
音乐停了一小会儿,开始奏一首明快的曲子,大家叫起来:快三快三。胡丽君早回来了,胡丽君放了嘴边磕着的瓜子,其实她整个晚会上几乎没怎么吃东西,剥了根香蕉,电只小小地咬了一口。她太忙了,跳舞,唱歌,没个停息,送到嘴边的香蕉和瓜子,只是她出场前的一个缓冲,或许只是一个道具,不能看起来太像盼着什么似的,那是不急不徐的一个借口。歌来了,舞来了,好像才不甘心情愿地放下嘴边的食物,勉为其难地敷衍一下似的。这个,刘冬是早看出来的。但是,刘冬不笑话她,刘冬倒佩服她的从容,佩服她英姿飒爽前的淡定。场子里没几个人,原来忙碌的一开曲前就急急邀着舞伴的男士们也坐得定定的,到底是快三,和先前能唬一下人的慢步曲不一样了,几步路袅袅婷婷地走下来,还能遮掩一下人的耳目,这快步,是真刀实枪的演练。有个男的伸过手来,低声朝胡丽君说了一下:“华尔兹。”胡丽君扬了一下眉,在蓝幽而显得阴森的光影下,刘冬也看出了她的一丝撩不住的喜悦。胡丽君伸过手去,自然地滑了一下身子,顺手就被拖到了宽敞的舞池里去。
她的裙裾开始翻飞起来,雪白的大摆裙,在幽深的光影里带出了一种神秘而令人窒息的蓝影,荧荧地发着光。裙摆是重的,悬垂感带出了立体的效果,露一小截雪白的腿,还没来得及看清,就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收住,留给人要多少回想有多少回想的遐思了。她的紧身上衣也在旋转中显出了夺目的身条,胸饱满起来,每一个转向,都骇得人担心它们支撑不住,会喷薄欲出,腰突然收得挺直,却在下窝处有一道弧,是那种俏丽,并且明目张胆地有了一种诱惑。鞋跟轻轻点地,掠水的蜻蜓一般,轻轻地就那样抚一下,而鞋尖撑着地面,左左右右地画着弧,一个一个的圆圈圆满地描出。她的舞伴盯着她,她也盯着他,一个转身又一个转身,稍纵即逝的一回头,眼睛还是四目盯着,就像被焊锡牢牢地粘住了一样,公然的坦白的调情,忘记了世间所有的其他。
舞场里其他的几对舞者都停了下来,不是舞伴不得力,就是彼此都有点力不从心,或者被强烈的音乐带着停不下舞步的其他人撞击着败了兴致的。退下来的人都有点讪讪的,看不清楚他们的表情,可是从动作上能猜得出他们的扫兴,失望的、怨怪的,甚至带点落寞。场上最终就剩下胡丽君和她的舞伴,他们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旋转,一轮接一轮的摆荡,旁若无人。
刘冬分明听见林月芹止不住的一声叹息,她回头瞥一下林月芹,不单是她,场下所有的人都被这一对舞者天衣无缝的默契表演惊住,微张了嘴,手僵僵地放在他们起舞前的动作里,像定格了一般,目不转睛。一种绝望的惊异。
不记得是几岁了,应该已经上了小学。有一次母亲换了班,大白天里便拉着她到小澡堂里洗澡去了。小澡堂是锅炉房特备的浴室,热气供得足,水量也大,一人一个龙头,奔涌的热水腾空而下,打在刘冬小小的身体上,生疼却暖和,身子是那样旋来旋去的,多长时间也舍不得离去。出来后还是冷的,腊月的天,头发还在寒风里飘散着,被滚烫的热水滋润过的脸庞是红彤彤的,北风生冷地吹过,还有氤氲的热气在回荡。后来就随母亲去了厂子里的幼儿园,母亲的一个老乡在那里当阿姨,两个人就拉着手说起闲话来。刘冬那时候的心情是极好的,一种沐浴后干净的爽,看见后架那儿摆了一架脚踏风琴,直直地走过去,那琴盖带着锁头,那会儿,那把锁头竟是开着的,刘冬心里没来由地一阵高兴,站了一会儿,掀了琴盖,坐在琴凳上。身体是净的,心也是净的。黑黑白白的琴键,有一股生涩却好闻的味道淌出来,小女孩搓了搓手,在琴键上弹了一首流利的曲子。
一个阿姨跑了出来,叫了一声:“谁家的小孩子?怎么乱翻东西?”刘冬噌地从琴凳上跳下。母亲这时也跑过来,抚了她的肩膀,朝那阿姨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怎么没看见她,就跑到这边来了?”那阿姨摇摇头,盖了琴盖,淡淡地说一句:“哦,没事。不知道是你的孩子。”阿姨当着她们的面把锁头锁住了,取了钥匙,扭转身子走掉了。刘冬看着母亲的脸由卑微变成恼恨变成愤怒,还蕴着澡堂里热气的红扑扑的脸,由酡红变成潮红变成粉红,最后成了一抹白。母亲最后的那抹白是给了她的,是一种挣不开来的羞。母亲原来所有的硬都只是给了刘冬姐弟的,包括父亲,这会儿,刘冬看见了母亲在人前的软,那种没有骨头支撑的滑溜溜的瘫软。
没有问过她是如何会弹这首曲子的,没有问过她这首好听的曲子是叫什么名字的,也没有问过一向小心的她是如何大了胆子去弹那架脚踏风琴的。那个阿姨老乡出来了,笑一笑:“这小妮子,有点天分的,不知会不会跳舞唱歌,像她外婆那样?”刘冬只看见母亲深深的一瞥,怨气从那两只眼睛里流出,死死地咬在唇尖上。
是记得有那么一个夜晚,天当时已经黑下来了,大院里亮了路灯,有几户邻居家的阿姨伯伯们在柳树下闲聊着什么,外婆家的房门却是紧闭的——很奇怪,那是个大门敞着也没人偷东西的年代,那一天,竟然却是紧闭着的。有昏黄的白炽灯光从门缝里泄了出来,一绺姜色的黄,陌生而透着挑衅。刘冬轻轻地拍了拍门,叫了声“外婆”,又唤了声“外婆”。那几个站着聊天的阿姨伯伯们停止了说话,都转头来看着她,那些眼神是陌生的,带着奇怪的表情,上上下下打量着她。她的心里突然有点发怵起来,小小的心,不知会遇上什么的那种惊惶。她隐隐地听到房间里传来了声音,是种好听的音乐,却镇定不了她失措的身体,还有轻轻的、试探响着的脚步声,这使她猛然觉得骇怕,无助的恐惧感环绕在她的周身,她忽然就大叫起来,她不知道为什么喊出口的竟是“妈妈”,这两个字声嘶力竭地从她的胸膛里穿过,钻出她喉腔的时候,竟带着绝望的悲怆。
门轻轻地开了一条缝,是外婆,最先露出来的,也是她烫过的卷发,黑发里缠着丝丝缕缕的白发,但是她很妩媚地把它用手帕绾了起来,她低着脑袋看了一眼刘冬,笑了起来,回头对屋里的人解释什么一样:“是我们家姑娘过来了。”刘冬就撑开门,自己钻了进去。
屋里只有外公,窗子紧闭着,帘子也打了下来,小小的房间里氤氲着一股呛人的烟味。外婆的房间简单到极致,一张雕花的老床,一张油漆斑驳的五斗橱柜,一张带着两只木椅的饭桌,饭桌上有一柄留声机,嗞嗞地转着,一张黑胶唱片流出陌生的曲调来。
外婆掩了门,细细地拉着刘冬的手,刘冬就坐到那只木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