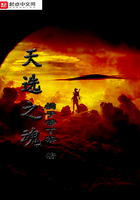说实话,很小的时候,小米就想象过自己有朝一日坐月子的情景。小米这么想完全是因为受了嫂子的启发。嫂子有一天从村南碰有家回来,一句话不说,就软绵绵歪在炕上了。碰有是庄上的先生,开着一间药铺子。这地方的人管医生不叫医生,也不叫大夫,叫先生。小米至今记得嫂子慢悠悠走进院子的情景。娘跟在后头,样子看上去又着急,又欢喜。她的身子往前扑着,脚步走得挺凌乱,挺没章法,嘴里念念有词,像是在骂人。小米愣了半晌,才从东屋门槛上咚的一声跳下来,她听见娘骂的是哥哥。兔崽子,臭小子,街门上的柴火也不收拾好,办事一点都不牢靠,还想当爹哩……小米看见这个时候嫂子的脸是红的,眼皮子向下耷着,下巴颏却是朝上扬着的。当天晚上,家里的那只芦花鸡就变成了热气腾腾的汤,盛进了嫂子的碗里。
那时候,小米在旁边一边咽着口水一边想,怀娃娃真好。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小米对未来的坐月子充满了憧憬。
小米人不丑,这是娘给她下的评语。小米对这个评语不满意。怎么说呢,娘就是这样,对自家的闺女横挑鼻子竖挑眼,怎么看都不对;对人家的呢,倒是宽宏的、厚道的、不吝赞美的。比方说吧,在街上见了人家抱的孩子,就说,看这小子,生得多排场!说着还凑上去捏捏人家孩子的脸蛋子。村西头娶了新媳妇,跑过去看了,回来称赞,这媳妇,眼睛毛茸茸的,欢实得很。小米有时候就不大服气,觉得娘的眼光有问题。
就说嫂子吧。嫂子是从司家庄嫁过来的。嫂子从进门的那一天起,就让小米不大痛快。其实,这事还得从娘说起。早在嫂子嫁过来之前,娘就一口一个俊子挂在嘴上。人家一只脚门里,一只脚门外,还指不定是谁家人哩,看把娘美的。俊子其实也不俊,只是人生得丰满,皮肤又白,就像刚出锅的白馒头,热腾腾,透着一股子喜气。娘私下里说,媳妇就要娶这样的,兴家呢!爹听了这话没吭声,只是很不自在地把烟锅在脚底板上磕了几下。
嫂子娘家家境不错,这一来,就多少有些下嫁的意思。嫂子倒还好,娘就有些沉不住气,在媳妇面前心虚得很,说话、做事都觑着媳妇的脸色。小米很看不惯娘这个样子。后来嫂子生了侄子,娘在媳妇面前就越发低伏了。乡间有这么一句话:媳妇越做越大,闺女越做越小。看来是对的。有时候,饭桌上,看着爹娘亲亲热热地逗侄子,小米心里就没来由地酸起来。娘是一个粗枝大叶的人,爱说笑话,在孙子面前,更是容易忘形。她挤着眼睛,做着各种各色的怪样子,嘴里不停地叫着——也听不出是在叫什么,然而嫂子怀里的胖小子却笑了,露出一嘴粉红色的牙床子,娘的兴致更高了。爹也笑。爹是一个木讷的人,平日里总是沉默的,这个时候,那张被日光晒得黑红的脸膛就生动起来,有了一种奇异的光芒。此时,小米心里是委屈的,觉着爹娘不是自己的爹娘了,家也不是原来那个家了。原来那个家,温暖,随意,理所当然。她是爹娘的老闺女,撒娇、使性子、耍赖皮,怎么样都是好的。还有哥哥。哥哥一向疼她,可自从嫂子进门,哥哥就不一样了。无论在哪里,什么时候,哥哥的眼睛老是离不开嫂子。有一回,哥哥和嫂子正说着话,叽叽咕咕的,嫂子没来由地红了脸,哥哥抬起手,把嫂子额前掉下来的那绺碎发抿到耳后。只这一下,小米心里就酸酸地疼起来。
侄子出世了,家里更多了一种欢腾的气息。到处都是小孩子的东西,捏起来吱吱叫的小鸭子,小拨浪鼓,五彩的气球,花花绿绿的尿片子。小米觉得家里简直没有了她的位置。嫂子喂奶的时候,娘和哥哥一边一个,给正在吃奶的小人儿喊着号子鼓劲。小米把帘子啪的一下摔在身后,珠串的帘子就惊慌失措地荡过来荡过去,半天定不下神来。娘在身后骂了一句,这死妮子,看把孩子给吓着。
阳光满满地铺了一院子。风一吹,蝉鸣就悠悠地落下来,鸡笼子旁,豆角架上,半笸箩豆子里,挤挤挨挨的,都是。小米把眼睛眯起来,无数个金粒子在她眼前跳来跳去。她忽然感到百无聊赖,就去找二霞。
二霞正在午睡,听见动静就睁开眼来,用手拍拍身旁的凉席,招呼小米躺下,小米就躺下来。二霞穿一件窄窄的小衫子,斜着身子躺着。小米忽然发现她跟以前不一样了。她的胸前突出来,腰是腰,屁股是屁股,让人看一眼就心慌意乱。小米看着二霞,觉得眼前这个二霞不是原来那个二霞了。这个二霞是陌生的,让她感到莫名的慌乱和忸怩。
晚上洗澡的时候,小米偷偷察看了自己的胸脯。她惊讶地发现,它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微微肿起来了,像花苞,静悄悄地绽放。小米看一回,又看了一回,心里涨得满满的,仿佛马上就要破裂了。
家里照常是一片欢腾。小家伙咿咿呀呀地嘟哝着,会咯咯笑了,笑得口水都流下来,亮晶晶地挂在嘴角。可是小米不关心这个。
这些日子,小米只关心一件事:去二霞家。
二霞在县城的地毯厂上过班,在小米眼里,算是见过世面的人。其实满打满算,二霞在县城才待了半年。后来地毯厂倒闭了,她的上班岁月也就仓促结束了。可是这并不妨碍二霞的眼光。小米一直认为,二霞是有眼光的。二霞给小米讲了很多新鲜事,这些事小米以前都没有听过。二霞问小米来了吗?小米困惑地看着她,不知道她在说什么。来了吗——谁?二霞就哧哧笑起来,笑得小米心里有些恼火。刚要发作,二霞又说,不来,就生不了孩子。小米心里咯噔一下子,看来坐月子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夏天的中午,寂静,悠长。小米和二霞歪在炕上咬耳朵。二霞了不得,知道的真多。小米听得脸上红红的,一颗心跳得扑通扑通的。后来,小米就把脸埋在被单子里,一双耳朵却尖起来,听二霞说话。听着听着,小米就走了神。二霞拿胳膊肘戳戳她,她才猛地吃一惊,把漫无边际的一点心思拽回来。
回到家,娘刚把饭桌摆出来,哥哥嫂子还在屋里磨蹭,爹蹲在脸盆旁哗啦哗啦地洗手。娘冲着东屋喊了一声哥哥说,快别磨蹭了,吃饭。小米看了一眼东屋的窗子,里面静悄悄的,孩子大约是睡了。娘又小声嘀咕一句,磨蹭。小米的心忽然就跳了一下。幸好是傍晚,院子里,天色已经暗下来了。小米知道自己走了神,在心里骂了自己一句,狠狠地咬了一口馒头。哥哥嫂子吃完饭,就一前一后地回屋了。小米想,刚才磨蹭,现在,倒走得怪急。娘叮叮当当地洗着碗,一边敷衍着在脚边转来转去的大黄狗。爹站在丝瓜架下面,察看着丝瓜的长势。小米又看了一眼东屋的窗子,窗帘已经拉上了,水红的底子上撒满了淡粉的小花,白天看倒不起眼,晚上,经了灯光的映射,竟有几分生动了。小米轻轻叹了口气。
晚上,小米就睡不着了。外屋,爹娘还在说话,有一句没一句的。有时候,好长一阵子静寂,忽然爹咳嗽起来,娘就嘟哝一句,像是抱怨,又像是心疼。月光透过窗户照过来,水银一般,半张炕就在这水银里一漾一漾的。小米闭眼躺着,一颗心像雨后刚开的南瓜花,毛茸茸,湿漉漉,让人奈何不得。小米脑子里乱糟糟的,她想起嫂子刚进门的时候。那时候,娘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别有事没事往东屋里钻。小米心里就愤愤的,凭啥?东屋多好!里里外外都是新的,满眼都是光华。东屋。现在,夜深了,东屋……小米不敢想下去了。
这些日子,小米忽然就沉默了。她常常一个人呆呆地坐着,望着某个地方,一坐就是半天。有好几回,她择菜,把好豆角扔了,把满是虫眼的倒留下来。摘西红柿,低头一看,篮子里都是青蛋蛋。娘没看见,她不会注意这些,爹也是。那个胖小子一天一个样子,家里的气氛是欢腾的、喧闹的、热烈的,大家的心都被成长的喜悦涨满了。小米默默地把豆角捡回来,把一篮子青蛋蛋剁碎,扔给鸡们。鸡们神情复杂地啄了一下,跑了。小米拿起一个青蛋蛋咬了一口,酸,而且涩。小米不由咧了咧嘴。
那天,是个傍晚吧,小米去二霞家。二霞家早吃过了晚饭。她爹娘都不在,一定是去听戏了。村东六指家老了人,从镇上请了戏。这地方红白事都要唱戏。戏台子上,盛装的几个人咿咿呀呀地唱着,台下,是熙熙攘攘的村人。戏腔,小孩子的锐叫,咳嗽声,葵花子的叫卖,此起彼伏,把儿孙们的悲伤都给淹没了。也有小孩子不愿意看戏,他们宁肯看电视。二霞也在看电视,见了小米,也不打声招呼,只管自己看。小米站了一会,就想走。二霞忽然说,别走啊小米。小米就停下来,等着二霞的下文。二霞说,咱玩个游戏吧,电视也没意思。
刚打过麦,麦秸垛一堆一堆的,像一朵朵盛开的蘑菇,在夜色中发出暗淡的银光。空气里流荡着一股子庄稼成熟的气息,湿润、香甜,夹杂着些许腐败的味道。二霞走在前面,小米在后面跟着。小米的后面,是胖涛。胖涛是二霞的弟弟,小时候胖得不成体统,人们都叫他胖涛。小米听见胖涛呼哧呼哧的喘气声,二霞,去哪儿啊?胖涛从来不叫二霞姐姐,他叫二霞。二霞不说话,只是低头走路。小米说,二霞……这时候二霞在一个麦秸垛前面站住了。麦秸垛像一个大馒头,已经被人掏走一块。二霞指挥着小米和胖涛钻进那个窝窝里,她说,现在,游戏开始了。小米看了一眼懵懂的胖涛,心里有什么地方呼啦亮了一下,她的心咚咚地跳起来。二霞说,来,这样。她让胖涛把裤衩脱下来,胖涛很不情愿,嘟哝了几句。二霞就劝他,许诺把自己那只电子表给他玩几天,胖涛就依了。
夜色朦胧,小米还是看清了胖涛的小雀子,它瘦小、绵软、青白,可怜巴巴。小米心里想笑,却不敢。一阵激烈的锣鼓声隐约传来,唱的是《卷席筒》。一个女声正在哭唱:兄弟——兄弟——呀……小米不敢看二霞,她瑟缩地低下头,说,回家了,天……不早了……
小米躺在黑影里,看着风把窗帘的一角撩拨来撩拨去,心里乱糟糟的,烦得很,她老是想着晚上的事。麦秸垛,浓郁的干草味,二霞闪闪发光的眼睛,胖涛的小雀子,可怜巴巴的小雀子,兄弟——兄弟——呀……《卷席筒》里嫂嫂的唱腔悲切动人……小米心想,二霞是不是生气了。私心里,她对二霞有那么一点,叫惧怕也好,二霞是成熟的,吸引人的,在言语和行为上,有主导性的。而且,二霞有见识。在二霞面前,小米愿意服从。可是,今天不一样,小米感觉今天的二霞有点陌生。二霞的声音、神情,甚至二霞的沉默,都有一种令她感到陌生的东西。陌生,然而又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吸引,还有恐惧,因为陌生带来的恐惧,以及对未知事物的天然拒斥。小米想起二霞的话。那些个午后,寂寞,肥沃,辽阔,无边无际。二霞的话像一粒粒种子,撒下去,就开出花来了。空气里是一种很特别的气息,妖娆,湿润,黏稠,蓬勃,让人喘不过气来。黑暗中,小米的脸一点一点烧起来了。她拿手捂住脸,发觉手心里湿漉漉的,都是汗。这时候,她才感觉两只手由于紧张用力而酸麻了。风掀起窗帘的一角,夜空幽深,黑暗。月亮不知躲到哪里去了。
第二天早上,小米起得很晚。爹娘叫了几遍,见没有应答,就由她去了。太阳都一房子高的时候,小米才苍白着一张脸出来。嫂子已经吃完了,正在给孩子喂奶。想必又是娘抱孩子,让嫂子先吃。这时候娘正端了一碗粥,一边喝一边逗孩子,见了小米说,这闺女,长懒筋了。小米不说话。她拿起一块馒头,慢慢地咬起来。孩子在嫂子怀里奋力地吃着奶,吭哧吭哧,能清晰地听见吞咽的声音。嫂子的奶水真足。小米想。这声音令小米很难堪。她看了一眼哥哥,哥哥正把头凑过去,轻轻刮着小家伙的鼻子。小米注意到,嫂子的乳房饱满、肥白,奶水充盈,一条条淡蓝色的血管很清晰地现出来。有时候孩子不留神,紫红色的硕大的乳头就会从那张粉嫩的小嘴里滑出来,只一闪,又被孩子敏捷地逮住了。小米看了一眼爹。爹坐在丝瓜架下抽烟,一副目不斜视的样子。小米把一片莴苣叶子卷起来,蘸了一下碗里的酱。小米喜欢莴苣,碧绿、水灵,看一眼就想吃。这时候,嫂子忽然惊叫一声,说这坏小子,疼死人了,一边说,一边作势拍了一下孩子的屁股。哥哥嘴里咝咝地吸着冷气,娘却笑了,说这小子,语气分明是自豪的。爹剧烈地咳嗽起来,止也止不住。一只白翎子鸡涎着脸凑过来,明目张胆地啄着南瓜叶子。爹嘴里哦啾哦啾地赶着,一时忘了咳嗽。
阳光从树枝的缝隙里漏下来,一点一点地,在地上画出不成样子的图案。小米把手伸出去,让一个亮亮的光斑落进手掌心里,然后,忽然把手掌合拢来,像是怕那个光斑溜走了。拳头上就亮闪闪的,像一只眼睛,眨呀眨。影壁前面传来索啦索啦的声音,娘在簸玉米。如今,玉米是稀罕物,通常是不吃的,只是有时候馋了,白面馒头也吃得不耐烦了,人们会仔细挑拣了玉米,细细磨了,蒸饼子,或者打白粥,都是新鲜的。娘簸玉米的样子很娴熟,一下一下,节奏分明。影子在地上一伸一缩,大黄狗从旁半卧着,看着看着就出了神。嫂子抱着孩子串门去了,家里一下子安静下来。爹去打棉花杈子,哥哥也不知到哪里去了。哥哥一向是这样,用娘的话说,是个媳妇迷。村里的壮劳力们大都出去打工了,哥哥没去。当然,也可能是嫂子不让去。总之,哥哥不去,做爹娘的也不好说什么。小两口整天黏在一处,人们都说,看人家小伏,岁数不大,倒懂得疼媳妇。一阵风吹过来,有一片阳光掉进小米的眼睛里,小米闭了闭眼。娘在簸玉米,这时候她停下来,擦了一把额头的汗。院子里很静,小米很想跟娘说点什么,可是想了想,又不知道说什么。小米看了一眼娘的脸,一绺汗湿的头发掉下来,随着她的动作一跳一跳。
吃完饭,小米睡午觉。小米躺在炕上,电扇嘤嘤嗡嗡地唱着,把身上的单子吹得一张一翕。小米闭上眼睛,酝酿着睡觉的事。
这是一明一暗的房子,爹娘睡外间,小米睡里间。平日里,小米是个头一沾枕头就睡的人,雷打不动。可是现在不行了。现在,小米发现,睡觉是一件很折磨人的事情。有时候,小米会突然惊醒过来,尖起耳朵。周围一片静寂,整个村庄仿佛都睡去了。外间屋传来爹的鼾声,偶尔,娘也磨牙,模模糊糊地说一句梦话。小米躺在黑影里,感到自己的脸慢慢烧了起来。
已经有阵子不见二霞了。其实,有好几回,小米的脚都开始往二霞家的方向走了,心底里忽然就探出一个东西,像缠人的瓜蔓,把脚给绊住了。小米拿自己没办法,想了想,就去地里摘甜瓜。
这地方,人们把甜瓜种在棉田里,叫套种。收花和吃瓜,两不耽误。村外的土路上坑坑洼洼的,深深浅浅的车辙把路面切割得不成样子。机器收割的麦茬齐斩斩的,已经有泼辣的玉米苗在风里摇头晃脑了。路两旁,田地里搭起了各式各样的简易房,它们在乡村的风中站立着,简单,潦草,漫不经心。房前房后抻起了绳子,晾晒着各色衣物。这是村里人家的养鸡场。周围很静,偶尔有母鸡咯咯地叫两声,引得一片鸡鸣,热烈地应和着。小米抬头看了一眼天边,太阳正慢慢地向西天坠下去。浅紫色的云彩在树梢上铺展开来,房子、树木、田野、人,都被染上一层深深浅浅的颜色。田边的垄沟上,零星开着几处野花,多是很干净的淡粉色,也有深紫的,吐着嫩黄的蕊子,很热烈,也很寂寞。小米不由得蹲下来,想掐一朵在手里,踌躇了一时,终于没有忍心。
天色渐渐暗下来了。远远地,一个人影慢慢从河堤下面升上来。逆着天光,小米只能看清来人的轮廓。这个人高大、黝黑,像黄昏中一座移动的铁塔。小米,你在这里,做什么?小米这才看清铁塔是村西的建社舅。建社舅是外地人,村里的上门女婿,论起来,算是娘的堂兄弟。小米看了一眼建社舅,他背了一只大筐,里面是堆尖的青草,颤颤巍巍的,很危险的样子。建社舅小心地把草筐卸下来,放在地上,有几蓬青草掉下来,滚到小米的脚边。建社舅说热,真热,一边把身上的背心脱下来,快速地扇着。小米看了一眼他的肚子,圆鼓鼓的,像扣了个大面盆。小米就笑起来。小米穿了一条布裙子,浅米白的底子,上面撒满了鹅黄色的花瓣。建社舅看了她一眼,说,米啊,建社舅给你打个谜,看你猜出猜不出。小米说,那你说。建社舅把汗淋淋的背心甩在肩膀上,从筐里拽出一根草,把它弯成一个圆,说,这是啥?小米说,还用问,傻瓜都知道。建社舅又从筐里拽出一根草,说,这个呢?小米扑哧一下笑了,草呗。建社舅也笑了一下说,傻。他把这根草从那个圆里穿过去,说,这个呢?小米想了想,说,这个,啥都不是。建社舅把那根草在圆里来来回回地穿进来,穿出去,穿出去,穿进来。他看着小米的脸,手下的动作越来越快。这个呢?小米感觉他的样子很滑稽,忍不住笑了。天色正一点一点暗淡下来,田野里,渐渐腾起一层薄薄的雾气,夹杂着庄稼汁水的青涩气息。远远地,村子上空升起淡青色的炊烟,和茂密的树梢缠绕在一起。建社舅不说话,他站在那里,手里拿着那两根青草。建社舅今天有点怪,小米想。她不想理他了,她要回家了。
暮色从四面八方涌过来,一点一点把小米包围。小米看了一眼树桩一样的建社舅,转身往回走。小米!“树桩”的声音从暮霭中穿过来,小米听得出他声音的不平常。她忽然有些害怕,撒腿就跑。
小米醒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太阳透过槐树的枝丫照过来,在窗户上描出婆娑的影子,画一般。小米听见院子里有人说话。
姐,吃了?
建社舅!小米感觉自己马上变得僵硬起来。娘说,吃了,建社你坐。
这天,也不下雨。
可不是,干透了都。青改还壮吧?几个月?
八个多。
快到时候了。
可不。
这一晃。
建社舅打了个哈欠问,米哩?
这闺女,长懒筋啦。娘在哗啦哗啦地洗衣裳,还睡哩,米——小米——
建社舅说,睡呗,没啥事。
小米忽然一下子就从炕上坐起来,拿手指拢了一把头发,噌噌两步就打开门,把帘子撩起来。院子里的人都没防备,吃了一惊。小米靠在门框上,一只脚门里,一只脚门外,阳光打在她的脸上,一跳一跳的,看不清她的表情。这闺女。娘嘟哝了一句,又低下头摆弄盆里的衣服。建社舅脸上讪讪的,一时没了话题。一只板凳横在门口,小米飞起一脚,把它踢个仰八叉。正在闭目养神的芦花鸡吓了一跳,嘴里咕咕叫着,张皇地走开。招你惹你了,这闺女。小米不吭声,往盆里舀了水,豁朗豁朗洗脸。建社舅说,那啥,待会子说是收鸡蛋的来,我回去盯着点。娘说,你忙,也叫青改过来坐坐,老闷家里。建社舅答应着往外走,小米洗完脸,抓起脸盆,哗啦一下泼出去,建社舅的裤脚就湿了半截。这闺女,怎么就没个谱。娘歪着头,使劲拧着衣裳,嘴巴咧得很开,老大不小了都。
这程子,小米心里老想着建社舅的那两根青草,想着想着就走了神。有一回,一家人吃晚饭,电视开着,是一个没头没尾的电视剧。男人和女人在说话,说着说着就抱在了一起,开始亲嘴。他们亲得很慢,很细致,像是要把对方的五脏六腑都吸出来。小米心里有些紧,她盼望电视里的人快点停下来。电视里的人却越来越有耐心,他们像两株蔓生的植物,彼此缠绕在一起,越缠越紧。小米不敢看了,她感觉手心里湿漉漉的都是汗水。屋子里的气氛也慢慢变了。有那么一会,大家停止了聊天,谁都不说话。电视里的人继续亲着,男人开始脱女人的衣服。屋子里静极了,只听见电视里的喘息声和模模糊糊的呢喃。小米感觉时间像是凝滞了,她木木地吃着饭,全然吃不出一点滋味。这时候爹终于站起来,他重重地咳嗽了一声说,这蚊子,挺厉害。他准备去拿蚊香了,可是又停下来,对着娘说,还有吧,蚊香?娘回头看了爹一眼,就起身到抽屉里找蚊香。抽屉乒乒乓乓开合的声音,把电视里的声音淹没了。哥哥回过头来,看了娘一眼。小米注意到,这一眼里似乎有些愠怒。趁着乱,小米走出屋子,装作上厕所的样子。一阵风吹过,院子弥漫着树木和蔬菜的气息,夹杂着人家的饭菜的香味。小米一直找不到借口出来,她怕大家知道她的害羞。害羞,就是懂了的意思。小米不愿意让家里人知道她不好意思。回到屋里的时候,电视上一切都过去了。画面上,是繁华的城市街道,阳光明媚,来来往往的行人、车辆,还有轻松的音乐。小米心里像有一根紧绷的弦,一下子松弛下来。一家人也恢复了正常,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气氛轻松。黏稠的空气开始慢慢流动,大家都暗暗舒了一口气。爹终于没有把蚊香点上。此刻,他神情自在,不慌不忙地卷着旱烟。
邻村四九逢集,一大早,娘就张罗着赶集的事。青改拖着笨重的身子走过来,娘见了,赶忙让她坐。青改却不坐,她站在那儿,一手扶着腰,一手扶着已经显山露水的肚子,两只脚分开来,像一个志得意满的将军。娘说,累吧?青改说,还好,就是脚肿得厉害。说着就让娘看她的脚脖子。小米看着青改艰难弯腰的笨拙样子,心里忽然有个地方疼了一下。她想起了建社舅的那两根青草。我怀小米那会,腿都肿了,一摁一个坑;小伏就没事。都说闺女养娘,这话也不能全信。青改说,噢,建社倒是盼小子呢。娘去赶集了,青改并不走。小米正不知道该怎么办,嫂子抱着孩子出来了,叫青改姨,亲亲热热地打着招呼。小米趁机溜出来,把青改留给了嫂子。
小米发现自己来事是在快中秋的时候。有一回,也是吃饭,小米站起来盛粥,回来看见板凳上有暗红的颜色,她心里一惊。她想起了二霞的话。这是来了,小米想。她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吃饭,心里却是慌乱的,扑通扑通跳得厉害。她不想把这事告诉娘。娘正专心致志地拿勺子一点一点把蛋黄往侄子嘴里抹,小家伙吧嗒吧嗒吃得很香。小米故意磨磨蹭蹭吃到最后,等大家都走开了,趁着娘去水缸舀水,小米飞快地把板凳面靠墙放好,跑进自己屋子里。
对于这件事,小米不是没有思想准备。该知道的,二霞都说给她听了。可是事到临头,小米还是有点措手不及。有一回,嫂子在厕所里喊她,她知道嫂子是忘了带纸,就撕了手纸送过去。嫂子却说,不是,不是这个。小米歪着头想了一会,也没想明白嫂子要什么。嫂子说,你去我屋里,抽屉里有。小米在嫂子抽屉里翻了半天,里面只有一包东西,还没有打开,淡粉色的底子上,有一个女人,女人很好看,一双眼睛似睡非睡。小米就拿了这包东西给嫂子送过去,嫂子接过来,忽然红了脸。小米就对这东西留了心。后来她才知道了那东西的用处。
小米关在屋里,费了好长时间才把自己收拾妥当。娘在外面喊她,小米,囫囵馒头啃成这样,还吃不吃了?
天气说冷就冷了。农历十月,有个十月庙,这地方的人很看重这个十月庙。庙就是村东的土地庙,其实是一间不起眼的小房子,香火却盛。说是土地庙,在村人眼里,就有了象征的意思。乡下人,对这种事是很虔诚的,谁家有了坎坷,都要来庙里拜一拜。求医问药,占卜吉凶,测问祸福,少不了要来烧一炷香。逢年过节,庙里就更热闹了。每年的十月庙,排场是很大的。村里请了戏班子唱戏,七天七夜,引得邻村的人们都过来看。一些小摊子就在庙会上摆出来,主要是吃食:瓜子花生、新鲜果子、馃子豆脑、驴肉烧饼、油炸糕。到处香气扑鼻,热气腾腾,整个村子像过年一样热闹。
只有小米例外。
怎么说呢?无论如何,小米是有些变了,小米是个有秘密的人了。小米的秘密不仅仅在二霞和胖涛,也不在建社舅,还有他手中的那两根草,当然也不仅仅是她“来了”。小米的秘密在于,她眼睛里的世界不一样了,或者说,她看世界的眼光不一样了。从前,在小米的眼睛里,世界是简单的,清澈、透明,一眼看到底。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有一天,小米出门看见大黄狗正在和建社舅家的黑狗纠缠,缠着缠着就缠到一处了,腿对着腿,不可开交的样子。小米的脸腾的一下就热了。她看看四周无人,捡起一块土坷垃就扔过去。两条狗却不理会,仍专心致志地做事。小米气得走过去踢了大黄狗一脚,大黄狗吃了一惊,身子并不分开,瞪着一双无辜的眼睛看着小米,嘴里呜呜地叫几声,表达自己的委屈。小米无法,跺一跺脚,就由它们去。回到家,小米心里恨恨的。她把门一下子关上,咣当一声,把自己都吓了一跳。
小米歪在炕上,看着墙角那个小小的蜘蛛网发呆。蜘蛛网很小,但很精致,蜘蛛去了哪里呢?小米想不出。可能蜘蛛趁小米不注意的时候,就会回来,这说不定。小米看着那个蜘蛛网,心里想,这个世界,总是有人们不知道的秘密。
乡下人憨直,嘴巴少有顾忌,尤其是男人们,他们总有说不完的俏皮话,荤的素的,黑的白的,热闹得很。逢这个时候小米就扭身走开了。她知道,男人说荤话是无妨的,女人却听不得,闺女家,尤其不能。其实,在内心里,小米是愿意听听这些荤话的。乡村的荤话,简单,却丰富,含蓄,却奔放,它们充满了无穷的想象力,耐人寻味。乡下人,有谁不是从这些荤话中接受了最初的启蒙?小米把这些话装进心里,没人的时候就拿出来想一想,想着想着就把脸想热了。
大人们都有秘密。小米想,哥哥和嫂子,建社舅和青改,爹和娘。想到这里小米心里颤了一下。她用最难听的话骂了自己。她不该这么想,尤其不该这么想爹和娘。爹沉默,甚至有点木讷,勤快得像头牛;娘呢,粗枝大叶,心直口快。爹和娘——小米艰难地想,究竟是怎样的呢?人前,爹和娘是不相干的,有时候,一天也说不上两句话。更多的时候,他们通过旁人进行交流。爹往往这样说,问你娘白娃家的砍刀还了没有;娘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叫你爹吃饭。在乡下,越是一家人,人前倒越是生分的,甚至是冷淡的。比方说,父子们在街上见了,彼此之间并不理会,也不打招呼,同旁人倒亲热地扯上几句,有时候干脆停下,热烈地聊起来,聊着聊着就嘎嘎笑了。爹和娘也是这样。走在街上,不知情的,谁能猜出他们是夫妻呢!这真是奇怪的事情。有时候,小米从父母屋子里穿过,心里是紧张的,她有些担心。担心什么?她说不出。可这紧张里又有一点期盼。期盼什么呢?小米也说不出。这真是一种折磨,为此,小米的一颗心就总是悬在那里。越是这样,小米就越觉得爹和娘之间的不磊落。她怀揣着很多纷乱的心思,想过来,想过去,就有些生气。究竟生谁的气呢?她也说不好。
十月庙,村子里是热闹的,人们的心都被大戏吸引了去,说话、做事,心不在肝上。娘是个戏迷,这机会更不能错过。爹醉心于戏台下面的事:几个人围在一起,掷骰子。哥哥嫂子也出去了。小米歪在炕上,把电视频道噼里啪啦地换来换去。换了一会,小米啪的一下关了电视,跳下炕来。
街上人来人往,空气里蒸腾着一股子热腾腾的喜气,仿佛发酵的馒头,香甜,带着些许酸。小米喜欢这种味道。她有些高兴起来。
村南的果园子旁边有一个草棚子,这地方人叫作窝棚,是看园子的人住的地方。如今,果园子早已经过了它的盛季,窝棚也就闲下来,显得寂寞而冷清。小米对身后的胖涛打个手势说,过来呀。十月,乡下的风终究是有些寒意了。胖涛的清鼻涕一闪一闪的,隔一会,他就慌忙吸一下。
小米是在家门口碰上胖涛的。胖涛手里举着一串糖葫芦,一边走,一边吃。小米说,胖涛,二霞哩?胖涛说,二霞去看戏了。小米说,噢。就转身走,没走几步,又停下了。胖涛——小米说,你跟我来。
周围很静。有风掠过果园子,树木簌簌地响着。窝棚里弥散着一股干草的气息,有点涩,有点苦,还有一点芬芳的谷草的腥气。小米和胖涛面对面躺着,谁也不说话。胖涛说,咱们,干啥?小米说,不知道。胖涛说,那,去看戏了。小米说,看戏有啥意思。胖涛说,那你说,干啥?小米说,你说呢?一阵风吹过,有丝弦的声音隐约飘过来,细细的,游丝一般,若隐若现。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残垣……胖涛吸了一下鼻子,说,不知道,要不,看戏去?小米白了他一眼,说,傻,就知道看戏。
冬天是乡下最清闲的时节。庄稼都收进了屋,人们也就放了心。爹专心摆弄自己那匹牲口,有时候也去给人家当厨子。爹的手艺不错,在村子里是有些声名的。冬天,办喜事的人家多起来,爹常常被请去,出了东家进西家。娘原是喜欢玩纸牌的——也不玩大,一角两角的,一晌下来,也分不出输赢,白白磨了手指头。如今娘却不怎么玩了。孩子正是淘的时候,不肯在屋子里待,娘和嫂子就轮流抱着出去。孩子在寒冽的空气里手舞足蹈,脸蛋子冻得通红。
这些日子小米总是郁郁的。有时候,小米也会想起窝棚里的事。她的慌乱,胖涛的委屈,麻雀在窝棚的地上跳来跳去,瞪着一双乌溜溜的小眼睛,好奇地看着他们。
月事照常来,一步都不差。小米的一颗心就放回肚子里,又有些怅怅的。小米想起了二霞的话,越想越感到烦恼。娘抱着孩子回来了,嘴里呼啸着,孩子的笑声像碎了的白瓷盘子,亮晶晶撒了一地。
小米,娘喊她。小米不答应。娘就教着孩子叫,姑姑——姑姑——不听话。小米还是不答应。孩子的小手肉乎乎的,一把把她的辫子抓在手心里。小米刚想回头,眼泪就在眼窝里打转。娘说,臭小子,看把你姑姑弄疼了。小米的眼泪终于扑簌扑簌落下来,怎么也收不住。
发表于《中国作家》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