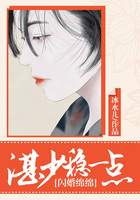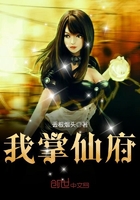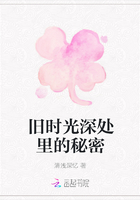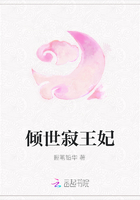梅老夫人——梅兰芳的遗孀福芝芳女士——那时还健在,正月初二是她的寿辰,每年这一天,我必去梅府,先给老太太拜寿,再给梅府一家人拜年。这一天梅府总是宾客盈门,绍武的朋友多半坐在西厢房他的客厅里喝茶聊天,中午到东厢房吃一顿寿面。因为人多,厨子准备的是比较简单的炸酱面。北京人爱吃炸酱面,这在梅家已成为招待客人的传统。多年以后,梅老夫人已经仙逝,绍武一家离开宣武门迁到另一处新居。我有时去他那里闲坐,仍旧惦记着留下来吃一顿炸酱面。
绍武走了。一个充满敬业精神、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一个几十年如一日一丝不苟的翻译家和作家;一个既可与之闲谈,又可与之切磋学问的长者;一个乐于助人,讲信义、重然诺的朋友。这样一个人理应享有更长的寿命,在文坛和翻译园地里种植出更多的奇葩。但造物者忌才,更忌妒有才华的好人,竟匆匆把他召走了。作为他的好友,我不仅感到悲痛,有时候还会自问:像绍武这样一个谦谦君子型的学问家,在我们今天的知识界还有几人?
我会见了七十八岁的格雷厄姆·格林
1981年10月16日,应邀赴H旅馆见G.格林先生,晤谈一小时又二十分钟。G在1956年曾来中国访问,远至重庆。
1981年10月19日,收到G邀请赴法信。携信去法国领事馆办理过境签证,仍不获通融。
1981年10月22日,下午四时自爱丁堡返伦敦。G曾赠作品十二册已寄达Y处。伊丽莎白·丹尼斯太太(G先生的妹妹)随书附有短笺。
虽然早已放弃记日记的习惯,但在国外几个月,偶然还做了一些流水账式的记录。主要是把见过的一些人,去过的一些地方的名字记录下来,存档备案,以防日久遗忘。翻阅一下旅居伦敦的记载,同格雷厄姆·格林的一点儿因缘,也就是前面那寥寥几笔,现在想要写下点什么来,很多细节都要像讨取欠债似的向记忆追索了。
同格林通信是1979年春天的事。1978年年底《问题的核心》已经基本译完,在遗留下的一些疑难问题中,有几个看来在国内是查询不到的(记得其中一个是书中人物威尔逊的公开身份——"U.A.C.的会计”。谁也不知道U.A.C.是United Africa Com-pany——非洲联合公司——的缩写),不得已向国外朋友写信请教。远在伦敦的热心肠的Y君“贸然”(从我的观点看)替我给格林写了一封信(通过鲍德莱·海德出版社),不久以后,格林先生就回信对提出的问题做了解释。1980年夏,这本书在国内出版后,我给格林寄去一本,并写了一封信,略诉我对这位当代名作家的仰慕之情。可能中国人的姓名、地址对外国人总是困难的,后来格林为国外某一大学图书馆索取另一本《问题的核心》中文译本时,信还是写到伦敦Y君处,Y只好把我送给他的那本转寄去了。这事还是我去年10月到了伦敦以后才听Y君说起的。
去年年初到了德国,又同格林通了信。格林表示愿意同我在欧洲某处相会。我当然不能请他到德国,但自己又无法到他长期定居的里维埃拉去,一直拖到回国前,借去英国的机会才同他见了面。这倒也好,我是在诞生这位作家的国土上和他会晤的,而且见面之前已经在以出产布赖顿棒糖出名的布赖顿住了两天。虽然早已过了消夏季节,但我也像《布赖顿棒糖》里的海尔一样站在皇宫码头上眺望了大海,在堡垒广场上一家小饭馆吃了午饭……一句话,在书本里探索了二十余年格林创造的奇妙的国土后,我已经踏上了其中一个小小的角落了。
像任何一个游历过“格林国度”而着了迷的人一样,自从我在20世纪50年代偶然闯入这个国度后,就一直寻找机会继续在他创造的这一既陌生又亲切的奇境里漫游。“秃鹫扑扇着翅膀飞过一个尘土飞扬的墨西哥小镇的广场,沉重地落在瓦楞铁房顶上……布赖顿的灯火熄灭了,留下皇宫码头上栈桥的漆黑的支架和桥下幽暗的流水……西贡的穿着黑裤子的满脸皱纹的老太婆蹲在小便所外面台阶上聊闲天……弗里敦郊外的红土路在日落时变成粉红色,转眼就被夜色吞噬了。”(见大卫·洛奇(David Lodge)的《格雷厄姆·格林评传》。)批评家们曾经指责格林太喜欢描写人世间一些卑劣、丑恶的东西,甚至认为在作者内心世界中也有这样一个“卑劣”的区域。虽然格林在《逃避之路》一书中对这一指责为自己进行过辩解(参见格林回忆录《逃避之路》(1980)选译,《世界文学》1982年第3期。),但是谁也不能否认,暴力、犯罪和死亡是经常出现在他作品中的主题。有时我也怀疑,有的读者(包括我自己)被“格林国度”迷惑住,是不是对于世界各地的阴暗面过多地感兴趣,是不是太容易被人世间的辛酸所触动,是不是基于一种不很健康的“猎奇”心理?这倒使我想起同格林谈话时,他向我提出的一个问题。当时我们在谈格林有哪些作品被译介到中国来。我谈起《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已经有人译出,尚未出版。格林说这本书在某个东欧国家竟被评价为“反宗教”的作品。(参见格林回忆录《逃避之路》(1980)选译,《世界文学》1982年第3期。)中国人大概不会这么看吧。“中国人喜欢不喜欢看描写‘异国情调’的东西?”格林问。我认为这个简单的问话可能涉及心理学、美学、文学鉴赏等等深奥的问题,远非我所能解释的,我对中国广大读者的爱好更未做过调查。我当时只能回答说,我个人是喜欢蛮荒探险一类书籍的,不过这也可能是童年时代留下的一个“固执观念”,这次到伦敦来还特意买了一本《所罗门国王的宝藏》(《所罗门国王的宝藏》是英国小说家赖德·哈格德(1856-1925)的小说。)。我知道这也是格林小时候喜欢读的一本书,我读过他的《失去的童年》。在那篇散文里,开头的一句话就是:“也许只有在童年时期书籍对我们的一生才能有那么深远的影响。”要解释一个作家的生活和创作道路,当然可以从他小时候喜爱的书籍中求得一些解释,但却绝不能从这里得到全部答案。以格林论,他自己不止在一处谈到他十四岁时读过的《米兰的毒蛇》(《米兰的毒蛇》是英国小说家梅介里·鲍恩(1888-1952)的一本有关意大利政坛阴谋的书。)对他终生的影响,许多格林研究者对此也津津乐道。但难道这就确定了格林喜欢以“阴谋”作为作品的主题吗?
为什么格林常常把自己要讲的故事放在不十分体面的环境背景中?这是格林著作的研究者的一个课题,而不是在我同他短短的一个多钟头的谈话中所应提出的问题。但是有一点我是敢肯定的:格林绝不是单纯为了猎奇而描写蛮荒、落后的场景的。他的新闻记者的敏锐感觉常常把他带到地球上一些“闹乱子”的地方,而乱子出得最多的又常常是那些“残酷”和“暴力”连一层虚伪的文明外罩都脱掉、横行无忌的地方。人生的戏剧——生与死的角逐,善与恶的斗争,只有在那些地方才表演得淋漓尽致。“邪恶在世间横行,至善无立锥之地。”这是《米兰的毒蛇》给予格林的认识格式,但也是同他的世界观和宗教思想相符合的。重要的是,格林的同情心总是在弱小者和无辜受难者的一方面。邪恶的势力尽管巨大,但人类的良心并未完全泯灭,为正义而进行的斗争不绝如缕,但最终到来的不会是一片黑暗;撇开格林的宗教观不谈,在他的作品中,不论“消遣作品”也好,严肃小说也好,总有一些发人深思的东西,一些召唤人追求高尚与善良的东西。也许这正是使格林有别于一般资产阶级作家、特别是天主教作家而跻身世界伟大作家之列的原因吧。
格林问我他的作品在中国有什么反应,可惜我回答不出来。
我只能告诉他一些他的作品在中国译介的情况。《一个沉静的美国人》早在50年代中就出版了,但是这以后除了一个短篇在《世界文学》发表外,是二十年的冷遇。“天主教作家”这个头衔把当时神经脆弱的中国出版界吓住了。直到最近两三年,随着文艺界真正贯彻了百花齐放的政策,中国广大读者才逐渐知道英国的格雷厄姆·格林。《人性的因素》已经出版了,《日内瓦的费舍尔博士或炸弹宴会》(1980)听说有三个译本,国内外国文学杂志陆续发表了不少他的短篇小说,另外还有几个长篇正在翻译中。是的,中国这几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外部世界的交往更多了。格林很高兴,中国除了引进技术设备、石油钻台和计算机外,连《布赖顿棒糖》(《布赖顿棒糖》(1938),是格林著名长篇小说之一。)也进口了。他认识的一个人,最近第三次从中国回来,告诉他北京城出现了更多的大楼,古老的城墙差不多完全被拆光了,四合院也很难看到,一定同格林1956年见到的北京大不相同了。那次他来中国,接待他的是Rickshaw Boy(英语,意为“拉人力车的小伙子”。)的作者(他不记得老舍这个名字,《骆驼祥子》这个书名对外国人也太困难了),那个作家对伦敦的情况很熟悉。“我同周恩来握过手,毛泽东我只是从远处看到一个侧影,那是在庆祝中国国庆的晚会上。”看得出来,格林对那次中国之行是很怀念的。但是在他的记忆里,印象最深的还是江面上舢板云集、江边纤夫唱着号子的重庆。四川的烹调似乎也很合他的口味,在重庆的一个招待所里,格林吃到了他终生难忘的中国饭菜。但就是当他和好客的主人享用稀有的佳肴美味的时候,在餐厅的另一角,几位“老大哥”却正在愁眉苦脸地吞咽远从莫斯科运来的罐头食品。“我不知道他们喝的水是不是也从苏联运来?长江看上去是有些浑浊。”格林的一双蓝眼睛里闪现着诙谐的笑容,我也报之以会心的微笑。
格林先生手里捧着的已经是第三杯威士忌酒,我则在啜饮第二杯橘子水。(“只喝一些soft drink(英语,意为“不含酒精的饮料”。)吗?中国的茅台可是世界驰名的。”)同这位大作家在一起一点也不叫人拘束。他很健谈,但又绝不把谈话全部垄断,而且时不时地你会听到一两句像上面引述的冷峻的幽默。在谈到中国的时候,你可以感到他对这个古老的国家怀着真诚的感情。年轻时代,格林甚至想到中国来工作。“前途就放在书架上的几个格子里等着孩子选择——领取了皇家特许状的会计师、殖民地文官、在中国经营一个种植园……”(见格林的《失去的童年》(1951).)V.S.普列契特在《格雷厄姆·格林的人情味》(见1980年第2期《世界文学》。)中似乎也记载了他想到中国来的愿望。“有没有计划再去中国访问一次呢?”是的,很愿意再去看看从T.S.艾略特(T.S.艾略特(1888-1965),20世纪的美英现代派大诗人、批评家,1948年因《四个四重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到萨缪尔·贝克特都已开禁的中国。但是未来的事谁也说不准。年纪太大了,这次到伦敦来是为了做例行的身体检查。虽然1961年在莫斯科害过很厉害的肺炎,而且还被一位很高明的苏联专家误断为肺癌,但是身体一直很好。从二十几年前写了《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就准备搁笔了。1966年离开伦敦准备在法国长期定居的时候,已经把过河的渡船一把火烧掉了。但是有谁会想到“在燃烧的船只的熊熊火光中,又开始了另外一本小说呢?”(见《逃避之路》,另一本小说指1969年出版的《随姨母旅行》。)作家的本能总是不听从理性劝告,不愿俯首帖耳地服从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但是写作计划是无法预先安排的。如果说《人性的因素》还在思想里酝酿过很长一个阶段,《日内瓦的费舍尔博士或炸弹宴会》的写作就来得非常突然,可以说是即兴创作。事实上,执笔创作常常是由一个非常微妙的契机引起的,有时候甚至是一个梦境。《荣誉领事》和《这是战场》就是这样产生的。格林在《逃避之路》中几次谈到这个问题。很多评论家都认为梦境同阴谋、背叛、死亡等一样,也是格林的一个“迷恋”(一个叫约翰·艾特金的批评家,甚至计算过格林作品中描写梦境的场合。据他说,截至并包括《一个沉静的美国人》在内,梦在格林的早期作品中已出现了六十三次。)。这个问题且留待研究弗洛伊德学说的人去解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