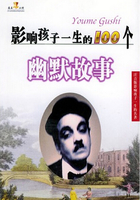丽奇·卡普兰成了我们家厨房里那张圆橡木餐桌前的常客。不像宝琳住在我们家那会儿,这次梅耶舅舅没有回避。
在汤普金斯大道的我们家的厨房里,在我们所有人头一回同坐在一张桌子前的那天晚上,他和丽奇面对面地坐着,一边被妈妈和艾米丽隔开,而另一边被我和爸爸隔开。本杰明很早就吃过饭了,正坐在厨房的地板上和他的小熊玩。我们其余所有人都坐在一起吃饭。
丽奇·卡普兰问了爸爸和妈妈泰迪熊生意的情况,问了艾米丽正在看什么书。当我们问到婕尔达姑妈时,她又说起她在房地产买卖上逐渐展露的才能。
刚开始时,她在餐桌上很文静,她专心听讲,彬彬有礼。
她一边听着每个人讲话,一边把脸从一个说话的人转向另一个说话的人,眼睛炯炯有神,显得饶有兴趣。第一天晚上的饭吃到甜品的时候,梅耶舅舅把餐桌上的话题转到政治上面,丽奇·卡普兰看似不大愿意发表意见,她转而谈起了歌剧。
“你爱看歌剧吗?”梅耶舅舅问。
原来他们俩都看过同几场演出。
“真有趣,”梅耶舅舅说,“跟另外一个人的生活轨迹一直重合,可又一直没发现。”
那晚之后,我就跟丽奇·卡普兰换了位置,她坐到了梅耶舅舅的旁边。到了第三天晚上,丽奇已经不再那么内向被动了,她也跟其他人一样,成为餐桌上欢声笑语中的一分子。
厨房里又热闹起来,连妈妈做的菜也似乎变得好吃了。
她终于记起了怎么去笑,爸爸也一样。
梅耶舅舅知道了一件事:只要是椰子做的,丽奇都爱吃。
“露丝,明晚的甜品让我来。”他轻轻地搭着妈妈的肩膀,对她说。
第二天晚上他带来了椰子蛋糕,是他亲手做的椰子蛋糕。
谁知道梅耶舅舅还会烤蛋糕呢?我还以为他不懂做菜,所以才跟我们一起吃饭呢。没想到,梅耶舅舅的香蕉手指在厨房里还有两下子嘛!
妈妈笑眯眯地看着他的弟弟。她给丽奇·卡普兰和梅耶舅舅之间的感情努力浇灌,就像在温室里培养一棵漂亮的盆栽。
我们家厨房的气氛再一次被热情、喧闹的讨论带动起来了,好像又回到了以前,回到妈妈和爸爸还没有一心扑在泰迪熊生意上的时候。我们喜欢上了丽奇·卡普兰。自打罗斯福总统到密西西比州转悠了一趟之后,我们就家不成家了。
是丽奇·卡普兰,是她把我们一家人又重新拧在了一起。
对此,宝琳·乌恩格尔也以她自己的方式做出了贡献。
她把她的俄国丈夫带到我们家,于是他被爸爸聘请为监工,负责监督剪裁的工人。宝琳的俄国丈夫只干了几个礼拜,就已经能够替爸爸减轻一些负担。虽然爸爸还是没能腾出一个晚上来带我们去康尼岛玩,但总算让我和爸爸没再吵架。
咳,其实我们也不常吵架啦。
有个游乐设施叫“跳跳蛙列车”,同样行驶在海面上……
两辆车载着头发飞扬的游客
在同一条轨道上迎头相遇。
如果在陆地上车就撞扁了,但在这轨道上,这两辆车却翻着筋斗擦身而过,继续前进。
——《纽约时报》
梅伊
大桥下的夜晚,发光的男孩自由出入。他的脚底在飘移,他的身后发散出一股股寒气。没有人妒忌他,因为发光的男孩肯定已经死了。不过大桥下的孩子们有时也无法判定一个人是死是活。像梅伊,他们就是无法判定她是生是死。这个女孩口唇乌青,嘴巴曾被石炭酸[1]灼伤,手臂上被划了一道道齐整的伤口。
她像发光的男孩一样,一身白装,所以有些孩子说:
这就能看出来啦——身上穿着白色衣服的,肯定是死了。
可有些人就喜欢穿白色的呀。
就算没被石炭酸灼伤,梅伊的脸也长得不太好看。她的眼、耳、口、鼻无法组合成一张好看的脸。像她这样的女孩,估计一辈子都不想见到镜中的自己。她从来不跟他们说话,所以又有些孩子说:
这就能看出来啦,死人不讲话的嘛。
也有可能是毒药把她的嗓子毒哑了呀。
她只知道哭,无声的眼泪从她的脸庞淌下。她的双眼像是乌黑的脸庞上被打出来的两块瘀青。她的脸上留下两行泪痕,嘴边的痂里渗出了脓。
如果你想正视她的双眼,她会避开。
然而她也不愿独处。她无时无刻不在留意他们,凑近他们。
她就像一窝狗仔中发育最不良的那一只,被其他兄弟姐妹嫌弃,被妈妈忽视,却又拼命挤到它们当中,扭捏不安。她渴望成为大桥下这个大狗窝中的一分子,分得它的温暖,共享它的气味。
而大桥下的孩子们虽然不知道她是生是死,还是让这个女孩,梅伊,留了下来。他们不给她食物,因为他们不清楚她是否能吃东西。她的嘴巴结满了痂,还怎么吃东西呢?有一次,但也只有这一次,新娘触碰到了梅伊的脸庞,梅伊也没回避。然后新娘说:
她活着。她的脸是暖的。
只要是新娘说“她活着”,那么大多数孩子就都会相信,尤其是迪奇。但还是会有人不信。有些孩子认为她:
死了。
所以无论她如何想方设法靠近这些孩子,他们都会敬而远之,与她保持距离。
奥托
大桥下的孩子们,他们的家有的让他们无立足之地,有的对他们漠不关心,有的则早已支离破碎,所以彼此在大桥下组成了一个家。有时他们互相扶持,有时又各有争吵,这就像一个正常的家。但是,即使是当中最不起眼的孩子,也是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分子。如果他吃了苦头,大桥下的孩子们会帮他出头,当机立断、毫不含糊地施展报复。
孩子们的忠心义气被奥托大大地考验了一番。奥托对以前的生活全无印象,只记得曾与一位孤寡老人住在一个叫因伍德的小镇上的日子,这位老人是奥托的曾祖父。
老人死了以后,奥托仍然留在他的遗体旁,守了三天三夜。
奥托在小棚屋里冻得瑟瑟发抖,却还是不敢离开,他盼望着老人能睁开双眼,对他说:
骗到你了吧,这次?
但最后男孩想通了,草地上的这间小棚屋永远也不会再暖和起来了,除非他一把火把它烧了。于是他把它烧了,然后一路流浪,又在大桥下找到了新生活。
奥托爱生火。孩子们便让他在夜里把垃圾桶当成火炉,给它生火,好让他们在大桥下能保持暖和。白天,奥托会跟着消防车跑,穿过布鲁克林的大街小巷。他常吹嘘自己有一天会穿上消防队员制服。他有时会在消防局里过夜,骑到锵锵作响的消防车的车顶上。对奥托而言,纵火的人和救火的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反正都是火。
但有一天,接近傍晚时,奥托被一帮流氓逮到了。他被他们拖到消防局的后面,剥光衣服。奥托拼命反抗,但他们人多,而且个头儿比他大。他们用个什么东西把他的嘴堵住,其间还要一直躲闪他的脚和拳头。他们推搡着赤身裸体的奥托,把他推到消防局的地下室里。他怒不可遏,猛烈还击,这让他们始料不及。他把他们吓怕了,却也让他们变得更残忍。这帮流氓将红漆涂在奥托裸露的身体上,然后他们把他捆起来,遗弃在黑夜里。
奥托终于逃了出来,飞奔着跑回大桥下。他暴跳如雷,赤身裸体,浑身上下只涂着一层红漆。大桥下的孩子们听着他咬牙切齿地把他的经历一个字、一个字地吐出来,他们听懂了他遭遇的不幸,然后新娘和海伦想在东河里给他洗掉他身上厚厚的那层油漆,但都被他甩开了。他如一头狂犬,朝可怜他的女孩们暴烈地嘶叫。
于是,只好由麦克斯和卡尔来为奥托洗。他们粗鲁地用力擦着,直把奥托弄得嗷嗷叫疼。第二天一早,麦克斯和卡尔离开大桥,走到奥托被羞辱的那个街区。他们监视着,守候着,最后终于逮到两个手上沾着红漆的男孩,其中一个还戴着奥托的黑色硬礼帽,那是奥托的曾祖父留给奥托的礼帽。
那天晚上,他们回到大桥下,手里拿着两套衣服。他们把奥托的帽子给他戴回到头上。
我们给他们全脱光了,连沾了油漆的衣服也没给他们留下。
然后奥托咧嘴笑了,他想象着袭击他的其中两个人被困在布鲁克林的街道上的模样:赤条条的,像被剃光了毛的猫。这回看他们怎么向他们的爸爸交代!
奥托在幸灾乐祸。奥托,这个从来无须向任何人交代的奥托。
卡尔递给奥托两套几乎没有破洞的漂亮衣服,让他选一套。
这身衣裤鞋袜,全都大了一号,但这是他有记忆以来第一次穿上有鞋带的鞋。奥托昂起头,嘴角抽搐,透着一丝冷酷的快意,而他的皮肤仍然染着淡淡的红。这让奥托看上去有点儿凶狠,比他平时还要凶狠。
然而,当卡尔把火柴递给奥托,让他把垃圾桶火炉点着时,奥托却说了一句:
免了。
然后他便走开了。
里面有个巨型剧场,
观众可以欣赏火灾救援表演,
大片大片房子着火,
真实的消防车开进剧场,
消防员从工厂窗户惊险地救人,
还有许许多多刺激的表演环节。
——《纽约时报》
注释:
[1]苯酚的别称,是一种具有特殊气味的无色晶体,有毒,具有腐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