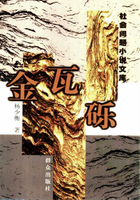我听见哨声,在窗前房后穿越着响,一阵紧似一阵,仿佛有无数根细长的针在空中横飞。随即是鸡叫,一只,又一只,比赛似的使劲儿往高处啼,好像在追赶那尖利的哨音,狗被招惹起来了,相当粗野地狂吠,远远近近乱纷纷响作一片。
睁开眼睛,感觉晨光十分扎眼,片刻内恢复知觉,才看清那并非晨光,而是低矮的屋顶上一个无罩的灯泡白蒙蒙照着。身边的林沂蒙已经穿好棉衣半跪在炕上,呼呼呼地叠被子,她顺手推我一把,说:出操哨,赶快出去集合!我应一声,立刻坐起,抖抖索索地把毛衣套到头上。同屋的人都在穿着蹬着。她们的面孔带着迟滞,大都眯着眼睛,动作却飞快。没人说话,只有紧张的嚓嚓声。
几分钟后,宿舍前面站好两列面影不清的队伍。我贴到队尾,随着一个连着一个快速转脸的人头报数:“35!”我是第35个。刚刚意识到这一点,脚下便腾腾地跟着跑起来。
是春寒料峭的时节,是在北国的冻土地上跑。昨天发给我的新棉靰鞡,鞋底比穿过的鞋子要厚实些,还是觉得地面梆硬震脚。冰冷的夜气冻结在身上,脸颊感到风如刀割,呼吸很是艰苦。然而不停地跑,不停地跑,还要高呼口号。
沉闷的脚步踏着寂寥的大地,最后的昏朦渐次散开,绝远的空中,有一道银灰的光亮正向四外扩展。宿舍、草棚、方块窖、高大的烟囱,所有静物的轮廓,逐一地清晰出来。烟囱直刺的天幕里,低悬着两颗银钉似的白星,正一点点变虚幻,像是什么人的灵魂,很萧索地隐匿掉。
“一、二、三——四!”前面传来粗豪的口号声,紧接着一片重喊——另一支男生的队伍从斜岔里跑过来。男生的队伍比我们的显得雄壮,他们从我们身边跑过,脚步故意踏得很响,像坦克车似的横冲过去。看不清他们的面孔,只觉得他们个个头发蓬乱,脸面乌涂。几人土黄色棉衣的后背布面撕开了,裸露出机器轧着的一条条棉花,显得那么褴褛,许多人拦腰扎了一道粗麻绳。
我感到跑不动了,心脏突突突地乱蹦,像要从喉咙里飞跳出来,眼前一阵阵发黑。坚持着,大口喘气,脸憋得像红布娃娃了。只想掉队,只想跌倒。
——真不明白为何要这样没完没了地跑,好像要跑到世界尽头去。我想到今后的每一个凌晨,想到无休止的日日月月……
出操结束,我蹲在地上,双手掩着脸,像一条刚刚脱水的鱼那样大口喘气,半天站不起来。林沂蒙站在旁边等我,问:你怎么啦?她拽我衣领,俯身看着我,惊讶地叫:呵,你的脸紫青紫青的,真吓人,这说明你平时太缺少锻炼啦!
我只想窝着喘个够,不在乎她说什么。
回宿舍时林沂蒙一直数叨我:你这样可不行啊,白天还要干活儿呢,你不知道干活儿是什么样子,你必须增强体力!
林沂蒙说得对,我们主要的任务是干活儿,干各种各样与制砖制瓦有关的活儿。头一天是挖排水沟。那些草棚要晾晒湿的砖坯,两侧必须疏通积水。林沂蒙推来一车铁锹,每人先选走一把,都是带了记号的,剩一把新的留给我。握住锹把比一比,看它和我个头差不多高。林沂蒙招呼一个面孔黑红的本地姑娘,说:小金子,你跟孙小婴去挖一号棚。
我和小金子从一号坯棚南侧的中心位置开始,一个朝东,一个朝西,一锹一锹地挖沟。很快就觉得吃力了。锹把是新砍下来的秃树杆儿,握着刺手,锹头上没有开口,使起来厚墩墩的蹬不上劲儿,一会儿的工夫,锹头就拖着一个沉甸甸的大泥坨子。拣根儿荆条不断地刮,进度便慢极了。看看身后的小金子,人家挖过去好大一截儿了。
眼望前方,面对着的荒原空阔无比,它从根儿上吞噬着我的精神。荒原袒露无遗,以侵占一切的趋势向外延展。未曾见过的景物全部真实如铁,我好像站在了北极圈的永冻土上。我想:大概人类首次从洞穴里出来,就是在这样又荒又冻的土地上开始耕种的。因为刚刚烧过荒火,黑漆漆的荒原上,没有一株树,甚至连一丛高些的茅草也没有,烟熏火燎的焦枯色给荒原罩上一派混沌之气。
荒原如此地逼近我,令我感到面对着的是一派汹涌的黑色大海,一种可怕的压迫力和震撼力全面地灌注下来,心里没有一点儿承受的准备。也许我宁愿见到密密匝匝荆棘丛生的草野,也不愿见到这般苍茫的焦土。面对它们,外界的荒凉与内心的荒凉纠合一起,形成打击,令我想到满目疮痍的战场、天灾人祸的劫难……
我正在荒原阔大的胸膛上开掘一条细纹般的小沟,这于整个荒原无关痛痒,可我已经筋疲力尽。并非我不知努力,事实上我已经相当拼命了。越是拼命越是显出笨拙。胃里一阵一阵发酸,想那早饭真是难吃,玉米面的发糕碱放少了,就着土豆汤往下咽,怎能不胃酸呢?
一阵哨声响,是叫人休息一会儿,小金子走过来,看了看我可怜的“战绩”,晃晃脑袋说:歇会儿吧。说着她猫腰钻进坯棚,铺开一卷苫坯子的苇帘,招呼我和她坐上去。
困顿地坐在坯棚里,想打瞌睡,又不敢。寒风呜呜地劲吹过来,携带着荒原上焚烧的气味,天是钢灰色的,大团大团边轮破碎的云朵在眼前飞驰,坯棚四外透着天,因此什么都遮挡不住。
小金子突然就唱起歌来。原来她是朝鲜族人,她的歌全是用朝鲜语来唱。我听不懂,但我能体味出内容的苍凉,能感到悱恻动人。她已经忘记我,只一味地面向旷野,双手抱住膝头一路嚎唱下去,黑红的脸膛布满简单的快乐。听着她唱,眼望莽莽荒野,我忧虑地想:这大荒野总该在什么地方有个完结,完结之后的地界该是何种样子的?
……是否,“广阔天地”,就是这样的,荒旷苍茫,无边无涯,什么也没有,哪怕走上七天七夜也不会走到尽头?
……“广阔天地”,应该叫我想到翅膀,想到飞翔,可是,飞翔的目标,在哪儿呢?人,是这样的小,包括我们的连队,我们的营地。“大有作为”,我们的作为能是怎样的?
显然我得纠正自己,我的忧虑很成问题,可是,我不知道,怎样想才算合适。我总相信,感觉比之觉悟是要快得多,就像光比声音要快得多一样。我发觉,荒原给我的压抑感,在头一天就深入于心,烙成了一道沉黯的永远难以抹掉的底色。
就这样,我加入到了身边的队伍里,以虚弱的体力、忧虑的情绪、困惑的心。听着双轮车里躺着的数把铁锹和十字镐不断地敲打车帮,我在想:也许此后一生都要这么脚跟脚,排着队,一步一步往前走。
我看清,负苦像空气一样铺天盖地,存在于每一个白天黑夜里。我不知道别样的生活该是什么样的,却深感现在的生活令人郁闷,心犹如一叶逆行的小舟,同整个队伍难以相合。但尽管如此,仍不断催促自己,跟上,跟上!
在头一天上工的路上,我紧随推着车子的林沂蒙在前边走,听到身后有人在窃窃地议论我,说我走路样子特别——她怎么走路的,怎么那么文呐?我听清了最后那个字眼是平声的“文”,而不是仄声的“稳”,辨得出来那种议论的口气绝非是赞赏,心里十分别扭。
——什么叫“文”?我怎么“文”啦?
仔细琢磨自己走路的样子,在左右没人时,藏到坯棚紧里边,自己走给自己看。发觉确是有点儿不大方,甚至于还带着微微侧头的痴呆状。我想,以前自己一直是有走路看小人书的毛病——是这毛病影响的我吗?一定是因为长期的走路看小人书,使我走路的姿势“文”了起来。我不想显得个别,偷偷在坯棚里自己给自己做纠正,又时时细心观察别人都怎样走路。
这天,我在小金子面前拿出一种新姿势,走给她看,问她:我这么走,行吗?
她莫名其妙,大笑不止。我没得着答案,心中憋闷。以后越发地没了信心,凡集体性上下工,只要不严格排队,我绝不主动往前走。
原来,像挖沟这样的活儿,在这里算最轻的一种,很难摊得上。一般情况下,都是集体作业。现在是乍暖还寒的春季,瓦厂是室内活儿,轧瓦机开着,砖厂露天作业,气温低,机器停着,活儿都是预备性的。二排是女生排,主要干些砖厂开工前的预备活儿。运沙子,挖水沟,修棚倒架……每项劳动都极其漫长,感觉不到时间的界限。
而所有的活儿干起来,大家总是显出一种比赛的气氛,似乎为着一种集体荣誉感,人人早都养成“力争上游”的习惯,表现出一种可怕的力量,一种不可理解的急骤的狂热。似乎干活儿本身足可以使人着迷,使人产生近乎疯癫的拼劲儿。而这拼劲儿背后是否真的具有意义,事实上已被忽略了。
我脆弱、沉闷,还不会思想,更缺少意志,心里老是拧着疙瘩,从根本上不愿接受这样的生活,这就必然会妨碍忍受力,难免常为一种明显的差距而苦恼——无论干什么活儿,我准是一个残兵败将,总抵除不了心中的畏怯与羞愧,总感觉在这个集体中抬不起头来。而所有的活儿对于我,全都变作一种惩罚,一种伤害,以致使我从生理上都产生厌恶。
又是尖利的哨声响过,我们领受了一项紧急任务:林沂蒙带着我们七人,要在半天里把二号窑内刚刚烧好的两万块红砖抢抱出来。连长强调说:这是我连烧出的质量最好的一窑砖,必须高度重视,好钢用在刀刃上!大家一上来就干得极猛。一趟趟上跳板,钻方窑。跳板是单行,女生推不了大独轮车,只能用双手抱砖,一长溜儿的热砖直码到下巴颏那儿。从跳板上一步一步踏下来抱到窑地,码成堡垒似的垛子。
人人都变得严峻了,人人都如铁人一般强硬,燥热的砖灰扑灌全身,满面棕红色。我手薄力小,像别人那样把砖码到下巴颏我做不到,每趟都要比别人少抱几块。尽管如此,上跳板时仍然笨拙害怕,老是担心会掉下去,再怎么鼓足勇气还是下意识地前后看着,跳板上,时刻有别人,我踩上去不敢快走,几乎是半步半步挪蹭。
心里万分紧张,一再叮嘱自己不要踩空不要踩空,踩空了你就全完啦……在每一趟回走的间隙得以空手,大口地喘气,尽量延长点儿时间以缓一缓劲儿,但稍微怠慢,背后就嘭嘭地震响,别人的大脚步急追过来,像要踩到头顶上。
我的节奏与众人不相符,明摆着我老耽搁大家,使大家的冲天干劲受到不应有的妨碍。看得出别人对我的忍耐,心里又急又慌。但越是这样,脚下越是乱颤不止。
榜样的力量是惊人的。我看见林沂蒙像个男生那样大步流星地上来下去。她和另一个女生两人比着干,砖比所有人都抱得多,不是码成单行,而是码成了方块田字,她们大步走在跳板上,一跃一跳地带着冲劲。她们工作服后面溻出深黑色的汗圈儿,脸上挂满汗溜子。她们使我从心里震惊佩服,却知道学不来,再怎么拼命也学不来。
然而明白,跟不上大家,必须得想办法。情急之中我干脆钻在窑里不出来,只为别人摞码砖行。竟没有人说我,都默默认可着,嗵嗵地奔进砖窑,接走我码好的砖行,好像这多少减少了一道工序。
可我错了。砖窑里太不好受,砖灰弥漫得十分厉害,没有办法躲藏,鼻孔里,眼睛耳朵里,哪儿哪儿都灌满砖灰,喉咙里呛得辣腥腥的,呼吸艰难,却一丝一毫不得间歇,总是转体九十度,一百八十度,猫腰,再猫腰,没有人换我。手指头磨得要破,脑袋天旋地转,忽然指甲又被厉害地挤撞一下,整个心脏都疼起来。我想到手套,想到口罩,想到外面的露天作业再苦再累也比这砖窑里面好。
——哦,这砖窑,真像地狱啊,这世上再没有什么地方比这红尘滚滚的砖窑更叫人难受了!
不知怎的鼻孔里蹿出血来,忽地一下,竟血流如注。触目惊心的血令我的身体一下子软了。我倒在窑里,捂着鼻子呜呜哭起来。林沂蒙扒开我的手,看我花红的脸,口气不满地说:你哭什么哭什么!
她又叫叶丹娆,就是那个和她比着干的女生。她叫叶丹娆送我回去。
宿舍是宁静的,空气也干净。叶丹娆为我拧了一把湿毛巾给我擦脸,又找块小纸帮我把鼻孔塞上。躺着,别动,她说。我仰脸躺着,血渐渐不流了。叶丹娆又将毛巾投了投水,叠成方块,递给我,说:拿它压住鼻梁,要是再止不住,就找卫生员郭小刚。
叶丹娆的嗓音柔似丝缎,很好听。不由得多看她几眼。她的长相也是很好看的。两条齐肩的小辫软软地拢着脸颊,脸上虽然糊满汗渍,仍掩不住五官少有的精致端庄,一双眼睛就像黑樱桃一样。
不知为何,我觉得这双眼睛更像幽深的水潭,隐藏着好多东西。而刚刚在窑地上奋力争先的那个人,并不像她。
很希望她陪我多待会儿,说上一会儿话,她的声音是好久不曾听到的,让我想起姐姐来。在她转身时,注意她脸颊的侧影显出流丽的线条,实在很像姐姐。可她仅是给我倒了杯水,自己不喝,温和说一句:好像不再流血了,那你就躺着吧,我还回工地去。说完,那张好看的汗脸朝我微微一笑,匆匆拉开门走了。
转天林沂蒙分配我单独干活儿,抱一把大竹笤帚清扫腾空的坯棚。这是一份轻活儿,用不着再被别人盯着。坯棚距砖窑不远,能望见林沂蒙她们一律的绿色工作服、蒙着红砖灰的头和脸。她们干活儿声响很大,沓沓沓的脚步声,哒哒哒的码砖声,都能听得清楚。但渐渐地,她们被码起来的高大的砖垛遮住。
我感到孤独,笤帚挥得缓慢拖沓。我想,我已经处于集体之外,被集体所照顾也就被集体所排斥——是由于我的低能。低能是一种不幸,也是一种宿命。可是毫无办法,我已经固定了在集体中的低等的姿态——落后。
落后,这是我的面目和我的厄运,在我充分认识它之前,它已跟定了我。
我想,我之所以为落后而悲哀,是因为,落后也是需要胆量的,这胆量我还不具备。
我产生了把手中的笤帚丢掉,跑过去跟大家一起干的念头……不要在乎窑里的粉尘,不要害怕颤动的跳板。去,像别人那样,动作铿锵有力,热乎乎的砖在手底下哒哒响……一再地命令自己,身体却不动弹。
忽地胃里泛上来一股酸水,压抑不住,赶紧蹲下,在新挖的水沟里大口地呕吐起来。
呕吐之后,竟想清楚,我不能走过去,不能加入那个拼命的队列,情愿付出孤独的代价,也要逃避那砖窑。精神上的痛苦和皮肉的痛苦相比较,现在我宁愿要前者。也许,这就是低能的弱者的逻辑吧。
休息哨响了,风送来窑地那边一阵清亮的说笑声,还有歌声。独自坐在笤帚把上,耳朵支起来,专心去听她们,感觉到她们如此放松,竟然和在学校课间时候差不多少。
我纳闷,我们年龄相仿,但为什么,她们就能泰然处之呢?我的那种战栗,那种畏怯,她们都没有,更不用说我的郁闷与厌恶。这是因为什么呢?仅仅就是因为她们比我来得早一些吗?那么,时间,会给我一个消解融化、习惯适应的过程吗?——我很难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