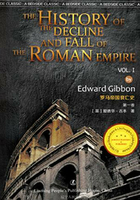石家庄除去工人,铁路员工,多数人都失业了,政府机关工作人员都有伪字当头,也等待接收,“教育馆”自然没人来抢,也没有人来管,当然也就没有了工资。不只教育馆,所有业余剧团的艺友们都遭了霜打,郑哀伶更是惶惶然,因为他本是调来专门搞业余剧团的。现在韩秘书已不在,据说日本投降前就在抓他,国军来了也抓他。郑哀伶也不敢再找他。但郑有三个孩子,都不过十岁,嗷嗷待哺,他不得不聚集“旧部”,成立了一个职业剧团(我记得好像叫“醒民”)。只不过《雷雨》的老班底多数不在了,又有铁路上的几位业余爱好者参加。他们都受过郑的“训练”,特别是有一位吴大哥,演反派角色,不输于郑哀伶演鲁贵。不管怎么说,这新剧团是演不出《雷雨》了。何况为了挣钱糊口,老郑也不得不顺应那时候的“口味”,搞到了一个歌颂国民党间谍以色相深入敌人内部牺牲报国的剧本(忘记是谁写的了),叫《天字第一号》。“女特务”是外请的一位女士扮演的,不知什么来路,但演技却相当熟练。那位吴大哥演那敌伪首脑人物。这种情节戏挺热闹。头几天,大家看着新鲜,上座率还好,只不过,这时在当地“国军”已经把自己搞臭了街,美化他们的“文艺”,似乎也不能吸引观众,演过了10场,就不到半场人了,哪养得起剧团20多口子。我忘了每天补贴多少钱,给我的,只够吃四个烧饼、两碗馄饨的。“大被窝票”已一钱不值,石家庄人谁手里有这种纸币谁倒霉。我们这些外乡人也无破烂儿可卖。国军来了一个月,大家手里没有法币,都只好靠劳力了。而这些肩不能挑又没手艺的人,能干什么呢?现在能解穷的,只有靠剧团这点收入了。郑哀伶急了,三日夜不睡,赶写了一个按照现在说法叫做“娱乐性”的剧本《红粉骷髅盗》,是三幕带武打的“闹剧”,这虽非郑哀伶本色,但他毕竟有几十年的戏剧修养,善于结构矛盾冲突。总之,这个戏写得很刺激,也有点惊险,但对郑哀伶来说,都毫无价值、毫无意义。
我一生,有32年是在做文艺编辑,后来又作了10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行政,工作需要,三四十年,可说是古今中外的各种戏剧形式,只要在北京演出,我差不多都看过,特别是当文艺编辑时,每逢调演或会演,都是要赶场的。在我的心目中,从导演艺术上讲,焦菊隐和他的北京人艺的弟子们,自然是第一位的,他导演的老舍先生的《茶馆》,可说是他的代表作,也是中国话剧的经典。他也导演过曹禺的《雷雨》和《北京人》,他是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运用到中国话剧舞台的第一人,但是,他还继承发扬了中国戏曲艺术的优秀传统,他不是照搬斯氏的体系,而是融中外艺术为一体,再加上他的个性化的创造。虽然和他同时的名导演,还有上海的黄佐临先生,他有不同于焦先生的导演风格,只不过我自己则更喜欢那时的北京人艺的演剧学派。这是由郑哀伶而想起的一些后话。
留在我记忆里的郑哀伶,确实是一位难得的戏剧人才,可惜他生不逢时。他本是一位进步的艺人,导演《雷雨》时,何等精神焕发;现在为了“求生”,竟走到了这一步,就是如此,也还是养不活剧团,恰好上海影剧名演员吕玉坤也领了一个剧团到石家庄来跑码头。吕玉坤演过不少电影,在上海“孤岛”前后,他似是没有到大后方去。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影片是他和周曼华主演的《晓风残月》。情节是一位富家小姐,在逃难中与一穷书生相遇相恋,以致怀孕。难产后,男主角送女回家,求婚不成,终成悲剧。男女主角的表演,都还相当感人。抗战胜利,吕玉坤似不大得意,“才跑起码头来”。他们一来,就抢了我们剧团的饭碗,“占领”了小剧场,吕玉坤毕竟是红影星,演的又是国民政府“陪都”的故事《重庆24小时》,引起轰动。不过,石家庄只是一座新兴的小城市,什么好戏演过十场,也就少人问津了。就算是吕玉坤,石家庄也养不活他,换了两出戏,也只得离去了。
郑哀伶挽留了吕团中正在恋爱中的男女二位,当然是想给剧团输入点新鲜血液。这两位男的是副导演,女的是演配角的。其实,外来的和尚未必能念好经。老郑为了表明诚意,把导演的位子让给了这位副导演,也为了重振剧团的“声威”,他又“回归”曹禺了。请这位导演排演《原野》,自己出演仇虎,女主角金子就由那位女演员扮演。演过鲁妈的傅大姐演焦母,演过周冲的小王出演焦大星。我“旁听”了彩排。我觉得,这位副导演并没有读懂《原野》,比如焦母和仇虎的几节对话,都内涵丰富,隐寓着两代人的血泪仇。郑演仇虎,自然用不着他说戏,演得很出色。仇虎野性十足,但内心又充满着人性善恶的交战,他全家都被焦阎王陷害,他自己也被诬陷入狱成了死囚,他半路逃脱,满腔愤怒,来找焦阎王复仇。可傅大姐演阴狠焦母,非其表演本色,而导演的说戏又不到位,就无法与老郑的仇虎形成对垒。这位导演的“艺术思维”很浅薄。倒是那位女演员演的金子,虽不够漂亮,却能把握角色的内蕴,金子那野、那泼、那敢作敢为,用现在的时髦话说,都是表演得很“刺激”。只不过,《原野》也没有给剧团找到出路。这时,石家庄已不只有一个话剧团,另外一拨戏剧人比我们有气魄,他们占领了石门剧场,并唱开了对台戏。首场就是曹禺的《日出》,还从我们这里挖走了一些“角色”。《日出》的主角陈白露,就是丁伶(墨农的爱人)扮演,我的二姐也参加了这个剧团。争演曹禺剧,这本是一件好事,但在那样的环境和条件下,生存竞争十分尖锐,小小石家庄哪里养得起两个话剧团,何况国军来了两个月,石家庄已开始物价飞涨了,最后两个剧团都难以维持。
我自然一直跟着郑哀伶,因为他忘词毛病很难治愈,有他的戏,我就得在后台盯着,再帮着搞点“效果”。这时我已身无分文,只靠剧团这点津贴吃两顿饭。混到年底,谭北生突然回来,他在北平没有找到工作,又来石家庄找机会。没有住处,没有饭辙。我这时还住在教育馆图书室的大条桌上,好在我有两床被子,我们就凑乎着挤在一起了。1945年那一年冬天十分寒冷,院里自来水管都已冻住,晚上搞到一盆水,第二天就结冰到底。要洗脸只得用手握化点冰水擦一擦,而我的四个烧饼和两碗馄饨,也只能分成两份,两个人挺过一天去。有时我还得跑到二姐那里蹭一顿中午饭,但我毕竟已经是18岁的大男人,不能再像小时候那样靠二姐养着,何况她也只有一份剧团补贴,比我多一点收入,也是靠她巧手“缝穷”缝来的,还要给家里妈妈和小弟寄一点。两个大小伙子,一天一顿饭,没过十几天,就挺不住了。北生和我商量,还是回北平想辙吧!我虽留恋石家庄的艺友们,但再继续留下去,已无生存希望。我索性把被褥和身边破烂全部卖掉,向艺友们,特别是郑哀伶、哈墨农告别,老郑自然不舍,但也知道没任何理由留我。就这样,我和北生买了两张火车票回到北平,我即转车回到通州。北生临别时留了我家的地址,叮嘱我在家等他的消息。
回通州不久,就从二姐来信中得知,石家庄的两个剧团,都被驻守该市的“国军”第三军收编了,成了“国军”的剧团,他们又演过什么戏,我就不得而知了。在石家庄这一年多,我虽然还没有脱离幼稚、混沌的思想状态,但总算有机会接触到新文艺,特别是曹禺的戏剧世界,也开阔了我的眼界,使我多懂了点世态人情。三人行,必有我师。艺友中给我影响最多的,是郑哀伶、哈墨农、谭北生。哈、谭二位,后来还有交往,我也写过纪念文章,老郑却是石家庄一别,终未再见。只在1951年大学寒假,我要去河南新乡,从石家庄转车,夜间10点多,住在车站的小店里,曾打过一个电话,那时他和石家庄几位艺友都已成为专业的话剧工作者。从声音听来,他苍老多了,听说我在上大学,替我高兴,为我祝福。可惜,我是第二天四点半就转车,不能去看他们,就在电话中珍重告别了。后来,在《文艺报》上看到他给铁路文工团导演的话剧《不是蝉》,调演到北京,《文艺报》有评论,有访问记,我没有看过剧本,也没有弄清剧名寓意。依我推想,大概是写铁路工人劳模的故事。既然能调演到北京,自然是很有现实意义的。艺术上我是相信老郑的。这可能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导演的第一个成名作。我虽看不到,却写过一封信向他表示祝贺。不过,并未得到复信。1953年我分配到北京,先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做研究生,第二年没有毕业就调到《人民日报》文艺部工作,再也没有看到老郑有新作演出。忘记是1955年,还是1956年,二姐告诉我,郑哀伶已去世。我们都很伤感,难忘石家庄那段“戏剧人生”。郑哀伶,就是一个“戏剧人”,此外,他别无所能。我们作为邻居一年多,他平素精神上很忧郁,又有一个“平庸”的家,妻子是一位不识字的家庭妇女,他是二婚。妻子并不难看,结婚不过五六年,就给他连续生了三个儿子,个个眉清目秀,粉捏玉琢,都像爸爸。老郑大我十几岁,那时大概30岁左右,头顶已脱发,中等个儿,肤色很白,一双大眼掩映在近视镜后,不知为什么,我想起来,总觉得他有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神韵”。大家都认为,这对夫妻很不相配。大家都知道,他曾有过一位前妻,可能也是演话剧的,他们有过一段“神雕侠侣”般的温馨爱情,不知什么原因出了意外,对老郑打击很大,为了纪念她,老郑把自己的艺名改成郑哀伶。总之,在我看来,老郑的二婚是勉强的、不幸福的,但生活的负担却很重,他去世时也不过40多岁,哀哉,哀伶!我每次看《雷雨》,都会想到郑哀伶,这是石家庄一年多生活中留给我最深的印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