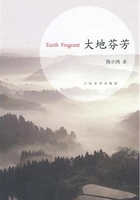我下面的牢门打开了,又砰地关上了,我想大概是克莱德·卡特终于来叫我了,但是那个人噔噔上楼时却开始哼起“小马车,慢慢跑”来,我马上知道这是爱弥尔·拉金,一度是尼克松总统的狗腿子。他体格魁梧,眼若铜铃,嘴唇发黑,曾经担任过密歇根州立大学橄榄球队中卫。他如今已被剥夺律师资格,整天祷告,向耶稣·基督祷告。这里附带提一句,拉金没有被送出去干活,也没有被分派打扫任务,那是他成天在坚硬的监牢地板上祷告的结果。他的膝盖骨因为老是跪地而发了炎,双腿行动不便。
他在楼梯顶上停了步,眼里含着泪。“唉,斯代布克兄弟,”他说,“爬这楼梯可真不容易。”
“我一点也不奇怪。”我说。
“耶稣刚才对我说,”他说,“你只有最后一次机会可以和斯代布克兄弟一起做祷告了,你一定要忘掉爬楼的痛苦,因为你知道什么?这一次斯代布克兄弟要跪下他的高贵的哈佛膝盖了,他要同你一起祷告了。”
“我不愿叫他失望。”我说。
“你难道还干过别的?”他说,“我从前干的就是:每天叫耶稣失望。”
我并不是想把这个哭哭啼啼的大人物刻画成宗教上的伪君子,我也没有权力那样做。他由于无条件接受宗教的安慰,结果成了一个低能的傻子。当初我在白宫工作的日子里,我害怕他就像我的祖先害怕伊凡雷帝一样,可是如今我可以愿意怎么顶撞他就怎么顶撞。他就像一个乡下白痴一样,你怎么样怠慢他、戏弄他,他都不在乎。
我甚至可以说,就是到今天,爱弥尔·拉金还把钱随便送掉。拉姆杰克集团有一个归我管辖的独资分公司,名叫“心地书店”,设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专门出版宗教书籍。七个星期以前,它出版了拉金的自传《兄弟,你愿和我一起祷告吗》。拉金的全部版税总数很可能达五十万元,还不算拍摄电影和出版平装书,他把它统统都送给了“救世军”[1]。
“是谁告诉你我在这里的?”我问他。我不愿他找到我。我本来打算出狱前躲开他,免得他要我同他一起做最后一次祷告。
“是克莱德·卡特。”他说。
那就是我在等得看守,美国总统的远房兄弟。“他在什么鬼地方?”我问。
拉金说整个监狱都闹翻了天,因为前卫生教育福利部部长,全国最富有的人之一,维吉尔·格雷特豪斯突然决定马上前来服刑,不再上诉,不再拖延。他很可能是要求联邦监狱收监的最有地位的人。
我同格雷特豪斯只有一面之缘——当然久闻大名。他是个著名的硬汉,格雷特豪斯暨斯迈莱公共关系公司的创办人,如今仍是最大的股东,这家公司专门为加勒比海盗和拉丁美洲各国的独裁政权、巴哈马群岛的赌场、利比亚和巴拿马的油船队、中央情报局在世界各地的伪装机构、像砂纸胶布工人国际兄弟会和燃料工人联合工会那样的匪徒控制的工会、像拉姆杰克集团和德克萨斯水果公司那样的国际大企业等等,做极尽其美化之能事的宣传。
他脑袋已秃,下颌有垂肉,前额的皱纹像洗衣板一样。他的嘴里总是叼着一只没有点燃的烟斗,甚至坐在证人席上也是这样。我有一次距他很近,发现他的烟斗能奏乐,就像小鸟叫一样。他进哈佛时我已毕业六年了。我们两人在白宫正面相视只有一次,那就是我点燃了那么多支香烟出洋相的那次会上。在他看来,我在白宫的地位只不过是食品储藏室里的一只小耗子。他同我只讲过一次话,那是我们两人都被捕以后。我们偶然在法院的过道里相遇,各自在等候传讯。他知道了我是谁以后,显然认为我掌握了他什么材料,其实我并没有。他就把脸挨得我很近,眨着眼睛,叼着烟斗,向我作了如下令人难忘的保证:“要是你揭发我什么,老兄,你出狱以后,能够在塞得港一家妓院里找到打扫厕所的差使,就算你交上好运了。”
就是在他说了这话以后,我听到了他的烟斗里的小鸟吱吱叫。
附带提一句,格雷特豪斯是公谊会派教徒——当然理查德·尼克松也是。这肯定是他们两人之间的一种特殊联系,使他们有一段时间里成为最要好的朋友。
爱弥尔·拉金则是长老会派教徒。
我本人什么也不是。我父亲在波兰时是个秘密受洗的罗马天主教徒,当时这一教派是受到压制的。他长大后成了不可知论者。我母亲在立陶宛受洗的是希腊东正教,后来在克利夫兰市成了天主教徒。父亲从来不和她一起上教堂。我自己受洗的是罗马天主教,但学我父亲的冷淡,十二岁上就不去教堂了。我申请入哈佛大学时,浸礼会派教徒麦康先生要我填作公理会派教徒,我就这样做了。
我听说,我的儿子是个活跃的唯一神派教徒。他的妻子告诉我说她自己是卫理公会派教徒,但是她每星期到一家圣公会派教堂去唱诗,有钱拿,为什么不去?
真是无奇不有。
长老会派教徒爱弥尔·拉金和公谊会派教徒维吉尔·格雷特豪斯在以前得意的时候就关系密切。他们不仅管白宫的夜盗、非法窃听,对国内税务局不听话的人进行刁难等等,而且也管早餐祷告。因此我问拉金对即将重聚做何感想。
“维吉尔·格雷特豪斯同你或别人一样都是我的兄弟,”他说,“我要想法把他从地狱里救出来,就像我现在要想救你一样。”接着他引述——据圣马太所说——耶稣代表上帝在审判日要对有罪的人说的令人害怕的话。
这句话是:“离开我,你们这受诅咒的人,到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准备的地狱之火中去吧[2]。”
这些话当时叫我吃惊,如今也叫我吃惊。基督教徒出名的残忍肯定是由此得到启发的。
“耶稣可能说过这话,”我对拉金说,“但是这同他说的别的话太不像了,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一天他有点糊涂了。”
拉金退后一步,歪着脑袋假装佩服。“我这一辈子见过不少歹徒硬汉,”他说,“可是你要数第一。你这些年来老是见风转向,把所有的朋友都得罪了,如今你又侮辱最后一个可能还愿意帮助你的人——耶稣·基督。”
我没说话,我希望他会走开。
“你举出一个例子来,谁还是你的朋友?”他说。
我心里想,我的傧相本·夏皮罗医生不管怎么样一定仍是我的朋友,很可能会开汽车到监狱来接我到他家中去。但是这只是我个人的单相思。他早到以色列去了,在六日战争中牺牲。我听说特拉维夫有一家小学用他的名字命名,以作纪念。
“举一个。”爱弥尔·拉金仍说。
“鲍伯·范德。”我说。这是监狱里唯一被判无期徒刑的,也是朝鲜战争中唯一被判犯有叛国罪的美国人。应该管他叫范德医生,因为他有兽医学位。他是供应科的主任科员,我一会儿就要到他那里去领回便服。供应科里总是放音乐,因为范德可以一天到晚放女歌手伊迪丝·琵雅芙[3]的唱片。他还是个相当有名的科幻小说家,用各种笔名一年出版好几本小说,笔名有“弗兰克·X·巴罗”和“基尔戈·屈鲁特”。
“鲍伯·范德同谁都是朋友,但同谁都没有交情。”拉金说。
“克莱德·卡特是我的朋友。”我说。
“我是说外面的人,”拉金说,“谁在外面等着要帮助你?谁也没有。甚至你儿子都算不上。”
“咱们等着瞧吧。”我说。
“你打算到纽约去?”他问。
“是的。”我说。
“为什么去纽约?”他问。
“对无亲无友、一文不名而想要做百万富翁的移民,纽约以好客出名。”我说。
“你打算去找你儿子帮忙,尽管你关在这里的时候他从来没有给你写过信?”他说。他管我这一楼的收发,因此他对我的信件知道得一清二楚。
“要是被他发现我和他在同一座城市,那绝对是偶然巧合。”我说。瓦尔特最后一次同我说话是我们在契维蔡斯郡犹太人小公墓里为他母亲下葬的时候。把她葬在那样的地方,同那样的人们葬在一起,完全是我的主意——这是一个突然丧偶的老人的主意。露斯会说这样做是发疯,一点也不错。
她是躺在一口价值一百五十六元的普通松木棺材里被埋葬的。我在棺材上面放了我家门前开花的酸苹果树的树枝,树枝是折的,不是砍的。
犹太教教士在她墓前用希伯来语说了祷词,这种语言她从来没有听到人说过,但在集中营时一定有无数次的机会学会。
我们的儿子对着我和墓穴转过身去,急着要上等在那里的出租汽车,转身以前这么对我说:“我可怜你,但是我永远无法爱你。我认为是你杀死了这个可怜的女人。我不能再把你当父亲,也不能把你当什么亲戚对待,我永远不想再见你,听到你的消息了。”
这话可不轻。
不过,我在监牢里做着去纽约的白日梦时的确想着,那里仍有我的一些老相识,可能帮我搞到一份差使。虽然我说不清他们到底有谁,但认为自己仍有朋友可以依靠的这种“白日梦”有时是很难丢掉的。要是我的境况稍许顺利一些的话,那些仍然对我以朋友相待的人大部分都留在纽约。我禁不住想,要是我一天又一天地在曼哈顿中闲逛,从西边的剧场区到东边的联合国大厦,从南边的公共图书馆到北边的普拉柴酒店,经过那些基金会、出版社、书店、男装店、绅士俱乐部、豪华酒店、餐厅,我一定会碰上一个认识我,记得我以前是个多么好,也没有特别看不起我的人,并且愿意出力帮我在什么地方弄个管酒吧的差使。
我会不顾面子地向他恳求,把我调酒学博士的文凭给他看。
如果我见到我儿子走来——白日梦是这样做的——我就会转过身去,等他走过去没事之后,再转过身来。
“真是,”拉金说,“耶稣叫我对谁都不要放弃希望,可我几乎要放弃你了。你就准备这样坐着,眼睛瞪着前方,不管我说什么。”
“恐怕是这样。”我说。
“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有人像你这样决心做个耍把戏的。”他说。
在嘉年华怪诞秀上,有个人躺在笼子里的一堆脏草上,把活鸡的头一口咬掉,或者嘴上发出野人的怪声,杂耍团的海报说他是婆罗洲的丛林中由野兽喂养长大的。这就是耍把戏的。在美国的社会阶层中,他是掉到最底层的人。最后埋在义冢中收场。
如今拉金,再三碰壁,就露了他的坏心眼的本色。“查克·科尔逊在白宫就叫你是耍把戏的。”他说。
“敢情是。”我说。
“尼克松从来没有瞧得起你,”他说,“他只是感到你可怜,这才给你那份差使。”
“我明白。”我说。
“你压根儿不用来上班。”他说。
“我明白。”我说。
“因此我们给了你那间没有窗户的办公室,旁边没有别人,让你明白你压根儿不用来上班。”
“不过我还是想做些事,”我说,“我希望你的耶稣因此会宽恕我。”
“要是你只想拿耶稣开玩笑,你最好不要提他。”他说。
“好吧,”我说,“是你先提的。”
“你知道你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个别人眼中耍把戏的人吗?”他问。
我知道我是在什么时候开始不走运的,在什么时候我的双翅给剪掉的,在什么时候永远不能再飞上天空的。那件事是我最痛心的事,我连想也不愿意想它,因此我正眼看着拉金说:“请你发发慈悲,放开我这个可怜的老头儿吧。”
他高兴之极。“好呀——我终于刺穿瓦尔特·F·斯代布克这层哈佛的厚皮了,”他说,“我碰到了痛处,是不是?”
“你碰到了痛处。”我说。
“我们总算有一些结果。”他说。
“我却不希望。”我说,眼睛又看着前面的墙。
“第一次听到你说话时,我还是密歇根州彼多斯基的一个穿短裤的小孩子。”
“敢情是。”我说。
“那是在收音机里。我父亲叫我和妹妹坐在收音机旁留心听。‘你们好生听着,你们是在听历史的缔造。’”
那一年一定是一千九百四十九年。我们的小家庭回到华盛顿。我们刚刚搬进我们在马里兰州契维蔡斯郡的砖砌单层宅院,房前还有一棵开花的酸苹果树。那正好是秋天。树上结了小小的酸苹果。我的妻子露斯要把它们做果酱,后来她每年都做。小爱弥尔·拉金在彼多斯基听到我说话的声音是从什么地方发出来的?对了,是从众议院的一个委员会会议室。我的面前放着许多无情的话筒,像花丛一样,我正在受讯问,问我关于以前同共产党的关系和我目前对美国的忠诚问题,向我提问的主要是一个从加利福尼亚州来的名叫理查德·尼克松的众议员。
一千九百四十九年:如果我一本正经板着脸说——那时候地面上仍是张牙舞爪的“老虎”的天下,因此国会的委员会是在“树顶”上开会的,今天的年轻人,不会不信我吧?不会不信的。当时温斯顿·丘吉尔还活着。约瑟夫·斯大林还活着。真不可想象。哈里·S·杜鲁门是总统。而国防部居然要我这个前共产党员把一批科学家和军人组成一个特遣组,领导他们工作,其任务是为地面部队提出战术方案,以对付战场上的小型核武器,当时认为那是不可避免会出现的。
委员会要想知道,特别是尼克松先生要想知道,有我这样政治背景的人能不能委以这样的重任?我不会把我国的战术计划递送给苏联吗?我不会篡改计划使之无法付诸实施,以致在与苏联作战时苏联必胜吗?
“你知道我在那个电台上听到的是什么吗?”爱弥尔·拉金问。
“不知道。”我答道——极其颓丧地。
“我听到的是有个人做了一件人人都永远无法原谅他的事——不管他们的政治态度怎样,都是不能这样做的。我听到的是他做了一件他自己也永远无法原谅自己的事,那就是出卖朋友。”
当时我听到他那么形容他以为自己听到的事情,我笑不出来,我如今也笑不出来——但这件事仍是十分荒唐可笑的。那次国会传讯,后来演变为民事诉讼,最后成为刑事审判,前后拖了两年多,他归结为这么简单,未免太可笑了。他小的时候在收音机旁听到的无非是一些枯燥无味的话,不比杂音有意思。拉金一定是在长大以后,从牛仔电影中学到了一套伦理观念后,才会认为他当时是极其清晰地听到了有一个人被最要好的朋友出卖的事。
“莱兰·克留斯从来不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说。这是那个被我的证词毁了一生的人的姓名,有一阵子人们的谈话中常常一起提出我们两人的姓氏“斯代布克和克留斯”,就像合写轻歌剧的词曲作家“吉尔伯特和沙利文[4]”,就像“萨柯和樊才蒂”,就像滑稽演员“劳莱和哈台”[5],就像少年杀人犯“利奥波德和洛勃[6]”。
我如今已不大听到我们两人的姓氏连在一起了。
克留斯是耶鲁大学出身的——年纪与我相仿。我们当初是在牛津大学认识的,我们在亨莱划船获胜,我是艇长,他是划手。我个子矮,他个子高。我如今仍矮,他如今仍高。我们同时到农业部去工作,办公室相连。天气好的话,我们每逢星期天上午一起打网球。那时我们入世不久,仍很稚嫩。
在农业部的时候,我们一起买了一辆福特菲顿旧车,常常一起开车带女朋友出去玩。菲顿是太阳神赫里欧斯的儿子。有一天他借了他父亲的火焰车,随便开到北非,结果那里变成了沙漠。宙斯为了使整个地球不至于全部荒芜,不得不用闪电击死了他。“宙斯做得对。”我说。他有什么别的办法?
但是我同克留斯的交情从来不深,自从他从我手中把一个姑娘抢走并同她结婚以后,我们就不来往了。那个姑娘是新英格兰一家名门望族的闺女,拥有的产业中有马萨诸塞州布罗克顿的威亚特钟表公司。她的哥哥是我在哈佛一年级时的室友,我就是这样认识她的。她是我真正爱过的四个女人之一。她叫莎拉·威亚特。
我无意中毁了莱兰·克留斯的时候,我们已有十多年不通音讯了。他和莎拉生了个孩子:一个女儿,比我的孩子大三岁。他在国务院很走红,是最明亮的彗星。大家普遍认为,他有一天会当国务卿,甚至总统,华盛顿没有一个人比他更光彩照人,更有魅力了。
我是这样毁了他的:在宣了誓的情况下,我在回答众议员尼克松的一个问题时,举出了在大萧条期间大家都知道是共产党员,但却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声称自己是杰出的爱国者的一些人的名字。在这张光荣的名单上,我列入了莱兰·克留斯的名字。当时对这件事没有人发表过什么意见。只是等到后来,那天下午很晚回了家,我才从我妻子那里得知,她听了我作证,又听了无线电上的各种新闻节目,发现莱兰·克留斯以前同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
等到露斯在一只打包箱上摆出晚餐——由于平房的家具还不齐,我们以此当饭桌——无线电上才把莱兰·克留斯的答复报道给我们听。他希望能一有机会就马上到国会去,宣誓声明他从来没有当过共产党员,从来没有同情过共产党的事业。他的上司国务卿也是耶鲁大学出身,记者引用他的话说,莱兰·克留斯是他所知最爱国的人,他在与苏联代表的谈判中已毫无疑问地证明自己是忠于美国的。他认为莱兰·克留斯多次战胜了共产党人。他认为我可能仍是共产党员,甚至有可能是我的主子派我存心毁掉莱兰·克留斯的。
过了难熬的两年以后,莱兰·克留斯以六款伪证定了罪。当时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城市外三十五英里的芬莱特空军基地边上新建了联邦最低限度安保措施成人改造所,他是第一批被送去服刑的犯人之一。
天下真小。
注释:
[1]“救世军”(The Salvation Army):一个成立于1865年的基督教教派,以街头布道和慈善活动、社会服务著称。其国际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维多利亚皇后街101号,在全世界有几千个分部,分布在70多个国家,据称有成员200万人,其中以美国较多。
[2]出自《圣经·马太福音》第25篇。
[3]伊迪丝·琵雅芙(Edith Piaf,1915-1963):法国最著名也是最受爱戴的女歌手之一。她的作品多是其悲剧一生的写照,最著名的歌曲包括《玫瑰人生》。
[4]“吉尔伯特和沙利文”(Gilbert & Sullivan):指的是维多利亚时期,歌剧创作上亲密无间的合作伙伴剧作家W.S.吉尔伯特和作曲家亚瑟·沙利文。其中最有名的包括《比纳佛》和《班战斯的海盗》。
[5]“劳莱和哈台”(Laurel & Hardy):指的是早期经典好莱坞时期的双人戏剧组合。斯坦·劳莱是个瘦高的英国人,而奥利弗·哈台是个胖硕的美国人。
[6]“利奥波德和洛勃”(Leopold & Loeb):指的是1924年5月联合绑架并杀害14岁中学生罗伯特·弗兰克的两个芝加哥大学的大学生利奥波德和洛勃。令人震惊的是他们的作案动机仅仅只是为了制造“完美的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