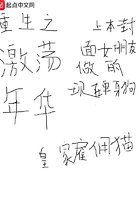张长锁刚高兴没几天,就又开始眉头紧缩起来,他又被别人议论纷纷了,而且话说得越来越难听,越传越邪乎,说他这个村长简直和马祥林没什么两样,都是二鬼子,日本人的走狗。
因为王成仁又来了,带来了大乡征粮的告示。张长锁看了大概的内容,征粮标准和去年一样,时间是5天,标准是:男丁三口以上一户25斤,男丁三口以下一户15斤,无男丁户也是15斤,按照这个标准,十里堡村一共3100斤。王成仁还说,如果不能按时交上粮食,大乡将把情况报告给县政府的毛利太君。
这毕竟是张长锁当村长后遇到的第一次征粮,他一时没了主张,便把几个乡绅找到村公所商量对策,而乡绅们却一个个面面相觑,闭口不言。
马祥林却洋洋得意地开了腔:“王乡长的话就是圣旨啊,我当村长那工夫,咱村可都是交粮的模范啊,我也看见过,没有按时交粮的后果,去年,李家村比规定的时间晚了半天,结果你猜怎么样?被送进了宪兵队打了个半死,最后还被抄了家,差点儿被以通共的罪名给枪毙了。所以呀,张村长,咱村交粮的事,你还真的多多费心,都是乡里乡亲的,要是谁有个闪失,你不仅是十里墩的罪人,也是俺们十里堡的罪人呀!”
张长锁知道马祥林说这话的真正目的是为了羞辱自己、难为自己、瞧自己的笑话,说到底他张长锁是十里墩的而不是十里堡的,十里墩的十几个人怎么能统治十里堡的四百多人呢,更何况又不是一个家族和姓氏呢。
张长锁想了想,开口说道:“以前咱村咋交的公粮我不知道,我想从今天起,有些章程应该改一改了。”
众乡绅听了这话,开始议论起来:“这是陈年旧规矩,你说咋改呀?”
张长锁说:“咱们几家都是村里的大户,种地纳粮,天经地义,咱得做个样板儿,那些孤儿寡母的连自己都吃不饱,也要交粮,打哪儿出这么多粮食呀,我再三琢磨过了,咱们几家带个好头,首先把自家的粮食交了,然后我去动员大家交粮,最后剩下实在交不上的,咱们几家把它均了,你们看行不?”
乡绅们议论道:“张村长说的也是,去年秋里遭了旱,村里多半人都接济不上,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如果再让乡亲们都如数交粮,恐怕做不到。”
“如果真交不上粮,马村长刚才也说了,俺们也不能让你去蹲小黑屋吧。这样吧,张村长,你先去和乡亲们去说说,能交的就交,实在交不了,咱们把它均了。”
马祥林重重地咳嗽了一声:“对不起,张村长,我的脑仁儿又疼了,我先回了,不过,你放心,我那份儿我一定交的。”说着,率先走出了村公所。众乡绅一看,也纷纷找了个头疼屁股疼的借口离开了。
张长锁走了几家本来可以交得起粮的乡亲,尽管他再三地央告,好话说了千千万,但最终人们还是不肯交粮。人们说,你张三是个好人,又是帮助俺们盖村公所,又是帮助俺们打狼,但是这粮俺们真的没法交。张长锁听了这些也有些起急,但也没有办法,明明是吃穿不愁的人家,也有很多的粮食,为啥就不肯交粮食呢?经过和申老汉深谈之后,他才明白了其中的原委,敢情马祥林从中做了不少手脚。
张长锁一觉醒来,已是天光大亮,他喊了一声:“老四。”见没有应声,便翻身坐起伸了个懒腰,跑出了豆腐房,他知道,张铁栓正在练习拳脚。
张铁栓自打到了张家后,人上进,手脚也很勤快,除了做活之外,还对武术挺感兴趣。原来有一年冬天,有一伙儿走江湖打把式卖艺的住在张家客栈,每天早上,那些人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到空闲地上练习拳脚,张铁栓没事就去看热闹,看着看着就着了迷,也跟着胡乱比画起来,拳师看张铁栓一门心思想学武术,就手把手地教了起来。那伙人在张家店一住就是十来天,不知是人家教得好,还是张铁栓心有灵犀,等那些人走的时候,张铁栓竟然学得了一身好拳脚,张元启为此很高兴,少收了人家好多店钱。
张铁栓正练习着拳脚,见张长锁来了,赶忙收住招式,笑着说:“三哥,你也练练吧,强身健体的,挺管用的。”说着他拍了拍胸脯上的肌肉块儿,摆出一副血气方刚的样子。
张长锁笑道:“你练吧,我还有事,对了,一会儿你把咱家那骒马拉到王庄去配配吧,我看它有点起骒了。”
张铁栓拿起衣服,看了看张长锁眉头紧锁的样子,边安慰道:“哥,不就是为了那点儿粮食吗?你犯不着整天上火的,大不了这个村长咱不干了。”
张长锁嘟囔了一句:“你懂个啥。”
眼看期限快到了,尽管张长锁把全村走了个遍,但最终还是没有收上一粒粮食来,他急得嘴上满是水泡,便和父亲商量对策。
张元启见儿子一脑门子官司,很是心疼,他叹了口气道:“唉,现在的村长就是两头受气的差事,我看这个粮大家还是要交的,种地纳粮,这是多少年的规矩,咱们家再有也是咱们家自己的,咱也不能为了乡亲们,把咱自己全都豁出去呀,我看马善人那天说的有道理,一会儿爹领着你再找他去。”
张元启买了二斤猪头肉,拎了两瓶好酒,又敲开了马祥林的家门。
原以为会吃闭门羹,不料马祥林却十分高兴地迎了出来:“我还以为谁呢,敢情是老哥哥,快请,快请。哎呀呀,您这么大岁数,还买啥东西呢!”
双方落座后,马祥林马上给张元启道喜:“老哥哥,你还不知道吧,你们家的三儿现在出了大风头儿啦,村里的乡里乡亲都一个劲儿地夸他呢!”
张元启呵呵一笑:“他大爷,你就别给他戴高帽了,再夸夸他,他连北都找不到了,俺们家的三儿,我没有管教好,说话办事有不周全的地儿,还请你多担待着点儿,来,三儿,快给你大爷赔不是。”
说实在的,张长锁打心眼儿里不愿意这么低三下四地去求马祥林,他知道这一切都是马祥林背后捣的鬼,但迫于无奈,他只得按父亲的吩咐,上前赔不是:“大爷,晚辈说话办事都是孩子气,请您多海涵点儿。”
马祥林呵呵一笑:“你哪儿会有什么错,没听村里乡亲说嘛,这个村长你当的可比我好多了。”
张元启一听马祥林话中有话,赶忙想把话岔开:“他大爷,你看咱俩也好长时间没坐了,咱老哥儿俩一块儿喝一盅,咋样?”
马祥林笑道:“咋不好,他娘,去摊个鸡蛋,弄俩儿菜,俺们老哥儿俩好好喝点。”马祥林向外屋吩咐道。
酒菜端上来了,张元启端起酒盅:“他大爷,这杯酒算是我替三儿给你赔个不是,三儿小不懂事,你看,都是乡里乡亲的,你就饶过他这一回吧!”
马祥林端着酒盅,哼笑着说:“老哥哥这话我可不敢接着,我看三儿做得对,有些事情,放在我还真做不了,一是我岁数大了,二是我又有病,三呢我也没老哥那么财大气粗。不过请老哥放心,你我都是过来人,我一定会帮三儿的。”
张元启马上切入了主题:“他大伯,你看咱村征粮这件事上,还麻烦你老出个面,和大家去说说,你当了这么多年的村长了,比三儿有经验,就帮帮他。”
马祥林摆出一副难为情的样子:“老哥哥,这你就冤枉我了不是,我哪有那么大的脸呢!上次我不是也和你说了吗,该硬的时候就得硬起来,这些人其实就是刁民,欺软怕硬。”
马祥林还要说什么,门帘儿一挑,穿着碎花袄的马寡妇走了进来:“呦,张大爷来啦,张村长也来了,你们这是?”马寡妇说着朝张长锁瞟了一眼。
张元启笑道:“没事过来坐坐,顺便领着三儿来个他大爷赔个不是。”
马寡妇嘻嘻笑道:“呦,我说的呢,这么热闹,在当街上就听到了,原来是这回事呀!”
马祥林瞥了马寡妇一眼:“老哥哥,您这就见外了不是,咱老哥儿俩不就是喝盅酒嘛,还赔啥不是。来,你也坐这儿。”
马寡妇也不客气,立刻上了炕,先给大家满了一盅酒,然后端起酒盅:“来,大爷,我敬您一盅。”她把酒喝完后,亮了亮酒盅的底儿,又斟了一盅,冲着张长锁笑道,“来,我陪村长一盅。张村长,我这个寡妇失业的,今后还真得仰仗着你这个大村长的照应呀。”
张长锁端着酒杯愣愣地发呆,当村长之前,他早就听说过马寡妇的风骚事,有点不正经,有时候见了面都绕着走,当了村长后,他曾经对村里人的人品盘算过一遍,唯独对马寡妇没有做过多的考虑,自打上次和父亲到马祥林家来碰见过她,便一直在心里防着她。听了这话,他不知道这个女人说这话的真正目的,当他抬起眼时,看到的却是马寡妇火辣辣的眼睛,他赶忙把眼睛低下,慢慢把酒喝掉。
马寡妇闪着风情万种的眼睛,关心地问:“呦,看把村长愁的,有什么事把村长难成了这样?”
张元启叹了口气:“桂枝呀,你有所不知,这征粮的事情确实难办,后天就到期了,可都到这工夫了,一粒粮食还没征上来呢!”
马寡妇瞟了一眼马祥林:“有马善人在,再难的事都不算事,你就帮帮他嘛,给我一个面子嘛!”
马祥林有点儿生气地说:“老娘儿们家家的,你懂什么,我是想帮,村里人见我一天到晚病秧子似的,谁还听我的。”
马寡妇红着脸道:“呦,你看你身体这么壮,哪像有病的样子,张大爷您说是吧?”
有了马寡妇这一通恭维话,再加上张元启带着张长锁来道歉,马祥林有点松动了,开口道:“我去试试吧。”
张元启赶忙说道:“三儿,你还不赶紧敬你嫂子一盅。”
张长锁答应一声,端起酒盅红着脸说道:“嫂子,我敬你一盅,谢谢你。”
不知是喝了酒的缘故,还是给张长锁帮了忙后的得意,马寡妇的脸色异常兴奋,她笑着看着张长锁,嬉笑道:“没事,你不用谢我,以后多走动走动,你就什么都明白了。”
张长锁没有想到,收粮的事情竟会变得如此迅速。
第二天一早,当他心中打着小鼓到村公所的时候,看到村公所门前排满了交粮的乡亲。
大家见到了张长锁后,尽管表情有些不自然,但还是和他打着招呼:“村长来啦。”
“村长早呀。”
张长锁一边和乡亲们打着招呼,一边安排壮工过称、装袋、记账。每交一份粮,他都给作了一个揖表示感谢。
突然,张长锁在交粮的人群中发现,村里的李老太太也拎着半小袋帮豆儿夹杂在人群中,跩跩地朝大门口挪动着一双小脚。李奶奶都七十多岁了,孤苦伶仃地一个人生活,怎么也来交粮?张长锁的眼泪都快下来了。
天擦黑的时候,粮食终于收齐了,而且还多了100斤,张长锁兴奋地看着一麻袋一麻袋粮食,开心地笑了。像是察觉到什么,他猛一抬头,看到马寡妇在墙角正看着自己,便赶忙走了过去,冲着马寡妇笑道:“嫂子,我真的谢谢你了,没有你的帮忙,马村长哪肯帮这个忙。”
马寡妇一笑,露出了瓷白瓷白的牙齿:“知道就好,不过,你也别高兴得太早,这个马祥林满肚子花花肠子,不知哪天还会给你整出点什么事来。”
张长锁心领神会地说:“谢谢嫂子的提醒,我都记下了。”
马寡妇冲着张长锁不好意思地一笑:“有时间到家里坐吧,但最好白天别来。”
听了这话,张长锁有些疑惑了,晚上到一个寡妇家里去,合适吗?
张长锁看马寡妇走了,让壮工们把粮食抬到村公所的屋里,又派了长工老张头帮助老王头看着,然后回到了十里墩,他打算第二天一早儿把这些粮食交到大乡里去。
事情还真的让马寡妇给说中了。
第二天一早,当张长锁套好大车,来到村公所拉粮食时,发现老张头不见了,喊了半天,老张头才跌跌撞撞地从屋里出来,张长锁见老张头喝得酩酊大醉,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刚要安排人装车,结果发现麻袋数不够了,他一连数了两遍,结果咋数咋不够数,少了两麻袋,两麻袋可是500斤粮食呀,张长锁的头一下大了,他把老张头叫过来,追问道:“昨天晚上你在哪儿喝的酒,为啥粮食少了500斤,你说,粮食哪儿去了?”
老张头一边扇着自己耳光,一边自责道:“我让你嘴馋,让你嘴馋!”接着才痛哭流涕地说,“我和十里堡的长工老赵都是李家庄的,俺俩好几年没见面了,夜黑时他来找我聊天,聊到半夜,我俩酒喝了点酒,喝完酒,老赵头就走了,我也没想到,才喝了两小盅就醉了。”
听了这话,张长锁顿时起了疑心,但看时候不早了,只得先从自己家弄了500斤粮食,把粮食先交到了大乡。
回来家里,张长锁又把老张头叫到屋里,再次问了一遍事情的经过。他感到事情有些蹊跷,一定是有人故意把老张头灌醉,把粮食偷走了,好在那个贼手下留情,要不然他根本交不了差。
张长锁让老张头暗地里把老赵头找到张家客栈,想问个究竟,老赵头说那天刚回到东家,自己也醉了,直到快中午了才醒,还被东家打了一顿。当张长锁追问酒是怎么来的时候,老赵头支吾半天才说:酒是东家给的。
后来张长锁找了个借口找到那个乡绅,转弯抹角地问起了老赵头喝醉酒的事情。乡绅想了半天才说:“那天晚上,马祥林来找自己喝酒,在院里看到了老赵头,就和他说‘十里墩的长工老张头在村公所呢,你不和他聊聊去吗,顺便再和他喝两盅。’老赵头说没有钱。不料马祥林说,我就知道你没钱,我早把酒给你准备好了。”
无利不起早,马祥林凭什么要给老赵头酒,这里面肯定有文章,很可能是把老张头灌醉,把粮食偷走。
张长锁决定去找马寡妇,想从她嘴里得到些东西,但他很快就犹豫了,这合适吗?思来想去,张长锁还是买了几瓶雪花膏,又撕了几尺花布,在一个下午敲开了马寡妇的家门。
马寡妇一看是张长锁,惊讶地说:“原来是你呀,我不是让你晚上来吗?你怎么……”
张长锁笑了笑:“白天不更方便?”
马寡妇向门口看了一眼:“白天才人多眼杂呢!”马寡妇说着用下巴向马祥林家示意了一下。
张长锁轻轻嘘了一声,然后道:“嫂子,有个事情请你帮忙。”
马寡妇看了看张长锁,冲他嘿嘿一笑:“进来说吧。”说着要拉张长锁进屋。
张长锁道:“不了,我简短说吧,嫂子,我虽然是十里墩的,但对十里堡怎么样?”
马寡妇一笑:“挺好的呀,没听见大家都在夸你呢,又是修村公所的,又是打狼,你比武二郎还厉害呢。呵呵。”
张长锁央求道:“嫂子,您能不能和马村长说一下,放过我呢?”
马寡妇一怔:“这是咋回事?”
张长锁道:“一言难尽,这么说吧,那天我没听你的话,大意了,结果被人家钻了空子,吃了哑巴亏。”
马寡妇说:“钻了啥空子?”
张长锁说:“有人把守夜的灌醉了,偷走了几麻袋粮食。”
马寡妇也感到纳闷:“竟有这事?”
张长锁想了想:“这事八成是马祥林干的,那天晚上,守夜的老张头喝的是马祥林给的酒。”
马寡妇顿时明白了:“我说的呢,这两天,那个老不死的这么开心,原来是这样呀。”
张长锁掏出了雪花膏和花布,塞在了马寡妇的怀里:“嫂子,你帮我从侧面打听一下,看看有没有这回事,这个给你。”。
马寡妇不解地笑了:“长锁哥,你送我这个呀,我可不敢要。”
张长锁却不好意思道:“我先谢谢你啦。”说着把雪花膏和花布硬塞到了马寡妇的手里。
张长锁从十里堡村回到家时,已经快半夜了。
他回到了豆腐房,还没进门,就喊道:“老四,老四。”从张长锁十五六岁开始,就一个人在豆腐房里住,张铁栓来了以后,两个人成了伴,在这里一块儿聊天、玩游戏、掏家雀,等长大了,两人便一块儿进学堂、学习做豆腐。
张铁栓此时还没有睡,他正在豆腐房里捣鼓着什么,要等着和三哥一块儿巡完夜后再睡。他见张长锁进了门,便从墙上摘下了土枪:“三哥,咋这两天又闷闷不乐呢,你当上村长是好事呀,你看看,村里人多拥护你。”
张长锁不高兴地说:“好个屁,整个是一个遭罪的苦差事,你没看见,现在十里堡的好多人见了我都绕着走,不敢跟我说话了,好像我都快成了臭狗屎了!”
张铁栓想了想:“要说可也是,你瞧瞧,你当村长才几天呀,又是征夫又是征粮的,看把你忙的,忙得都不着家了,人家当村长都是往家里搂钱,你可倒好,往里贴还不说,还落了个费力不讨好的结果,可真是的,我就纳闷呢,咱家又不愁吃又不愁穿的,你这个破村长还当上瘾了,心气儿这么高!”
张长锁苦笑了一下:“谁当上瘾了,我现在是风箱里的耗子——两头受气呀,咱总不能让老爹再跟着上阵吧!要不为了咱爹,我才不去当这个窝窝囊囊的破村长呢。”
张铁栓冲着哥哥一笑:“对了,三哥,我那天听那个卖雪花膏的人说,解放区那边的老百姓的日子可好过了,比延庆川的好多了,鬼子根本不敢去瞎折腾,哪儿像咱们这儿呀,到处杀人放火糟蹋妇女不说,经常征粮要夫的,多可恶。”
张长锁看了一眼张铁栓:“那个卖雪花膏的还和你说啥了?没用的话千万别到外边瞎说八道呀,免得让那些侦缉队的抓住话把儿,又让咱爹费心。”
张铁栓看到三哥疑心重重的样子,不再说什么了,过了好久,才又提醒道:“三哥,二嫂他们也在议论你呢,怕是你一天到晚的为了乡亲们,忘了咱们家。村里的事有大伙儿呢,反正咱们家可不能大包大揽呀,那不是败家吗?”
张长锁叹了口气:“二嫂说的有道理呀,可这会儿我有啥办法呢,我总不能像马祥林那样,仗着是一个破村长,整天危害乡里,装足了自己的腰包,这种人早晚会遭到报应的。”
两个人在张家的围墙里转了一圈,看到没有情况,便又回到了豆腐房。张铁栓见张长锁还是一脸愁云,便做了个鬼脸儿:“哥,你好歹也算个官,当村长都快一个月了,今天咱哥儿俩喝点儿咋样?也算是给你暖暖官儿嘛。”
张长锁看了看张铁栓,苦笑道:“我这算个啥官,你要是想喝酒就直说,用不着拿这个做幌子。”
张铁栓顿时高兴了:“那咱哥儿俩分分工,你去客栈找点儿酒,我到菜园子弄菜去。”
等张长锁从客栈里拿回酒的时候,张铁栓已经从菜园子摘来了黄瓜和辣椒,他先把黄瓜和辣椒切好,放好了作料,接着他又点着火,从水缸边儿上拿出一大串鱼肉,放在火上烤,不一会儿,豆腐房就弥漫开了喷香的烤肉味儿。
张长锁把酒倒好:“老四,你从哪儿弄的这么多鱼肉呢?”
张铁栓把一个烤好的鱼在张长锁眼前晃了晃:“今儿下午从河沟里捉的,你尝尝,香着呢!”
张长锁吃了口鱼肉:“嗯,确实挺好吃的。”接着他端起了酒碗,“来,咱哥儿俩喝一口。”
张铁栓笑道:“干了,祝贺哥哥当了村长。”说着使劲儿喝了一大口酒,然后说道,“三哥,我就纳闷了,你都这么大了,咋不赶紧娶媳妇呢?”
张长锁一笑:“我咋不想呢,十里堡村和我大小相仿的,早都结婚抱孩子了,哎,你说你哥我要模样有模样,要家产有家产的,咋就没个对眼的呢。”
张铁栓端着酒碗,说道:“不是没对眼的,是你的眼眶忒高了,其实我早就听爹说,康家那个丫头挺不错的嘛!”
张长锁摇了摇头:“那丫头人样子长得确实不赖,可咱家娶媳妇是将来居家过日子的,又不是摆设,你没看见她那双小脚儿,来一股风,准能吹跑了,将来咋下地干活儿?”
张铁栓这才明白过来:“咳,我当是啥原因呢,原来就为这个呀。我看着挺好的,你知道吗,老书上都说那叫三寸金莲。你没听说过吗,早先有个奸臣为了讨好皇上,把自己闺女的脚单单弄小了,送到皇宫里去了,皇上一高兴,就让全国的女人都裹小脚,那叫美,叫顺眼,多亏了那个皇上,咱们才见到小脚女人。”
张长锁差一点笑喷了:“你就胡诌吧。要说那些女人也够苦的了,为了裹小脚遭了多大罪!从七岁就开始裹,那些小脚都是把其他几个脚指头勒得快断了,才变成这样的。”
张长锁和张铁栓一边喝着酒,一边海阔天空地聊着,不大一会儿,两个人喝得都有点多了,便和衣躺在炕上睡着了,呼噜打得震天响。
深夜时分,张长锁和张铁栓正在熟睡,突然传来了一声枪响,工夫不大,二哥张连锁便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三儿,不好啦,咱爹出事啦!”
“啥?!”张长锁揉了揉眼睛,顿时急了,赶忙跑出豆腐房,看到沈忠等几个长工拿着铁锨和叉子什么的,站在当院里。
二哥哭丧着脸道:“咱爹让大帮给绑走了,娘的身上还挨了一枪托。”
张长锁一听,赶忙提着枪追了出去,但外面早已经没了人影儿。张长锁等人围着土围子转了一圈,最后在东南角发现了一个大窟窿。原来,张家大院四周是被土围子围着的,只有南北两个大门,围墙外面全是棒子地。那些土匪见从两个大门进不来,就打起了土围子的主意,因为土墙年久失修,有些地方有点松软了,他们就在墙角掏了个大洞钻进来,先到上房把张元启绑了,等出了土围子才放了一枪,算是给报了信儿。
“二哥、三哥,你们看。”铁栓拿过了一封信,是在父亲的炕上找到的。
张长锁打开一看,顿时不言语了。
信是南山的土匪头子王老五留下的,信上说山上的弟兄没得花了,请在三天内送去500个大洋,否则就撕票。
“500呀!”二哥一听就急了。
张连锁早已把两个叔叔请了过来,几个男人正在屋里急得团团乱转。
二叔看着张长锁说道:“三儿呀,你现在不是村长嘛,你去找找大乡队看看,让他们出出面,看能不能把人给放回来,现在是官匪一家嘛,没准儿能管用,他们还指望着你给他们当差呢!”
三叔说一拍脑门儿:“对了,咱村的马洪林不是在王老五的大帮里吗,找他去。”
二叔说没好气地说:“找了也没用,那个马洪林黑着呢,你没听说吗?有一回,马洪林在山下看上一个小媳妇,就让人把那个小媳妇弄到山上给糟蹋了,这还不算,他又看上那个小媳妇手上的镯子,弄不下来,最后把人家的手砍掉了才拿下镯子。”
三叔说:“那是对外人,对乡里乡亲没准儿网开一面。”
二叔把头摇成了拨浪鼓:“自古以来,土匪都丧失人性,说不定这次大哥被绑,就是他使的坏呢。要我说,还是去找大乡队吧。”
张长锁知道王成仁是个老财迷,空着手去肯定不行,但自己不知道家里的钱都放在哪儿。
母亲此时正躺在炕上疼得“哎呀哎呀”叫着,老丫头已经哭得成了一个泪人,母亲听说要去赎张元启,赶忙让张长锁掀开了炕席,龇牙咧嘴地指着指了指边上的一块炕坯说:“三儿呀,快把那块炕坯弄开。”
张长锁用手试了试,感觉炕坯是松动的,便一使劲儿,搬起了炕坯。只见里面是一个瓷罐,他用手一摸,里面全是洋钱。
天麻麻亮的时候,张长锁揣着200个大洋,心急火燎地来到了王河营大乡长王成仁的家门前,他敲了半天门,才从里面出来两个拿枪的伪军。
伪军一看是张长锁,便问:“这不是张村长吗?你不在村里好好待着,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张长锁从怀里掏出洋钱,递了过去:“两位老总,您行行好,我们家老爷子让南山的王老五的大帮给绑了,我来找王乡长,救救我爹。”
伪军看了看张长锁:“是王老五的土匪呀,我们哪儿敢惹,你回去吧,这事我们办不了。”
“您就行行好,进去通报一下吧。”张长锁央求着,掏出几个大洋,塞到伪军兜里。
伪军想了想:“等天亮了吧,王乡长前两天刚娶了三姨太,这会儿正和她热乎着呢,这工夫叫醒他,我俩不是找死吗?”说完又进去了,再也没出来。
直到日出三竿,王成仁才从院里出来,他一边伸着懒腰,一边打量着张长锁:“张村长,这么早来找我,有啥事呀?”
张长锁苦笑着说:“王乡长,我们家老爷子让南山王老五的大帮给绑了。”
王成仁哈哈一笑:“你们家老爷子让土匪绑了,这管我屁事,我管不了。”
张长锁央求道:“您在县里做事,眼路宽,您能不能帮我托托人,让大帮把我爹放了,我往后一定认认真真替您做事。”
王成仁想了想,说道:“张村长啊,大帮我们也不敢惹呀,这样吧,我给你托托皇军,看有办法没有,你回去等着吧。”
张长锁小心翼翼说:“王乡长,您可要多费费心,晚了就来不及了。大帮说了,三天不送钱,就要撕票。”
张长锁把大洋交给了王成仁,然后千恩万谢地离开了王成仁家,回到了十里墩。
一连两天,张长锁如坐针毡,门外稍微有个动静,他都以为是父亲回来了,但王成仁那边始终没信儿。第三天一早,张长锁又到了王成仁家,任凭咋敲门,也没人理茬儿。
看来王成仁这边没指望了,张长锁回到家,找到两个叔叔商量对策。
二叔说:“要不把钱给人家送去吧,要是晚了,别把我哥哥给耽误了。”
张长锁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叫花子,怀里揣着500大洋刚要出门,张铁栓回来了,只见他跑得满头大汗的,一进了门,就坐在了地上,然后有气无力地说:“咱爹有救了。”
一家人顾不得看张铁栓的狼狈样,忙问:“老四,你说清楚,到底是咋回事?”
张铁栓拿起水瓢,喝了一瓢凉水,对张长锁说道:“你还记得前几天咱们店住的那个卖雪花膏的吗?”
张长锁纳闷地说:“记得,咋不记得。”
张铁栓笑着说:“他是这个。”张铁栓说着伸手比画出一个“八”字形。
张家人顿时都大吃一惊,二叔道:“你怎么能跟这种人来往呢,你不要命啦?”
张铁栓一笑:“没事的,他们待人可好着呢。他上次跟我说过,咱们家如果有什么大事跟他打一声招呼,这次我看王成仁那边没指望了,今儿个早上我就到北山找他们去了,他们听说了这件事,说能帮这个忙。”
听到掌柜的有救了,一家人都高兴了起来。
傍晚时分,张元启被几个打扮成老百姓的人送了回来。其中一个人正是那天那个卖雪花膏的。
张长锁拉着那个人的手说:“真不知道该咋感谢您。”说着要留下那些恩人吃饭。
卖雪花膏的把张长锁叫到一边,说:“铁栓兄弟可能已经跟你说了,我姓郭,你叫我郭队长好了,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即使没有老太爷这件事情,过几天我还也会专门找你的。这里是城边儿上,情况复杂,这样吧,今天我们先走,过几天我再来。”
张长锁心里打着鼓问道:“如果王成仁问起来,我咋说呢?”
郭队长拍了拍张长锁的肩膀:“如果王成仁问起这事,你就说,是自己花钱赎出来的。”
看着郭队长等人的身影消失在棒子地里,再想想王成仁成天鬼话连篇的样子,张长锁的眼睛眯成了一道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