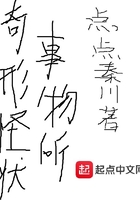家里的太阳能坏了,不出热水。晚上沈鹏要开车带我去镇上澡堂子洗澡。我坚持要骑自行车,上中学的时候我哥就天天骑车带我去上学,我坐在后面感觉那就是最大的幸福。小北风飕飕的,回家的路上,他把军大衣披在我身上,上坡我也懒得下来,他把屁股抬起来卖力地蹬着自行车。
我说:“哥,加油哎。嘿嘿!”
沈鹏气喘吁吁地说:“唉,长时间不锻炼,上坡都费劲了,洗澡的时候我看了一圈儿,就数我的啤酒肚最大了。”
我打趣地回了一句:“注意形象哦,上次你说的那个对象是怎么回事,快说说什么时候结婚。”
“谈着呢,我高中同学,现在在县医院当护士,现在咱家这情况,鸡飞狗跳的,怎么结婚?我还是先等着单位分房再说吧,也不知道要到什么猴年马月。还是先解决你的问题吧,女的好找对象,让咱妈也高兴高兴,冲冲喜。”
坡太长了,我哥终于蹬不动了,下来推着车走。
到了坡顶,他停下来帮我戴好帽子,若有所思地说:“你呀,上大学几年一个没谈,我都觉得惊讶。我们单位有好多优秀青年,趁春节聚会,我帮你撮合撮合。你说说,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
“我喜欢上一个永远无法在一起的人,再也没有一个人可以让我觉得会比他好。”
我哥怔住了,过了一会儿才说:“总有一天,会有一个正好适合你的人深情款款地来到你身边,带给你幸福。”
沈鹏说这句话的时候,月亮刚好从云层里钻出来,又圆又亮。
“哥,看着点路,好好骑你的车吧。争取今年嫂子娶进门,来年生个大胖小子,这样也好有人陪妈做个伴。”
我一直记得那晚如水的月光,跟我哥聊完天,心里稍微敞亮了些。
沈大河居然回来了。
在我爷爷七十大寿的前一天。他开了一辆白色保时捷回到村里,他雄赳赳地把车嘎吱停在家门口,很多邻居根本不认得这个牌子,但是都知道很贵。跑了长途都脏了,但是仍然有掩饰不住的霸气。那牛哄哄的劲儿,跟常胜将军凯旋一样,不屑一顾的样子。
他的鬓角都有白头发了,额头堆满了皱纹,背也驼了,不似我小时候那么矫健。眼神对视的时候他有些许不安,长久以来让我心灵感到蒙羞的人,居然没有想象中那么让人憎恨。
人家散烟都是一根一根的,他老人家是一盒一盒的。皮夹克好多口袋啊,里面跟变魔术一样装了好多盒,散完一圈,从车后备厢里再拿。
不装能死啊,一盒烟都快够我妈一个星期的生活费了。没有一个人敢在他面前唾弃他,除了我。人家都说站得越高摔得越狠,后来果然应验了,这是以后的事情了。
爷爷的寿辰办得非常风光,在镇上万宝酒店。在外务工的很多年轻人都回村了,难得一聚,所以很热闹。好多送礼的乡亲,他们都想巴结沈大河,想过完年去他矿上打工能当个小队长啥的。
还有很多乡上的干部都赏脸来喝酒,沈大河风光无限,像见过大世面的人一样侃侃而谈。我在角落,冷漠地看着这些不同面具下的人脸。
他还当着那些人耍大爷的劲儿,对我妈呼来唤去的,我妈居然一句没反抗,还露出了久违的笑容。爷爷也咧着没牙的嘴笑着,一年在村里见到的人加起来也没有今天来得多,因为他有个出息的儿子,所以这些人都对他毕恭毕敬的。
沈大河说今年在家过年。我心里还有一丝窃喜,是不是厌倦了狐狸精,正式回归家庭了?
我也没敢细问我妈喝农药的前因后果。
总之,表面看来这是一个完整的家庭,过了一个还算团结祥和的新年。
看着春晚,我按惯例群发了一条微信:新年快乐。
几乎是同时,我收到九日的微信:同乐。玩那个船了吗?
我拿着手机傻愣了一会儿,突然想起来那日希希发烧,我说起我们老家的春节风俗,我春节会玩旱船庆新春,就是用竹子做的船蒙上鲜艳的布,上面挂各种装饰品,有人坐在船里跳舞,有人在前面撑船唱我们当地的小调,旁边还有乡村乐队配合着敲锣打鼓,祈祷来年风调雨顺,很有特色。没想到他还记得,我赶紧发了一堆玩旱船的照片和视频。
过了一会儿他回:挺好。
我看着窗外被雪光照亮的院子,感觉天要晴了。
大年初一发生了一件让我极其不爽的事儿。
上午邻里亲戚拜完年,下午很多男的聚在我家二楼客厅炸金花。我在一楼厨房烧好水提着暖瓶上楼泡了几杯茶,沈大河放在沙发上充电的手机响了。
快五十岁的老头还玩微信,微信用的名字就是真名:沈大河。
微信窗口还是打开的,是跟村里柱子叔的聊天记录。
沈大河:你小嫂子,一定替我安排好了。
柱子:放心,在县教育宾馆好吃好喝伺候着呢。
沈大河:挺会来事儿,给你留了两瓶好酒,晚上来拿。
柱子发来两张照片。一个是县教育宾馆金碧辉煌的大厅,一个是豪华套房里,有个女人侧着身子在衣柜旁整理行李箱。几年过去了,她还是那个发型,样子几乎没变,只是衣着越来越时髦了。
我一股无名火往外冒,而此刻我妈还在手脚麻利地擀着饺子皮儿,面带微笑,自言自语。
我坐了村口二路公共汽车,往县城里赶。狐狸精,今天不是你死就是你亡。
我想去问问她怎么做到这么厚脸皮的,要不要去家里坐坐,谈谈心得,准备什么时候转正。
一路上我都在准备台词。
有个北京的陌生号码打电话给我,打通就挂,我回拨过去居然无法接通。反复三四遍,弄得我都想发火了,浪费我的漫游费是啥意思。
我到教育宾馆门口下车的时候,电话又响了。我在宾馆一楼大厅沙发上坐定。
“喂?谁啊?”
传来一声清嗓子的声音,貌似是个女的。
“谁啊,说话啊,打骚扰啊。”
世界如此美好,我却如此暴躁,大清早的,这样实在不好。
“是沈蔷薇吧?”一个低沉而神秘的中年女声传来。我不由自主地一颤,强大的气场震着耳膜。
“我是希希的妈妈,我叫郝菲。我有话说,想约你谈谈。”
那个在路虎车上露半张脸的女人突然在我脑海里对号入座。
“哦,是跟希希有关吗?可以的,开学以后到幼儿园来谈吧。”
“不,不是希希的事儿。希希过完年不在你们幼儿园了,我要带她去美国了。”
“啊?什么时候去?不回来了吗?柳先生也去吗?”我焦急地问。
“呵呵,看来我找你是对的。你想知道的答案我都会告诉你。我想跟你谈的,就是柳旭。我相信你一定对我们的谈话内容很感兴趣。至于为什么是你,我会当面告诉你的。”
“啊?这样啊,为什么啊?”我警惕地问道。
“时间地点我会发短信给你,我希望你能来,我在国内的时间不多了。你不来会后悔的。”
我脑子的内存都快不够了,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的好奇心暂时弱化了我对眼前狐狸精的愤怒。
我在县城教育宾馆一楼徘徊了好久,突然就没了上楼去找狐狸精拼命的兴趣。这个事情最应该问责的应该是沈大河吧,一个巴掌也拍不响。至于这个女人,这么些年她背负着小三的名声,心安吗?大过年的,住在宾馆里,男人都不能来陪,心酸吗?
我只能说,花心的男人,真的很会左右逢源。那他回来到底是良心发现还是另有企图?我必须叮嘱沈鹏防着他点。
我又去了江边小吃城,吃了碗胡辣汤,然后直接去火车站买了最近一趟去北京的火车票。
初二的火车上只有寥寥无几的几个乘客和列车员,百无聊赖之际我在车厢里越来越冷,直接跑步取暖了,根本不需要注意形象。
其实一上火车我就后悔了,我干吗要答应她呢,大初二的,这么冲动,而且除了随身带的小背包,衣服一件没带。
我决定还是再咨询一下彤彤。这种关键时刻,她帮我出出主意也是好的。
电话接通了,她说她跟杨得在放烟花。呵,大白天的,在放烟花玩,可想而知有多极品。我把这通蹊跷而神秘的电话内容告诉了彤彤。
“彤彤,你快说啊。给出个主意。”我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焦急地问。
“哎呦,老公,你别闹,我跟蔷薇说话呢。”电话里居然传出彤彤和杨得打情骂俏的声音,真受不了。
“她电话里说得很神秘的样子,说了很多莫名其妙的话,还要带希希去美国。”
“希希是她女儿,去呗,你们班还少个大麻烦呢。肯定是关于那个假日本鬼子的事儿,可惜我不能陪你去,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为了安全起见,你挑门口的位置,万一她泼硫酸你能跑快点。”
“如果明天联系不上了,你记得看北京新闻啊。”我一脸黑线地挂了电话。
紧接着手机可真忙啊。快没电了,也没带充电器,我跑了两节车厢,都没借到合适的充电器。原来三星都弱爆了,我看见大爷都用上苹果了。
手机吱吱震动起来,都是祝福的短信,达子还打来电话拜年,他跟二娟要结婚了,盖新房的地基也选好了,二娟过完年同意跟她来北京找工作了。
一连串的好消息。
我问他,你父母还好吗?他说好极了。二娟父母身体也健康。
我想起之前我们一起躺在幼儿园滑梯上聊天的时候说的话,他说幸福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简简单单,平平淡淡,复杂的多角恋都是城里人的事儿。想到这里,我看着窗外渐渐暗下去的天,模模糊糊后退的远山,抿嘴笑了一下。我的手机电量已经在抗议了,我不得不最后总结发言,我真羡慕你啊,达子,真的,姐说的是认真的。
到北京以后,我的手机已然自动关机了。
忐忑不安地回到龙泽苑住处已经黑透了,春节期间的北京俨然一座空城,还好房门钥匙就在兜里。手机充上电,我就给沈鹏打电话,让他帮我把行李托运过来。
沈鹏说:“爸到处找你,还开车去县城找了,到现在都没回来。”
我看了一下墙上的钟表,都快半夜十二点了。
“去,去县城找我?还没回来?他今晚不会回来了,不信我们打赌。”我一想到狐狸精在县城,心里隐隐觉得不安,就像吃了只苍蝇一样恶心。
我发了一条短信给沈大河:你既然回来了,大年初二的就忍不住去鬼混吗,那么迫不及待吗,欺人太甚!
沈大河:我跟你阿姨是有感情的,你妈那个脾气我都忍多少年了,一般人都受不了,成天寻死觅活的。
我:你居然这么说她,明明是你乱搞在先,还说这些不中听的。
沈大河:蔷薇啊,你看到的都是表象,你妈在你面前一直都是报喜不报忧。咱俩看到的都不是一个人,我没找你阿姨的时候她就老怀疑我,矿上净出事儿,压力那么大,我干脆找一个,说实话我和你妈早没有感情了,分居这么多年早就算自动离婚了。
我:人在做天在看。有一天你会遭报应的。
我挺恨我这张破嘴,因为这个报应后来真的来了。而我,为了替他偿还这个报应,差点搭进去了我的一生。
跟沈大河斗完气,我扔了电话。脑细胞死亡过多,饿了。
冰箱被彤彤断电了,打开门儿一股霉味儿扑面而来,就剩下一袋大黄酱和几个鸡蛋,还有一块干巴得像袖珍木乃伊的姜。
苍天有眼,终于在茶几柜子底下找到吃的了,五种口味!彤彤要不要对我这么好?有红烧排骨,翡翠鲜虾,香菇鸡块,香辣牛肉,老坛酸菜。
你赢了啊,果真是方便面啊。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泡上了。等待吃的工夫,我翻看了一下微信。静静躺着的都是无关紧要的朋友的问候,我关心的那个人一个字都没有联系我。
我揭开泡面盖儿,香气扑鼻,一种幸福感油然而生。
邵嘉瑞:又到了一切矛盾都可以用“大过年的”来化解的时候了。
我:美男子,你干吗呢?
邵嘉瑞:你是不是有事儿求我啊?
我发了一串惊恐的表情:神算哪,明天如果你没事儿的话,陪我去见个人呗,壮壮胆,最好你什么都别问,因为问了也白问。
邵嘉瑞:行。
我:你也太爽快了,也不问问为什么啊?
邵嘉瑞:请看倒数第二条,蔷薇姑娘有交代,不能问。
这性格挺好,那感觉,嘿,暖男。
第二天上午十点,我刚起床还没来得及换睡衣,邵嘉瑞就在楼下按喇叭了。他开着自己的破夏利从房山一路驶来,停在楼道口,跟我们这九十年代的破楼房交相辉映,真是配套,都是怀旧系列。
我手忙脚乱地开门,脸上敷着从微信朋友圈买的什么美白的黑了吧唧的面膜,给邵嘉瑞吓了一跳。他以为我要戴着面具去呢。
洗了面膜,我把柜子打开,一件件地试衣服。其实我跟彤彤的衣服加起来也没多少,还都偏粉色系,最后挑了一件黑色拼接蕾丝边风衣,这件衣服印象中我找工作的时候穿过,平时都视若珍宝,零下几度,有点美丽冻人。搭配小脚牛仔裤,百丽的高筒靴。
我打了粉底、腮红,擦了唇膏、眼影,睫毛膏就刷了十多分钟,可见我对这次见面还是相当重视的,虽然我知道是以卵击石,我还是努力了。
这样打扮中规中矩的,也不失档次,勉勉强强吧。
又看了会儿电视剧,磨蹭到中午,我们俩随便找个春节也营业的馆子吃了刀削面。
快吃完的时候,邵嘉瑞一看中午十二点半了,跟上了闹铃一样拿出手机神神秘秘地捯饬。
我一把抢过来,看见他正打开微信对话框编辑笑话。
我说:“哎,这笑话不是你从网上复制粘贴的啊,你每天都手动输入的?”
“对啊,复制的多没意思,针对你的智商,笑点,偏好,纯手工打造。怎么样?”他玩世不恭地看着我。
“对啊,我每次看到好笑的笑话都会特地多看几遍,然后储存在脑子里,然后发给你和我妹。”他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说,“我最大的优点就是记性好。”
我仿佛捧着暖宝宝,心口热乎乎的。吃完我俩就驱车赶往国贸。
我心里一直琢磨,九日知道郝菲来找我吗?九日会不会来?
我要不要告诉他?
脑壳都快想破了,最后决定先会会郝菲,见机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