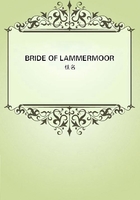我从早晨一直等到中午,终于看到一辆风尘仆仆的农用车--这肯定是矿上的车了--出现在马蹄山下那条泛白的水泥路上。隔着老远,我就嗅到了它散出的黑色的死亡气息。没多久,车进了前面的沟谷,坡梁和树木遮去了车身和它后面拖着的那道毛茸茸的尾巴。时令已值深秋,这一带包括马蹄山在内的老火山一派肃杀,山上山下的老头杨都剥光了叶片。
我抻着脖子又看了一会儿,便匆匆离开村口,返回我家院子,把二叔和几个本家亲戚喊了出来。他们一大早就来了,可因为矿上的车没露头,一时还找不到事做,每个人的脸上都布满了焦虑,有在窗台前走来走去的,有蹲在院墙根下吸烟的,有立在门道里唉声叹气的。这正是运煤的高峰时节,可能车还没离开矿山或走出没多远就堵了,要不然,两个钟点前就该进村了。现在,一听我说看见了车影儿,都忙不迭地跑出来,一排溜站在门前,脸葵花盘似的转向巷子口。十几分钟后,车轰隆隆的声音就听得清晰了,慢慢地,车头冒出来了,甲壳虫似的移向我家门口。
车“扑哧”一停,众人立刻围了上去。
从驾驶室跳出一个人,黑不溜秋的,扫了我们一眼,然后绕到车屁股后,“砰”地打开了后马槽。马槽一打开,我就看到了我爹和他身边那个给白布蒙住的东西——不用说,这就是我哥的尸体了。布新崭崭的,上面却横一抹竖一抹地涂满了血,像雪地上绽开一枝枝梅花。我直直地盯着,指望我哥突然一掀布坐起来,但半天也没见他动弹一下。我颤着手掀起了白布一角,只看了一眼,泪水就禁不住夺眶而出。怎么说呢,我哥的面相彻底给毁了,早眼睛不是眼睛、鼻子不是鼻子了,谁看了都会起一身鸡皮疙瘩。我哆嗦了一下,赶紧又把那张脸蒙上了,我真有些害怕。一个月前他回来探亲时还好端端的,这会儿却沉沉地躺在那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我真不明白这究竟怎么回事。
再看我爹,目光迟滞,面色憔悴,额上和眼角的皱纹灌满了煤尘,与几天前相比都不是一个人了。昨天我正在教室给学生们上课,他突然打来了电话,说我哥出事了,让我赶紧回来一趟。等我丢了魂似的赶回村时,家里冷清清的没一个人,邻居说春生你怎么才回来,你爹刚刚给矿上的车接走了。我就拨他给我打电话用的那个号,但一直没人接,后来通了一下,又给掐了。一直等到傍晚,才又有了我爹的消息,他让我通知二叔他们明天都过来帮忙,匆匆说了两句就又挂了。我去了二叔家,门锁着,院子里黑灯瞎火的没一个人。正是秋忙时节,我想他们一家人肯定都在马蹄山下那块地里掰玉茭棒子呢,等我赶去时,正碰着二叔出来了,二婶和连生跟在后面,脸上都沾惹着毛茸茸的玉米须。一听我哥出了事,二叔就怔在了那里,抹着眼圈嘀咕,好端端的咋就殁了呢。又问我都谈妥了吗,人都死了,矿上少说也得赔个三几十万吧?我说不知道,这得问我爹。
“都别磨蹭了,赶紧往下抬人吧。”黑不溜秋的人催促道。
我爹这才身子动了一下,但还是瓷愣愣的样子,好像还没有从梦中挣出来,半天,他身子又动了一下,慢慢伸出两只手臂——看那样是想把我哥抱起来。这当然不是他一个人做得了的事。我看了二叔一眼,先跳上了车,二叔跟着也跳了上来。我揽住了我哥这半侧的腰和手臂,二叔揽住了他那半侧的腰身,连生他们把手伸到我哥腿弯里,几个人同时一用力,我哥就离开了车厢底。
“都轻一点啊,”我爹一惊一乍地说,“可不敢把福生的胳膊腿扭了。”
我想他这就说的是傻话了,人早死了,这会儿还能有啥感觉呢?说句不恭敬的话,现在你就是随便把我哥塞到麻袋里背回去,他也什么都不会觉晓了。我们抬着我哥慢慢下了车,进院门时,不知谁踉跄了一下,我哥的脑袋突然歪在了一边,我爹早看在了眼里,立刻又喊了声“停”,小心地把我哥扶端正,这才让我们走。司机见车厢腾空了,“砰”地把后马槽合上,一缩脖子钻进了驾驶室。我爹努力扭过脸去,可能是想跟司机打个招呼,可还没等他开口,车就轰隆隆地开走了。
进了院子,我爹叫人把堂屋的门拆上一扇,赶紧放到炕上去。这是我们万家堡的风俗,说是死去的人停在门板上,有可能还阳。我们把我哥抬进了东房,停在了那扇门板上。我哥瘦得像只山羊,可他个子高,停在炕上,两条腿根本就舒展不开。我们只好又把他往上移了移,让他的头枕在炕沿上,但那一双腿还是舒展不开,脚死死地抵住了炕角。自打十八岁到了矿上,我哥怕误班一直很少回家,现在死了,拉回来了,这个家又只能委屈他,连条让他舒舒服服躺一会儿的大炕都没有。我爹早坐到了我哥身边,守得紧紧的,似乎怕谁抢走了他的儿子。以前我哥休假回来,要是睡着了,我爹就这样守着他,不允许谁弄出稍微一点响动,放个屁都不行。
“家有三件事,先从紧处来。”二叔老半天开了腔,他年轻时当过几天民办教员,说话老这么咬文嚼字的。“福生还没棺材呢,我们得赶紧给他弄一口,天黑前无论如何也得入殓。”
“早没准备下,这会儿上哪去买呢?”我爹木呆呆地说。
“离咱村不远的周家店就有个棺材铺,挑好了,就会给送上门的。”
“那快去弄呀,要好的,有柏木的吗?”
“都是柏木的,好的一万多,中档的三四千,一般的得个一千来块。”
“那就要三四千的吧。”我爹想都没想就出了声。
“三四千的?”二叔眼睛睁得多大,“是不是有点贵?哥你可得想好,这不是个小数目啊。”
“贵啥贵,福生早挣下了这口棺材。”
“这个你拿舵,你说买啥价位的就买啥价位的。”二叔好像明白了什么,又转过身对连生说,“你去跑一趟吧。”
连生却站着不动。
“你给连生拿钱啊,”我捅了我爹一下。
我爹点了点头,磨磨蹭蹭地下了地,朝靠后墙摆放的那口大瓮前走去,走到边儿上,可能是记起了什么,又退了回来,立在那里不动了。二叔好像看出了什么,冲着我爹点点头,领着亲戚们先出去了。我没动,还立在屋里。我爹看了我一眼,摆了摆手,意思是你也出去吧。我这才醒悟过来,他这是要从大瓮里或某个隐秘的地方取钱了。他让我出去,可见是连我也信不过。我看了他一眼,就也出了屋。
老半天,才看到我爹从东房里出来了。
“你得挑仔细点啊,”我爹将一沓钱给了连生,“可不敢让人家糊弄了。”
连生点点头,发着摩托车,“突突突”去了。
等连生走了,二叔忽又出了声。“哥,咱福生还连个天日都没见过呢,你看,要不要给他阴配个?”
“阴配个?”我爹还那么木呆呆的,“这一时半会儿的,到哪儿给他问寻个合适的呢?”
“哥,这事你别犯愁。昨天听了福生的事,我是一夜没睡啊,翻来覆去想着怎么把丧事办好。好多事我都替你想过了,比如买棺材,比如打坟做纸扎,比如阴配。我一夜想了好多好多,越想越睡不着啊。”说到这里,二叔两只胳膊拼命朝头顶上伸出去,然后长长打了个哈欠。“阴配是个大事,我嘛,想得也最多,想来想去,想到了个茬儿,你当是谁呢?就是春生他二婶娘家村张家洼的,对,牛百顺的闺女,这女人上个月死的,我看她跟福生挺般配。我就怕……”
“怕啥?”我爹打断了二叔的话,“有啥你尽管说,甭含半截露半截的。”
“就怕……”二叔笑了笑,“就怕钱的事不好说,现如今阴配个女人,不出个大价钱不行啊。”
“你只管去问寻,钱的事好说,好说。”
“哥,你可得想好了,这事,没个三几万下不来。”
“老二你甭跟我文摆了,你只管去问寻,合适了咱就办。”
“哥,听你这口气,矿上没少赔、赔钱吧?”
二叔眼巴巴地看着我爹,言语变得有些结巴了。
“这事不用你操心。”
我爹显见得对二叔这话有些不满,把脸扭到一边去了。
“我知道一提赔钱的事你就伤心,这样吧哥,你们给福生洗身,我去黄家洼请一下张半仙,让他择个日子。”好像是怕我爹责怪,说完这话,二叔就匆匆忙忙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