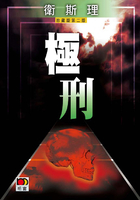礼拜六夜里。他只能再活一夜了。当他意识到这一点时,天已经破晓——礼拜天到了。
直到这可怕的最后一夜,一种意识到自己已经濒临绝境的幻灭感向他那晦暗的灵魂全力袭来。他倒也不是抱有什么明确的或者说很大的希望,以为自己能够得到宽恕,而是他认为死亡近在眼前的可能性仍然很模糊,根本无法细想下去。他同那两个轮流看守他的男子很少谈话,两人也没打算引起他的注意。他醒着坐在那里,却又在做梦。他时时惊跳而起,嘴里喘着大气,浑身皮肤滚烫,慌乱地跑来跑去,恐惧与愤怒骤然发作,连那两名看守——他们对这类场面早已屡见不鲜——也胆战心惊地躲着他。末了,在歹心邪念的折磨下,他变得十分可怕,看守吓得不敢单独和他面对面坐在那里;只得两个人一块儿看着他。
他蜷缩在石床上,回想着往事。被捕那天,他被人群中飞来的什么东西打伤,脑袋上还扎着一块亚麻布。红头发技散在毫无血色的脸上,胡须给扯掉了不少,这时成了一绺一绺的。双眼放射出可怕的光泽。好久没有洗澡,皮肤给体内的高烧烤得起了折皱。八点——九点——十点。如果这不是吓唬他的恶作剧,而是果真这样接踵而至的一个又一个小时,到它们转回来的时候,他又在什么地方。十一点。前一个小时的钟声刚刚停止轰鸣,钟又敲响了。到八点钟,他将成为自己的葬礼行列里唯一的送丧人。现在是十一点——
新门监狱那些可怕的墙壁把那么多的不幸和无法用言语形容的痛苦隐藏起来,不单单瞒过了人们的眼睛,而且更多更长久的是瞒过了人们的思考——那些墙壁也从未见过如此可怕的惨状。几个从门外路过的人放慢脚步,很想知道明天就要上绞刑架的那个人在干什么,人们要是看得见他,那天夜里可就别想安然入睡了。
从黄昏直到差不多午夜,人们三两成群来到接待室门口,神色焦虑地打听有没有接到什么缓期执行的命令。得到的回答是否定的,他们又将这个大快人心的消息传给了大街上一簇簇的人群,大家比比划划,相互议论,说他肯定会从那道门里出来,绞刑台会搭在那里,然后恋恋不舍地走开,还不断回头,想像着那个场面。人们渐渐散去。在深夜的一个小时里,街道留给了幽静与黑暗。
监狱前边的空场已经清理出来,几道结实的黑漆栅栏横架在马路上,用来抵挡预期的人群的挤压。这时,布朗罗先生和奥立弗出现在木栅入口,他们出示了由一位司法长官签署的准予探访犯人的指令,便立刻被让进了接待室。
“这位小绅士也一块儿去吗,先生?”负责替他们引路的警察说道。“这种情形不适合小孩子看,先生。”
“的确不适合,朋友,”布朗罗先生回答,“但我与这个人的事情同他密切相关。并且,在这个人得意忘形、为非作歹达到顶峰的时候,这孩子见过他,所以我认为不妨——即使需要忍受一定程度的痛苦和惧怕也是值得的——眼下他应该去见见他。”
这番话是在旁边说的,为的是不让奥立弗听见。警察举手敬了一个礼,又颇为好奇地看了奥立弗一眼,打开与他们进来的那道门相对的另一道门,带着他们穿过阴暗曲折的通道,往牢房走去。
“这儿,”狱警在一个黑洞洞的走廊里停下来,有两名工人正一声不吭地在走廊里做某些准备工作。警察说道——“这就是他上路的地方,如果您走这一边,还可以看见他出去经过的门。”
狱警领着他俩来到一间石板铺地的厨房,里边安放着好几口为犯人做饭的铜锅,他朝一道门指了指。门的上方有一个敞开的格子窗,窗外传来七嘴八舌的说话声,其中还混杂着榔头起落和木板掉在地上的响声。人们正在搭绞刑架。
他们朝前走去,穿过一道道由别的狱警从里边打开的坚固的牢门,走进一个大院,登上狭窄的阶梯,进入走廊,走廊左侧又是一排坚固的牢门。狱警示意他们在原地等一等,自己用一串钥匙敲了敲其中的一道门。两名看守小声嘀咕了几句,才来到门外走廊里,他们伸伸懒腰,似乎对这一轮临时的换班感到很高兴,然后示意两位探视人跟着那名警察进牢房里去。布朗罗先生和奥立弗走了进去。
死刑犯坐在床上,身子晃来晃去,脸上的表情不大像人,倒像是一头落入陷阱的野兽。他的心思显然正在昔时的生活中游荡,嘴里不停地喃喃自语,除了把他们的到来当作幻觉的一部分而外,什么也没有意识到。
“好小子,查理——干得漂亮,”他嘴里咕噜着,“还有奥立弗,哈哈哈!还有奥立弗——整个是一位上等人了——整个是——把那小子带去睡觉。”
狱警拉起奥立弗空着的那只手,低声嘱咐他不要惊慌,自己一言不发地在一旁静观。
“带他睡觉去!”费金高声嚷道,“你们听见没有,你们几个?他就是——就是——所有这些事情的起因。花钱把他养大还真值得——割断波尔特的喉咙,比尔。别理那丫头——波尔特的脖子你尽量往深里割。干脆把他脑袋锯下来。”
“费金。”狱警开口了。
“在!”顷刻间,老犹太又恢复了受审时那副凝神谛听的姿势,大声说道,“我年纪大了,大人,一个很老的老头儿。”
“喂,”狱警把手搁在费金胸口上,要他坐着别动,说道,“有人来看你,恐怕要问你几个问题。费金,费金。你是人不是?”
“我就要永世不作人了,”他抬起头来回答,脸上看不到一点人类的表情,唯有愤怒和恐惧,“把他们全都揍死。他们有什么权利宰我?”
说话间,他一眼看见了奥立弗与布朗罗先生。他退缩到石凳上最远的角落,一边问他们上这儿来想要知道什么。
“别着急,”狱警仍旧按住他说道,“请吧,先生,你想说什么就告诉他好了。请快一点,时间越往后拖,他情况越糟糕。”
“你手头有几份文件,”布朗罗先生上前说道,“是一个叫孟可司的人为了保险交给你的。”
“这完全是胡说八道,”费金回答,“我没有文件——一份也没有。”
“看在上帝的分上,”布朗罗先生严肃地说,“眼下就别说那个了,死亡正在步步迈逼,还是告诉我文件在什么地方。你知道赛克斯已经送了命,孟可司也招认了,别指望再捞到点什么,那些文件在哪儿?”
“奥立弗,”费金挥了挥手,嚷嚷着,“过来,这儿来。让我小声告诉你。”
“我不怕。”奥立弗松开布朗罗先生的手,低声说了一句。
“文件,”费金将奥立弗拉到身边,说道,“放在一个帆布包里,在烟囱上边一点点,那儿有个窟窿,就是最前边那间屋子。我想和你聊聊,亲爱的。我想和你聊聊。”
“好的,好的,”奥立弗答道,“我来念一段祷告。来吧。我念一段祷告。只念一段,你跪在我身边,我们可以一直聊到早晨。”
“我们到外头去,到外头去,”费金推着孩子往门口走去,眼睛越过他的头顶视而不见地张望着,答道,“就说我已经睡觉了——他们会相信你的。只要你答应我,准能把我弄出去。快呀,快!”
“噢!上帝保佑这个不幸的人吧!”奥立弗放声大哭起来。
“好咧,好咧,”费金说道,“这样对我们有好处。这道门顶要紧。经过绞刑架的时候,我要是摇摇晃晃,浑身哆嗦,你别介意,赶紧走就是了。快,快,快!”
“先生,您没别的事情问他了吧?”狱警问道。
“没有别的问题了,”布朗罗先生回答,“我本来以为能够促使他看清自己的处境——”
“事情无可挽回了,先生,”狱警摇摇头,口答,“您最好别管他。”
牢门开了,两名看守回来了。
“快啊,快啊,”费金嚷嚷着,“轻轻地,也别那么慢啊。快一点,快一点!”
几个人伸手按住他,帮助奥立弗挣脱了他的手,将他拉回去。费金拼命挣扎了一下,随即便一声接一声地嚎叫起来,叫声甚而透过了那些厚厚实实的牢门,直至他们来到大院里,仍在他们的耳边鸣响。
他们还要过一会儿才离开监狱。目睹了这样一个可怕的场面,奥立弗险些晕过去。他是如此衰弱,足有一个小时连步子都迈不开。
当他们走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一大群人早已聚集起来。一家家户户的窗日上挤满了人,抽烟的抽烟,玩牌的玩牌,消磨着时间;人们推来拥去,争吵说笑。一切都显得生气勃勃,唯有在这一切中间的一堆黑黝黝的东西除外——黑色的台子,十字横木,绞索,以及所有那些可怕的死刑器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