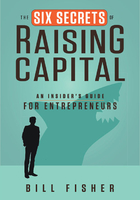如前所述,尽管我认为能否对思潮性的重大文学现象及时地作出重要发言,是衡估一个批评家量级的重要准绳,而且雷达也已在这方面屡屡成功地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但是,相比较而言,以我的私心论,我更喜欢的却是他那些对于单篇的主要是长篇小说所作出的洋洋洒洒的长文。譬如《历史的灵魂与灵魂的历史——论红高粱系列小说的艺术独创性》;《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论》;《心灵的挣扎——〈废都〉辨析与批判》;《民族心史的一块厚重碑石——论〈古船〉》;《历史的人与人的历史——〈少年天子〉沉思录》等等。在这些文章中,往往更能见出雷达的本真性情和个性光彩。据说刘再复先生当年曾为雷达作过一个未及刊布的序言,题目就叫《理性的激情》,文章我们暂已无缘读到,但仅从题目推敲,刘氏肯定他的理性思辨能力,似乎还更欣赏他的激情魅力(“理性”是“激情”的修饰与限定词)。这一点与伯勇先生指出的“他属于情感情绪型的评论家,但又不缺少相当的理论深度”的看法可谓灵犀相通,所见略同罢。当然,理性与激情二者在雷达身上不能截然分开,恰恰相反,它们结合得很好,水乳交融,相得益彰。只是在我个人感觉中,它们仍然有倚重倚轻之区分,常常的情形是,酣烈的情感和眩目的文采掩盖了理性的光芒。
我这样说,丝毫不意味着轻视这些文章的思想深度或拆解它们的理论框架,如果这样的话,它们将难以独立,或者变成一些闪光的片断,或者变成一堆语言的散珠。事实上,理性的钻探对它们的统摄是深刻有力和显而易见的。譬如评“红高粱系列”就是在“主体论”光照下从容展开的;又譬如《古船》论和《白鹿原》论就是“民族灵魂发现与重铸论”的实证分析与理论深化;再譬如《(少年天子)沉思录》其着眼点也不仅止于一部作品,而是关涉到历史题材长篇创作中诸如“史家眼光与历史小说家眼光的异同”、“历史小说家在面对历史创造人物时,是侧重于强调历史作为一种自然客观进程,从而让人服务于规律,还是侧重于把历史看做人的有目的有意识的创造,从而突出人的选择”、“人与历史运动的深刻联系和交互作用”等若干带有普泛性问题的辩证与探讨。如此种种,都说明雷达是一个由自成一家之说的理论系统武装起来的强大批评主体,它可以涵盖和超越一般的批评对象,它和强大的批评对象也能相抗衡、相较量。甚至是批评对象的质量愈庞大,就愈能激发起他与之搏击和交锋的欲望与热情。因此之故,他往往面对那些杰出厚重的长篇之作表现出了最佳的竞技状态和爆发力,也最容易进入他所向往的“主客体交相感应的浑一境界”。尤其是当批评对象和他个人的人生与文化背景贴得越近,他的批评主体也就被滋养被刺激得越强壮雄健。譬如孕育诞生于关中大地的《白鹿原》,就使得他如鱼在水,如云在天,忽而神游其里,忽而超拔其外,相互进入撞击而出的思想火花和心灵激流闪闪烁烁,滔滔滚滚,以一种凝重沉郁的情感基调和斑斓顿挫的语言旋律将人震慑和打动。而我,也许是弱于理性思辨的缘故,总是首先被这种磅礴沛然的精气神所魅惑,所牵引,在滞重而又愉悦的审美阅读中细细领会与呼吸弥漫其间的思想和理论气息。质言之,雷达最大的本领就是用激情去燃烧他的思想,使之云蒸霞蔚成一片灿烂的光华,将他的读者照耀与引领。写到这里,我觉得与其如此饶舌费神,还不如让雷达直面我们来得干脆。请看《〈白鹿原〉论》的开篇——
我从未像读《白鹿原》这样强烈地体验到静与动、稳与乱、空间与时间这些截然对立的因素被浑然地扭结在一起所形成的巨大而奇异的魅力。古老的白鹿原静静地伫立在关中大地上,它已伫立了数千载,我仿佛一个游子在夕阳下来到它的身旁眺望,除了炊烟袅袅,犬吠几声,周遭一片安详。夏雨,冬雪,春种,秋收,传宗接代,敬天祭祖,宗祠里缭绕着仁义的香火,村巷里弥漫着古朴的乡风,这情调多么像吱呀呀缓缓转动的水磨,沉重而且悠久。可是,突然间,一只掀天揭地的手乐队指挥似的奋力一挥,这块土地上所有的生灵就全都动了起来,呼号、挣扎、冲突;碰撞、交叉、起落,诉不尽的恩恩怨怨、死死生生,整个白鹿原有如一鼎沸锅。在从清末民元到建国之初的半个世纪里,一阵阵飓风掠过了白鹿原的上空,而每一次的变动,都震荡着它的内在结构:打乱了再恢复,恢复了再打乱。在这里,人物的命运是纵线,百回千转,社会历史的演进是横面,愈拓愈宽,传统文化的兴衰则是精神主体,大厦将倾,于是,人、社会历史、文化精神三者之间相互激荡,相互作用,共同推进了作品的时空,我们眼前便铺开了一轴恢宏的、动态的、纵深感很强的关于我们民族灵魂的现实主义的画卷。
这既是一种感性的描述,也是一种理性的概括,但它又以散文的面目呈现,同时还充满着张承志小说式的炽烈而凝重的语言热度和力度。何况这仅仅还只是个开头,好戏还在后面。更多更深入的举例分析既无篇幅也无必要,所谓窥一斑可见全豹是也。正是由于情、理、文的交相辉映,才使雷达对《白鹿原》、《古船》、《废都》等作品的批评成为了近年来长篇小说评论的扛鼎之作,它们相互发明与印证,都堪可视为长篇小说创作与理论研究的宝贵收获。
四
说到《废都》,我觉得有必要再简单谈谈雷达专门为它写下的《心灵的挣扎——〈废都〉辨析与批判》。由于《废都》的原因,这篇文章也许没有引起多少关注和反响,但我认为,这是雷达的一篇用心之作,它体现了雷达对文学事业认真负责的精神,对作家才华的爱惜之心,以及不随波逐流的独立品格和坚持实事求是的严肃态度。
现在来谈《废都》,似乎有点不合时宜,而且我本人也缺乏对它的深入研究。但是,我凭直觉敢斗胆妄言一句:如果要说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坛有所谓“奇书”的话,那么,一部是张承志的《心灵史》,一部就是贾平凹的《废都》。这不仅因为他们两位都是当代的重要作家,也不仅因为他们自己对这两部作品的态度——前者一度将《心灵史》视为自己“惟一的真正的大书”、一部“绝笔之作”;后者则将《废都》看做“惟一能安妥自己灵魂的书”,而确实是因为这两部作品自身的复杂形态。虽然它们内容有别,风貌迥异,遭际不同——张作是先冷后热,贾作是先热后冷等等,但有一点却惊人地相似:那就是它们的奇异、突兀、叛逆和不羁所带给人们的普遍的愕然、惊怪的反应,以及灵魂和肉体的强烈的震悚与刺激,尽管关于它们的或激赏或痛责的言论已经连篇累牍和充塞视听了,但我认为,该说的话还远远没有说完,两位奇人两部奇书给当代文坛丢下了两个不易索解的“谜”,两个暂时还难以深究和充分展开的话题,也许长期下去湮没无闻,也许或一朝醒来又重新拾起。这里亦暂且按下不表。
回头再接着说雷达与《废都》。
面对“《废都》热”——阅读热与狙击热,雷达却是冷静的,他没有一哄而上凑热闹,更没有简单地“捧”或“棒”,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批评家,他也没有视而不见绕道而走。他的选择是坐下来细读文本,潜心研究题旨正误,着意考察人的蕴含,和作家平等对话,爱其才华,惜其偏颇,情辞恳切地进行抉幽发微和鞭辟人里的辨析与批判。他认为——“庄之蝶的所作所为,实在不足为训,与许多并非不存在的意志坚韧的、信念坚定的献身者和殉道者型的知识分子相比,庄之蝶显得多么赢弱和可怜”。“但是,即便如此,庄之蝶的苦闷和颓废,仍不无深意。”“庄之蝶精神状态的总特征,正可以‘泼烦’喻之。这‘泼烦’包含三层内容,一是社会性烦恼,二是生存性烦恼,三是形而上的烦恼,而核心问题在于,不断丧失本真性悲哀”。“庄之蝶的沉溺女色,一是为了逃避现实,二是为了拯救灵魂,三是为了安全感,四是觉得轻松”。同时,他又溯源而上地指出,庄之蝶的“家谱源远流长,他的血管里至今滞留着诸如元稹、李煜、柳永、李渔、冒辟疆、沈三白们的血液……他也就成了这个家族的末代飘零子弟。”至于作家以玩赏态度津津乐道于感官刺激,“那就是拿肉麻当有趣,视腐朽为圭臬,丧失了起码的美感和道德感”。这样缜密和有深度的分析是容易让人信服的。尤为难能可贵之处还在于,当某种意见成为一种倾向一边倒时,人们往往不免忽略“倾向”以外的东西,而雷达之眼却疏而不漏。他在比较研究了《西厢记》、《金瓶梅》、《九尾龟》等作品之后,还注意到“在小说的叙事形态和风格类型上,《废都》与我国古典小说确有极密切的血缘关系,它不止在表达方式上,语感和语境上,而且是在内在神髓上,美学精神上,完成了令人惊叹的创造性转化”。进而大胆肯定:“作者把古典小说中有生命力的东西与当代生活巧妙化合,把叙事艺术提到了一个新高度。”虽然这种断语尚可商榷,但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惟“倾向”马首是瞻的治学态度,却表现了一个严肃批评家的胆识与品格。惟其如此,该文才在一大堆《废都》论中显示出它的独特存在与价值。
其实,当年我也写过一篇题为《“废都”还是废镇》的小文,除了“性描写”的问题之外,还谈到了该作的其它一些“硬伤”——诸如结构问题,唱民谣的老头与“哲学牛”两条副线与故事主线之间显得游离;又如语言问题,写得过于流畅,放纵而缺乏节制;有“拉稀”之嫌;再如作品的“气象”问题,由于作家人生和人文背景的局限,处处泄漏出“小”来,屑碎乃至委琐,而无大家之气宇。如此等等。但是,我也同时指出,贾平凹是当下在中国传统士文化中浸泡得最深而又最具有创作活力和才华的一位中年作家,他既得“士文化”之滋润亦受其侵蚀,一颗多情而痛苦、敏感而脆弱的心灵在时代剧变中所发出的呻吟、泣诉与呼号,也就郁结成了一部《废都》,而《废都》则成了中国士文化的挽歌(如《红楼梦》等)在二十世纪末的最后一声回响。它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研究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化转型期传统文人(士)心灵裂变的经典文本。这就是《废都》的全部意义,也是贾平凹的贡献所在。从此一角度看,我与雷达的见解颇有暗合之处——雷达在他长文的最后结论道:
《废都》是一部这样的作品:它生成在二十世纪末中国的一座文化古城,它沿袭本民族特有的美学风格,描写了古老文化精神在现代生活中的消沉,展现了由“士”演变而来的中国某些知识分子在文化交错的特定时空中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透过知识分子的精神矛盾来探索人的生存价值和终极关怀,原是本世纪许多大作家反复吟诵的主题,在这一点上,《废都》与这一世界性文学现象有所沟通。但《度都》是以性为透视焦点的,它试图从这最隐秘的生存层面切入,暴露一个病态而痛苦的真实灵魂,让人看到,知识分子一旦放弃了使命和信仰,将是多么可怕,多么凄凉;同时,透过这灵魂,又可看到某些浮靡和物化的世相。
五
纵观起来,我们清晰地望见,雷达随着新时期文学的启动而启动,随着当代文学运动的深入推进而升高旋转,以极大的热情和能量关注着小说创作的飞跃、转变与沉浮,以尽可能广阔的覆盖面扫瞄一批批重要作家和作品,为他们加油、喝彩、导引、校正、提醒或警策。十余年来,在一浪赶一浪的域外文艺思潮的汹涌澎湃和起落消长中,他始终保持了比较清醒的头脑,一方面采取“拿来主义”,不封闭、不拒外,尽努力地对理论背景和批评武器进行更新与改良;另一方面却更坚信“只是袭用别人形式的皮毛,作为过程不可避免,但不可能真正走向世界”。因而牢牢地把根基扎在本土之中,紧紧维系和传统文化、民族精神与社会运动的深刻连结,注意从当代文学实践中发现、提升和构筑自己的理论框架,运用从本土从自身生长出来的智慧、思想以及从传统中创化出来的富有个性的批评话语系统参与当代文学的建设进程。这是雷达的特色之所在,也是他的成功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