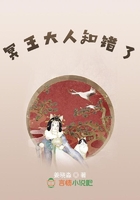“噢,想想有一天我居然没有可以说话的倾诉对象!”
就在那时,一名女子从路口拐角处闯入了她的眼帘。她是陌生来客,同是农村妇女的她挎着一大捆报纸和一只沉重无比的手提袋。邓利维夫人走出花园来到门口,一直等到陌生人走上前停下来询问事情。
“安·伯根是住这儿的不?”
“不是的。”房子的女主人恭敬地回答道。
“我想也是,你知道她住哪儿不?”
“不知道。”邓利维夫人回答道。
“我也是,没事,我会找到她的。今天天气不错,夫人。”
邓利维夫人根本连陌生人也不想放过。她一直注视着她沿着小山而下走向桥边,然后才转身回了屋里。她坐在紧挨康纳利夫人家的窗子边,完全沉浸在了自己的世界里。旅客来到门前时,熨斗生戛然而止,而且再也没有响起过。康纳利夫人走到门口,她印花裙子的下摆、她凹凸不平的围裙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从她这边正好看不到陌生旅客。她甚至跑到了门口,这是她这么多星期以来第一次怀着友善的意图打量邻居的宅子。然后她又来到了边窗前坐下。邓利维夫人的心脏开始激动得砰砰直跳。
“由于她愚蠢的行为带来的厄运,她过会想过来的时候我不能对她太冷淡。”邓利维夫人说着,抓起一片缝纫布耐心地检查着。“不管怎样,我不认识什么安·伯根,也许她认识,她在这里住过的时间比我多五、六年。也许她认得那人的长相,已经迫不及待想知道她从我这里打听点什么了。她可以就坐在那里,然后任由熨斗慢慢变凉!
“我第一次来这儿时,磨坊下边曾住着伯根一家,是弗莱厄蒂那家的邻居。”邓利维夫人继续愤愤而谈,“比迪·康利应该认识弗莱厄蒂一家,因为她们是远亲。那是个大嗓门的女人。当然比迪也完全可以听到她在问我事,并且可以走出家门,说自己知道安·伯根这个人,以此抚慰这个满镇子狂找的可怜陌生人。不,我认识的人里没有叫安·伯根的,所以我才不那么干。”邓利维夫人提高了嗓门,“我连个能问路的人都没,那些本是我邻居的人们都闭口不谈,在我被冒犯时积怨的反而是他们。”
“是我自己撞到鼻子的。”康纳利夫人出人意料地接过话题。她径直望向窗边,蓝色纱帐后面坐着邓利维夫人。她们同时意识无疑是康纳利夫人拉开了和平的序幕。
“刚刚经过这儿的女人说话很有礼貌。”邓利维夫人说道,她全然不提吵架的事情,对目前饶有兴趣的话题开门见山,“今天是安·伯根倒霉的一天。她应该很快就会发现事实。”
“安·伯根一家过去是曾住在这里,然后,上帝的旨意让她们走了!有两个安·伯根,是一对母女,我第一次来这儿时她们住在弗莱厄特一家下沿。她们也在同一年离世了。最久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布里奇特·康纳利用最友好的语气说道。
“她最先应该会去弗莱厄特家,然而十二年前他们全搬去了劳伦斯,她从任何人那里打听来的只会是废址。那里一度知道安·伯根的人很多。那个女人我很久很久以前见过一次,但名字想不起来。她有没有自报家门?”她的友邻问道。
“没有,我也为这个可怜人感到遗憾。”邓利维夫人同样友善地接过话题,“她一脸对这次美好拜访和朋友相见的期待,她还拖着一大堆行李。她看上去好像最近刚刚出门,衣着得体却有些过时。如果她愿意停下了歇歇,我会沏一杯茶给她,但是她充满干劲地走掉了。”
“我不清楚,但我下午要戴上遮阳帽去找她。”比迪·康纳利以主人的姿态热情地说道,“我以前见过她,也许是很久以前在家的时候。”
“我也考虑过这么做,”邓利维夫人赞成道,“也许我们最好是等她回来,现在没火车,要到三点才有,她可以在这里待到五点,然后我们可以了解她的所有情况。不管她是谁,今天对她来说会是孤寂的一日。看到那只吭我怒放鲜花的最好部分的老羊么?”她激动地问道,生怕她们的对话随时会无疾而终,但康纳利夫人无视了这么琐碎的小事。
“我的甜瓜都熟了,”她满足地说,“有一颗大的需要现在就分着吃掉,放在地窖下面冷藏着,我下楼拿去。是我吃早饭前摘的,瓜自己已经裂开了。它那么喜欢吃甜瓜,我不放心没人看管它。来吧,玛丽,你会帮我的吧?”
“我当然会。”邓利维夫人说,她把脸凑近纱帐。“那些老的南瓜藤已经长得不太好了,你看到有一根已经有攀上栅栏大开花朵的架势吗?经过一场大雨的浇灌,它们都枯萎了。我再也不会自说自话就种这些大家伙了,它们把卷心菜的精华都吸尽了。”
III.
那个下午,这对和好如初的友人一边齐坐在客厅里,一边留神着路边。她们之间有说不完的话,一切都是那么和睦,再沉湎于过去这段互相疏远的往事未免太得不偿失了。甜瓜吃到一半的时候,早上来访的陌生人又带着一大捆没开封的报纸和沉重的手提袋往山上走来。她的脸上写满了倦意和失落,两位夫人都上前招呼她并请她进来坐坐,她的确是康纳利夫人的旧知,她一道加入了她们吃喝的行列。
“是的,我最后一次在那儿出现是十七年前的事,”她解释道,“我在劳伦斯工作,我过来和霍诺拉·弗莱厄蒂生活了两星期,然后我回到家乡照顾我年老的母亲,她当时已经九十多了。没有什么能再让我留下的事了,并且我回美国后一直很思乡,所以我又回去了,但我的老朋友和老邻居们都搬走了。这是我第一次受到别人的邀请。太美好了,我去行李箱里把围裙拿出来,康利夫人,请别见怪,你和弗莱厄蒂家的人太详细了,果然是亲戚。有善良的邻居作伴是好事情。你和邓利维夫人住得那么近真是太好了。”
“好吧夫人,我们有时候确实会出口成粗。”邓利维夫人承认这点。“但这么多年来我们都是和睦相处的邻居。朋友之间的吵架算不上吵架,所以我们之间拌嘴也算不了什么,不是吗?”
“大多数争吵都是相似的。”陌生人说道,不喜欢吃甜瓜的她却接受了一杯热茶的款待。“当然,吵架时一个巴掌拍不响,而且要从一方开始终结。这是我母亲经常对我说的,她一生中从不对他人出言不逊。”
“瓜好甜。”这是邓利维夫人第七次说这句话了。“当然,我明年还会撒几颗种子,我愚蠢的自尊心下种得的南瓜一点也不好。也许这块地不适合种南瓜,不过谢天谢地,我的卷心菜遍地都是,你可以挑最好的采摘,康利夫人。”
“不管是甜瓜还是卷心菜,朋友之间的东西哪会有什么麻烦呢?”康利夫人潇洒地作答,长久以来积攒的恩怨永远地烟消云散了。
但是那位陌生人还全然不知是自己带来了和平,她完全不明白为什么布里奇特···康纳利坚持要她留下来过夜并叙叙旧话,为什么这两个女人在那个晚上戴上遮阳帽和她手挽手地漫步整个小镇。当她们走过大桥时,互相羞愧地对望了一眼,随后开怀大笑。
“周日独自穿过人群时是我错过了最重要的东西。”玛丽·邓利维承认这点。“在这里没有其他人看到我们真是太好了,我是认真的。”
“曾经是我们自己在桥上吵架,现在我们可以用笑容去看开它了。”康纳利夫人和蔼地对陌生人解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