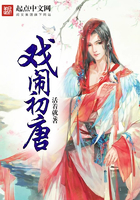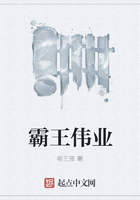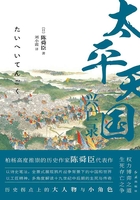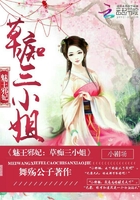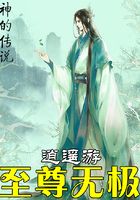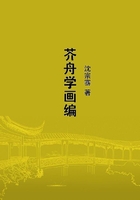半个世纪前,俞平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回顾与前瞻》,谈到作为当事人,“每逢‘五四’,北京大学的同学们总来要我写点纪念文字,但我往往推托着、延宕着不写”。之所以如此“矜持”,表面的理由是作为“一名马前小卒,实在不配谈这光荣的故事”;可实际上,让他深感不安的是,关于“五四”的纪念活动,很大程度上已经蜕变成为“例行公事”。
从1920年5月4日《晨报》组织专版纪念文章起,谈论“五四”,起码在北京大学里,是“时尚”,也是必不可少的“仪式”。如此年复一年的“纪念”,对于传播“五四”运动的声名,固然大有好处;可反过来,又容易使原本生气淋漓的“五四”,简化成一句激动人心、简单明了的口号。这可是诗人俞平伯所不愿意看到的,于是,有了如下感慨:
在这古城的大学里,虽亦年年纪念“五四”,但很像官样文章,有些朋友逐渐冷却了当时的热情,老实说,我也不免如此。甚至于有时候并不能公开热烈地纪念它。新来的同学们对这佳节,想一例感到欣悦和怀慕罢,但既不曾身历其境,总不太亲切,亦是难免的。俞平伯:《回顾与前瞻》,《人民日报》1949年5月4日。
出于对新政权的体认,俞平伯终于改变初衷,开口述说起“五四”来,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几十年间,忠实于自己的感觉,拒绝随波逐流,基本上不使用大话、空话、套话,使得俞先生之谈论“五四”,始终卓然独立。读读分别撰于1959和1979年的《五四忆往》、《“五四”六十周年忆往事》,你会对文章的“情调”印象格外深刻,因其与同时代诸多“政治正确”的“宏文”味道迥异。
有趣的是,用如此笔墨谈论“五四”的,不只俞氏一人;以下所列十位当事人的回忆文章,大都有此倾向,只是作者的“兴致”与“才气”不一定像俞先生那么高而已。
杨振声(1890—1956)北京大学学生
《五四与新文学》,《五四卅周年纪念专辑》,上海:新华书店,1949年;
*《从文化观点上回首五四》,《观察》第6卷13期,1950年5月;
*《回忆五四》,《人民文学》1954年5月号。
孙伏园(1894—1966)北京大学学生
*《五四运动中的鲁迅先生》,《中国青年》1953年9期;
*《回忆“五四”当年》,《人民文学》1954年5月号。
王统照(1897—1957)中国大学学生
《“五四”之日》,《民言报》1947年5月4日;
*《三十五年前的五月四日》,《人民文学》1954年5月号。
许钦文(1897—1984)北京大学偷听生
*《五四时期的学生生活》,《文艺报》1959年8期;
*《忆沙滩》,《文汇报》1959年5月4日;
*《鲁迅在五四时期》,《人民文学》1979年5期。
郑振铎(1898—1958)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学生
*《前事不忘——记五四运动》,《中学生》1946年5月号;
《五四运动的意义》,《民主周刊》29期,1946年5月;
《“人”的发现——为纪念“五四”作》,《新民晚报》1948年5月4日;
*《记瞿秋白早年的二三事》,《新观察》1955年12期,6月16日。
周予同(1898—1981)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
《五四的前夕——悼互生兄》,载1933年出版的《追悼匡互生先生专号》,另见《五四运动与北京高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
*《五四和六三》,《解放日报》1959年5月4日;
*《五四回忆片断》,《展望》1959年17期(1979年所撰《火烧赵家楼》,大致同此)。
闻一多(1899—1946)清华学堂学生
《五四历史座谈》,《大路》第5号,1944年;
《“五四”运动的历史法则》,《民主周刊》1卷20期,1945年5月10日;
《“五四”断想》,西南联大“悠悠体育会”《五四纪念特刊》,1945年5月。
俞平伯(1900—1990)北京大学学生
《回顾与前瞻》,《人民日报》1949年5月4日;
*《五四忆往——谈〈诗〉杂志》,《文学知识》1959年5月;
《“五四”六十周年忆往事》(十首),《文汇报》1979年5月4日。
冰心(1900—1999)北京协和女子大学学生
*《回忆“五四”》,《人民文学》1959年5月号;
《回忆五四》,《文艺论丛》第八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9月;
《从“五四”到“四五”》,《文艺研究》创刊号,1979年5月。
川岛(1901—1981)北京大学学生
*《少年中国学会》,《北大周刊》1950年5月4日;
*《五四回忆》,《文艺报》1959年8期;
*《五四杂忆》,《北京文艺》1959年9期。
(有 * 号者,已收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五四运动回忆录》及其“续编”,其中不少文章被编者删节或改题)
“五四”运动值得纪念,这点毫无疑义;问题在于,采取何种方式更有效。大致说来,有三种策略可供选择。第一,“发扬光大”——如此立说,唱主角的必定是政治家,且着眼于现实需求;第二,“诠释历史”——那是学者的立场,主要面向过去,注重抽象的学理;第三,“追忆往事”——强调并把玩细节、场景与心境,那只能属于广义的“文人”。无论在政坛还是学界,前两者的声名远比个人化的“追忆”显赫;后者因其无关大局,始终处于边缘,不大为世人所关注。
我之所以特别看重这些个人化的叙述,既基于当事人的精神需求,也着眼后世的知识视野。对于有幸参与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文人来说,关于“五四”的记忆,永远不会被时间所锈蚀,而且很可能成为伴随终身的精神印记。50年代中期,王统照撰文追忆“五四”,称“我现在能够静静地回念三十五年前这一天的经过,自有特殊的兴感。即使是极冷静的回想起来,还不能不跃然欲起”;70年代末,当来客请周予同讲讲他参加“五四”运动的情况时,“他感慨地说:‘老了老了!’激动地哭了,很久才平静下来”参见王统照《三十五年前的五月四日》(《人民文学》1954年5期),云复、侯刚《访周予同先生》(《五四运动与北京高师》182页)。。至于闻一多之拍案而起,与其发表追忆“五四”运动的文章同步;冰心之谈论从“五四”到“四五”,更是预示着其进入80年代以后的政治姿态。可以这么说,早年参加“五四”运动的历史记忆,绝不仅仅是茶余饭后的谈资,更可能随时召唤出青春、理想与激情。
至于俞平伯所说的“不曾身历其境”、虽十分仰慕但“总不太亲切”的后来者,其进入“五四”的最大障碍,不在理念的差异,而在实感的缺失。作为当事人,孙伏园尚且有“五四运动的具体印象,却一年比一年更趋淡忘了”的担忧,从未谋面的后来者,更是难识庐山真面目。借助俞、谢等先辈们琐碎但真切的“追忆”,我们方才得以比较从容地进入“五四”的规定情境。
倘若希望“五四”活在一代代年轻人的记忆中,单靠准确无误的意义阐发显然不够,还必须有真实可感的具体印象。对于希望通过“触摸历史”来“进入五四”的读者来说,俞平伯、冰心等人“琐碎”的回忆文字,很可能是“最佳读物”。
随着冰心老人的去世,我们与“五四”运动的直接联系,基本上已不再存在。三四十年代,活跃在中国政治、学术、文化舞台上的重要人物,大都与“五四”运动有直接间接的关联;五六十年代,“五四”的当事人依然健在,加上新政权的大力提倡,“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家喻户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距离“五四”的规定情境越来越远,更多地将其作为政治/文化符号来表彰或使用,而很少顾及此“血肉之躯”本身的喜怒哀乐。
对过分讲求整齐划一、干净利落的专家论述,我向来不无戒心。引入“私人记忆”,目的是突破固定的理论框架,呈现更加纷纭复杂的“五四”图景,丰富甚至修正史家的想象。而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它更可能提供一种高头讲章所不具备的“现场感”,诱惑你兴趣盎然地进入历史。当然,岁月流逝,几十年后的回忆难保不失真,再加上叙述者自身视角的限制,此类“追忆”,必须与原始报道、档案材料等相参照,方能真正发挥作用。
人们常说“以史为鉴”,似乎谈论“五四”,只是为了今日的现实需求。我怀疑,这种急功近利的研究思路,容易导致用今人的眼光来剪裁历史。阅读八十年来无数关于“五四”的研究著述,感触良多。假如暂时搁置“什么是真正的五四精神”之类严肃的叩问,跟随俞平伯等人的笔墨,轻松自如地进入历史,我敢担保,你会喜欢上“五四”,并进而体贴、拥抱“五四”的。至于如何理解、怎样评判,那得看各人的立场和道行,实在勉强不得。
开列十位当年北京学生的回忆文章(除周予同日后成为学者,余者均为作家;川岛和许钦文“五四”运动爆发半年多后才到北京,但仍能感受到那一时代特殊的精神氛围),目的是让对“五四”真感兴趣的读者,从当事人的眼光来解读那一场不只影响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而且注定成为下个世纪长期谈论的话题以及重要思想资源的伟大事件。
说白了,我的愿望其实很卑微,那便是:让“五四”的图景在年轻人的头脑里变得“鲜活”起来。
§§附记
此章的主体部分,曾以《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为题,发表在台湾首次举办的关于“五四”运动的学术研讨会上(“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政治大学文学院主办,1999年4月24、25日),获得了广泛的好评;1999年4月26日的《联合报》上,更刊出记者江中明撰写的专题报道《陈平原论文重建五四现场》。经过一番修整,此文收入我在台湾出版的《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台北:二鱼文化,2003年)一书。位于高雄的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陈燕女士读后,给我写信,告知我她曾整理其父陈其樵先生1919年5月4日至12日的日记,刊于《传记文学》54卷6期(1989年6月)。此后,陈教授先后惠赠《传记文学》上的《七十年前“五四”参加者的日记——一个当时北京高师学生亲笔留下的见证》,以及陈其樵先生就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系一年级时的日记——《自瞗轩日记》(己未孟春)——的影印件,图三陈其樵《自轩日记》手稿
让我得以印证当初的研究心得。比如,“五四”前一天,作者逛中央公园的印象,便可做拙文中“花开春日”一节的佐证:
下午两句半钟,赴公园,见牡丹花大半已残谢,唯来今雨轩前面,尚有数十株尚未凋残。丹园之西,有数株方盛开。凡盆中所栽者,则唯存绿叶,不着一花。尚忆去年春日,余至公园,所见者皆盆花也。花坞中,奇花异草,芬香扑鼻,小坐其中,颇觉神思清爽。
至于第二天那千余言的“见闻录”,更是我所见到的最为详尽的“五四日记”。现参照日记原稿及陈燕教授的整理本,重新校订,附录于此,以供学界参考。
五日(即五月四日) 晴暖
前日着棉,今日着单,北京气候之不定如此。
今日下午一钟,为外交失败在天安门外开国民大会。
午饭后小睡二句钟,雇车至天安门。见北京大学、法政专门、中国大学及吾校学生均到,数约三千人。余以种痘发烧,不敢十分劳动,拟听演说后便回校。后见演说已完,各校学生人手一旗,将为游街之举;自度体力尚可步行十里,乃向尤君索一白布旗,上书“还我青岛”,同大队前进。
自天安门出发南行,出中华门东折,将穿东交民巷。至美使馆门前,不能前进。举代表四人与美领署说明学生此举之真意。美使馆恐有他虞,未允穿过东交巷。乃由美使馆北行,经长安街、崇文门大街。沿途散布全体学界之通告(另详),并白纸书就“卖国曹汝霖”、“卖国贼章宗祥”之字样。及至赵家楼曹汝霖宅门口,人心愈激昂,大声骂:“卖国贼曹汝霖该死!”“杀曹汝霖!”各校代表复言:到曹贼门首,举将卖国贼旗投掷其宅内以辱之。于是白旗乱飞,且杂以砖石,怒骂之声直冲云霄。
大队过未及半,忽然一时大乱,跌倒者甚多,弃帽丢鞋、碰碎眼镜者不计其数。如此,一时群呼止步,并无危险。此时人心愈愤,乃齐集曹氏之门。时门已坚闭,激烈者乃以石敲门,群呼杀卖国贼!时巡警已满布,但不干涉。有某校学生破街窗而入,开门纳众,于是大群涌入,将曹宅家具陈设捣毁一空。遍寻曹贼不见。旋见一日本人保护一人,有识之者大呼曰:此即卖国贼章宗祥!众怒不可遏,乃饱以老拳。头部已破,腰部亦伤,卒赖日本人保护,由后门送往日华同仁医院。大家四处寻曹汝霖,卒不可得,盖已由后门逃走矣。凡曹之妻妾子女,均放其逃走。众人正肆力捣毁之际,忽见宅内火起。巡警大呼火起,请学生速整队归去。于是大队纷纷散归。有力弱不能走者,巡警乃以武力逮捕(此时巡警已接段、吴等命令,令其相机逮捕)。当场逮去学生卅九人(北大廿三人,高师八人,工专八人)。
余当捣毁正凶时,乃同仲实绕道至墨卿处。当经过曹宅后门时,见巡警数十人持枪守住。至甘雨胡同口,遇墨卿、丹庭二人自市场归。至墨寓小坐,即同仲、丹赴大学公寓。见金、辰湘已早归,正吃饭。余以烧未大好,吃鸡子一个。
饭后,辰湘赴大学开会。墨卿、承庵相继至。辰湘旋归,报告开会情形:蔡孑民到会,言过去之事不必重提,但讨论善后办法,明日请学生安心上课,渠必至警厅保释被捕学生。学生提议:派人到各报馆接洽;派人到警厅安慰学生;联合各校取一致行动;派人到外交协会,请其辅助进行。
今晚,余同承庵相商,均在公寓过夜。墨卿先辞去。钟鸣一下始寝。
今日学生之举动,非原意之所及。一时激起众怒,始破扇而入,打伤贼头。若早有计画如此下手,则前后门同时把住,曹、章两贼恐难逃活命。章贼受伤甚重,性命不甚可保;曹贼虽未被打,想已胆破心惊矣。痛快!痛快!愿其余卖国贼看样!愿天下人从兹警醒!
出人力车费五枚。
§§第二章 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同人杂志“精神之团结”
1919年底,《新青年》为重印前五卷刊登广告,其中有这么一句:“这《新青年》,仿佛可以算得‘中国近五年的思想变迁史’了。不独社员的思想变迁在这里面表现,就是外边人的思想变迁也有一大部在这里面表现。”《〈新青年〉第一、二、三、四、五卷合装本全五册再版》,《新青年》7卷1号,1919年12月。这则广告,应出自《新青年》同人之手,因其与半年前所刊代表群益书社立场的《〈新青年〉自一至五卷再版预约》大不相同,后者只是强调《新青年》乃“提倡新文学,鼓吹新思想,通前到后,一丝不懈,可算近来极有精彩的杂志”《〈新青年〉自一至五卷再版预约》,《新青年》6卷5号,1919年5月。;不若前者之立意高迈,直接从思想史角度切入。
四年后,胡适在其主编的《努力周报》上发表《与高一涵等四位的信》,既是讲述历史,也在表达志向:
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而《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胡适:《与高一涵等四位的信》,《努力周报》75期,1923年10月。
胡适并没解释为何谈论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杂志时,不提读者面很广的《东方杂志》或备受史家推崇的《民报》。我的推测是:可以称得上“创造了”一个时代的杂志,首先必须有明确的政治立场,这样方才可能直接介入并影响时代思潮之走向;其次必须有广泛而且相对固定的读者群;再则必须有较长的生存时间。依此三者衡量,存在时间很长的《东方杂志》与生气淋漓的《民报》,“还算不上”是“代表”并“创造了”一个新时代参见拙文《杂志与时代》,《掬水集》140—142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
十几年后,思想史家郭湛波正式坐实《新青年》同人的自我期待,称“由《新青年》可以看他(指陈独秀——引者按)个人思想的变迁,同时可以看到当时思想界的变迁”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82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据1936年北平人文书店版重印)。。此后,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评述《新青年》,成为学界的主流声音。政治立场迥异的学者,在论述《新青年》的历史意义时,居然能找到不少共同语言——比如同样表彰其对于“民主”与“科学”的提倡等参看彭明《五四运动史》(修订本)第五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第二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周策纵著、周子平等译:《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三章,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微拉·施瓦支著、李国英等译《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第二章,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可作为一代名刊的《新青年》,毕竟不同于个人著述;如何在思想史、文学史、报刊史三者的互动中,理解其工作程序并诠释其文化/文学价值《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北京:三联书店,1978年),《〈新青年〉》章的最后一节专门讨论《新青年》与报刊工作;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一章题为《〈新青年〉及其作者》; 拙文《学问家与舆论家》(《读书》1997年11期)关注《新青年》中的“通信”与“随感”;李宪瑜《〈新青年〉研究》(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0年,未刊)设第五章《栏目与文体》。,则有待进一步深入开掘。
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创刊于1915年9月15日;第二卷起改题《新青年》,杂志面貌日渐清晰。《新青年》第二卷最后一期出版时(1917年2月),陈独秀已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故第三卷起改在北京编辑,出版发行则仍由上海群益书社负责。1920年春,陈独秀因从事实际政治活动而南下,《新青年》随其迁回上海,后又迁至广州,1922年7月出满九卷后休刊。1923至1926年间出现的季刊或不定期出版物《新青年》,乃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不再是新文化人的同人杂志。故谈论作为“五四”新文化“经典文献”的《新青年》,我主张仅限于前九卷。
是否将瞿秋白主编的季刊或不定期出版物《新青年》纳入考察视野,牵涉到对该刊的宗旨、性质、人员构成以及运营方式的理解,将在以下的论述中逐渐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