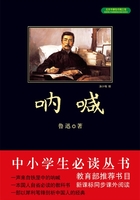侯爵大发脾气,让于连感到非常惊讶。“这个可怜的人,长久以来,在他思想深处珍藏着多少美好的计划,如今竟毁于一旦!但是我应该回答他,我保持沉默会更增加他的怒火。”“我不是一个天使……我尽心尽力为您效劳,您慷慨大方地酬谢我……我非常感激,但是我才二十二岁……在这座府邸里能理解我的思想的只有您和这个可爱的人……”
“魔鬼!”侯爵叫起来,“可爱的!可爱的!您觉得她可爱的一天,就应该离开。”他几乎用尽了所有侮辱性的话语。
“我曾经努力过,当时我要求您让我到南方去。”
被痛苦压倒的侯爵已经极度疲劳,他又一屁股坐在扶手椅上。于连听见他自言自语:“他不是一个坏人。”
“是的,侯爵先生,我不是一个坏人,”于连一边说,一边跪倒在地。
侯爵看到于连的这个动作,他又重新破口大骂,骂的那些话粗鲁难听,简直像是出自一个马车夫的嘴里。也许这些骂人话的新奇能够起到消气的作用。
“怎么,我的女儿将来叫索雷尔太太!怎么,我的女儿将来不是公爵夫人!”每当这两个念头清晰地出现,德·拉莫尔先生就痛苦难熬如同受刑一般,他的情绪就再也无法控制住了。于连担心自己挨打。
侯爵开始渐渐冷静了,而且他也开始对自己的不幸渐渐习惯了,他对于连说了一些相当合情合理的责备话。
“您应该离开,先生,”他对于连说,“您的职责是离开……您是最最卑劣的人……”
于连走到桌子跟前,写下:
很久以来,活着对我来说就是一件难以忍受的事,我决定结束我的一生。我请求侯爵先生在接受我无限感激的表示的同时,也接受我对死在他府邸里可能引起的麻烦的歉意。
“请侯爵先生俯允,屈尊把这张纸看完……然后,请杀死我吧。”于连说,“现在是夜里一点钟,我到花园里,向后墙慢慢走过去。”
“给我滚得远远的,滚到魔鬼那里去吧。”侯爵大叫。
“让他把我杀死,好吧,这是我愿意给他的一个满意的答复……但是,见鬼,我热爱人生……我对我的女人负有责任。”这个念头第一次如此清晰地出现在于连的脑海中,把他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了。
在巴黎,拉莫尔正陷在绝望之中。她七点钟左右见到她的父亲。他让她看于连的信,她担心于连会认为自杀是一件高尚的事。“没有得到我的允许?”她对自己说,感到从愤怒中产生出来的痛苦。
“如果他死了,我也不会活下去,”她对父亲说,“您将对他的死负责……您也许会感到高兴……但是指着他的亡灵起誓,首先我要戴孝,我将公开我的索雷尔寡妇的身份,我要发讣闻,您等着瞧好了……您不会发现我胆怯、懦弱。”
于连骑着马回来了,拉莫尔打发人叫他回来,几乎当着女仆的面儿投入他的怀抱。于连对她的这种感情爆发并不是很感激。他和彼拉神父商量了很长时间以后,变得非常沉着,非常慎重。拉莫尔噙着眼泪告诉他,她看见了他的遗书。
“我的父亲可能改变主意了,请您立刻动身到维尔基埃去,重新骑上马,趁着他们还在吃饭时赶快离开府邸。”
看到于连脸上的惊讶和冷淡的表情没有丝毫改变,她“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让我来应付我们的事。”她把他紧紧搂在怀里,激动地嚷道,“您知道得很清楚,我并不是有意要和您分开。给我来信,寄给我的贴身女仆,信封让别人写,我也会给你写很长很长的信。再见吧!快逃!”
这最后两个字刺伤了于连那男子汉的刚毅的自尊心,不过他还是服从了。
拉莫尔坚决抵制她父亲所有那些所谓的慎重的计划。
她不管怎么说,只肯在以下这些基础上进行协商:她应该是索雷尔太太,跟她丈夫在瑞士过贫困的日子,或者是住在巴黎她父亲的家里。她坚决反对秘密分娩的主意。
“在结婚以后两个月,我跟我丈夫出门旅行,我们把我们的儿子说成是一个适当的日期出生的,这并不难。”
她的这种坚定的态度开始遇到的是大怒,但最后侯爵发生了动摇。
他一时心软了,对女儿说:“这是年金一万法郎的证书,把它送到你的心上人那儿去吧!”
于连深知拉莫尔喜欢发号施令,为了服从她,他毫无必要地赶了四十里的路。他留在维尔基埃,跟佃户们把账目算清。侯爵的让步成了他回来的理由,他去请求彼拉神父收留他,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彼拉神父变成了拉莫尔最有用的同盟者。每一次侯爵问到他,他都向侯爵证明,公开举行婚礼是唯一在自己眼里不是罪恶的办法。“幸好,”神父补充说,“世俗的看法在这一点上是与宗教教义完全一致的。德·拉莫尔小姐性格开朗热情,连她自己都不肯保守的秘密,您能够有一分一秒的时间指望这件事不会为人所知吗?除非您不允许采取公开举行婚礼的这种光明磊落的做法,不然上流社会就会在很长的时间里关心这桩奇怪的门户不当的婚事。应该一下子把什么都说出来,不论表面上,还是实际上,都不留下半点儿神秘的地方。”
“确实如此,”侯爵沉思着说,“如果按照这个办法,三天之后还谈论这桩婚事,就会变成思想贫乏的人的啰唆了,应该抓紧时机悄悄地把事情办了。”
德·拉莫尔先生的两三个密友也跟彼拉神父有着相同的想法。在他们眼里,最大的障碍是德·拉莫尔小姐的果断的性格。然而在听了这么多极好的意见以后,侯爵的那颗心还是无法全然接受放弃他女儿做公爵夫人的希望。
十年来他为了这个心爱女儿的前途所做的那些美梦,如今全付诸东流了……
十年的美梦难道就这样被轻易地摧毁了?侯爵翻来覆去地想,也下不了决心。一个月过去了,协商还没能成功。
于连原以为侯爵的拖拖拉拉后面会有什么深远的打算,但是几个星期后,他开始感到德·拉莫尔先生在这件事情中,还没有任何确定的计划。
德·拉莫尔夫人和全家人都以为于连为了管理田产的事到外省旅行去了。而他躲藏在彼拉神父的住宅里,几乎天天都能见到拉莫尔。她每天早上去和她父亲在一起过上一个小时,但是他们有时候一连几个星期都闭口不谈占据他们全部思想的那件事。
“我没兴趣知道这个人在哪里!”有一天,侯爵对她说,“把这封信交给他。”拉莫尔看这封信:
朗格多克的田产每年收入是两万法郎。我将一万法郎给我的女儿,一万法郎给于连·索雷尔先生。在这之后,我们之间不再有任何关系。
德·拉莫尔侯爵“非常感谢您,亲爱的爸爸。”拉莫尔高兴地说,“我们到埃居荣城堡去定居。听说那里像意大利一样美丽。”。
这次赠予使于连大为惊讶。这笔意外的财产,对一个像他这样贫困的人来说,数目相当可观,而且可以让他实现他成为大人物的野心。至于拉莫尔,她的一切感情都集中在对她的丈夫的崇拜中。出于自尊心,她现在一直把他称为她的丈夫。她的最大的、也是唯一的愿望,就是让她的婚姻得到社会的承认。
拉莫尔能够和她真正爱上了的男人见面的时间是那么少,最后她失去了耐心。
她在情绪很坏的情况下,写了一封信给她父亲:
我和我的丈夫分居马上就要满六个星期了。这足以证明我的耐心——它来自对您的敬重,在下个星期四以前,我将离开父亲的家。您的赠予已经使我们富有,我们将由可敬的彼拉神父主持婚礼。在婚礼举行一小时以后,我们动身去胡格多克,永远不再出现在巴黎,除非有您的命令。但是使我伤心的是,这一切将会被人编成耸人听闻的故事来嘲笑我和您。为了避免它们的发生,我跪在地上恳求您,我的父亲啊!下个星期四,到彼拉先生的教堂来参加我的婚礼吧。
这封信,使得侯爵的那颗心陷入到难以言表的困窘之中。这么说,他必须最后做出一个决定。
拉莫尔的信将他从反复思考中拉出来。他开始考虑怎样杀死于连或者怎样使他消失,想了很久以后,却又想象怎样帮他建立一个辉煌的前程。
“我不得不承认于连有办事能力,有胆量,有才华,”侯爵对自己说,“可是在他性格的深处,我却发现有可怕的东西,这是他给每一个人留下的印象。”
“他对高贵出身并不顶礼膜拜。确实如此,他不是出于本能地尊敬我们……而他呢,又不能忍受别人的轻蔑。”
在女儿来信的催逼下,德·拉莫尔先生知道自己必须做出决定:“总之,最重要的问题是:于连追求我女儿是因为他知道我爱她胜过一切,知道我有十万埃居的年金吗?这是出人意料的真正爱情吗?还是想爬上显赫地位的庸俗欲望?一个性格如此高傲的女孩子会忘掉自己的身份,甚至对他做出露骨的主动接近的表示!……他到底有什么巨大的魅力?”
他决定拖延时间,给女儿写了封信:
千万别再干出新的蠢事来。这儿有一份给于连·索雷尔·德·拉维尔内骑士的轻骑兵中尉的委任状。让他在二十四小时内动身,到他那个团的所在地报到。我希望他遵从命令。拉莫尔的爱情和快乐再也没有止境了。她希望乘胜追击,于是立刻回信:
只有听到您对我许下诺言,下个月我的婚礼在维尔基埃公开举行,我才会把委任状送给德·拉维尔内先生。我请求您不要超过这个期限,因为过了这个期限,您的女儿将不能再在公开场合露面。
回信却出乎意料:
服从吧,否则我就收回一切。我还不了解您的于连是怎样一种人,而您自己并不比我知道得多。让他动身到斯特拉斯堡去,想着走正道。我在半个月之内让您知道我的决定。
这封回信态度如此坚决,让拉莫尔不免吃了一惊。“我不了解于连”这句话使她陷入了沉思。
“如果我不服从他的这个想法,我看很可能会发生一场公开的争吵。事情宣扬出去会降低我在上流社会里的地位,而且很可能使我在于连的眼里变得没有以前那么可爱了。在宣扬出去以后……十年的贫困生活……”
她决定服从,但是没有把父亲的这封信转给于连。他性子火暴,说不定会干出傻事。
晚上,她告诉于连,他已经是轻骑兵中尉。他快乐极了,姓氏的改换使他大感惊讶。
他想:“这完全归功于我一个人。我能够让自己被这个骄傲的家伙爱上。她的父亲不能没有她,而她不能没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