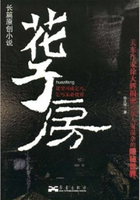自从瓦尔德·朱力知道自己是一个性无能者后,一股火,一股对女人仇视的火便在胸膛里熊熊燃烧起来。他觉得自己仿佛是一匹有文化修养而被骟过的公马,由于自己可耻的懦弱,让海因里希·希姆莱这样虚伪而狡诈的男人进入到自己的家庭,把自己年轻漂亮的妻子偷偷地霸占。而在这种情况下,自己竟然没有冲上前去把门踹开,用那把镀镍的手枪,去打爆他的脑袋。怯懦呀,可耻的怯懦,希姆莱布置安排的家庭氛围包围着他,企图使他溶解在里面,瓦尔德·朱力想粉碎这一切。没有进入的时候渴望进入,进入之后又向往着如何逃脱。
就是这种复杂的情感,使瓦尔德·朱力经常处于莫名的烦躁、嫉妒和悔恨之中。这种烦躁、妒嫉和悔恨只有在一次次杀人的满足之中才能得到平复。当他把那一群群裸体的犹太女囚赶尽毒气室,施放“旋风B”毒气,听到她们在死亡前尖叫时,他心里便油然而生一种快感。当他手握冲锋枪对准欧美、俄罗斯等国家年轻漂亮的女战俘时,他的心便激动地狂跳起来,一种从未有过的愉悦在全身弥漫,快乐荡漾在心间。激烈的枪声之后,望着眼前横七竖八躺在血泊里的女性尸体,他心里没有一丝丝恐惧,反而增添了几分满足和轻松。然而,满足之后,他又陷入更加莫名其妙的烦躁、妒嫉和悔恨之中,如此循环往复,使瓦尔德·朱力这个文化修养很高、知识渊博的党卫队上校军官备受折磨。在这种折磨下,数以万计的犹太人和男女战俘被他杀死。
克拉尔并不完全了解这个心理变态的男人的感受。在瓦尔德·朱力的办公室里,她盯着天蓝色墙壁上画着的两把纳粹军刀托起的那个白森森硕大的骷髅头问:“多恐怖呀,干吗要在墙壁上画一个骷髅头?”瓦尔德·朱力正在整理真皮沙发上的东西,头也不抬地说:“因为我们是党卫队特别旗队,绰号就叫‘骷髅队’。”克拉尔太天真了,以为丈夫心中已消除了对她的积怨,她蹲在地上,抚摸着阿拉伯金丝绒地毯上欧罗巴公主骑着神牛的绣像说:“挂欧罗巴公主骑神牛的地毯多好看呀,为什么要每天去面对一个骷髅头?”
“因为我们每天的任务就是杀人,并把尸体运出去焚化。”瓦尔德·朱力冷冰冰地撂下一句。
克拉尔望着博古架上琳琅满目的文物珍品,禁不住地欣赏起来。
这里有迈锡尼的书板、哥本哈根的陶器、雅典的武士双耳爵、奥地利的铜制殉葬战车、伊特鲁立亚的阿蒂卡盘、君士坦丁钱币、罗马圣阶餐厅的镶嵌画等等。粗略懂一点文物考古知识的克拉尔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天哪,这博古架的任何一件东西都是珍品,每一件都价值连城。短短几年,身在党卫队的丈夫竟变得如此富有。她边欣赏边说:“朱力,亲爱的,你真了不起,这里的收藏是世界之最!”瓦尔德·朱力望了妻子一眼,冷冷地说:“当然,只有从死亡和坟墓里挖掘出来的东西才是真实而有价值的。”
克拉尔知道丈夫对自己和希姆莱之间的一夜之欢仍然心存芥蒂,她走过来,把脸温存地靠在丈夫的背上。忽然怯生生对瓦尔德·朱力说:“要是,要是你觉得不公平,你也跟别的女人睡几次好了……”
“我不像你!”瓦尔德·朱力冷笑了一声,“你是什么男人都可以,我可不是什么女人都行。”
“那你叫我怎么办呢?”克拉尔畏畏缩缩一脸可怜状。
“怎么办?”瓦尔德·朱力冷静地说,“叫希姆莱离婚,娶了你!”
“这怎么可能呢?他是全国党卫队的领袖,他和妻子之间的事情已经让元首骂了几次了。”克拉尔说着眼泪又涌了上来。
“去去去!”瓦尔德·朱力阴阳怪气地说:“你的眼泪只能让海因里希·希姆莱动心,而我看了只会心烦。”
女人双手捂着脸嘤嘤地哭了,这是从心底里哭出来的声音。月亮钻进了云层,屋子里的灯光显得格外明亮。窗外那朦胧的深灰色的光,仿佛是阴间的一片寒气。一对肉体距离很近而心灵距离很远的夫妻,静静地立在坟墓一样的屋里,没有意识,没有理性,没有时间和空间,没有过去和将来,只有搅成一团无法辨别的冷冰冰的感觉。这里已没有情的温度,爱的回味,只有纯而又纯的、由神经的本能所接受的感觉。而这种感觉瞬息万变,可以将人折磨至死!
“好了好了,别哭了,你哭的人心烦。”
“你刚刚说的是气话吧?”眼圈红了的克拉尔小心地问。
“人嘛,”瓦尔德·朱力哼了一声,“总得有气,没有气就只能往焚尸炉里送,那还算什么活人?”
神经在颤动,如一张狂风中的蜘蛛网。她积蓄了足够的勇气说:
“我不是在信中给你说过,过去的事情不再提了吗?”
“过去的事情不提?”瓦尔德·朱力兀地又暴躁起来,风中的蜘蛛网破裂了,“说得轻巧,我现在真懊悔,为什么那天晚上没闯进来用枪把你们两个……”
“你别这样!你别这样!”克拉尔哭着跪在地上。“我该死,是我不好!我不该……”
提起克拉尔的表哥海因里希·希姆莱,瓦尔德·朱力的脾气又暴燥起来:“什么全国党卫队领袖,什么狗屁上将,说的是人话,屙的却是狗屎!满口仁义道德,干的却是不道德的事情。”
“他再怎么也是我的表哥呀!”
“是啊,他确实是你的表哥。他都在柏林天子街12号给你买了房子。”
“没有,没有啊!这纯属造谣!”
“你睡里面套间吧,”瓦尔德·朱力说,“人有时候活着真不如死了好。”
“呜呜……”克拉尔抽泣着说,“你知道,我是爱你的,我迫不得已才和他发生了关系。”
“算啦,算啦,”瓦尔德·朱力不耐烦地打断她的话,“我不听你说,你的那些臭隐私我也懒得去听。”瓦尔德·朱力开始给沙发上铺了一条军用毛毯,打算在沙发上住一宿。
“你,你就住沙发?”克拉尔抹了一下眼泪,怯生生地说,“这样,这样不好吧?”
“有什么不好?睡吧!”瓦尔德·朱力“吧哒”一声关了灯,房间立即黑了下来,黑暗像水一样弥漫过来,让人感到一种恐怖和窒息。
克拉尔“吱呀”一声推开套间卧室的门,又“吧哒”一声打开了套间的壁灯,不开灯不要紧,开灯后,墙壁上悬挂的几张人皮差点没把她吓死。那是几张犹太女人的人皮,都是党卫队军医腊彻尔在扭断了犹太女囚的脖子后,亲手执刀剥下来的。人皮剥得很完整,没有半点破损。那些经过晾晒和药物处理后的人皮挂在墙上,像一个个赤身裸体的活女人一样。克拉尔惊惧地睁大双眼,尖叫一声冲出了卧室。
“怎么啦?”已经躺在沙发上,盖着党卫队黑色真皮大衣的瓦尔德·朱力坐了起来。
“墙上,墙上……”吓得脸色像纸一样白的克拉尔扑进他的怀抱里,结结巴巴地说,“墙上,墙上有人……”
“那是人皮。”瓦尔德·朱力冷笑了两声说,“几张犹太女人的人皮值得大惊小怪么?”
“人皮?”克拉尔瞪大了眼睛,眼前这高大英俊且冷漠的男人,竟然是活剥人皮的刽子手。女人有几分不相信,“你,你竟然敢剥人皮?”
“那有什么,党卫队的老军医腊彻尔经常活剥人皮。”瓦尔德·朱力拍了拍这个令其憎恶的女人的背说,“其实人和动物一样,人能剥老虎皮、狼皮、羊皮、牛皮,就不能剥人皮吗?当你把那些犹太女人和欧罗巴战场的女战俘当动物一样看待时,剥人皮就像剥各种动物皮一样。”
血淋淋、令人发指的行为,却被瓦尔德·朱力说得相当轻松。克拉尔打了一个哆嗦,感到骨头缝里发冷。眼前的男人变成了吃人肉喝人血的魔鬼。她要逃离,要逃离这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屋子,如果自己迷迷糊糊地睡下了,谁知道这个心理变态的男人,会不会半夜手执利刃闯进来,在烦躁和悔恨情绪的驱动下,冷笑着用绳索捆了自己,在鲜血淋漓中一点一点活活剥下自己的人皮?想到这里,几乎被墙上几张人皮吓傻了的克拉尔一把推开瓦尔德·朱力,怪叫一声发疯般逃出了地狱一样的房间。
55.夜半时分,有人在敲门
党卫队军医汉斯·科赫做梦也没有想到,已经与他分手的姑娘伊尔雅·格蕾,会乘坐全国党卫队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将军的军用飞机来到奥斯维辛。心爱的姑娘看完由集中营男女囚犯演奏的音乐晚会枟鸟儿都已经飞来枠后,夜半三更悄悄来到汉斯·科赫的门前,“笃笃笃”,女友的敲门声把在灯下偷偷掩藏绝密文本的他吓得魂飞魄散。
汉斯·科赫掩藏的绝密文本,正是党卫队总部下发给各个集中营的0977密令。自从瓦尔德·朱力上校在整个党卫队军官会议上传达了0977命令后,汉斯·科赫的心里就像燃烧了一团火一样,他想阻止这场以研究俄罗斯战俘头盖骨为名义的屠杀,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代号为0977的绝密文本搞到手,然后通过别的什么渠道让这份骇人听闻的命令公布于世。机会终于来了,当党卫队的大部分官兵去克拉科夫军用机场迎接海因里希·希姆莱将军时,他以为党卫队司令部和集中营司令官鲁道夫·赫斯少将房间消毒的名义,来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党卫队司令部。
然而,党卫队士兵的警惕性非常高,尽管与汉斯·科赫很熟悉,仍然将其挡在门外。那个名叫比尔的大个子党卫队士兵很有礼貌地说:
“对不起,请出示证件。”
身着白大褂,戴着党卫队黑色军官大檐帽身背喷雾药箱的汉斯·科赫军医被挡在门外。他非常生气地说:“你不认识我吗?我是汉斯·科赫军医,要给司令部消毒!”
“对不起,先生,请出示你的证件。”
“你是党卫队三中队的士兵叫比尔,对吧?”
“对不起,先生,请出示你的军官证和通行证!”
“死心眼,教条主义!”
汉斯·科赫见这个经常见面的大个子哨兵执法如山,一点面子都不给,气呼呼地掏出了他的军官证和一张由集中营最高司令官鲁道夫·赫斯少将亲自签发的特别通行证。党卫队士兵仔细地查看后,敬了个纳粹军礼,归还了军官证和特别通行证,让他进入。汉斯·科赫进入司令部大门后,他的心就狂跳起来,主啊,万能的上帝,你认识你的羔羊,你的羔羊也认识你,只有你,唯有你,才能保佑我拿到关于0977的绝密文本。他迅速戴上大口罩,身背喷雾药箱,左手紧握压力曲把,右手握着细长的喷雾管头,“哧哧”地喷着雾状的过氧乙酸消毒液。身子虽然在喷药,汉斯·科赫的心里却想着如何盗走0977绝密文本。也许是过于紧张,乱哄哄的脑袋里却回想起枟圣经枠里枟遭难中的祈祷枠里面的话来:
耶和华啊,求你听我的祷告,容我的呼求达到你面前。我在急难的日子,求你向我侧耳,不要向我掩面,我呼求的日子,求你快快应允我!因为我的年月如烟云消散,我的骨头如火把燃烧,我的心被伤害,如青草枯干,甚至我已忘记吃饭。我如同旷野的鹈鹕,我好像荒原的鸮鸟。我沉睡不醒,像房顶上孤单的麻雀。我的仇敌终日辱骂我,猖狂地指着我诅咒。我吃过炉灰,如同吃饭,我所喝的与眼泪搀杂。这都因你的恼恨和愤怒,你把我提起来,又把我重重地摔下去。我的年月如日影偏斜,我也如青草枯干。唯有你耶和华必存到永远,你可记念的名字也存到万代。你必起来怜恤锡安,因为现在可怜他的时候,日期已经到了。你的仆人原来喜悦他的石头,可怜他的尘土。列国要敬畏耶和华的名,世上诸王都敬畏你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建造了锡安,在他的荣耀里显现。他垂听穷人的祷告,并不藐视他们的祈求。
这必将为后代的人记下,将来受恩的人民要赞美耶和华。因为他从至高的圣庭垂看,耶和华从天上向地下观察,要垂听被囚人的叹息,要释放将要死的人。使人在锡安传扬耶和华的名,顺耶路撒冷传扬赞美的话。我的神啊,不要使我中年去世,你的年岁世世无穷。
不知不觉中,汉斯·科赫已来到二楼鲁道夫·赫斯少将的门前。
怎么办?是用自己偷配的钥匙开门,还是让值勤的警务军官来开,进去以后如何打开保险柜?正当身背喷雾药箱的汉斯·科赫在门外徘徊的时候,一位胳臂上佩戴“卐”字袖章的警务军官走了过来:“先生,请问需要帮忙吗?”汉斯·科赫冷不丁地吓了一跳,急中生智地说:“我要进入少将的办公室消毒,可是,门无法打开,你能帮忙吗?”警务军官说了声“原来是这么回事。”便掏出钥匙拧开少将房间办公室的门。汉斯·科赫“哧哧”地喷洒着消毒液。刺鼻的过氧乙酸味,使那位警务军官退出了房间。警务军官出去后,汉斯·科赫的心又激烈地跳动起来,他迅速地放下药箱,从怀里掏出那本伊尔雅·格蕾送给他的袖珍枟圣经枠,以虔诚的心吻了吻黑绒封面的烫金字母,双手合着枟圣经枠闭上眼睛默默祈祷:“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也许冥冥之中真有神灵帮助,汉斯·科赫进入少将卧室后,惊讶地发现保险柜上插着一串亮晶晶的钥匙。天啊,这不是在做梦吧?汉斯·科赫几乎没费吹灰之力,便打开了保险柜,找到了0977绝密文本,就在他刚刚取出只有两页的绝密文本后,楼道里传来了皮靴踩着楼梯的脚步声和两个男人的问话。
“怎么回事?是谁打开了少将的房间?”
“报告上尉,是党卫队医生汉斯·科赫在给少将房间消毒。”
“糊涂!我不是早就说过,当少将和我都不在的时候,谁也不允许进入这个房间吗?”
“可是,他来消毒……我……”
鲁道夫·赫斯少将的秘书铁瓦托上尉瞪了值勤军官一眼,大步跨进少将的房间。铁瓦托进门后大吃一惊,他拔出手枪,打开机头,警惕地问:“喂,你在干吗?”正蹲在地上佯装检查喷雾药箱的汉斯·科赫早已将绝密文本揣在怀里,因为他背对着门的方向,慢慢地转过身来说:
“上尉,喷雾管的喷头喷不出药来了。”汉斯·科赫要站起来,警惕的铁瓦托握着手枪大声说:“别动,医生,我要检查一下。”铁瓦托说着走了过来,汉斯·科赫的心差点跳了出来。心想,完了,完了!这下彻底完蛋了,如果少将的秘书上前一搜身,一切都完了。在关键时刻,他也握紧了裤子口袋的手枪。然而,铁瓦托进来后仔细地查看了一番,没有发现任何翻动的痕迹后,反锁了少将的保险柜后,把手枪慢慢地装进枪套里,和颜悦色地说:“怎么回事?”汉斯·科赫装着沮丧的样子说:
“喷头坏了。”警惕性很高的铁瓦托狐疑地看了汉斯·科赫一眼,又蹲下身子仔细检查喷雾药箱和细长的喷雾管头,也许是天意,这会儿喷雾管头不知怎么真的喷不出消毒液来。铁瓦托站起来,拍了拍已经弄湿的白手套说:“也许是管子堵了吧,你明天换一个药箱再来!”汉斯·科赫如释重负地吐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