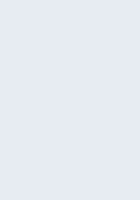浩浩荡荡的车队向奥斯维辛集中营开去。车队武装警戒非常严密,这是瓦尔德·朱力和鲁道夫·赫斯为了保证海因里希·希姆莱将军视察奥斯维辛集中营一路安全而精心布署的。车队前面有20辆武装三轮摩托巡逻开道,每辆摩托车上配备3名党卫队官兵和一挺轻机枪,机枪填满子弹架在摩托车车斗上。摩托车车队后面是十辆满载着党卫队士兵的军用卡车,每辆军用卡车上也配备一挺轻机枪,机枪就架在驾驶室的车顶上,车厢里的所有士兵全部荷枪实弹,军用卡车后面才是海因里希·希姆莱一行的3辆黑色小轿车。将军一行小车的后面还有10辆用以防止波兰游击队从后面偷袭的军用卡车。每辆卡车也照样配备一挺轻机枪和相应数额的党卫队士兵。
炎夏已经过去,秋霜还未降临,波兰南部的山野美丽得像一幅油画。沼泽和洼坑里的水显得异常宁静,在蒲草和芦苇丛中,倒映着蓝天白云的水面仿佛是凝固的晶体。瓦尔德·朱力喜欢骑着那匹枣红马穿过沼泽地。狂奔的马蹄在四周溅起无数银色的水花,水花洒在明镜似的水面,把蔚蓝的天空溅得支离破碎。有时,他放开坐骑,任它在集中营外的草滩上狂奔一阵。然后,猛地一勒马缰,使那匹枣红马扬起前蹄,人立般指向高高的天空。然而今天他只能隔着玻璃窗看沼泽地里如银的水泊和碧绿的蒲草。几只白色的水鸟在远处的沼泽地上空从容地翱翔,对浩浩荡荡的车队视而不见。小车在沼泽地的土道上颠簸,车轮不时溅起一片水花。海因里希·希姆莱平静地问:“朱力,你们党卫队里有一名叫汉斯·科赫的军医吗?”瓦尔德·朱力歪过头看着希姆莱说:“有,将军。”海因里希·希姆莱推了推他的夹鼻近视眼镜又问:“这个人怎么样?”瓦尔德·朱力说:“这个年轻人很好,工作非常刻苦努力,就是性格有点孤僻,不大合群。”希姆莱长吐了一口气说:“这个人不得了啊,他在柏林有很大的政治靠山。”瓦尔德·朱力吃惊地说:“哦,他有很大的靠山,这我倒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么他的靠山是谁呢?”希姆莱神秘地侧望了瓦尔德·朱力一眼,意味深长地说:
“他的靠山就是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元首对他非常器重而且信任,并称赞他是德意志帝国未来的栋梁。”瓦尔德·朱力说:“真没想到啊!”克拉尔双手搂着瓦尔德·朱力的一只臂膀,轻声说:“你想不到的事情还多着呢。”希姆莱接着说:“你注意到同克拉尔一起下火车的那个年轻姑娘没有,她就是汉斯·科赫的女朋友,波罗的海费尔马恩岛的乡村女教师伊尔雅·格蕾。你想想,元首每天有多忙,他要指挥千军万马,不断为日耳曼人拓展生存空间。然而,元首在日理万机的同时,却关注着一个党卫队军医的爱情问题。当元首听说汉斯·科赫为了参加党卫队同女朋友含泪分手的事情后非常恼火,命令戈培尔要‘不惜一切代价,不择一切手段’,让这对有情人重归于好!戈培尔在做通了伊尔雅·格蕾及其家人的思想工作后,让我利用这次来奥斯维辛集中营视察的机会,把格蕾小姐带到波兰,让她与汉斯·科赫破镜重圆。”瓦尔德·朱力听了冷笑道:“破镜重圆?将军你这样做只会适得其反!”希姆莱不解地问:“此话怎讲?”瓦尔德·朱力说:“集中营每天都要把数千名犹太人和男女战俘用毒气杀死,停尸场的尸体堆积如山,焚尸炉浓烟滚滚,难道那个姑娘到集中营后看不见、听不到?如果她知道了我们的集中营是杀人工厂后,她又将如何看待党卫队还有她的男朋友呢?”希姆莱叹息道:“难道元首处心积虑的做法会适得其反?”瓦尔德·朱力冷冷地说:“难说。目前唯一的做法就是把这个姑娘和两名美国战地记者软禁在女看守头目依尔斯·卜莉的住处,杀人和停尸的地方坚决不要让他们去看!”希姆莱感慨道:“看来也只能如此了。让克拉尔住你的房间,有些视察活动她就不要参加了。”克拉尔听了,俏皮地吐了吐舌头。瓦尔德·朱力看到妻子这个表情后,心里像吞了一只红头绿苍蝇。
53.视察集中营
安排伊尔雅·格蕾和两名美国战地记者住下后,海因里希·希姆莱将军一行在集中营的广场上检阅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全体党卫队部队。希姆莱一行站在高高的阅兵台上,司令官鲁道夫·赫斯跑步过来,“叭”地立正,敬了一个纳粹军礼后说:“报告将军,奥斯维辛集中营党卫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希姆莱还礼后,走下阅兵台,在鲁道夫·赫斯等人的陪同下,步行检阅了党卫队。宽阔的广场,站满了黑压压的党卫队方队,所有的中队长、突击队长、突击大队队长、旗队长、区队长、旅队长都站在方队的最前方,所有的党卫队军官都戴着黑色大檐帽,身着黑色的军官礼服,腰扎武装带,挎着手枪;所有的党卫队队员都头戴暗绿色的钢盔,身着黑色的党卫队士兵礼服,手持装了明晃晃枪刺的冲锋枪。希姆莱一边走,一边向大家招手致意,全体党卫队官兵都向这个全国党卫队领袖行注目礼。阅兵仪式结束后,党卫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阅兵分列式。瓦尔德·朱力手持一把闪着寒光的纳粹军刀,他的后面是两名党卫队护旗手和一名旗手。瓦尔德·朱力把纳粹军刀向左边一挥,阅兵台上锐声高叫:“迎战旗!”在雄壮的音乐声中,只见两名护旗士兵迅速端枪,正步走过。旗手“哗啦”一声,将那面白色圆圈里标有黑色“卐”的红色大旗抖开直指前方,同样正步走过阅兵台下。旗手们刚刚走过去,数百人的军官持刀方队走了过来,大家呼着口号,军刀同指一个方向,昂首阔步地正步走过阅兵道。紧接着数千名的举旗方队走了过来,大家高举着数千面红色的纳粹战旗,唱着雄浑有力的枟党卫队进行曲枠,昂首阔步地走过。后面,摩托方队、军卡车方队、装甲车方队、自行火炮方队也一一走过阅兵台。希姆莱检阅了集中营的人员和武器装备后非常高兴,他对鲁道夫·赫斯说:
“要把德国本土上雇来的女看守也武装起来,发给她们相应的武器。”
阅兵式、分列式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结束后,希姆莱一行又在鲁道夫·赫斯、瓦尔德·朱力的陪同下,视察了集中营的3号和4号焚尸场和毒气室。
风袭黄昏,残阳如血,西天的晚霞透过白桦树的阔叶,将斑驳的悲凉铺在林荫道上。不知为什么,这里很寂静。仿佛连空气也是死亡后的寂灭状态。几名负责站岗警戒的党卫队哨兵,也像雕塑一样,悄无声息地肃立着。“啾啾”,“啾啾”几只不知名的小鸟站在白桦树的枝头争相啼叫,给这杀人的地方送来了一种活泼的生命气息。海因里希·希姆莱对焚尸场建在一片树林里很满意。听着鲁道夫·赫斯的介绍,他不停地点头。正是秋季,地上一丛一丛的败叶草上绽放着几朵醉人的红花。希姆莱蹲了下来,拔了一株败叶草。瘦而长的菱形叶片又绿又嫩,挤满枝头。枝叶间绽放着几朵醉人的红花。希姆莱仔细观察着那株败叶草问:“这是什么花?”鲁道夫·赫斯虽然经常从这条道上走过,也看过无数次这种花草,却不知道它的名字,他把目光投向瓦尔德·朱力。瓦尔德·朱力说:“将军,据波兰战俘说这种花名叫败叶草,属于落叶植株,每年秋天开一次花,花蕾有核桃般大小,当一株草上的花蕾全部绽放的时候,败叶草的叶子便会自动落光,只剩下满枝的红花在怒放。败叶草的花期特别长,有30天左右。当花朵开败之后,枝茎上又会重新生长灰绿色的叶子。这种草的生命力特别旺盛,只有在花期才落叶,其余时间都生着那灰绿色的叶子,就是大雪天叶子也不败。”希姆莱听了摇摇头说:“真奇怪,波兰竟然生长这种怪草。明明叶子不败却偏偏起名为败叶草,真是不可思议。”他把那株草递给副官叮咛道:“把这株败叶草保管好,回到柏林后,放进我的植物珍藏册里。”
毒气室里很像淋浴室,室内有莲蓬头和水管,但喷头上不喷细细的水雾,专喷名叫“旋风B”的毒气,毒气室外的窗子和门封得密不透风,犯人一旦进去,3至5分钟就可以致死。半个小时后,尸体就被运往停尸窖,等待焚烧。毒气室外的门口竖着“浴室入口”的牌子,希姆莱看见笑了笑说:“有意思,浴室入口?”鲁道夫·赫斯少将上前介绍道:“这个毒气室可容纳1000人左右。犹太人或者战俘在外边脱下衣服和鞋子后便进去。往往是女人带着孩子先进去,后面是男人,但男人总是少数。然后,把窗子和门都锁上。已经待命的党卫队军医便让‘旋风B’从小天花板上的小窗和莲蓬头流进室内。半个小时后,门被打开,通风机开始运转,直到室内没有一丝毒气。党卫队士兵立刻冲进来,拔下金牙,剪下女人的头发。然后,将尸体从电梯搬到一楼地下室的停尸窖里。这时候,焚尸炉已经点燃,根据尸体大小,最多可以同时塞进3具尸体,火化的时间依尸体的大小而定。”
从毒气室出来,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夕阳的余晖还没有完全消散,如镜的皓月已升上天空。皎洁的月光,雾丝一般泼洒在白桦林和草丛中,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希姆莱一行在鲁道夫·赫斯、瓦尔德·朱力等人的陪同下,步行来到白桦林后面视察停尸场和焚尸炉。快到一座焚尸炉跟前时,海因里希·希姆莱将军的脚下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差点摔倒。希姆莱低头一看,吓得“啊”地一声大叫,差点坐在地上。将军的两名保镖“噌”地护在将军左右。这声惊叫是骇人而凄厉的,在场的党卫队军官全被这声吓人的惊叫吓得哆嗦了一下,有人迅速拔出了手枪。原来,绊倒希姆莱的是一个白森森的骷髅头。那颗骷髅头在淡淡的月光下显得阴森而恐怖,那双黑洞洞的眼窝,那白森森的牙齿,让人看了不寒而栗。见将军受到惊吓,鲁道夫·赫斯怒吼道:“朱力,你们怎么搞的?”瓦尔德·朱力难为情地说:
“这,我们……”他弯下腰,抓起了那颗白森森的骷髅头向路边的草丛扔去。这只骷髅头不偏不倚正好砸在一只在草丛里睡觉的野猫身上。
可怜的野猫在睡梦中被死人头骨砸了一下,吓得“喵”一声箭一般向前面堆积如山的尸骨上逃去。野猫的那声惊叫,又把惊魂未定的希姆莱吓了一跳。他气势汹汹地问:“赫斯,怎么搞的?这集中营里还养猫?”
鲁道夫·赫斯自知理亏,讪笑着说:“没有人养,可能是一只野猫吧。”
那只猫受到惊吓后,“噌噌”几下,蹿到尸骨山的顶上,它虎踞山顶,两只猫眼射出绿莹莹鬼火般的贼光。月光被一朵飘过来的云挡住了,前面只能看见一大堆黑乎乎的东西。那只波斯猫仿佛知道了是谁袭击了它,它蹲踞着,两眼放射出复仇般绿油油的光亮,嘴里“咪噢咪噢”地叫个不停。
海因里希·希姆莱从惊惧中镇定下来,指着前面不远处一大堆黑乎乎的东西问:“那是什么?”见瓦尔德·朱力没有吱声,鲁道夫·赫斯吞吞吐吐地说:“那是,那是……”希姆莱见他们吞吞吐吐,一把从一名党卫队军官手里夺过手电筒,打开开关,一道雪亮的电光向波斯猫蹲踞的地方照去,不照则已,一照让希姆莱又惊得倒抽一口凉气。他看见了大堆的人骨和重重叠叠的没穿衣服的尸体。那些骷髅和白森森的人骨垒起来的尸骨山足有两米多高,那些瞪着黑洞洞眼窝的骷髅头,眦着白森森残缺不齐的牙齿,仿佛要寻找什么人报仇雪恨似的。
那只波斯猫不知什么原因,仿佛也很愤怒似的,一边“咪噢咪噢”地吼叫,一边用两只前爪刨着顶上的尸骨,不断有骷髅头从尸骨山上滚下来。希姆莱看见了这些堆积如山的尸骨,脸色阴沉下来,几乎是声嘶力竭地怒吼:“说!这些尸骨为什么没有焚烧?”瓦尔德·朱力解释道:
“这个月,我们旗队执行了党卫队总部关于根据战争需要对犹太人实行彻底解决的指示,每天进入毒气室的有数千人,这几座焚尸炉完全不够用,地下停尸窖也全部堆满了,所以好多尸骨就只能堆放在野外。”希姆莱暴跳如雷:“蠢货!把这些尸骨暴露在野外,是故意让外国战地记者来拍照吗?元首对我说过,要把奥斯维辛集中营建设成文明而富有人性的集中营,这就是你们的文明和人性?”鲁道夫·赫斯上前解释道:“将军,我们集中营有由囚犯组成的吉祥鸟交响乐队、弦乐四重奏、钢琴音乐晚会和合唱团,这是全世界所有国家集中营所没有的,我们的文明和人性就在这里。”希姆莱的火气仍然没消:“不管怎么样,让尸骨堆积如山是愚蠢透顶的行为。”瓦尔德·朱力说:“我们马上处理这些尸骨。”鲁道夫·赫斯说:“我经常听奥斯维辛集中营吉祥鸟交响乐队的演奏,每次他们演奏舒曼的枟梦幻曲枠时,我都动情地落泪。”
希姆莱沉吟了一下,说:“既然如此,吃过晚饭就看看囚犯演奏的音乐晚会。”由于受了惊吓,希姆莱看了一座地下停尸窖后,就驱车回到集中营的党卫队司令部。
月光从菩提树的树丛斜射下来,在地上落下斑驳的树影。月光如流水一样,静静地泻在一片小苍兰和香石竹的叶子和花上,薄薄的月光浮在夜色苍茫的草丛中。透着肃杀之气的集中营此刻显得温柔起来。
吃过晚饭,海因里希·希姆莱同鲁道夫·赫斯、瓦尔德·朱力等人来到集中营的音乐礼堂,等待“鸟儿都已飞来音乐晚会”的开幕。由于这是展示集中营人性化管理的大好时机,希姆莱让人通知了两名美国男女记者和克拉尔、伊尔雅·格蕾等人,让大家都来观看集中营犯人的音乐晚会。随着绛红色的大幕徐徐开启,身着黑色党卫队军官服的副司令克拉麦走上主席台报告说:“鸟儿都已飞来音乐晚会现在开始。”克拉麦下去后,身着燕尾服、手拿指挥棒的犹太音乐指挥走上台弯腰行礼,台下的党卫队官兵和各个营区的囚犯代表鼓起了雷鸣般的掌声。随着指挥棒轻轻一划,优美、舒缓的音乐渐渐响起,这首由吉祥鸟交响乐队和弦乐四重奏演奏的曲子是枟鸟儿都已飞来枠。优美的音乐把人引入到高山森林的空旷境界。美国战地记者,一边观看节目,一边听希姆莱将军把这杀人的集中营吹得天花乱坠。两名记者坐在两侧飞快地做着记录。伊尔雅·格蕾因为没有见到汉斯·科赫,根本没有心思去聆听天籁般的音乐。瓦尔德·朱力上校冷冷地盯了一眼陶醉在优美音乐声中的克拉尔,嘴角里浮现一个不易察觉的冷笑。
演唱会在台下雷鸣般的掌声中闭幕了。那些身着新鲜光艳服装的男女囚犯从乐队位置上站起来谢幕。
54.名义上的婚姻是一条两头蛇
瓦尔德·朱力对克拉尔的爱情夹缠着许多杂质。既有吸引力,又有排斥力,既有内聚力,又有外张力。既想爱抚她,又想折磨她,既心疼她,又痛恨她。相互矛盾的各种情感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这种名义上的婚姻和事实上的分居背叛是一条恶毒的两头蛇,在慢慢吞噬着瓦尔德·朱力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