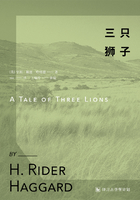此时已是夏天。当他第一次在一封刚到的信上看到他生病儿子的笔迹时,幸福和秘密占有的惊恐从头到脚流贯他的全身——他们现在知道他的居留地,他感到这就像一座巨大的防御工事。他在这里,噢,如今一切人们全都知道,他再也不必解释什么了。草地上一片片白色和紫罗兰色,绿色和棕色。他不是幽灵。翠绿色斜坡上是一片古老针叶林,淡绿色毛针叶毛茸茸的,简直就是一个童话世界。苔藓下可能存在紫罗兰色和白色的水晶。小溪曾经在林子中央从一块石头上流过,让这小溪看上去就像一把大的银压发梳。他不再回复妻子的来信。这个自然界有种种奥秘,其中之一就是所有事物都休戚相关。有一种柔和的、绯红色的花,别的男人的世界里没有这种花,只有他的世界里才有,这是上帝的安排,完全是一个奇迹。身体上有一个部位,它隐藏着,只要他不死,就谁也不可能看到它,只有一个人可以。此刻他觉得这无比美好,非同寻常,且不切实际,只有一种深刻丰富的宗教才会是这样子。这个夏天他把自己隔离起来,随波逐流,现在才认识到,自己做了什么。他在根须绿得发亮的树木之间跪下,伸开双臂,他这辈子还从未这样做过,他心里觉得,仿佛此刻有人将他的自我从他的臂弯里拿走了。他感觉他情人的手在他的手中,她的声音在他的耳中,他身体的各个部位好像刚刚才被触摸过,他觉得自己犹如一个被另一个身体塑成的模子。但是他已经使自己的生命失效了。他的心在情人面前变得谦恭了,像一个乞丐那样贫穷了,誓言和眼泪几乎从他心底涌出。尽管如此,他不会悔改,而说来也奇怪,他的情绪激动竟与一幅森林边上鲜花盛开的草地的画面联系在一起,渴望着未来但仍与这种感觉联系在一起,他将会躺在那儿,躺在风信子、勿忘我、兰花、龙胆和华丽的青灰色酸梅之间死去。他在苔藓旁边伸展开四肢。“怎么把你带过去?”霍莫问自己。他的身体感到特别疲倦,犹如一张僵硬的脸,正在被一丝微笑融解。他曾一直以为自己生活在现实之中,可是一些东西不比这更现实吗:一个人对于他来说,与其他人不大相同。在无数个身体中有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几乎跟他自己的身体一样,支撑着他的内心活动?这个身体的饥饿和疲倦,一听和一看,都与他有关联?当这孩子成长时,就像土地的秘密长进一棵小树那样,长进尘世的忧愁和惬意之中。他爱他的孩子,但当这孩子经历这些之后活下来时,却已经扼杀了现实世界之外的那个部分。一种新的确实无疑的情况突然使他内心无比激动。他不是一个热衷信仰的人,但此刻他的内心被照亮了。在他感情的强光中这些思想像阴暗的蜡烛,光亮却颇为微弱,那只是一个美妙的、青春洋溢的词儿:重新结合。他永远随身带着这些想法,而此刻,就在他沉醉于这一想法时,岁月使情人遭受的小小损伤已从她身上消失,这是永恒的第一个开端。每一种世俗观念,每一种嫌恶和不忠诚的可能性都在沉没,因为没有人会为了一刻钟的轻率而献出永恒,而他则第一次深信不疑地体验到爱情是一种神圣的圣礼。他认识到这是个人的天命,它已经把他引入这孤独之中,他感觉到脚下这片有黄金和宝石的土地根本不再是人世间的宝藏,而是像一个注定属于他的魔幻世界。
从这一天起他摆脱了一个束缚,有如摆脱了一个僵硬的膝盖或一个沉重的背包。摆脱了想活着的束缚,摆脱了对死亡的恐惧。他曾经一直以为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人们如果在身体强健时预见到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就会疯狂地尽情享受生活;可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在他身上,相反他感觉到自己仅仅是不再纠结,感觉自己充满一份美妙的轻快,这份轻松愉快的感觉使他成为自己生存的主宰。
虽然钻探工作无大的进展,但他们整天沉浸在一种淘金者的生活之中。一个小伙子偷喝了葡萄酒,这是侵害公共利益的犯罪行为,大家都同意对他实施惩罚,人们把他双手捆绑着押来了。莫扎特·阿马迪奥·霍芬戈特要将他绑在一棵树上示众一天一夜。但是当工头拿来绳子,寻开心地、狠狠地将他摇来晃去,并暂且吊到一颗钉子上时,小伙子浑身颤抖,满以为自己要被吊死了。每逢马队抵达,驮来补给品的或者拉下山来修养几天的马,就会出现同样的状况,实在难以说明是为什么。它们分组站立在草地上或躺下,似乎毫无规则可言,却又符合某种秘而不宣的审美法则,使人一看就想起塞尔伏特山下那些绿色、蓝色和淡红色的小房子。但是如果它们在高处,夜里每三匹或四匹一起拴在某个山谷中的一棵倒下的树上,当人们凌晨三点踏着月光出发并于四点半从这儿经过,那么它们就会朝人望去,你就会在这空寂的晨曦中觉得自己是一个很缓慢的思维过程中的一个念头。由于偷窃和某些治安事件时有发生,他们买下了四周所有的狗,用来看家护院。巡逻队成群成群地领着它们,两条或三条一组拿绳子牵头,没有颈圈。如此一来,工地上的狗一下子就与人一样多了,于是人们也许会思考,两个群体究竟哪个觉得自己是这块土地的主人,另一个只是被收留的常住客。其中有高贵的猎狗——威尼斯布拉肯猎狗,当地偶尔还有人养这种狗,还有像凶恶的小猴子一样好咬人的看家狗。它们分组站立,它们不知为何聚集到一起,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但它们在每个群体里不时会狂暴地互相撕咬。有些饿得半死,有些拒不进食。一条小白狗在厨子把盛有肉和汤的碗给它递过去时,猛扑上去,咬断了厨子的一根手指头。——凌晨三点半,天已大亮,但还不见太阳。如果此时从马尔根山旁边走过,会看到牛群正半醒半睡地躺在草地上。它们形如暗白色的大石头曲腿躺着,躯体后部朝一侧耷拉着。它们既不看人从一旁走过,也不目送人离去,脸一动不动地对着它们所盼望的光亮,而以同样方式反刍着的嘴则似乎在祈祷。人们迈步穿越它们的圈子时,犹如在穿越一种朦胧、崇高的存在;而如果人们从山上回头望去,它们则看上去就像白晃晃撒落的无声高音谱号,脊椎、后腿和尾巴的线条构成了这些谱号。各式各样的事总在发生。譬如,一个人摔断了腿,两个人抱着他走过;或者突然有人喊“着火了”;还有,修路爆破一块大石头,众人四散奔跑,寻找躲避的场所;一阵雨掠过浇湿了草地。小溪对岸一处灌木丛中间着火了,由于新的事件人们已经忘了这场火灾,而这件事在那时曾是很重要的事。只有一棵幼小的白杨树还在火场旁作为唯一的旁观者。还有一头黑猪被绑在这棵白杨树上,单腿悬空。现在只剩下火场、白杨树和猪了。当一个人牵着它并对它说好话,哄它往前走,这头猪曾大声号叫。后来它看到另有两个男人兴高采烈地朝自己奔来,就叫得更响亮了。好可怜呀,男人们二话没说就抓住它的双耳拖曳。它用四条腿抵住,但耳朵痛不可支,只得一蹦一跳地朝前走。在桥的另一头有个人一把抓起斧子向它的脑门儿砍去。从此刻起一切事情都做得安安静静。两条前腿同时折断,当尖刀刺进这头小猪的咽喉,它才又叫了起来;这虽然是一声尖利、战栗的吼叫,但随即减弱为一种呼噜声,充满激情的呼噜声。这一切都是霍莫平生第一次见到。
天一黑,大家就聚集在教士的小宅院里,他们在这里租了一个房间作为娱乐场。诚然,一星期两次长途跋涉弄上来的肉常常有些腐败了,轻度食物中毒并不罕见。尽管如此,只要天一黑,大家还是提着小灯笼经由漆黑的山路跌跌撞撞朝这儿走来。因为忧伤和单调乏味之苦远甚于肉中毒素之痛,即使景色优美如画。他们以酒浇愁,一小时后这间教士房间就笼罩在一片愁云之中了。留声机的嘎嘎响声冲破这片愁绪,宛如一辆镀金铁皮小手推车驶过一块布满神奇星星的松软草地。他们不再交谈,只是各讲各的。他们,一位学者、一个工厂主、一名前流放地督察、一个矿山工程师、一位退休少校,在一起会有什么要说呢?他们用表示不愉快、相对愉快、渴望的手势——即使这可能也是言语——来说话,他们在说一种动物语言。他们常常激烈争执某个与谁都毫不相干的问题,甚至彼此侮辱,第二天表示要决斗的挑战书来回递送。随后的事实表明,根本没人到场。他们这样做,仅仅是因为穷极无聊,不知怎样打发时间,而即使他们之中谁也不曾真正生活过,也仍然觉得自己粗鲁得像屠夫,彼此不共戴天。
这是到处都一样的心灵的统一群体:欧罗巴。一种空闲无事,跟往常的有事可干一样不清不楚。想老婆、孩子、舒适安逸。这期间一再响起留声机的声音。罗莎,我们去洛茨,洛茨,洛茨……到我的爱情屋里来吧……幽灵假体上的药粉、纱布气味,一团远方杂耍演出和欧洲性生活的烟雾。不正经的俏皮话引得哄堂大笑,而且全都一再从这句话开始:从前有个犹太人坐着火车……只有一回有个人问:从地球到月球需用多少条老鼠尾巴?这时甚至出现了冷场,少校让人放《托斯卡》[3],并在留声机换放唱片的空隙神情忧郁地说:“我曾经一度想娶吉拉蒂娜·法拉尔[4]的。”随后她的声音就从喇叭口进入这个房间,进入一部上山吊椅,这令醉醺醺的男人们惊叹咂舌的女人声音,由上山吊椅载着飞速向高处驶去,没到达目的地,又降下,在空中弹动。大伙儿的衣服因晃动而一件件鼓起,这一上一下,这贴紧着停歇在一个声调上的片刻,这升升降降,这流泻,还有这总是被一阵新的战栗攫住,继而又倾泻而出:这是性欲快感。这是赤裸裸分摊给城市中众生万物的极大快乐,它不再能与杀人、嫉妒、生意、赛车加以区分——啊,这根本不是极大的快乐,这是冒险奇遇瘾——这不是冒险奇遇瘾,而是一把从天空落下的刀,一位死亡天使,是极大的疯狂,是战争!
从天花板上垂挂下来许多张长长的粘蝇纸中,有一只苍蝇掉了下来,中了毒仰卧在地上,躺在一个水洼的中央,煤油灯的亮光融入几乎觉察不出来的油布褶痕里的一个个水洼。这些水洼透着早春的忧伤,仿佛雨后已有一阵强风刮过。那只苍蝇越来越无力地挣扎了几下,想把身子翻过来,第二只苍蝇在桌布边上吃食,它不时跑过去,想看个究竟。霍莫也在一旁观看那只苍蝇,因为苍蝇是这儿的一大灾害。但当死神降临时,濒死的苍蝇把它的六条小细腿尖尖地拢成一团并高高拱起,然后就在油布上苍白的光斑里死去了,有如躺在一个宁静的坟墓里——这坟墓公制卷尺量不出来,众人闻所未闻,但确实存在。有人正在讲:“据说有一回有个人实实在在计算过,整个罗特席尔德[5]家族的全部财富不够支付一张去月球的三等车票。”霍莫低声自言自语:“杀生,却感觉到上帝存在;感觉到上帝存在,却杀生?”说罢,他用食指将苍蝇正好弹到了坐在对面的少校的脸上,这又引发一场风波,直到次日晚上才平息。
那时他早已认识格丽吉娅,也许少校也认识她。她叫茉妮·玛丽娅·伦齐,这听上去像塞尔伏特、格隆莱特或玛尔佳·门达纳一样有紫晶石和鲜花的味道,拖长“格丽”,轻吐“吉娅”,这是按她养的一头母牛的名字叫的,她喊这头灰牛格丽吉娅。她身穿紫褐色裙子,头扎有斑点的头巾,坐在草地边上,荷兰鞋的尖头弯曲着向上翘起,双手交叉着放在彩色围裙上,看上去那么自然可爱,像一株修长的小毒菌,她时不时向在低处吃草的母牛发出指示。其实这些指示就“Geh ea”和“Geh aua”两个词儿,意思似乎是“这儿”“上来”,因为母牛离得太远了。但是如果格丽吉娅的指挥不管事,随之而来的便是一声怒喝:“见鬼,你去哪儿?”作为最后一招她自己会轰轰隆隆像一块小石头那样冲下草地,就近捡起一块木头向灰牛扔过去。由于灰牛格丽吉娅有一个特别的癖好,总爱一再顺着山谷越走越远,所以这一状况总是周而复始不断发生。这极可爱而又无意义,因此他就喊她本人格丽吉娅,以此戏弄她。他无法向自己掩饰,每逢他从远处走近这个这样坐着的女人时,他就心跳得厉害——一个人突然走进芬芳的枞树林或一片长着许多菌类的林地散发着的馥郁香味之中时,心便是这样跳动的。这一印象始终含有一些对自然界的畏惧,人们要清晰地认识到自然界一点儿也不自然——它是泥土味的,有棱角的,有毒的,并且在所有方面不通人情的,倘若人不强制它。大概这正是这农妇把他拴住的东西吧,另一点则是那永不疲倦的惊异,因为它跟一个女人何其相似。假如人们在林子中央看见一位贵妇人手里拿着茶杯坐着,你也会惊讶不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