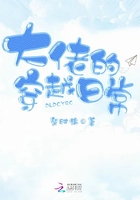白陆二人生怕走漏了风声,一路上马不停蹄,自是到了处驿站便是换马,未过七日便是到了渝州城,二人进了渝州城便已是傍晚,见得一路上没露出马脚,二人着装亦和往常相同,见得转眼便是黑夜,不便赶路,便在渝州城落了脚,投了处客栈,安顿下来。
二人皆是没什么胃口,随意噎了些干粮,便早早睡下,忽的听到一楼大厅传来从未听过的话音,听那话音竟不知说话之人是何方人士,白玉良连忙叫起熟睡的陆长风,陆长风正要说话,却被白玉良捂住嘴,白玉良连忙摇头,神色紧张,却又冷静。陆长风低声道。
“师兄,怎么了?怎么如此谨慎?”
白玉良瞥了一眼门外,拿起一旁半月剑,紧紧握在手中,做出拔剑姿态,陆长风见得白玉良如此谨慎,顿时消得睡意全无,同白玉良悄无声息的挪到门口,白玉良将门轻轻掩出一道细小缝隙,低声道。
“我听那几人口音,很是陌生,不像是中原人。”
陆长风便道。
“渝州城何时进了蛮夷,真是奇怪。”
白陆二人透过门缝,借着昏暗灯光,见得一楼那十三个身着黑色长袍的人,身材大都矮小,却有一人身材高挑,腰间别着三把佩刀,那佩刀长短不一,长的犹如长剑般长度,短的和匕首无异。其余十二人也是都带佩刀,似乎武功不弱,却倒像是仆从一般,对那高挑男子毕恭毕敬,那身材高挑的男子叽里咕噜的说些听不懂的话,十余人喝了些酒,便是一齐离开,白玉良见的那群人走出客栈,便是掌了灯,忧心仲仲,本来就是毫无睡意,而今见得那些人似乎各个身怀武功,且武功不弱,顿时更是担忧。
陆长风便道。
“师兄,借你半月令一用。”
白玉良抬起头,连忙道。
“做什么?”
陆长风便道。
“进了渝州,便是咱们自家地界,我用半月令去找当地舵主,让他们查一查这群人是什么来历?”
白玉良便道。
“长风,这事我是万万不可应了你。”
陆长风便道。
“为何?”
白玉良又道。
“你这五更半夜的去渝州分舵,又拿着半月令,这不是明摆着告诉他们师父过世的消息吗?师父历来不肯轻易拿出半月令,那渝州舵主又是老江湖,脑筋一转,也就猜得出个八九不离十。我不是信不过分舵舵主,只是不想在这等危难关头再节外生枝。”
陆长风连忙点头,道。
“还是师兄想的长远。”
白玉良又道。
“而今局势和从前不同,星月教如今命悬一线,树大枯枝多,人心难测,若是走漏了风声,那心怀鬼胎之人趁此机会生了事端,只怕星月教定是内忧外患,霎时便要倾覆。而你我二人便成了星月教的万古罪人。”
陆长风连忙点头,见得白玉良自打公孙染轩辞世,便是成熟了不少,略显老辣,行事也是更加谨慎,如履薄冰。
二人便又是睡下,白玉良听得陆长风的鼾声,便是暗道:还是个孩子啊。自己则是一夜未眠,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踏实,正要闭上双眼,望江亭的惨状便会浮现眼前,挥之不去。
第二日拂晓,二人便是结了房钱,直奔现月峰前去,二人也顾不得疲惫,只是一股脑的从渝州入了川地,川地道路狭窄,处处悬崖峭壁,二人不得放慢速度,待到第二日傍晚方才到了现月峰。此时夕阳西下,西边云朵如同火烧般挂在天边,殷红的微光照射在现月峰上,显得异常萧瑟。白玉良站在山下,“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声音颤抖,如鲠在喉道。
“师父,咱,咱,咱,咱到家了。”
陆长风连忙搀起白玉良,便道。
“师兄,早些上山吧。”
白玉良连连点头,拖着早已疲惫不堪的身子,挪着步子,上了山,双手捧着一个一尺宽的方盒,那方盒之中装的正是公孙染轩的遗物。待到上了现月峰,只见得星月教门前挂满白绫,门前守卫也是披麻戴孝,神色悲切,白玉良见状,心说:这一路上,我与长风怕走漏风声,只顾赶路,没有半分异色,现月峰又是如何得知?
陆长风便道。
“他娘的,定是那洛老七散播的消息。”
那守卫见得白陆二人归来,连忙上前迎接,白玉良见得门前白绫,门上白灯,酸楚便是一时间涌上心头,不由得跪地痛哭,院内陆长凌听得这哭声,连忙跑出,见得白玉良跪地痛哭,也是不禁流泪,白玉良将那木盒放在身前,不住的扣头,直是额头流血,也是感觉不到丝毫疼痛。
三人肝肠寸断,闻者亦是无不悲伤,却见的从堂内走出一男子,这男子身高不足七尺,身着孝服,面若铜镜,獐头鼠目,一副小人嘴脸,便道。
“哭什么哭?你们这群窝囊废,难不成能把杀害我爹的凶手哭死不成?”
陆长风一路上不知憋了多少火气,起身怒道。
“你说的什么话?”
那男子见得陆长风,冷哼一声,便道。
“就是这话,我爹难不成养了一群废物?”
陆长风正要破口大骂,却被白玉良拉住衣袖,道。
“师父而今回了家,定是看不得教内弟子争执不休。”
陆长风听罢,怒目圆瞪,瞥了一眼那男子,捧起木盒,正要向堂内走去,却见的那男子伸手拦住,便道。
“我爹的灵堂,你们算什么东西?有什么资格进去?”
陆长风便道。
“公孙固,你不要太过分,今日我还非进不可。”
说罢,便要强行进门,白玉良缓缓起身,道。
“长风,不可无礼,师兄说的没错,这遗物还是交给师兄的好。”
陆长风听罢,将那木盒狠狠的推给公孙固,公孙固抱住木盒,说道。
“等着吧,一会我会让你们进来的。”
说罢,快步进门,却是将那木盒子暗自打开,见得盒内除了一件长袍,更无其他,公孙固本以为那半月令在这木盒之中,便是从陆长风手中夺了过来,却没曾想打开木盒,竟是的这番景象,随即怒道。
“给我把那三个人叫进来。”
灵前一人应着跑出门外,将三人引进堂内,见得那木盒盒盖放在一旁,便是已知那木盒被公孙固暗自打开,又见公孙固倚在一旁的椅子上,神色逍遥,没有半分悲色,陆长风见状,便是怒道。
“你爹的遗物,你也好打开?”
公孙固起身便道。
“我爹的东西就是我的,有什么不能打开的。”
陆长风见得公孙固好不遵守礼数,和这灵堂格格不入,握紧拳头,双眼似的喷出烈火,骂道。
“你睁开你的狗眼看看,这他娘的是灵堂,你他娘的行这败坏伦理之事,就不怕天打雷劈吗?”
公孙固听得陆长风破口大骂,竟是面露邪笑道。
“骂够了吗?我爹的事,和你们这群杂碎有什么关系?你们能进这灵堂,便也是我宽宏大度。”
陆长风听罢,便是撸起袖子,走到一旁的剑架,抽出的一把剑,气势冲冲的走向灵堂,白玉良见状,怒道。
“陆长风,把剑放下,师父灵前,你岂敢放肆?”
陆长风听罢,回过头,看着白玉良此时也是气恼,眼中含泪,无奈之下,将手中剑丢向一旁。
公孙固便道。
“陆长凌,你现在且去七星台通知众位门主,说我有要事相商。”
陆长凌抬眼打量着公孙固一副丑恶嘴脸,便是动也不动,只当方才起了阵风,将公孙固话音吹得干净。白玉良便道。
“长凌,去吧,这事得告诉各位门主。”
陆长凌点了点头,走到门口时,停住步子,便道。
“若是少主再有出格行为,我回来定不容他。”
说罢,便是衬着残阳余辉,身影被拉的修长,快步走出大堂。
公孙固见得陆长凌走远,道。
“白玉良,我倒是有很多问题想问问你。”
白玉良便道。
“少主请讲。在下定然知无不言。”
公孙固便道。
“我爹爹是怎么死的?”
白玉良便将望江亭上的事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公孙固听罢,微微点头,冷笑道。
“原来如此,我道是你杀了我爹?但转念一想,你不过是个小小的教徒,怎会有这等本事?”
陆长风听罢,更是气恼,双眼犹如夜晚的猎豹,闪烁着寒义凛然的光芒,怒道。
“你他娘的,当我们都和你一般下作吗?”
公孙固便道。
“闭嘴,这里有你说话的地方吗?我不问你,你便闭嘴。”
陆长凌便道。
“谁不知道你的心思,你是想做教主想到疯癫了吧?”
公孙固见得自己心思被陆长风一语道破,脸上顿时生了怒色,道。
“你若再敢出言不逊,当心我拔光你嘴里的牙。”
陆长风便道。
“你以为我怕你吗?我就摆明了和你说,而今若不是师父英灵在上,我早就想痛打你一顿了。”
白玉良便道。
“长风,既然少主想知道这事,便告诉他。”
陆长风见得白玉良今日甚是唯诺,任由公孙固出言辱骂,更是恼怒,却只得在一旁喘着粗气,见得公孙固一副小人嘴脸,甚是恶心。
公孙固又道。
“既是我爹辞世,你二人为何不是披麻戴孝?”
白玉良道。
“在下生怕从中再生事端,便没敢声张。”
公孙固道。
“怕生事端?我看是你做贼心虚吧?”
白玉良便道。
“我做的是哪家的贼?还请少主明示。”
公孙固又道。
“既是没做贼,那我问你,我爹的半月令可在你身上?”
白玉良便道。
“在我身上,师父临终嘱托令我继任星月教第十代教主。”
公孙固听罢,不由得发笑道。
“哈哈,我看你小子是想当教主想疯了吧?你也不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不过是我爹爹身旁的一条狗罢了?还想当教主,我看你是痴人说梦。就当你说的是真的,既是我爹爹让你做教主,可曾有信笺?若是有信笺,交于我看看。”
白玉良便道。
“确实有信笺,但却被我撕了。”
公孙固听罢,又是发笑,道。
“哈哈哈,你连扯谎都扯不圆,还说被撕了,你怎么不说被你们这两条疯狗吃了呢?真是荒谬。”
白玉良听罢,顿时怒道。
“你当我和你一样的卑鄙无耻吗?这教主之位,我本无心贪恋,却不像你一般,自己爹爹死于贼人之手,自己不思报仇,反而为了教主之位,百般与自家兄弟过不去,我且告诉你,你羞辱我没关系,这事与长风无关,你若是再敢说些不敬不礼的话,我定不饶你。”
公孙固笑道。
“就凭你?还不配,废话少说,将那半月令给我,我便放你一条生路。”
白玉良便道。
“看起来这星月教若是落了你的手里,定是会一落千丈,名落孙山。”
公孙固便道。
“听你这意思是不想给了?”
陆长风便道。
“就是扔了,被野狗叼了去,也不给你这卑鄙无耻的小人。”
公孙固便道。
“你给我闭嘴,我今日不为难你,我只要半月令。”
白玉良便道。
“你这小人怎配拿着这半月令?”
公孙固听罢,顿时大怒,道。
“看来你当真是不想给了?”
话音刚落,只见得公孙固双脚点在椅子上,借力猛地冲向白玉良,这一招出手之快,竟让白陆二人没瞧个仔细。挥掌打出一招寒月千里,掌风凌厉直取白玉良面门,白玉良立即闪身躲避,抬脚踢向公孙固胸口,公孙固侧身躲闪,趁势单手着地,一招江淮逆流,这招“江淮逆流”本不是星月教的武功招式,却是这公孙固昔日里仗势欺人之时,和那些出手制止的英雄好汉过招之时,学的功夫,这功夫非得将拳脚倒转,借以让对方找不得破绽,白玉良见得这招式怪异,不知如何破解,只得慌忙抬手挡下,这拳腿招式大有不同,白玉良内力尚且浅薄,没过几合,便是震得双手手腕酸痛难当,挡架的招式也便的凌乱开来,破绽百出。公孙固趁机又是一招“星月倒转”这招式载于“七星半月大法”之中,力道柔中带刚,绝妙无比,白玉良见得这招法乃是“七星半月大法”不由得大惊,公孙固借得白玉良分神之际,左脚猛地蹬向白玉良下颚,白玉良连忙出拳抵挡,却不料公孙固突然变招一招“斗转星移”闪电般闪到白玉良身后,配合着“半月神剑掌”左掌猛地运功,只听得掌中风声微做,向白玉良背部拍去,白玉良见得公孙固变招极快,便已深知自己绝非他的敌手,而今躲闪已是不及,更莫要说变招抵抗,便是被这“半月神剑掌”打了个正着,不由得向前涌去,只觉这一掌力道十足,打在身上便是彻骨疼痛。白玉良踉跄了几步,还未站定,只见得公孙固又是铆足了气力,闪到白玉良身前,双手猛地伸出,抓住白玉良双臂,又向后扯去,白玉良此时早已无力再战,四肢无力,又被那那方才一掌打得不轻,神情恍惚,却也只感双手手臂剧痛难当,那疼痛之感直达心府。
此时白玉良胸前没了防备,空荡荡的矗在前方,公孙固猛地收手,借机伸出右手深入白玉良怀中,摸出半月令,又是“砰”的一掌将白玉良打出数尺之外,白玉良踉跄几步,勉强站定,口呕鲜血。
白玉良道。
“你竟是身上有了“七星半月大法”的一成功力?”
公孙固把玩着手上的半月令,笑道。
“就凭你的武功,就是做得上教主,又拿什么服众?”
公孙固见得那半月令背面刻有文字,便道。
“这文字又作何解释?”
白玉良便道。
“不知道。”
公孙固冷冷一笑,双脚步伐扑朔迷离,令人看不清轨迹,便是闪到陆长风身后,从怀中摸出一把钢刺,直抵在陆长风勃颈处,便道。
“我知道你是断然不会说的。若不用些手段,你怎会乖乖说出这经文的奥秘?”
白玉良见得公孙固手上钢刺,已是划开陆长风脖颈的表皮,鲜红的血液也流了出来,生怕公孙固狗急跳墙,将那钢刺插进陆长风脖颈之中,正要开口,陆长风便道。
“你这狗贼,真够下三滥的。师兄,莫要告诉他,不过是死,谁不死啊?难不成这狗杂碎不死吗?”
公孙固冷笑道。
“小子,你是当我不敢杀你吗?”
说罢,将那钢刺略微深入,只见得陆长风表情愈见狰狞,却是咬牙坚持。白玉良心道:这本是我和公孙固的事情,若是让长风白白送了性命,那还了得?便道。
“你先放开他,我便告诉你。”
公孙固听罢,转念一想:这二人就是合力,也是敌不过我,就是放了陆长风,也不打紧。遂即将陆长风推到一旁,白玉良见陆长风无碍,便道。
“半月令和七星牌乃是进入月光洞的钥匙,月光洞石壁之上刻有“七星半月大法”的修炼法门。”
公孙固听罢,笑道。
“好,算你识相。”
陆长风便道。
“师兄,你我二人合力,定能拿下这狗贼,岂容他放肆?”
说罢,捡起地上长剑,便要提剑斩去,白玉良连忙拉住陆长风袖口,道。
“而今,他的功力远在你我二人之上,莫要白白送了性命。”
陆长风便道。
“那也不能任由着狗贼在星月教兴风作浪?”
白玉良连连摇头,他深知若是二人合力,公孙固又是动了杀心,只怕二人定要白白送了性命,自己死了倒也不打紧,若是连累着自家兄弟陪着自己送命,就是到了地下,也无颜面对公孙染轩。公孙固顿时心生毒计,缓步走向堂上,将半月令拿在手上,喝道。
“如今七星牌,半月令皆在我手,我便是星月教第十代教主。传我教令,星月教弟子白玉良盗取半月令,被我夺回,又多次出言不逊,辱我威名,着白玉良逐出星月教,永世不得踏入现月峰半步,如有不遵者,皆斩不论。”
陆长风听罢,指着公孙固的鼻子骂道。
“去你奶奶的,你他娘的说的还是人话?说我师兄盗取半月令,你放的什么狗屁?你何德何能做着一教之主?你既不配做这教主,更不配做人。”
白玉良生怕公孙固再动杀心,将陆长风处死,连忙道。
“长风,不可无礼,而今他是教主,凡本教事务,皆凭他意,他既是逐我出教便遂了他的愿吧。”
陆长风便道。
“好,你既是逐我师兄出教,老子也不会乞求你,若是师兄要走,我和大哥也断然不会伺候你这混账东西。”
公孙固便笑道。
“而今,本座贵为一教之主,又得了神功的修炼法门,岂会在乎你们是去是留?”
白玉良便道。
“陆长风,你糊涂啊。师父带我等恩重如山,而今星月教倾覆之际,你怎可为的一己私利,弃教而去?就算所有人都弃教而去,你和长凌也不可有半分动摇之心。只有这样,才算对得起师父对我等众弟子天高地厚之恩。”
陆长风便道。
“可是师兄,被逐出了星月教,你又能去哪里啊?”
说罢,双眼便是流下泪水。白玉良笑道。
“傻兄弟,哭什么啊?天地之大,岂会没有师兄容身之地?你便好生在星月教,尽心尽力辅佐教主,且不可逞一时之快,顽固任性。”
说罢,转过身,对这公孙固冷道。
“你记着,若是你敢对陆家兄弟有半分残害之心,对教内兄弟有半分暴戾之念,我就是在天涯海角,也定会找你算账。”
公孙固道。
“而今我是教主,如何做教主,岂用你来教?”
白玉良便道。
“你便记住今日你说的话。”
说罢,转身走出灵堂,公孙固又道。
“而今,你还配拿着星月教的服饰吗?那半月剑也留下吧。”
白玉良听罢,愣在远处片刻,片刻过后,将包裹扔了过去,道。
“这半月剑乃是我祖传之宝,给不得你。”
公孙固笑道。
“罢了,就给你这废物留着吧,就是旷世神兵,在你这废物手中,也不过是破铜烂铁罢了。”
白玉良也没理睬,左手拿着半月剑,右手空空,快步走出灵堂,殷红余晖映在他的身上,将那黑色侠客便装映照的如同沾了鲜血,本就修长的身影,映在地上,更显孤独,凄凉。远处早已枯死的榆树,此时便于他绝无两样。
陆长风便是含泪喊道。
“师兄。”
白玉良回过头,夕阳照在他冷峻的脸上,更显冷峻,却硬是强露出笑容,嘴角微微扬起,许是添了几分温暖。
陆长风停了片刻,低头思索着,又抬起头,喊道。
“保重。”
白玉良微笑着点了点头,转过身,内心却是无比的悲痛,酸楚,顿时流下泪来,任凭着陆长风再怎么嘶喊,也是不为所动,只是加快脚步,走下现月峰。
白玉良自打出了星月教,便一直失魂落魄,每走三步必会回头向皓月堂望去,此时已临近傍晚,日落西山,几只乌鸦在榆树上叫个不停,更是悲凉万分,正到山根,白玉良便见一信使策马疾驰,在山根下了马,疾步向现月峰奔去,白玉良见那信使身穿青黑短衫,头戴斗笠,不像是星月教教内之人,倒像是前些日子在客栈遇见的那伙人,便迎了过去,拦住那信使,那信使见到白玉良,更是将斗笠向下压了压,那信使道。
“来者可是星月教白少侠?”
白玉良看着那信使,心生疑惑,心说:这人是如何认识的我?
“正是在下,不知小哥来此有何贵干?”
“这是渝州星月教分舵寄来的信件,要交给星月教总舵。”那信使说着从腰间摸出信件,交到白羽手中。白玉良伸手接过,刚要发问,那信使转过身,头也没回的便骑上马飞奔而去。
白玉良见那信使所骑之马高大,骠肥体壮,马脖子较长,马头略小,定是北方军马,更是心生疑惑,白玉良见信使走远,立即打开信封,只见信上写道。
“念我教教主仙逝,属下恳请总舵新任教主于五月十七午时驾临渝州城东十里外的重山亭一聚,商议教内大事。落款:星月教渝州分舵。”
信件末尾更是印上了星月教的标识,白玉良见这标识,更是心生疑惑,将信笺收进怀中,心说:这渝州分舵怎会得知师父离世的消息?
白玉良暗说道:没错了,只怕写这封信的人,正是杀害师父的人,但他如此做意欲何为?
白玉良正要飞身追赶那人,却是转念一想,只觉得那人若是算计了师父,自己断然不是他的敌手。便是算了算日子,今日便是五月十五。想到这里,白玉良便决定于五月十七前去重山亭一探究竟。
那重山亭位于渝州城东崇山峻岭之间,白玉良倒也熟悉那地方,心说:此时,尽得地利,也不怕他在做什么把戏。
白玉良耽误了些时辰,此时太阳已落了山,在成都市井之内寻了一客栈,先安顿了下来。
一更刚过,白玉良便听得有人敲门,白玉良暗自拿起半月剑,拔剑出鞘。心说:难不成是公孙固派了杀手要杀我灭口?从床上起身,轻声轻步的走到门前,问道。
“来者何人?有何贵干?”
门外一中年男子的声音应答着。
“玉良,是我们。”
白玉良听到这声顿时收剑入鞘,打开房门,门外站着七个中年男子,约摸着四五十岁,白玉良自是认识这七个人,这七个人正是星月教教内的七星门的七大门主。
老大赵天枢,天武门门主,正是刚才敲门之人,这人身高七尺有余,浓眉大眼,面色蜡黄,脸上有些许皱纹,但不显衰老,身材魁梧,掌管星月教七星门武学典籍,也是七门门主中功力最为深厚的。老二钱天璇,天速门门主,身高不足六尺,一双腿便占了有四尺之长,身材干瘦,面色黝黑发亮,目如黑夜之中的狸猫,主管星月教的江湖消息来源,此人轻功一绝,可日行千里,堪比宝马良驹。老三孙天玑,天算门门主,身高八尺,身材匀称,一双大眼炯炯有神,精于算计,腰间总别着一副算筹,平日总管教内大小财务,管理星月教所有商栈。老四李天权,天相门门主,平日里道士打扮,沉默寡言,身高七尺,似有仙风道骨,精通观星,占卜之术。老五周玉衡,长生门门主,身材略胖,眼如牛目,面色光润,平日里炼丹制药,总管星月教的医疗之事。老六吴开阳,天器门门主,脸色铁青,面颊殷红,脸上时常挂有微笑,平日里像顽童一般,嬉闹异常。身高不足七尺,体态精瘦,善打奇门兵器,掌管星月教的兵器制作。老七郑瑶光,天狼门门主,身长不过六尺,眉稀眼大,双眼聚神,似有光芒闪出。双臂粗的惊人,平日里因为双臂粗壮,穿一身短衫,将两臂露出,双臂之上青筋暴起,剑法可百步穿杨。
白玉良见得众人,行礼参拜。
“晚辈白玉良见过众位前辈。”
“免礼,又不是在星月教,不用多礼,你我叔侄相称就好。”赵天枢说着,带领身后六人进了房间。
“玉良,你与钱叔说一说,教主到底是怎么死的?”钱天璇说着,找了把椅子,坐在上面,一旁的白玉良为这几位叔叔奉茶过后,站在一旁,将群英大会事件的来龙去脉说了出来。
“那新任教主为何说是你盗取了半月令呢?”孙天玑说道。
“唉,三哥,那公孙固是什么人,咱们兄弟七人还不了解吗,他若不这么说,那玉良不是就做了教主?”吴开阳说着,笑了笑。
“其实,师父本是想把教主之位传给晚辈的。”白玉良说着,低下头,无奈的苦笑着。
那七人皆是瞪大了眼,探着头,注视着白玉良,片刻后,又相互瞧了瞧,摇了摇头,叹了口气。
“玉良,你小子是不是傻了?这教主之位怎么能轻易就让出去呢?”郑瑶光说着站起身,用食指轻怼了一下白羽的额头,无奈的叹了口气。
白玉良又将方才自己在现月峰所经历的事情说了出来。
“你们说,这公孙固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呢?”赵天枢说着,咧了咧嘴。
“要我看,公孙固如果不这么做,玉良也就不会不声不响的离开星月教。”一旁的李天权说着,端起茶杯,抿了一口,又一言不发。
“老四啊,你这是什么意思?怎么说话总说一半呢,难不成这也是天机?”赵天枢说道。
“很简单,”
李天权话没说完,一旁的吴开阳把话接了过去,轻咳了一声,好像讲故事一般,端上了架子。
“你能不能快点说。”郑瑶光说着,瞪向吴开阳。
“催什么催,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说出的话像射出去的箭一样。”吴开阳说着,瞥了一眼,笑嘻嘻的接着说道。
“那公孙固让长凌来找咱们说是有要事相商,目的就是让整个皓月堂就留下玉良和他两个人,而公孙固早就算计好如何逼玉良离开星月教,等到咱们到的时候,玉良早就下了山,到时候还不是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喽。”
“长风不是一直在皓月堂吗?”钱天璇说道。
“长风确实一直在皓月堂,这也可能就是公孙固的一个纰漏,他本打算着将长风先阻隔在外面,却是没曾想二人私交如此深厚,玉良走之前一定和长风交代过什么话。”吴开阳说着,笑了笑看向白玉良。
白玉良也点了点头。
“那就错不了了,等咱们到了之后,长风这孩子本来就直来直去,自然不愿意多看公孙固一眼,所以他就和长凌走开了,留下我们七人和公孙固商议接任教主之位的事情。”
“老六,看你平时嘻嘻哈哈的没个正形,这分析起事情来,也是头头是道啊。”赵天枢说着,笑了笑,吴开阳就好像受到嘉奖一般,像个孩子一般笑了起来。
“那也就是说,玉良,你当真不打算和公孙固争教主之位了?”钱天璇说着,看向站在一旁的白玉良。
“罢了,师父仙逝不久,他老人家也一定不希望我和公孙固为了争教主之位把星月教搞得四分五裂,既然他容不下我,我走便是了,这天下之大,难不成没有我的容身之地,另外,师父的死,我一定要查清楚,不能让师父不明不白的死了。”白玉良说罢,走向窗口,低下头,叹了一口气。
“要我说,玉良这孩子就是比公孙固强百倍,那公孙固今日可没和咱们几人说如何替父报仇吧。”钱天璇说道。
“可惜啊,玉良啊,凭我对教主的了解,他若传位给你,理应会给你一封他亲笔的信笺啊?”孙天玑说道。
“是啊,师父生前是给过我一封信,只不过回来的时候,我悲痛欲绝,早就没了当教主的欲望,在路上被我撕了。”
“哎呀,你这娃娃怎么这么糊涂啊,那教主的继任信笺你怎么撕了呢,你是不是没东西玩了?”吴开阳说着,猛地拍了拍自己的大腿,暗叹了一声。
“吴叔,当时晚辈的确有心想把教主之位让给公孙固,但我没想到他既然为了教主之位如此不择手段,多次言语上中伤于我。”
“真是后悔,我悔不该交给他七星拳法,更可恨的是半月门门主王光七,这老东西见公孙固当了教主,手舞足蹈,摆宴庆贺,那公孙固更是披麻戴孝前去饮酒食肉,还厚颜无耻的邀请我们几人前去,我们几人商议过后,决定不去,这不就到你这里来了。”赵天枢说着,猛地砸了一下桌子。
“王光七还把圆月掌法传给了公孙固,这王光七卑鄙无耻,教主在世之时便对教主阿谀奉承,哄骗教主传他七星半月大法,教主为人光明磊落,也没看出来此人心机,便传给了他七星半月大法的第一层内功心法。”郑瑶光说道。
白玉良心说:怪不得公孙固身上有七星半月大法的一层功力,原来是王光七传给他的。
“各位叔叔,七星牌在谁的身上?”白羽突然问道。
“本来是在我这里的,可是教主继位,按教规教主应该拥有七星牌,我便给了他。”赵天枢说道。
“罢了,给他就给他了,若是七星半月大法被这等无耻小人所掌握,只怕星月教危矣。”白玉良道。
“玉良,多虑了,公孙固虽说凭借着七星牌和半月令可以进入月光洞,练习七星半月大法,但是凭借他现在的内功修为,只怕没个十年八年练不成,这人好吃懒做,贪图享乐,莫说十年八年,就是需要一年学会的武功,他都不会坚持下来的,更别说七星半月大法这种星月教的上乘武功了。”周玉衡说着,双眼透出蔑视的目光,笑了笑。
“现在晚辈所担心的则是星月教的未来,这等小人做了教主,只怕是天要亡我星月教啊。”白玉良说着,低下头,长呼了一口气。
“玉良,有众位叔叔在,定然不会让他胡作非为,教主当初带领我们众兄弟把星月教发展成川蜀之地最大的帮派,我们是不会让那个混蛋毁了我们的心血的。”赵天枢说道。
白玉良听罢,“噗通”一声跪在地上,扣了三个响头,哭道。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父仙逝,晚辈未能继承师父遗愿,是为不孝。不能辅助星月教称霸武林,是为不忠,但晚辈有一事相求,就是恳请各位前辈一定要让星月教存在于中原武林。”
“玉良,你这娃娃,快起来,这些话你就是不说,我们这些做叔叔的,也会尽心尽力辅助星月教的,你这是做什么啊,快起来吧。”吴开阳说着,走了过去搀起跪着的白玉良。
“玉良,你记着,你是我们看着长大的,日后独自一人涉猎江湖,需万事谨慎,更要懂得自我保护,你武功不高,但是宅心仁厚,相信日后定有福报,若是有什么事情需要叔叔们帮忙,你便写封信,送到七星台,我们自会帮你。另外,叔叔们平日里也攒下不少钱财,你一人在江湖漂泊,没有银子是不成的。”赵天枢话音刚落,从自己腰间取下教内门主大印放到桌子上,郑瑶光也从腰间摸出钱袋,放到桌子上。
“叔叔,这是何意啊?”白玉良问道。
“玉良,这是我的印章,若是遇了事,至少星月教在渝州和成都一带的商栈见到这印章都会助你,这些许银两,你就当做盘缠吧。”郑瑶光说道。
“多谢叔叔好意,这银子晚辈便收下,当做向叔叔借的,至于大印,叔叔务必要收回。”白玉良说着,又是跪在地上,扣了三个响头。
“好孩子,江湖险恶,你要照顾好自己。”李天权说着,拍了拍白羽的肩膀。
“晚辈记下了,叔叔对晚辈的大恩,晚辈永生难忘。若来日晚辈闯出个名号之时,定会报答各位叔叔的深情厚谊。”白玉良说道。
“行了,这时候也不早了,我们兄弟就先回去了,免得公孙固起疑。你日后好生照顾自己。”赵天枢说着,带着另外六人出了白玉良的房间。
五月十六正午,白玉良便上了街,街上仍旧往日般繁华热闹,人挨着人,黑压压的一片连着一片。
倏地,白玉良听得身后似有惊雷响过,回头定睛一看,只见一匹高壮雄俊的红枣马疾驰而来,这马在街上奔袭,犹如出海蛟龙,速度也是快如疾风,却不见踏伤一人,转瞬之间便已距白玉良不过一丈之远,白玉良这才看清马背上还有一三十岁左右的男子,这男子镇静自若,马术绝伦,举世无双。莫说踩伤行人,连一旁摊位都未曾碰到,白玉良大骇惊叹道:此人马术之绝妙,只怕天下难以有人可与之匹敌。
正当白玉良发愣之际,那马已经距白玉良不足两尺,只见那男子猛地拽起缰绳,那马顿时凌空飞跃,直从白玉良头顶跃过,那马着地之时,更是平稳异常。
“小兄弟,没吓着你吧。”马上那人见到白玉良两眼发直,调转马头,说道。
“啊,没有,没有。”白玉良听到那男子讲话这才缓过神来,摇了摇头,说道。
“那就好,在下方盛驹,不知小兄弟叫什么?”那男子下马后,白玉良见到这人面色枯黄,浓眉大眼,体态干瘦,显着身体修长。
“在下白玉良,大哥这马真是宝马良驹。”白玉良说着,摸了摸那匹骏马,那马生的高大,体态肥硕,浑身毛发通体光亮,没有一根杂毛。
“小兄弟,在下这一生没有别的爱好,就喜欢这马,什么马都好,只要是好马,在下就移不开眼了。”方盛驹说着,从马鞍旁边的布袋里拿出一块沾了灰的面饼放到嘴里咀嚼着。又从布袋里拿出一精雕木盒,木盒之中是青草制成的草饼,方盛驹将草饼喂到马嘴里,有拿出水袋,喂了些水进去。
“大哥,您这是?”白玉良问道。
“兄弟莫要取笑,这良马就是我的命根子,哈哈。”方盛驹笑道。
“前些日子,我家那婆娘,怨我乱花钱,从突厥那里买了这匹马,我实在受不了这娘们家的嘟囔个不休,便一纸休书,送她回了娘家,这马也当真不错,从冀州跑到川蜀,也仅仅用了两天半的时间。”方盛驹说着,笑了起来。
白玉良听罢,更是吃惊不已,心说:从冀州到川蜀,就是赶最近的路,也得一千多里近两千里,这马就是体态再过肥硕,也要每跑二百里就要休息半个时辰,可这马能有如此脚力当真是宝马良驹。
“大哥对马的确痴迷,小弟佩服。”白玉良说道。
“哈哈,这有什么值得佩服的?白兄弟,我看你这形色焦急,不知是要去哪?”
“小弟打算去一趟渝州,这坐骑半路上暴毙而亡,正打算寻匹好马。”
“这样啊,那咱俩刚好顺路,如若兄弟不弃,我可以载你一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