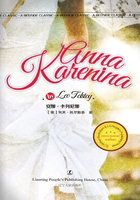他在市作协召开的会议上第一次见到她。四十多人绕墙坐了一圈,唯有她一位女性,给会场带来了一种特殊的气氛。他不习惯用专注的眼神看一个陌生的年轻的女性,只知道那儿搁置着一盆鲜花——正是八月,她穿着一件红连衣裙,腰间的带子舒展地垂在腿上,自然而飘逸。
他是主持会的,平时是非常严谨的,今天却很活泼,轻松地讲着话。凭感觉,他知道她在一眼不眨地注视着自己。他虽然已经三十八岁了,但显得比实际年龄小五六岁。这样,在整个会场中,除她之外从外形上看就数他年轻了。他觉得很满足。
会议中间,他上了一趟厕所。出来时正好碰到她,她大约也是去厕所。他和她都微微一笑,眼神对视了一霎耶,并没有打招呼。那微笑是恬淡的,像掠过一丝细缕的风。
散会了,她带着幽香出了门。
作协的会员会是两个月举行一次。两个月后,天已经有了些许的凉意。她穿了件淡黄色的毛衣外套,头上松松地挽了一个发髻,虽然坐在会场的一角,但仍然很显眼。这次会的主要议程是会员汇报创作情况。别人都谈完了,只剩下她。
“你,夏谨同志,”虽然陌生,他还是记庄了她的不同于一般女孩子的名字,“谈谈吧。”他的目光转向那黄色的角落。
“我没什么可谈的。”她显得很拘谨,像一个小学生面对着老师的提问。“我只发表过一篇很幼稚的小说,没有什么经验。”停了片刻,她抬起胳膊很随便地把耳边的垂发撩了撩,“下一步吧,我想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写些关于青年人生活的东西……总之,我还很年轻,希望各位老师多指教。”
她抬起头,目光朝他这儿一瞥,意思是我的话完了。
他燃起了一支烟,侃侃而谈起来。从文学作品的思想性谈到艺术性,随口举出了许多中外著名的作品,并时而插进作家的小幽默,使会场的气氛活跃起来。最后他又从作家深入生活的问题谈到艺术的本质,大约由于很抽象,也很肤浅(在这种会上谈这类问题完全是废话),在座的人渐渐地显示出不耐烦的神态:欠身,打哈欠。唯有她,仍然专心致志、饶有兴味地听着,并不时在一本蓝皮笔记本上记着。在偶尔抬起头时,目光正好与他相对。那目光中有一种迷人的东西,他想努力捕捉,但很快,她就埋下了头。
散会时,已是十二点半了。他看看表,有些抱歉地但又不失体面地说:“噢,我的表停止了转动。”
其实呢,他的表运转得非常正常。
那天晚上,他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妻子已经熟睡了,他开了台灯,侧身注视着妻子。那是一张熟悉得不带任何掩饰的脸容,额头、眼角已经出现了微细的皱纹。他努力想从妻子的脸上寻找什么,可是失望了,因为直到今天,那张脸对他来说依然很模糊,鼻梁呢?嘴巴呢?额头呢?还有眼睛、睫毛……以至于她不在面前的时候,一切都成了一个谜。也许走在大街上,他会认不出来是她呢。他叹了口气,关上灯背对着妻子躺下了。然而有一点,他在关灯的一霎那,他肯定了,她比妻子年轻,也有魅力。
大约,陌生、模糊,也是一种魅力?
他毕竟有许多事情要做。他是作协的负责人之一,要处理繁多的日常事务,要参加有关的会议,还要写稿,为女儿辅导功课。他的女儿九月份已经上初中了。于是,渐渐地,他便忘却了她。
他第三次见她,是在一个分不清是雨是雪的日子。那天作协召开年终总结会,他撑着伞从家里出来刚走到莲花街拐弯的地方碰见了她,是她先招呼池的。
“王老师,您好。”她撑着一把带白花点的雨伞,穿着红色的鸭绒外套。他怔了一下,马上就醒悟过来,那张脸使他立刻感觉到一种温暖。
“是你——来得这么早。”他脸上浮上了笑容,“是搭车来的吗?”
“不是。”她的普通话说得非常准确,不像他,总是把“是”读成“死”。“昨晚我住在姑妈家,在西八路,离这儿很近。”
“噢,单位离这儿很远吗?”
“在郊县,离这儿有三十多里。”
“哦?”他一愣,“什么地方?”
“周安中学。”
“那么说,你是老师啦?”他立刻觉得了一种亲切感,感情上那么自然地接近了点。因为他也做过八年教师。
他们愉快地一见如故地交谈着。
路上,不断碰见一些熟人。都热情地和他打招呼,使他时时能感受到自己在这座城市的地应。作协副主席、青年作家,是多少文学作者羡慕而尊敬的职位和头衔。他并且能感觉到她的目光不时地在注视他。他努力使自己的每一个动作变得潇洒,富有活力,目光总是望着遥远的街头。他被一种惬意的氛围渲染着。
这次会上,她显得活跃了些,扭着腰肢给与会者泡茶、倒水,“请喝茶。”她的声调和动作都自然而轻柔,使那些高傲的作家们都轻轻地动了动刚刚添过水的杯子。作协的那位秘书今天没来,没有任何人暗示她,她就坐在他身旁打开了会议记录本……
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会上给十名成绩突出的会员发了奖,他最后作了总结发言。简短、浪漫、幽默,对作协新的一年的工作做了布置安排,使每个与会者都增添了龙年到来的紧迫感和自信心。
散会时,不知为什么,她和他不约而同地最后离开会场。
“王老师,我可以走了吗?”她走到他面前。
“走吧。”他点点头,“一路小心。”瞬间,他想留下她好好地谈点什么,但是却没有。
在门口,她向他扬起了手。他平时不习惯和人挥手告别,这时也下意识地举了一下手。
回到家,妻子已做好了午饭在等他。女儿偎过来,甜甜地叫了声爸爸。他抚摸着女儿的头,对她做了个怪脸。蒸米饭,四个菜:炒芋丝、绿豆芽、酸白菜、炒鸡蛋,都是他喜欢吃的。妻子比他大一岁,看去却比他大了许多。对她,他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正像她开玩笑时说的:不是我,你能当上作家么?唯一不满足的是:她从不爱读他的作品,对他的稿费也看得很淡,使他觉得生活和事业上的一种缺憾。
坐下来吃饭时,他不知怎么想起了她。于是,心情便有些黯淡了,低着头闷闷地吃。
“怎么了,你?”妻子轻声问。
“不怎么。”他淡淡地回答了一句,又胡乱塞了几口菜,起身躺到他书房的床上了。妻子不再问什么,只是招呼着女儿吃饭。十几年来,她习惯了丈夫在偶然间的情绪变化,知道他一定在写作上遇到了不顺心的时候。
午睡,他破例地失眠了。那张模糊而迷人的脸怎么也从脑子里驱赶不走。这真是奇怪的反应。婚前不说了,婚后他还从来没有真正把那一位女性放在心里。有时见到一些漂亮的姑娘,也忍不住多看那么一眼——绝不多看第二眼。他是本市大名鼎鼎的人物,绝不会让任何一位女性在他面前显示出高傲的神态,以至于获得某种满足。他只能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让她们注目惊叹:嗬,那就是作家王捷!在惊叹之余让她们滋生一种望洋兴叹的感触,那才是他真正愉快的事情。
即使他产生过这么一种潜在的意识,他也不否认自己的正派。的确,在本市文艺界,他这一点是颇令人称道的。他不像有些作家,一出了名便会拥有诸多的情人。然而,今天是怎么了?他努力使自己的心境平静下来,淡漠起来,但是却不能。
他的手头正在写一部反映城市经济改革的中篇小说,正写到高潮处。睡不着,干脆起来写稿吧,他铺开了稿纸。面对着稿纸,却感觉脑子里一片乱麻,心不在焉起来稿纸隐约现出了一张脸和一副微笑……见鬼,他扔下笔,在房子里走动起来,回味着上午散会时她的那句:“我可以走了吗?”什么意思呢?难道她想和我谈什么吗?想在我身边多呆会儿吗?还有那恋恋不舍地举手告别,都似乎暗示着什么。他的心不禁骚动起来。
他再也写不下去了,躺在床上翻开一本小说读了起来,是一位很轰动的青年作家写的,都编成了电视剧。读了几页,他被一段话吸引住了:“没有隐情的男人是无思想可言的男人,没有隆情的女人是没有灵性的女人……”他翻来覆去地咀嚼着这句话,心头蓦然一亮,尽管自己出版了两本小说集,但评论界总没有对他的作品给予足够的重视。过去他常为此感到不平,现在忽然觉得自己的作品并不是很出色的,而这,大约是由于自己缺少“隐情”吧?我为什么不去寻找这种“隐情”呢?真的,有一个情人,生活中多一份色彩,又不破坏已经建立起来的家庭,为什么不可以呢?退一步说,即使真的使一个或两个(因为他还不清楚她是否有了家庭,或者恋人)家庭解体,又有什么不值得的呢?和她组成一个家庭,那一定会是和谐的,美满的,她将成为他事业上的第一个知音……他断定,她无疑是一位温柔而有内涵,多情而有事业心,懂得生活,能忍受挫折和坎坷的女性。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会成为文坛上令人瞩目的一对作家夫妇……
他陡然涌起一个念头:去找她!在这种事情上,男人当然应该主动一点,她不是已经隐约地向你表示了吗?他躺不住了,拉开门,真想一步就出现在她的面前。然而,就在他走下楼梯的一刹那,他又犹豫了:上午刚见过面,彼此双方都还来不及认真地品味刚刚过去的每一个眼神和动作,那种相见是不会达到某种理想的境界的。
第二天是礼拜天,他带着妻子和女儿到渭湖公园玩了一上午。过去,礼拜天他从来都是把自己关在房子里伏案写作,妻子常常抱怨,但由于成了习惯,也只能抱怨抱怨罢了。当他宣布了这个决定后,妻子惊喜地问:“怎么今天有时间了?”女儿也乐得扑在了他怀里。
他对妻子装出一副笑脸,没有说什么。不知为什么,他觉得有点对不起妻子,总想用什么来弥补一下心灵上的隐秘。在向公园走的路上,他又想着:我绝不能背叛妻子,与她的感情,只能是一种真正的隐情。
好不容易熬过了礼拜天和礼拜一上午,中午吃了饭,他精心地打扮了一下自己,洗了头,刮了胡须,换了一身衣服,灰西服,潇洒而又庄重——好在妻子不在,否则她又要惊疑了,因为过去从来都是妻子“命令”他换衣服他才换的,边脱衣服边责怪妻子衣服洗得太勤了。
他想了想,在书柜里挑几本女作家的书:《简爱》《牛虻》、法国乔治·桑的传记《我的一生》及台湾三毛的《夏日烟愁》,出门后,他又返回去,翻出了自己的那两本小说集也装在包里。
近一个小时,他乘车到了周安县城。打听了一下,中学还在郊外呢。他又走了约半个小时,才找到了那所学校。门房老头拦住了他,细细地盘问了他才放他进去。老头告诉他。她的房子是东边第二排靠路第一个门,如果没在,那一定是在上课,请不要闯进教室。他心里有些好笑,我做过教师,难道不懂这?
他在那间房子门口站住了,紧张地轻轻地敲了敲门,没有响动。等了会,又敲了敲,里边响起了声音:“谁呀?”
他心头像钻进了一只兔子,又惊又喜。他没有答声。他想叫她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看见池,那一瞬间的情景他想一定很有意思。他想看看她邵慌乱而惊喜的神态。
门开了。她微散着头发,床上被子乱成一团,显然是正在睡觉。他打量了她一眼,她的脸上一副倦态,一点找不到想象中的那种迷人的色彩。
一副平常得再也不能平常的脸容。
在这一刹那间,他感到一种失望。
她很惊讶他的到来,但又手忙脚乱地给他倒水,一不小心又将水杯碰倒,水在桌面上缓缓地流淌,她又匆忙找抹布去擦。
“您喝水。”她坐在床边,拘束地说。她穿着一件灰旧的裤子,两腿拢得很紧。
他坐下来打量着她的房间,墙壁陈旧而黯淡,墙角有很大一张蜘蛛网,墙上没有一幅画,床围是用报纸糊的,桌上零乱地堆放着两沓学生的作文本,一个落满灰尘的墨水瓶……一点不像他想象中的那样清淡、素雅。
她低着头,用手不时地拉着未铺展的床单,也许她对他的出现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显得十分尴尬。
他喉咙动了几次,一句合适的话也没有说出来。路上想了那么多,文学、人生……他觉得有许多话要对她倾诉。当然这些都是在一种亲切而和谐的气氛下自然而然地讲出来的,生动、幽默、含义深长。他想象着她见了他一定非常激动,有问不完的问题:您的文学之路?您发表过多少作品?怎样才能写出好作品?怎样观察和体验生活?……把他作为人生和文学道路上的一位师长,一位可以信赖和依靠的朋友,当然,其中也夹杂着倾慕和某种渴望……,他呢,就可以居高临下地展示他对文学和人生的深刻体验,有掌握分寸的激动,含蓄的感情流露,把她的感情纽带一步步引到自己手里。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出现,因此他也就失去了表达思想和感情的条件——缺少那种气氛。
和她的单独相见怎么会是这佯?他事先为什么一点都没有预料到?难道他和她的相见只能在作协的会议上?在那豪华而富有情调的会议室里?
真是不可思议!
“你在这儿生活习惯吗?”他到底还是想起了一句合适的问话。
“怎么说呢?”她稍抬了抬头,眼光却望着那陈旧而黯淡的墙壁。“我很寂寞,很痛苦。”
哦,痛苦?他不知道她为什么痛苦,难道就为这间狭小而破旧的房子?换句话说,痛苦不是人生的财富么?没有痛苦怎么有文学?他想起了他插队时的生活:不足一百斤的体重却要拼着命去扛装着一百三四十斤的小麦或者玉米的麻袋上楼;三伏天穿着裤衩锄玉米,汗水从头淌到脚,浑身像涂满了黑色的油泥;满手血泡割那没有尽头的麦子,星星出来了,别人都回去了,他却一头栽倒在麦捆上昏睡了几个钟头……
“也许这段生活会成为你珍贵的回忆呢?人生需要痛苦,文学更需要……”他觉得自己有资格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对她讲些什么了。
“你说的也许是对的。”她打断了他的话,看了他一眼。“可是再这样呆下去,我还能搞文学吗?”她叙述了学校的生活:学生不听话,校长不给她安排好房子,屋顶上的灰土往下落,地上有虫子,水不卫生,伙食太差,午睡噪音太大,晚饭后没地方散步,厕所太脏,影院太远……
他听着听着,突然觉得乏味极了,仿佛面前坐着的是一个唠唠叨叨的老婆子。他想不出她叙述那些与搞文学有什么关系,想不出她怎么会发表了一篇小说,怎么会参加了作协?他有点坐不住了,喝了一口她倒的水,看着桌面上带来的那包东西,想着:要不要送给她呢?
“我来你们县采访,顺路来看看你。”他说了这句谎话后,心情开始平静下来。哦——她抬头看了看他,苍白的脸色有了些红晕,“作协发了些书,顺便给你带来。”他取出了那几本书。他的那两本小说集,他没有拿出来。他突然觉得,那两本书实在是浅薄极了。
“啊——谢谢,谢谢。”她站起来到桌前翻着那几本书。他看出来,她还是喜欢文学的,但缺少某种搞文学的气质。
“好好地生活吧。”他站了起来。他明明知道,这句话对她不会有什么深刻的启示,但还是说出来了。
“再坐一会吧。”她流露出渴求的神态。
这是他曾盼望过的神态,然而此刻,他却看了看表,淡淡地一笑,“打扰你休息了,对不起。”
她送他出了学校大门。
在大门口,他们站住了。
“王老师,我快要调回城了。”她露出了欣喜的神态。“我的男朋友在城里公安局工作,他已经把我的户口都转走了,只是现在学校还不肯放……”
男明友,她有了男朋友?他心中一惊,转念又想:她为什么不能有男朋友呢?他微笑了一下,没有说什么。
她也微笑了一下。那微笑,跟她的整个人一样,此刻在他的心灵中再不是那么神秘而迷人了。谜底一旦揭开,一切就都平淡了。
“再见。”她又扬起了手。
“再见。”他也挥了挥手,直到走出很远,他都没有回一下头。他觉得那一点都不必要了。
他并不后悔这次相见,因为它帮助他解开了一个谜。使他明白了什么道理。要不然,他心中的那片隐情,不知道要纠缠他多长时间呢?
人生,是不是都要经历某种体验才能获得生活的真谛呢?他想。
乘车回到家里,妻子还没下班。他首先把那身西服脱下来,换上了上午穿的那身旧中山服,把那身西服刷了刷,叠得整整齐齐地又放回原位。然后,他挽起袖子,拉开了火炉。做起饭来。他在农村插队时学会了做饭,还颇受知青们赞扬呢。多少年没干过了,他有些笨手笨脚起来、饭烧糊了不说菜也炒得有些过了。妻子回来后,看着桌上已经摆好的饭菜,竟愣了。
晚饭后,乘妻子不注意,他从床底下拉出了一堆脏衣服。抱到水池里搓洗起来。妻子发现后,想拦住池。他平静而诚恳地说了声:“让我洗吧。你累了一天,歇吧。”说完,他对她微笑了一下。
妻子的眼睛忽然有些发红。
当然,只有他,才知道这其中的奥秘呢。在他的人生道路上,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刚刚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