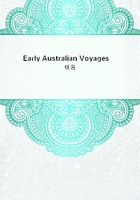第一节 汉代《诗经》学兴起的背景
汉代《诗经》学的兴起有着特定的背景,概括说来,主要包括思想、学术和社会文化三个方面。下面就从这三个方面,对汉代《诗经》学兴起的背景作一具体的讨论。
汉代《诗经》学兴起的思想背景主要是《诗经》“经”化在先汉的完成。
何谓《诗经》的“经”化?要弄清这个问题,先必须搞清楚“经”的含义。“经”字出现较早,至少在商周时就已经产生;当时出现的一些青铜器如虢季子白盘、齐陈曼簠等用金文铸刻的文字中就有“经”字。“经”开始出现时当与丝织有关,《说文解字》十三篇上丝部云:“经,织从丝也”,段玉裁注云:“织之从丝谓之经”[1]。“从丝”,即丝“织时的直线”[2]。周予同在《群经概论》中也有“经的本义是线”的说法[3]。后来学者用“经”字时,在“从丝”的基础上加以引伸,逐渐赋予“经”以“径”、“书籍”等含义。贾公彦在给《周礼·冬官考工记下》“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作疏时云:“南北之道爲經”;《释名·釋典藝》云:“經,俓也;如俓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韦昭给《国语·吴语》“挾經秉枹”作注时云:“經,兵書也”;陈延杰在《经学概论》中说:“編冊用韋連綴用絲,故借從絲之名爲典籍之號”[4]。随着内涵的扩展,“经”字又出现了“常”的含义。孔安国为《尚书·大禹谟》“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传云:“經,常”;《广雅·释诂》也说:经,“常也”。本文所谈的“经”就是“常”的意思。《白虎通义·五经》云:“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常”,“包括常道、常法”[5]等意思,也就是刘勰《文心雕龙·宗经》所说的“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文心雕龙·宗经》)。《诗经》的“经”化,就是《诗经》的“常”化,也就是使《诗经》成为“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作为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虽然“是周代社会生活及其礼乐制度的产物”[6],但本身是一部文学作品。儒家学者在长期的解诗传诗过程中,逐渐赋予了《诗经》特定的政治使命,把《诗经》变成载道传道的工具,认为《诗经》所讲的是“忠臣孝子之道,是治国平天下的道理”[7],利用《诗经》来宣扬儒家思想文化,指导政教方略和伦理行为,为个人修行和社会生活提供评判标准,使《诗经》法典化。这种法典化,就是《诗经》的“经”化。
《诗经》的“经”化是从孔子开始的。孔子之前,《诗经》就已经“在上层社会、贵族生活中被广泛应用”[8];“它不仅被用于各种典礼仪式,还被公卿士大夫们用作……赋诗言志的工具”[9]。孔子在继承《诗经》这种致用原则的前提下,对《诗经》进行“价值转换”[10],用《诗经》“来讨论做学问做人的道理”[11],对人进行政事、德行教育,使《诗经》的解读获得了“比较确定的内容与形式”[12],从而开始了《诗经》的“经”化。对于孔子导致《诗经》发展过程中的这种转变,许志刚在《诗经论略》中有详细的表述。他说:
《诗》的早期流传过程,就是被包装的过程,是被礼化的过程。在春秋赋诗中,《诗》的文本所受到的重视还要多一些,解《诗》者多为地位较高的政治家或各诸侯国的使者、行人。他们的礼的修养虽然普遍较高,但毕竟不是哲学家、思想家……因此,在解《诗》之时,其个人的理念还不是很突出,也不可能用这理念对《诗》进行新的包装,作出合于自己理想的阐释。
孔子则不然。他对西周时代的礼乐文化,对三代文化乃至上古文化有系统的、精湛的了解,并通过对前代文化的扬弃,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他站在这样的理论基点上阐释《诗》,借以发挥自己的理论主张,……他开创了以《诗》注我的先例,……这是二千余年的《诗经》学的滥觞,也为《诗经》学留下一些足以昭示其发展的思维定式和思维观点。[13]
孔子之后,“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史记·儒林传》)。与孔子相比,孟荀诸子,无论是在《诗经》内容的解读还是解《诗》方式上都有了极大的推进。孔子论《诗》,在讨论诗的政治功能的同时,还非常“注重诗的文学功能”[14];孟子论《诗》,有了很大的改变,开始着重“宣扬儒家的政治理想、伦理道德,而不再欣赏诗的文学造诣”[15]。在解《诗》方式上,孔子注重论诗,主要是通过讨论《诗经》的文句和内涵来阐发自己的思想;孟子在论诗的同时,逐渐把重点转向了对《诗经》的征引上了,“引《诗》证言”,通过“引《诗》证成己说”[16],在“引《诗》证言”的过程中体现自己对《诗经》的解说。据洪湛侯的统计,《论语》中涉及《诗经》的有二十处,其中,孔子论诗有十处,孔子本人引诗只有三处;《孟子》中涉及《诗经》的有三十九处,孟子本人引诗有三十处,论诗只有四处[17]。并开始形成引《诗》的习惯用语:引《诗》之前用“诗云”开头,引《诗》之后用“此之谓也”结束。解《诗》方式的这种转变,说明孟子已经开始有了“依《诗》立义”的意识。这无疑推动了《诗经》“经”化的发展。在孟子解《诗》的基础上,荀子又强调《诗经》以“圣人之道为归依”[18],指出《诗》“一之而可再也,有之而可久也,广之而可通也,虑之而可安也,反鈆察之而俞可好也。以治情则利,以为名则荣,以群则和,以独则足”(《荀子·荣辱篇》),认为对《诗》“少不讽诵,壮不论议,虽可,未成也”(《荀子·大略篇》),并把孟子在引《诗》过程中形成的习惯用语格式化(只不过是荀子把“诗云”换成了“诗曰”)。据洪湛侯的统计,《孟子》全书用“《诗》云……此之谓也”的只有五处,而《荀子》用“《诗》曰……此之谓也”的已经占到了四十九例之多[19]。这种发展无疑使《诗经》作为立义标准依据的性质和地位得到了彰显。由此可见,《诗》到荀子手中已基本具有了“经”的内涵。在这种背景下,《诗》开始有了“经”的称呼。《荀子·劝学篇》云:“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楊倞注云:“经,谓《诗》、《书》”。不过,这时对《诗》在政教中的地位、功用还没有确切的表述。作为“经”,《诗》的政教功能也是其法典化的一个重要体现,而这种政教功能一直到《礼记·经解》中才有确切的阐述和明确的界定。《礼记·经解》云: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於《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於《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於《乐》者也;絜静精微而不贼,则深於《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於《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於《春秋》者也。”
《经解》把诗教列为六教之首。根据孔颖达的疏,《经解》在这里表达出了这样的意思:《诗经》是“人君施化”,“为政以教民”的工具之一,“人君以六经之道,各随其民教之”;由于具有“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的特点,《诗经》能对民众进行“温柔敦厚”之教;这种教化决定着民风民俗的形成,人们从民风民俗中即可看出人君是否“深达於《诗》”教(引文均出自孔颖达疏)。《诗》的政教内涵在这里表述得是比较清楚的。因此,《诗经》“经”化的最后完成应该是在《礼记·经解》出现的时候。而据徐复观推测,《经解》是“秦初统一天下以后的荀子的一位门人的作品”[20]。因此,《诗经》“经”化的最后完成当在秦初统一天下之后。这也是《诗经》为什么在先秦一直称《诗》或《诗三百》,直到西汉才出现“诗”、“经”连称的根本原因。《诗经》在先汉“经”化的完成,是汉代《诗经》学兴起的思想背景。
汉代《诗经》学兴起的学术背景主要是先汉儒家在解《诗》传《诗》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的思想方法、在注经传经过程中使用和发明的一系列注经体式,具体说来有这么几点:
一是指导思想上的“《诗》言是,其志”。“《诗》言是,其志”语出《荀子·儒效》篇。原文为:“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对于这句话,杨倞注云:“是儒之志”。何谓“志”?《说文解字》云:“志,意也,从心”。闻一多先生考释:
志字从“?”,卜辞“?”作“?”,从“止”下“一”,像人足停止在地上,所以“ ”本训停止……“志”从“?”从“心”,本义是停止在心上。停在心上亦可说是藏在心里。[21]
萧华荣先生说:“‘志’既为‘藏在心里’,则诗所表达的,自然便是心灵的东西。心灵的东西包罗甚广,可以是意向、愿望、思想、怀抱,也可以是喜怒哀乐诸种情绪,所谓‘情、志一也’。不过在先秦以至后世,‘言志’往往侧重于指思想、意向、怀抱等,而与魏晋以后的‘诗缘情’说有异”[22]。“《诗》言是其志”,也就是说,《诗》言的是儒家的思想、意向、怀抱。
实际上,与“《诗》言是其志”相类的说法,早在孔子之前就已出现了。《尚书·舜典》云:“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不过,这个“志”还没有“严格的限定,它只是说明诗是诗人心灵的外现或其生命意蕴的流露,而不是对自然的模仿或理念的复制”[23]。《春秋左传》中也有“赋《诗》言志”的记载。《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云: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笫之言不踰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曰:“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曰:“‘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後亡。”
文中的“诗”,就是指《诗》;“诗以言志”,就是以《诗》言志[24],也就是赋《诗》言志。当时,诸侯之间会盟、朝聘,大夫之间交往,常常通过引用、诵读《诗经》来沟通、交流,赋《诗》言志。不过,这里所言的“志”,也不是“儒之志”,而是诸侯大夫之间相互交往上的一种“意向、愿望和虚与委蛇的酬酢周旋”[25]。
“志”的含义由这些表现向“儒之志”内涵的转变是从孔子开始的。孔子“将‘志’的意义在人性论的过滤中加以转换,从而限于‘仁义’的范围中,……迄于孟子,他更进一步强化了孔子的观念,……认定《诗》三百天然具有仁义的内质,……认为《诗》负有历史使命。”[26]孔子的《诗》可以“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和孟子的《诗》是“王者之迹”(《孟子·离娄下》)的说法都是这一认识的具体体现。“《诗》言是,其志”与孔孟的这种认识是一脉相承的,是这种认识的逻辑发展,是先秦儒家关于《诗经》属性认识的总结。这一思想把对《诗经》的解读引向了“儒家仁政礼治的思想体系”[27],成为先秦儒家对《诗》进行儒学化解读的前提和基础。上述《诗经》的“经”化过程就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也是这一思想的实践和运用。
二是解《诗》方法上的“断章取义”、“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断章取义”,就是说《诗》时,“其所取者,并非诗文本义,仅以诗文迁就自己所要表达之……意义”[28]。断章取义,是儒家说《诗》的“基本原则和方法”[29];孔孟荀说《诗》主要采用的是这种方法。《论语·八佾》还有这么一段文字: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是《卫风·硕人》的诗句,“素以为绚兮”为逸句。马融注云:“倩,笑貌;盼,动目貌;绚,文貌”。这本是用来赞美女子不假粉饰、美丽天成的,而孔子却用“绘事後素”来概括它的主题。“绘事后素”,郑玄曰:“绘,画文也。凡绘画先布众色,然后以素分布其间,以成其文,喻美女虽有倩盼美质,亦须礼以成之。”用诗来说明,“礼”在“成人”中的重要作用。又比如《孟子·万章下》记孟子对万章说:“欲见贤人而不以其道,犹欲其入而闭之门也。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诗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此诗出自《小雅·大东》,原是用来描绘西周官道的,孟子却用来说明“见贤人”之“道”。荀子解《诗》时也是“断章取义,随兴引用”[30]。用断章取义的方法说《诗》,是出于阐“经”的需要。儒家说《诗》,“旨在以‘道’导志,而《诗三百》不尽合于‘道’,甚至与‘道’无关,那自然非断章取义曲为发挥不可”[31]。
实际上,断章取义之法在春秋赋《诗》之中就已经开始了。据《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记载:
齐庆封好田而耆酒,与庆舍政。则以其内实迁于卢蒲嫳氏,易内而饮酒。数日,国迁朝焉。使诸亡人得贼者,以告而反之。故反卢蒲癸。癸臣子之,有宠,妻之。庆舍之士谓卢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独焉辟之?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恶识宗?”
从卢蒲癸之言,足可见在春秋赋《诗》中,断章取义的做法已很普遍。不过,儒家的断章取义与春秋赋《诗》的断章取义是有本质区别的。春秋断章,是“就当前的环境,做政治的暗示”[32],是一种临时取用;儒家断章,是为了阐发儒家思想和教化,“带有明确的指向性,事先规定了礼、仁义、无邪等儒家观念”[33]。自孔子开始,这种做法,即成为儒家说《诗》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以意逆志”也是一种解《诗》之法,语出孟子。《孟子·万章上》: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於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馀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
赵岐注云:“文,诗之文章所引以兴事也。辞,诗人所歌咏之辞。志,诗人志所欲之事。意,学者之心意也。”“以意逆志”,就是“指读者以自己之意,推求作者之心志与诗文之真正含义”[34]。由于“诗辞多隐约微婉,不肯明言,或寄托以寓意,或夸言而惊人,皆非其志之所在,若徒泥辞以求,鲜有不害志者”[35],因此,赵岐在注中接着说:
孟子言说诗者当本之,不可以文害其辞,文不显乃反显也。不可以辞害其志,辞曰“周馀黎民,靡有孑遗”,志在忧旱灾,民无孑然遗脱不遭旱灾者,非无民也。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实矣。
“以意逆志”,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断章取义”的解《诗》方法,是一种“坚守作品自身的‘本文批评’”[36],确切地说,是不利于对《诗》作儒学化的解读的。但由于强调了解《诗》者的“意”在解《诗》中的作用,强调了解《诗》者的主动性,有利于解《诗》者解《诗》时抛开成见,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同时,“以意的意,本身是漫无定准的”[37],也为“穿凿附会”解《诗》埋下了伏笔;孟子本人,由于执著于以《诗》明“道”,在具体解《诗》时仍然是断章取义,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除了“以意逆志”外,孟子还提出了“知人论世”的解《诗》方法。《孟子·万章下》云:
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这段话讨论的主要是士的修养问题。在讨论过程中,作者为我们提出了“知人论世”的解《诗》方法。所谓“知人论世”,就是要求解《诗》者“了解作者的生平事迹及其所处的时世环境,方能准确把捉诗人之志”[38]。也就是说,解《诗》时要注重作者情况与作品创作的历史文化背景[39]。这个方法,在孟子解《诗》过程中也得到了极大的应用。如《孟子·梁惠王上》载: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顾鸿鴈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於牣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
等等。
三是使用和发明了一系列注经体式。《诗经》学的学术内容和形式主要是通过故、传、说、章句等手段来反映和体现的,两汉《诗经》学的繁盛与注《诗》体式的发达是分不开的。而两汉诸如故、传、说、章句等主要注《诗》体式在先汉均已为儒家所使用和发明。先汉儒家在注经体式上的运用和发明为汉代《诗经》学的兴起准备了条件。传,“是转述的意思,是阐明经义的”[40]。《祭统》注“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徳善、功烈、動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云:“酌之祭器,言斟酌其美,傅著於鐘鼎也”,《释文》云:传,“谓传述”;《春秋谷梁传序疏》:“傳之解經,隨事則釋”。《荀子·大略》云:“国风之好色也,传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诚可比於金石,其声可内於宗庙。’”;吕思勉在《燕石札记·传说记》中证实:此为“孔门诗传”[41]。说,《说文》云:“说,释也;一曰谈说”;又云:“释,解也”。《周易》中先秦儒家所作的《十翼》里有《说卦》一文。故,与诂、古字通,“是以今言释古言”[42]。《孟子·离娄上》云:“诗曰:‘天之方蹶,无然泄泄。’泄泄,犹沓沓也。”“泄泄,犹沓沓也”,就是以当时流行语解释古语。黄以周在《读〈汉书·艺文志〉》中说:“《十翼》,本不名传,《彖》、《象》依经立训,与故训近”[43]。章炳麟《国故论衡·明解故上》云:“先民言故,总举之矣,有故事者,有故训者。《毛诗》以外,三家亦有《鲁故》、《韩故》、《齐后氏故》、《齐孙氏故》,斯故训之流也。《书》、《春秋》者,记事之籍,是以有故事。《太誓》有故,犹《春秋》有传。”[44]传、说、故诸体,并非儒家首创和独用。《国语·周语下》记单襄公云:“吾闻之大誓故曰:‘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韦注云:“故,故事也”;这也就是章炳麟所说的“《太誓》有故”。说体如《墨子·经说》、《韩非子·说林》等。传体在孔子之前也已出现,像《史记·伯夷列传》记载的佚诗传即是。不过,他家用这些体式,非专用来注六经;而且也没有哪一家像儒家这样比较全面地使用这些体式。儒家这样做,主要还是注经的需要。当然,除了这些体式之外,儒家在注经的过程中,根据需要,也有创新和发明,如章句这种体式,就是儒家首创。后汉徐防在上疏中说,《诗》、《书》、《礼》、《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后汉书·徐防传》)。章句,就“是在解释词义之外,再以分章析句的方式串讲经文大意,为的是使文章意义更为明显。”[45]《后汉书·桓谭传》记桓谭:“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李贤注云:“章句谓离章辨句,委曲枝派也。”沈钦韩《汉书疏证》云:“章句者,经师指括其文,敷畅其义,以相教授”[46]。章句也是传注的一种,但往往传注比较简明而章句比较繁琐。
先汉儒家在解《诗》传《诗》过程中形成的思想方法以及在注经传经过程中使用和发明的注经体式,是汉代《诗经》学兴起的学术背景。
汉代《诗经》学兴起的社会文化背景是《诗经》在秦汉之际的广泛流传。《诗经》产生的确切年代现在已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诗经》的产生至少是为了官府教育的需要。《礼记·王制》云:“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嫡子、国之俊选,皆造焉。”。匡亚明在《孔子评传》中说:
周代贵族教育,是随着人的年龄的上升而循序渐进的。幼年时在小学里学习认字、写字、算术、音乐、唱歌、舞蹈和射箭、驾车等,这些就是六种技艺性的“小艺”。成年以后,进“大学”学习上述六种高级的典籍即《诗》、《书》、《礼》、《乐》、《易》、《春秋》,使人的知识由知其然进而知其所以然,从而提高学业和道德水平。[47]
一直到春秋后期,这种教《诗》之风在官府教学中依然存在。据《国语·楚语上》记载:楚庄王使士亹傅太子箴,士亹就此向申叔请教,申叔指出要“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还强调要“诵《诗》以辅相之”。这种风气使得《诗经》在当时上层社会和知识分子阶层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春秋引《诗》赋《诗》之盛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据萧华容先生统计,《左传》、《国语》引诗多达二百五十条,其中百分之九十五见于今本《诗经》,佚诗甚少;赋《诗》《左传》也有七十余次,《国语》也有一些记载[48]。这种盛况说明了当时《诗经》在上层社会的流布之广。春秋末年,随着“王室衰微”,学术下移,开始出现私人办学。孔子是私人办学的开创者。他在开创私学时,“也沿袭着当时官府之学的教学内容”[49],用《诗经》等教学生,“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史记·孔子世家》)。《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三千肯定不是确数,但至少可以说明孔子教授的学生确实是很多的。在办学过程中,孔子推行“有教无类”的教学思想(《论语·卫灵公》),不论国籍、贫富、贵贱等[50],只要“自行束脩以上”,就“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这种做法,在推进《诗经》传播的同时,无疑也使《诗经》走向了下层社会,为《诗经》的传习奠定了雄厚的群众基础。
孔子之后,其学生继承他的事业,继续传学。《史记·儒林传》云:“仲尼既没,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进一步推动了《诗经》的流布,使得“后陵迟以至于始皇,……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门学者独弗废也”(《史记·儒林传》)。
此外,战国之后,随着由孔子开其端的私人办学日盛,《诗经》的私藏也越来越普遍。《史记·六国年表》所记“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即是实证。这种私藏,为《诗经》广泛传播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而《诗经》独特的传播方式也有利于《诗经》的保护和流传。《汉书·艺文志》云:《诗》“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
与此同时,秦汉之际儒家文化又有着比较宽松的发展环境。二世无道,天下分崩,混乱的政局打破了始皇时期对文化的禁锢。《汉书·儒林传》云:“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术士,六学从此缺矣。陈涉之王也,鲁诸儒持孔氏礼器往归之,于是孔甲为涉博士”。尽管当时的农民政权并没有为儒家文化的复苏提供实在的发展环境、创设必需的发展条件,但至少还是给了儒学一片可以生长的土壤。及至后来,“高皇帝诛项籍,引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汉书·儒林传》),固然是鲁地受儒家教化之深的表现,也反映了起义政权对儒家文化的宽松和温和。汉初,推行的是无为之治,对儒家文化也是颇为客气的。《史记·儒林传》云:“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孝惠当政,虽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史记·儒林传》),却也有“除挟书律”的举措(《汉书·惠帝纪》),对儒家文化并不苛刻。孝文虽然好刑名之言,对儒士还是“颇征用”(《史记·儒林传》)。景帝虽然“不任儒者”,至少还是给了他们“具官待问”的资格(《史记·儒林传》)。各藩国对儒家文化也不排斥,并且在诸侯王中“颇有倾心养士,致意于文术者”,如楚元王交、吴王濞、梁孝王武等[51]。
在这种宽松的环境下,《诗经》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无论是汉初的“《诗》、《书》往往间出”(《汉书·司马迁传》),还是孝武时期的“颇有《诗》、《礼》、《春秋》先师”(《汉书·刘歆传》),都说明《诗经》在秦汉之际的传播已有雄厚的基础。
《诗经》在秦汉之际的广泛流传是汉代《诗经》学兴起的社会文化背景。
第二节 汉代《诗经》学的兴起和发展
汉代《诗经》学的兴起,以四家诗的出现为标志。四家诗,即鲁、齐、韩、毛诗。《后汉书·儒林传下》云:“鲁人申公受《诗》于浮丘伯,为作诂训,是为《鲁诗》;齐人辕固生亦传《诗》,是为《齐诗》。燕人韩婴亦传《诗》,是为《韩诗》;……赵人毛苌传《诗》,是为《毛诗》”。《诗》分为四,反映了各家《诗》学特点已成,汉代《诗经》学的内涵已经有了明确的界定;因此,汉代《诗经》学的兴起应以四家诗的出现为标志。四家诗出现的时间,《史记·儒林传》云:“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今上”,是指武帝。根据《汉书·武帝纪》记载,武帝开始诏举“贤良方正”之士是在建元元年,从行文看,鲁、齐、韩等诗的明确区分和申培、辕固诸人《诗》宗地位的确立好像是在武帝建元元年之后。实际上,武帝之前文景时期,四家诗就已形成并得到流传。《汉书·儒林传》云:“申公,……少与楚元王交俱事齐人浮丘伯受《诗》。汉兴,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于鲁南宫。吕太后时,浮丘伯在长安,楚元王遣子郢与申公俱卒学。元王薨,郢嗣立为楚王,令申公傅太子戊。戊不好学,病申公。及戊立为王,胥靡申公。申公愧之,归鲁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复谢宾客,独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千余人,申公独以《诗经》为训故以教,亡传,疑者则阙弗传。兰陵王藏既从受《诗》,已通,事景帝,为太子少傅,免去”。兰陵王藏受《诗》当在孝景帝时,受《诗》之前,申公已“以《诗经》为训故以教”,因此,鲁诗出现当不晚于景帝之时。《汉书·楚元王交传》又云:“文帝时,……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则知,在文帝时鲁诗就应已出现。辕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诸齐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也”(《汉书·儒林传》);至于其开业授徒始于何时,史料没有明确记载,但从他至武帝时年“已九十余”的情况看,当也不至于晚于文景之时。韩婴,“孝文时为博士,景帝时至常山太傅。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汉书·儒林传》)。史书未言韩婴为《诗》作内外传及以《诗》教的时间,但从接下来的“武帝时,婴尝与董仲舒论于上前,其人精悍,处事分明,仲舒不能难也”(《汉书·儒林传》)句;亦可推见,韩婴解《诗》成一家之言并广泛传学亦当在武帝之前。毛诗,郑玄《诗谱》是这样说的:“鲁人大毛公为《诂训传》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晋陆玑《诗草木虫鱼疏·序》云:“毛亨作《诂训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亨大毛公,苌小毛公”;由此可见,毛诗在河间献王得到之前就已成学。而献王得毛诗也是在武帝之前。《汉书·景十三王传》云献王“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未言时间。但从接下来的“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句的行文可知,毛诗被立为博士应在武帝前。《汉名臣奏》亦可佐证,其曰:杜业奏:“河间献王经术通明,积德累行,天下雄俊众儒皆归之。孝武帝时,献王朝,被服造次必于仁义。问以五策,献王辄对无穷。孝武帝色然难之,谓献王曰:‘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归即纵酒听乐”,不再理儒事,并“因以终”。因此,四家《诗》的出现应该是汉初武帝之前不晚于文景之时。
当然,汉代《诗经》学是不是只有这四家,现在还有争论。《汉书·楚元王交传》曾经说过:“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但这个《元王诗》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否流传了,《汉书》只有一句“世或有之”(《汉书·楚元王交传》),此后再无交待。《汉书·艺文志》录刘歆《七略》云:“凡《诗》六家,四百一十六卷”。这六家是指那六家,周寿昌《汉书注校补》认为:“六家者,鲁、齐、韩、后氏、孙氏、毛氏也。然后氏《故》与《传》、孙氏《故》与《传》仍说《齐诗》也。实则止四家”[52]。张舜徽先生认为:“《诗》之《经》文二十八卷,一也;《鲁故》、《鲁说》,二也;《齐后氏故》、《传》、《杂记》,三也;《齐孙氏故》、《传》,四也;《韩故》、《内传》、《外传》、《韩说》,五也;《毛诗》、《故训传》,六也。六家之说,当以此定之”[53]。从张先生的分析来看,实际还是指鲁、齐、韩、毛四家。1977年,安徽阜阳汉墓出土了一些《诗经》残简,简文与四家诗有出入,据此又有学者认为,《阜诗》“可能是未被《汉志》著录而流传于民间的另外一家”[54],洪湛侯甚至认为,可能与《元王诗》有关[55]。实际上,仔细分析一下当时的环境,这些疑问应该都是可以得到开解的。据考证,阜阳《诗》简是汉文帝十五年以前的版本[56],而当时正是秦火之后,文化刚刚开始复苏的时候,《诗经》主要是来自民间私藏,讽诵传抄之间,肯定会出现诗文不同的情况。特别是四家诗尚处在最初的诞生阶段,还没有足够的实力和社会地位去广泛推行自己的《诗经》版本和《诗》学主张。经过汉初多年的发展,在政府和诸侯的推动下,四家诗以自己富有成果的《诗》学思想获得社会的广泛接受,并形成四家鼎立的局面,而其他一些《诗》学主张因失去接受者而逐渐湮没散亡,汉代《诗经》学最终形成四家各自传授的格局。因此,汉代《诗经》学兴起之后,特别是武帝之后,应该就不存在还有他家流传的情况,否则,绝不至在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中没有留下任何印迹。
从四家诗的出现看,汉代《诗经》学的兴起有这么几个特点:
首先是治《诗》的学者专门化。汉初传《诗》者,无论是申培、辕固,还是韩婴、毛苌,均有别于先汉诸如孟子、荀子这样的思想家。孟子、荀子非以传经为业,主要是通过经来阐发思想;他们综治六经或几经。申、辕诸人,也用经来阐发思想,但主要是以治《诗》为主;他们以《诗经》为中心,围绕《诗经》作解释和创发工作,并顺着《诗经》形成他们的思想。从史料看,申培、辕固、韩婴、毛苌的主要事迹都是习《诗》、解《诗》、传《诗》。申培用《谷梁春秋》教过学生,但未为之作过传或训诂以阐发自己的思想,不然史籍不会无载;也未大肆传授。韩婴“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为之传”,然“燕赵间好《诗》,故其《易》微”(《汉书·儒林传》),因此,他毕生的事业主要还是阐《诗》、传《诗》。申、辕、韩、毛四人治《诗》的专门化,从他们被汉廷或诸侯置为《诗》博士就可看出来。
博士,本指“博学通达之士”[57]。据徐复观先生推测,博士一词,与儒家的“博学于文,约之以礼”有关[58]。博士称谓,最早出现在战国初期。《史记·循吏列传》云:“公仪休者,鲁博士也”,《孟子·告子下》记:“淳于髡曰:‘鲁缪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王国维先生认为:“公仪休即《孟子》之公仪子”[59]。当时博士与职官无关,“所云博士者,犹言儒生耳”[60]。战国末年,齐、魏、秦等开始设置博士之官;秦统一六国之后,整齐官制,置博士官七十人,主要是“通古今”、“辨然否”、“典政教”[61]。汉承秦制,也设立了博士官制度。至孝文皇帝,“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文帝均“为置博士”(《汉书·刘歆传》)。此处“所言‘立于学官’,非指学官博士,因为文帝时博士还不是学官,这里的学官即学馆”,“立于学官”是指诸子传说“已经被允许在学馆公开讲授;‘为置博士’是指具有一书之专长者就可能被任为博士官”[62]。随着儒家经籍的兴起,文帝还为“《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赵岐《孟子章句题辞》),并立《诗》博士[63]。景帝时,一些治儒学的经生如董仲舒等继续被立为博士。尽管治书的内容有所改变,但“具有一书之专长者就可能被任为博士官”的性质没有改变。
辕固为孝景帝《诗》博士,这在上引资料中已有反映。申培,《汉书·楚元王交传》记载:“文帝时,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而当时文帝“始置一经博士”(《后汉书·翟傅酺传》);这个博士,除了《诗》之外当然就不可能是别的博士了。韩婴,史书虽未指明为何博士,有关资料还是给了交代。韩婴为博士是在文帝的时候,文帝除了给《论语》、《孝经》、《孟子》、《尔雅》、《诗》置博士了外,没有给其他儒家经籍置博士,韩婴虽然作过《易传》,不可能是《易》博士,而应该是《诗》博士;秦学颀在《中国经学史》中也说韩婴是“以治《诗》为博士”[64]。既然三人均是《诗》博士,当然是以治《诗》为专长了。毛苌为河间献王德《诗》博士,而诸侯“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汉书·百官公卿表上》),故其职掌所司,亦当如申、辕诸人。因此,无论是申公、辕固还是韩婴、毛苌,在传学过程中主要还是专门以《诗》为业。
治《诗》学者的专门化,既是《诗》“经”化的结果,也是私学发展的产物,对两汉《诗经》学诸如师法、家法等诸多学术形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文景之后,治《诗》专门化成为汉代《诗经》学发展的主要潮流。
汉代《诗经》学兴起的第二个特点是四家师承渊源相同。四家诗渊源,除了齐诗,另外三家文献均有记载。鲁诗申培,师从浮丘伯;浮丘伯,根据《汉书·楚元王交传》记载,是“孙卿门人”。孙卿,颜师古注云:“姓荀名况,为楚兰陵令,汉以避宣帝讳,改之曰孙”。也就是,鲁诗源自荀子。毛诗,据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记载:孔子授《诗》“卜商,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曾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荀卿授鲁国毛亨,亨……授赵国毛苌”。荀卿就是荀子。由此可见,毛诗也是师承荀子。韩诗,《新唐书·艺文志一》云:“卜商《序》,韩婴《注》二十二卷”。卜商即子夏,荀子之学源自子夏。韩诗是否出自荀子,此处无文,但既然是由子夏所传,其源亦应与鲁毛同。实际上,关于四家诗学渊源,刘申叔在《诗分四家说》里已经作了讨论。他说:“子夏之时,四家之说实同列一书……荀卿之世,四家之诗仍未分立。嗣由荀卿弟子所记各偏,各本所记相教授,由是诗谊由合而分”[65]。除了师承荀子之说外,一些学者又提出,四家《诗》学与孟子也有关联。刘立志在《孟子与两汉〈诗〉学》中认为,“纵览《诗经》学的发展历程,孟子是一个开创新风的人物,它对于汉代《诗经》学的发展与演进有着特殊的贡献”。在详细考证有关资料的基础上,他指出,“孟子的某些思想观点,直接为汉代诗学三家(指鲁齐韩)经师所继承,有的还在孟子说解的基础上有所发挥”,“孟子与毛诗也是渊源极深。毛诗学派吸收了不少孟子的解诗观点,欧阳修曾云:‘今考毛诗诸序与孟子说《诗》多合’”,“孟子对汉代《诗》学的影响并不局限于这些零碎的解说,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诗论初步限定了汉代《诗经》学体系的框架,奠定了汉儒说《诗》的规范”[66]。这些认识都是有道理的。儒家通《诗》本是为了致用,先汉儒学也不像两汉那样有着严格的门户师规。他们在解《诗》用《诗》过程中,吸收孟荀等先师的思想精华,以此为基础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因此,确切地说,两汉诗学的师承渊源是孟荀诸子,而不仅仅是荀子。同源决定了四家在《诗》说大义和说《诗》方法等诸多方面的一致性。
汉代《诗经》学兴起的第三个特点是四家诗存在着不同的流传地域。四家诗传者申公、辕固、韩婴和毛苌都不是一个地方的人,申公为鲁人,辕固为齐人,韩婴为燕人,毛苌为赵人;各自传《诗》,也不出其故土。上文所说,申公受王戊胥靡之后,“愧之,归鲁退居家教”,传《诗》之地在鲁,所习者当以鲁人为主,其弟子孔安国等均为鲁人。齐诗史料未言传《诗》之地,但从“诸齐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看,其传当以齐地为主。韩诗,史书已明言“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说明韩诗所传以燕赵为主。毛诗,诗书仅言毛苌“授同国贯长卿”(《汉书·儒林传》);但从其为河间献王德博士亦可看出,毛诗所传以赵地为主。《汉书·地理志下》云:“赵地,……东有广平、巨鹿、清河、河间”。河间为赵地,毛苌既为河间博士,其所传当亦为赵地。地域不同,当然就会影响到《诗》的解读和传授。
汉代《诗经》学兴起的第四个特点是四家说《诗》要旨和方法相同。受流传地域等因素的影响,四家诗在对经文的解读上有互异的地方,正如《史记·儒林传》评论韩诗时所说:“其语颇与齐鲁间殊”,这种“殊”不仅仅限于三家诗,实际上是四家解《诗》时都存在的。不过,这种互异仅仅只是表现为用词习惯和对一些具体《诗》篇理解的不同,大旨并无差别。四家解《诗》的“精神实质和归趣皆是一致的”[67]。其互异是在要旨相同下的互异。正如徐复观先生所言:“从内容上言四家《诗》的异同,应在‘推诗人之意’的传而不在文字与故训,但齐、鲁《诗》的传、说、记皆早已亡佚,无可比较,就现存的《韩诗传》与《毛诗故训传》中的传来说,虽小有异同。但《汉志》所谓‘其归一也’的断定,可应用于四家《诗》的《诗》传,是客观而合理的断定”,四家诗并无“水火不容的门户异同之帜”[68]。也就是说,四家在传解《诗》时,是有互异,但是这种互异是在大义“归一”下的互异。在说《诗》方法上,四家“大抵以解说、作传与章句为主”[69],亦无本质差别。
从武帝开始,汉代《诗经》学特别是鲁齐韩三家又获得极大的发展。武帝之前,鲁齐韩三家就已经立于学官;武帝上台,置五经博士,继续将鲁齐韩三家分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武帝又接受公孙弘的建议,用考试之法,明经取士,“诱以利禄”[70],以推动经学的传习。在这种背景下,三家诗学者分别以《诗》教授,徒众广布,《汉书·儒林传》就有:“申公卒以《诗》……授,而瑕丘江公尽能传之,徒众最盛……(齐诗)满昌授九江张邯、琅邪皮容,……徒众尤盛……(韩诗栗)丰授山阳张就,顺授东海发福,……徒众尤盛”等等这样的说法;有的为谋取利禄,甚至还“家世传业”(《汉书·儒林传》)。一直到“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大师众至千余人”(《汉书·儒林传》)。在传习过程中,三家诗开始出现一些支学流派,如《鲁诗》有韦氏学、张、唐、褚氏之学、许氏学,《齐诗》有翼、匡、师、伏之学,《韩诗》有王、食、长孙之学等等;对《诗》的解说也越来越详密,有的甚至出现了“一经说至百余万言”(《汉书·儒林传》)。这种状况,既是当时三家《诗》学繁盛的表现,又极大地推动了三家《诗》学的发展。三家诗也因此卿相辈出,如鲁诗学者韦贤、韦玄成父子皆位至丞相,齐诗学者翼奉至谏大夫、萧望之至前将军、匡衡至丞相,韩诗学者蔡谊亦至丞相等等;有的甚至还为王者师傅,如韦玄成及兄子赏曾以《诗》授哀帝,元帝在诏书中也有过“故前将军望之傅朕八年”的说法(《汉书·元帝纪》)等等,对当时的政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这种发展,到西汉末年,因“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后汉书·儒林传上》),而出现困挫,但时间很短,光武中兴,继续立五经博士,并仍将《诗》齐、鲁、韩三家分设。明、章继踵,三家诗的发展势头不减武宣之世,正如皮锡瑞所言:“经学自汉元、成至后汉,为极盛时代。……由汉武开其端,元、成、及光武、明、章继其轨”[71]。经学所云,自然包括三家诗在内。
与三家诗官学兴盛形成鲜明的对比,自武帝开始,毛诗就未立学官,一直到哀帝的时候,还是以私学形式出现。个中原因,徐复观先生认为是汉代“在专制下对诸侯王的特别猜嫌禁制”所致[72]。他说:
两汉承先秦余绪,游士之风尚盛。此即诸侯王及富贵者门下的宾客。宾客之品类不齐,多随主人之所好而类集。但有一共同特点,他们都是社会上比较富有活力的一群。诸侯王中若有好学自修之人,则其所集者多在学术上有某种成就之士;于是宾客之所集常成为某种学术的活动中心,亦为名誉流布之集中点。这对知识分子及学术的发展而言,常可以发生很大的鼓励作用。但却触犯了专制者的大忌。……刘德的河间,乃当时一学术中心之地。而他本人则系其领导人物……则武帝的猜嫌逼迫乃自然之事。[73]
而毛诗博士因为刘德所立,“遂为当时的大讳;尔后遂为鄙陋之儒,为保持其学术上之特权所借口,以专擅利禄之途”[74]。这个看法,我认为是很有见地的。
尽管未立于学官,毛诗在当时的流传仍然是通畅的。由于未立于学官,对毛诗的传授情况,史书记载不如三家诗明确具体,但其传授线条仍然清晰可见。《汉书·儒林传》云:“毛公……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授同国贯长卿。长卿授解延年。延年为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陈侠,为王莽讲学大夫。由是言《毛诗》者,本之徐敖。”这个线条说明,毛诗并没有因为流落民间而萎顿和衰败,而是继续为士人所接受和传习。平帝登基后,毛诗因刘歆被列于学官,设置博士,不过这已经是末世。光武中兴,毛诗仍被排除在官学之外,但其官学影响却在进一步扩大,并逐渐得到皇帝的重视。章帝时,诏令贾逵“撰《齐》、《鲁》、《韩诗》与《毛氏》异同”(《后汉书·贾逵传》);建初八年(83年),又“诏高才生受……《毛诗》……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后汉书·儒林传上》)。诏书颁布后,毛诗“由是……遂行于世。皆拜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朝夕受业黄门署,学者皆欣欣羡慕焉”(《后汉书·贾逵传》)。在这种背景下,从贾逵撰四家诗异同开始,一些大儒如马融、郑玄等开始沟通四家诗说,从而直接导致了鲁齐韩三家诗的衰败。
实际上,鲁齐韩三家诗的衰败是从和帝开始的。两汉经学传承重师法和家法,诗学亦不例外,而和帝永元十四年徐防在上疏中云“太学试博士弟子,皆以意说,不修家法”(《后汉书·徐防传》),由此可见三家诗学当时已露败相。邓太后称制之后,进一步加剧了这个衰败过程。《后汉书·儒林传上》云:
及邓后称制,学者颇懈。时樊准、徐防并陈敦学之宜,又言儒职多非其人,于是制诏公卿妙简其选,三署郎能通经术者,皆得察举。自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牧儿荛竖,至于薪刈其下。顺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黉宇,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试明经下第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除郡国耆儒皆补郎、舍人。本初元年,梁太后诏曰:“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飨会之,以此为常。”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
在这种情况下,三家诗开始走向没落。
随着三家诗的衰微和毛诗的兴盛,马融开始遍注群经,“混淆家法”[75]。马融之后,郑玄继承他的治学方法,并把它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进一步打破了之前家法林立的局面。“他笺《诗》以毛本为主,又博采鲁、齐、韩三家之所长”,使四家“不复分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混然一体”[76]。郑玄综合四家的做法,窒息了汉代《诗经》学的研究气氛。郑学出现之后,虽然遭到很多儒士的反对,但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继承了郑学,当然,更多的是把《诗经》学束之高阁。在这种背景下,汉代《诗经》学也就逐渐走向了“中衰”。这也就是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所说的“郑学出而汉学衰”[77]。
注释:
[1](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644页。
[2]徐复观:《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50页。
[3]朱维铮:《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07页。
[4]陈延傑:《经学概论》,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十九年,第1页。
[5]徐复观:《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50页。
[6]洪湛侯:《诗经学史》,中华书局,2002年,第1页。
[7]李申:《中国儒教史》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1页。
[8]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先秦卷,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87页。
[9]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先秦卷,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88页。
[10]徐复观:《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3页。
[11]朱自清:《经典常谈》,三联书店,2004年,第32页。
[12]徐复观:《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3页。
[13]许志刚:《诗经论略》,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1页。
[14]洪湛侯:《诗经学史》,中华书局,2002年,第90页。
[15]洪湛侯:《诗经学史》,中华书局,2002年,第90页。
[16]洪湛侯:《诗经学史》,中华书局,2002年,第90页。
[17]洪湛侯:《诗经学史》,中华书局,2002年,第78页。
[18]洪湛侯:《诗经学史》,中华书局,2002年,第97页。
[19]洪湛侯:《诗经学史》,中华书局,2002年,第96页。
[20]徐复观:《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51页。
[21]朱自清:《诗言志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页。
[22]萧华荣:《中国诗学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9页。
[23]刘立志:《孟子与两汉<诗>学》,《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
[24]萧华荣:《中国诗学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0页。
[25]萧华荣:《中国诗学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0页。
[26]刘立志:《孟子与两汉<诗>学》,《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
[27]萧华荣:《中国诗学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3页。
[28]康晓城:《先秦儒家诗教思想研究》,文史哲出版社,中华民国七十七年,第42页。
[29]萧华荣:《中国诗学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5页。
[30]康晓城:《先秦儒家诗教思想研究》,文史哲出版社,中华民国七十七年,第239页。
[31]萧华荣:《中国诗学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5页。
[32]朱自清:《经典常谈》,三联书店,2004年,第32页。
[33]刘立志:《荀子与两汉〈诗〉学》,《中国文学研究》,2001(2)。
[34]康晓城:《先秦儒家诗教思想研究》,文史哲出版社,中华民国七十七年,第217页。
[35]康晓城:《先秦儒家诗教思想研究》,文史哲出版社,中华民国七十七年,第218页。
[36]萧华荣:《中国诗学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6页。
[37]康晓城:《先秦儒家诗教思想研究》,文史哲出版社,中华民国七十七年,第220页。
[38]萧华荣:《中国诗学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6页。
[39]陈桐生:《孟子是西汉今文经学的先驱》,《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0(2)。
[40]张三夕:《中国古典文献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07页。
[41]吕思勉:《燕石札记》,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六年,第8页。
[42]张三夕师:《中国古典文献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08页。
[43]转引自周大璞:《训诂学初稿》,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1页。
[44]章太炎:《国故论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69页。
[45]张三夕师:《中国古典文献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10页。
[46]转引自周大璞《训诂学初稿》(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7页)。
[47]匡亚明:《孔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37页。
[48]萧华荣:《中国诗学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6-7页。
[49]吴雁南等:《中国经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页。
[50]赵吉惠在《中国儒学史》中通过对孔子所教学生进行详细梳理之后指出:“孔门弟子,不但国籍不同,而且贫富、贵贱不等”(赵吉惠等主编《中国儒学史》第64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51]鲁迅:《汉文学史纲》,《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95页。
[52]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中华书局,1983年,第40页。
[53]张舜徽:《广校雠略 汉书艺文志通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05页。
[54]胡平生、韩自强:《阜阳汉简〈诗经〉简论》,《文物》,1984(8)。
[55]洪湛侯:《诗经学史》,中华书局,2002年,第148页。
[56]刘跃进:《贾谊《诗》学寻踪》,《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3(1)。
[57]吴雁南等:《中国经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8页。
[58]徐复观:《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56页。
[59]王国维:《汉魏博士考》,《观堂集林》卷四,中华书局,1959年。
[60]王国维:《汉魏博士考》,《观堂集林》卷四,中华书局,1959年。
[61]吴雁南等:《中国经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9页。
[62]赵吉惠等:《中国儒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45页。
[63]吴雁南等:《中国经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9页。
[64]吴雁南等:《中国经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9页。
[65]刘师培:《左庵集》(一),《刘申叔先生遗书》(37),宁武南氏校印。
[66]刘立志:《孟子与两汉〈诗〉学》,《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
[67]萧华荣:《中国诗学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2页。
[68]徐复观:《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15页。
[69]孙筱:《两汉经学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19页。
[70]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第73页。
[71]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第101页。
[72]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1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7页。
[73]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1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7,111页。
[74]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1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1页。
[75]章权才:《两汉经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50页。
[76]章权才:《两汉经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50页。
[77]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第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