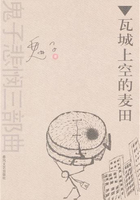阳春三月,太阳暖洋洋的。各个大队组织社员,排练革命样板戏,要层层汇演,六月初全省集中优秀节目,要汇报演出。大队定了《沙家浜》和《红灯记》选段,由俊明家老二安民扮演胡司令、三队的周联社扮演刁德一、五队的菊香装扮阿庆嫂。排练了一个星期,孙书记在喇叭上通知,晚上给社员们汇报演出。
几个演员化好装,随着边鼓敲起,锣鼓家伙跟上,阿庆嫂碎步走出来,做了个造型,刚张开嘴,露出了龇着的门牙。四队的琅琅在台下喊道:“牙龇得很,不像阿庆嫂!”
台下哄笑着。菊香阴下脸,离开了节奏,瞪了琅琅一眼,又回到戏中。安民长得精干,穿上胡司令的军服,宽松但有点短,脚腕子露出了一截子,表情仪态秀美。胡司令走上台,二省挥着手喊道:“安民,好好演,你伯来了!”
保民笑了一下,不敢向二省这边看了。刁德一阴着脸上台,腮下一撮毛不停地动着,一副精明刁钻的模样。智亮看到一半,笑着说:“联社,眼睛要不停地转,有点呆!”
联社一只手插在皮带中,另一只手里夹着羊群烟,他看了智亮一眼,笑着又和阿庆嫂聊了起来。
公社组织农民诗歌比赛,请村上有文化的人和学校老师一起写诗,一字一句地教给目不识丁的老农民。二队推荐智亮到大队比赛,孙书记觉得智亮像个算命先生,整天眨么着眉毛,不知道想些啥,而且还被公社批斗过,就把智亮给刷下来了。村上有好些农民,张嘴就是一串顺口溜,虽然朗朗上口,内容却有点低俗,没有达到上面在田间地头体现政治的要求,孙书记都没有通过。
公社戏曲汇演的时候,大队只有《红灯记》选段被公社干部一致通过,参加县上的文艺汇演。扮演铁梅的是在公社编篮篮的吴晓梅,听说十分活跃。她的节目入选后,公社田干事还专门请县剧团的专业演员,对她进行了指导,板胡也是县上的专业人士。
铁梅甩着长辫子,穿着红底白花的上衣,靛蓝色的裤子飘出来的时候,台下的人都愣住了,屏住了呼吸,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的每一个神态。田干事坐在杨主任的边上,不停地给他介绍着演员。吴晓梅不用假辫子,平时走路的时候,一条长辫子随着胳膊的摆动,辫梢在浑圆翘起的屁股上荡来荡去,后面总是跟着几个小伙子。她知道他们在看什么,她很大方,总是回过头来掩着嘴,咯咯地笑着。铁梅在台子上转身提红灯的时候,整条裤子都很空,只有屁股撑得实实的,随着腰肢的摆动,一颤一颤的。
小麦返青了,麦垄间生出了杂草和野菜。放学的时候,村上的小孩提着担笼,到麦田里挖野菜,农家汤面碗里有了青色。
老五带着三护队的两个人,在坟冢之间打胡基。他们将湿湿的黄土捣碎,堆成一堆,地上放着一个碾盘子,上面放上胡基架子。窑娃提起架子,用挡板来回刷了一下碾盘,敲打着架子,收拾干净后,将胡基架子放在碾盘中间,插进挡板,从粪笼里抓起一把灰,晃动着手腕,将炕灰撒在架子里。联社操起锨,铲起两锨土,倒在胡基架子的槽中。窑娃抓起西瓜大小的平底青石锤子的柄,跳上架子,先抬起脚后跟,在长方形架子的四个角上,踩踏几下,然后提起锤子,轻轻地平捶几下。黄土粘住了,成了一个凸起的垒。他再将锤子把举到额头高,嘴里喊着号子,使劲捶打几下。胡基架子咯吱着,凸起的部分下去了,一块胡基成形了。窑娃赶紧卸掉架子,去掉挡板,两只手将胡基板起来,双手提着夹着垒在太阳底下。胡基是塬上人盖房砌墙的材料,刚打好的胡基最怕下雨,晒干的胡基十分坚硬。
大省领着社员锄地,到了地头正要坐下来休息,看着他们正在打胡基。他卷了个旱烟,蹲在地头点着抽着,吐了口烟,对社员们说:“老五就是和人不一样,又在张罗着给公墓盖房子了,我肯定夏天他就会睡在乱坟之间。”
宏斌笑着说:“五哥爱地,他在家里待不住,没事的时候,总爱在地里刨腾。”
二省蹲在田坎上,看见提锤子的人屁股一撅一撅的,他想起了到公社看戏时吴晓梅的屁股,他吐了一口痰,晃着头说:“赶集的时候,我听见十一队的人说,那个吴晓梅,走路屁股总是一摆一摆的,害得跟在后面挑水的小伙蒙了神,忘了自己家,跟着她出了村口。”
海军拄着锄头,站直了身子说:“人家都说她的屁股跟纸一样白。一般的女娃到医疗站打针,都会放下门帘,掩上房门,头朝外屁股向里。吴晓梅不一样,她打针的时候,总是头朝内,屁股向外。医生打针都是用棉签蘸上碘酒涂抹,碰到她,总要给指头蛋蛋上倒上碘酒,在她的大白屁股上搓揉一会儿,看得大队干部十分眼馋。”
路南陈家有两个老弟兄。老大陈德和有两个儿子,大儿子陈洪武解放初到了兰州,二儿子陈洪文一队种田;老二陈德明也有两个儿子,大儿子陈宏发抗美援朝提干后,转业到县上工作,二儿子陈宏远在家里种地。这一族和老五家族出了五服,宏字辈和老五平辈。洪武十几年前父亲去世,下葬的前一个晚上回来了,埋完父亲的当天下午就走了,村子里的人知道有这么个人,但都不认识。洪武从西头进村的时候,见到扛着锨,站在自留地田头的老五。他走过来笑着和老五聊着天,看见他愣愣的,他报上名字,老五才拍着脑门认了出来。他递来一根烟,老五说不会,却推托不了,就接过香烟,夹在耳朵后面。老五走到马路中间,对着洪文家喊着:“洪武回来了!”
洪文家的老大练练正啃着锅塌塌,蹲在门前头,仰头看着树上的洋槐花,准备脱了鞋子上树。听见伯伯回来了,他倏地跳起来,快步跑到家门口,对着院子喊道:“我兰州伯回来了!”又掉过头,向洪武跑来,伸手接过行李,仰着头嘿嘿笑着说:“伯,我是练练!”
洪武摸着侄子的头,跟着回家。洪文的媳妇走到门口,用围裙擦着手,招呼着哥哥。
洪武坐在门前的青石板上,接过弟媳递过来的茶缸,对准备上树的练练说:“上去摘洋槐花,叫你妈给咱蒸菜疙瘩吃!”
练练吃着洋糖,甩掉鞋子,像猴子一样飞快地爬上树,折下一串串白啦啦的槐花枝,扔了下来。洪武站起来,手接住树枝,捋下一把槐花,放在嘴里,津津有味地嚼着。社员们下地回来,纷纷围了过来,询问洪武的情况。洪武说自己现在在兰州炼油厂劳动服务公司工作,专门采购吃用的东西。见到大省,洪文介绍这是二队的队长。洪武和大省从小一起长大,他们拉着手,亲热得不得了。洪武给大省发了一根烟,说:“这次回家,就是想给村里帮点忙,晚饭后叫上一队队长一齐到家里聊聊。”
洪文媳妇把鲜嫩的洋槐花淘洗干净,在洋瓷盆里颠了几下,槐花抖动着。她在面袋子里舀了一碗面粉,撒在湿漉漉的槐花上,用手搓揉一会儿,面和槐花黏在一起,然后放进冒着热气的锅里蒸。她从水缸下拿出一把在东北地里挑下的小蒜,洗净切碎,放在熟好油的铁勺里炒熟,拌好辣子蒜水。槐花疙瘩出锅,凉了以后,她盛上一碟子,拌上炒好的小蒜,淋上辣子酸水,用筷子搅拌均匀,放在洪武面前。
洪武吃着软馒头,喝着稀饭,就着槐花疙瘩,辣得直哈气,点着头直呼过瘾。快吃完晚饭的时候,大省和一队队长走了进来。他站起来,给他们发烟点上火。他打着饱嗝,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慢慢地吐出来。他弯腰从自己的包里拿出一个翘着角的塑胶本子,从封皮的夹层中抽出一张纸,递给大省,说:“我们厂很大,这两年肉蛋和副食匮乏,厂革委会决定适当调剂一下职工生活。服务公司领导知道我是关中人,也知道关中富庶,让我回来联系一下,这是介绍信和我的工作证。”
大省和一队队长接过红本本和介绍信,仔细地看着,抬起头笑着点头。洪武继续说:“组织社员收购猪和鸡蛋,钱由我们出。猪要杀掉剁成肉块,鸡蛋用麦草垫着装进我们的箱子里。我们的汽车下来的时候,会装上化肥,给你们作为劳务报酬。”
洪文蹲在地上,抽着旱烟。这些年他一直埋怨哥哥不管家里,现在看到哥哥回来了,要在村子里收购东西,他喜上眉梢,合计着自己该做点什么。
一队队长有点脑筋,笑着问:“要不要给大队报告一下?弄不好就是投机倒把,我看孙书记好说,那金尚武左得很,什么事情都喜欢上纲上线!”
洪武倒吸了一口气,心里一下子凉了半截,他知道这件事如果过于认真,很难做成,到时自己咋有脸面回去交差。思谋了一会儿,他吐了口烟说:“我看这样,稳重期间,明天上午,我们一起到大队,将情况说明一下,看看大队的态度!”
洪武走进大队部,孙书记一只脚放在炕上,将报纸放在腿上,借着窗户的阳光,正在专心学习。自从被认为是全公社理论水平最高的大队书记以后,他更加卖力了,凡是重要的文件和社论,他都要看几遍。年前,总理走了,即使在普通的农家,家里也要追思一段时间,今年开春却大搞文艺汇演,他有点不明白。大省走过来,向他介绍了洪武。孙书记站起来了,走上前握着手,另一只手热情地拍打着洪武的胳膊。洪武说着情况,将有关证件递给他看。听完情况后,孙书记说这是天大的好事,现在村子有水了,化肥对土地就像农民对菜油,十分紧缺。一队的队长说要不要给尚武讲讲。孙书记将他叫进来,将情况说了一遍。金尚武晃着脑袋,严肃地看着洪武,认真地说:“严格地说,这就是投机倒倒,最好向公社汇报一下,听听公社的意见。”
孙书记走到门口,看着院子里的白杨树,他回过身来,摊开双手说:“公社知道了,一定会让收购站去做,到时我们大队就没有啥好处了!”他走到尚武跟前,继续说,“工农一家嘛!现在大家都有困难,互相帮一下,有什么不好,这也符合我们党的建党宗旨。没有尚武说得那么严重。”
洪武为了缓和气氛,他给每个人发烟,火苗到了尚武的嘴巴前。他将洪武的手推开了,偏着头看着窗外。孙书记瞥了一眼尚武,使劲抽了几口烟,将烟屁股扔在地上,踩着灭了。他走到桌子前,干脆地说:“公社春天分配给大队的劳动任务,由其他几个队平分,一二队腾出劳力,按照要求,尽快完成收购。得到的化肥调剂一些给其他生产队!”
洪武和两个队长点着头,互相扯着衣袖,含笑离开了。金尚武嘟着脸,没有作声。
晚上,一二队社员集中在饲养室前的老槐树下开会。一队队长将情况讲了一遍,社员们的情绪被调动起来了,闹哄哄交头接耳地议论着。大省站在粪堆上,让大家安静,将商量的结果向大家公布。智亮在兰州上过学,熟悉那边的风土人情,协助洪武接待兰州来的客人,安排吃住;老五熟悉猪的行情,带上几个社员到附近集市上买猪,赶回来圈在饲养室后面;志义联系后堡子周顺发,筹划安排宰猪;宏斌心细,组织两个队的女社员串村走户收购鸡蛋,收鸡蛋时要盯着摇一摇,确保鸡蛋新鲜;洪文协助队长统筹遇到的问题。
太阳从东边壕岸上升起,老五带着几个懂猪的老人,手提着绳子,拿着棍子,沿着田畴上的小径,到有集市的镇子买猪去了。村上的妇女带着小孩,头上顶着帕帕,手里提着篮子,走出村口,互相交流着想去的村子,心里盘算着不能重复,然后顺着小路出发了。宏斌整理着装鸡蛋的木筐子,用背篓背来麦粒壳子,准备铺在筐子里放鸡蛋。养田和陆军给饲养室前拉土,二省和栓和将能用的瓷瓮从社员家里搬出来,挖个坑固定在地上。保民和养地扛着椽,忙活着搭架子。屠夫顺发叼着烟锅,蹲在粪堆上挥手指挥着。
桂琴带着孙蛋,在塬上串了几个村子。她的舅家和姨姐家住在塬下,她有好多年都没有去过了。站在塬上,瞭望朝霞映照下,飘着薄薄炊烟的塬下的村寨,她想起了小时候和妈妈走亲戚的情形。现在自己结婚育子,孙蛋已经半人高了,带着儿子收鸡蛋串亲戚,她感到十分高兴。舅家的门已经记不清了,她问了村口的老人,顺着指点来到一户农院前。她敲了下门上的铁环,妗子正在用铁叉翻院里的柴草。她打量着门口的娘俩,愣了一下,随即放下铁叉,快步走过来,亲热地拉着桂琴的胳膊,笑着说:“快进屋,你舅还在地里,一会儿就回来了。”
妗子倒了一缸水,放在桂琴面前,走出了院子。孙蛋陌生地张望着,他看见麦囤下卧着一只灰白相间的猫,走过去,摸着猫的脊背。猫仰起头,用陌生的眼神打量着他,吐着舌头,喵喵地叫着。
院子外面传来喧闹声,几个叔伯妗子走进来,后面跟着表兄弟的媳妇。她们拉着桂琴的手,摸着孙蛋的头,问长道短。院子响起了咳嗽声,妗子说你舅回来了,说着走出屋子,对老汉说桂琴和娃来了。舅舅弯着腰,走进来,满是皱纹的脸上绽开了憨憨的笑容,他摸着孙蛋的头说:“你看几年不见,娃都这么高了!”
桂琴说队里要社员收鸡蛋,晃着晃着就到了舅家,心里还是和舅家亲。舅舅蹲靠在门扇上,抽出烟锅,捻上一锅烟,划着火点上。他询问姐姐的身体,然后,转过头交代家里人,到村子叫喊几下,让卖鸡蛋的人家,把鸡蛋提过来。又对老婆说:“快去做饭,桂琴好不容易来了,总要吃顿饭嘛!”
桂琴知道舅舅家日子紧张,她连忙推托着。舅舅脸阴了下来,生气地说:“是看不起你这舅舅?还是嫌弃舅舅家里穷?”
桂琴不敢作声了。孙蛋抱着猫,捋着皮毛,将脸贴在猫的耳朵上。
妗子麻利地和面,一会儿擀好了面。几个表兄弟从田里回来了,他们和桂琴聊了一会儿,都出去了。妗子给桂琴和孙蛋每个人挑了一碗凉面,拌上炒好的韭菜,倒上蒜水,递给他们。桂琴朝门外望了望,对妗子说:“叫我舅和几个兄弟一起进来吃饭!”
舅舅蹲在厨房外的屋檐下,瓮声瓮气地说:“他们队里还有事,你吃你的,甭管他们。”
孙蛋几下子刨完了一碗面,眼睛不停地盯着案板。桂琴看到案板上的面不多了,用脚踢了下儿子,使了个眼色。孙蛋低下了头,看着边上的猫。妗子看到孙蛋吃完了,从灶膛前的柴堆中起来,拿起碗说:“来,婆再给你挑一碗面!”
孙蛋摇着头,说吃饱了。院子里嘈杂起来,卖鸡蛋的人来了。桂琴放下碗,走了出去。宏斌给社员定的价格是每个鸡蛋一毛钱,比行情高出两分钱,每个社员既有两分钱的差价,还可挣到工分。一位小脚老太太颤巍巍地走过来,手掂着一个大肚子褐色瓷罐,颤抖着手从里面拿出鸡蛋,每拿出一个鸡蛋,都会用手搓弄着看上一会儿,再放在草堆里。舅舅走过来说:“桂琴,这是你六婆,认识不?”
桂琴笑着叫了声六婆。后面跟着一位大脚老太太,双手撩着围裙,里面放着鸡蛋。六婆问:“多钱?”
桂琴从来没有做过生意。她洗锅的时候,经常听家公叨咕着买卖,就顺着他的套路说:“你说?”
老太太指着鸡蛋上的血丝,拿起一个在手里掂着,有点舍不得地说:“个大,又是初生的,九分一个。”桂琴应了声好,就开始清点数量。孙蛋拿出本本,计算着数量和价格,帮助妈妈算账。
桂琴很快收了大半担笼的鸡蛋。她蹲在地上,将鸡蛋摆好,在舅舅的谦让下回到屋子。几个表兄弟蹲在屋檐下,将玉米塌塌掰开,放进面汤里,围着一碟腌萝卜,津津有味地吃着。看着桂琴走过来,他们不好意思地笑着。桂琴这才明白,中午的凉面是为她们娘俩单独做的。她对舅舅说:“好多年没有到塬下来了,也想趁机到姨姐家看看。”
舅舅喊来小儿子,交代他提上鸡蛋,将表姐送过去。
舅舅家在刚下塬的坡底下,村里大部分的地是坡地。从舅舅家向西北走三里地,就是姨姐家,她的村子正好在塬下的中央,村子四周布满了小渠,渠网的节点上是一座座水井,打开电闸,水管里就会冒出清清的井水。
舅家的老小眼睛很好,刚进村口,就看着远处几个人,他转过头,笑着说:“我姐在门前哩!”
往前走了一段,舅家老小喊道:“姐!”
几个人还在聊天,没有反应过来。几声连续的喊声,姨姐缓缓地回过身来,手交叉放在围裙上面,愣了一下认出了表弟,连忙走上前来。表弟转过身来,指着身后的桂琴说:“姐,你看谁来了!”
姨姐呆愣一下,快步走上前,手在围裙上拍了几下,高兴地拉着桂琴的手,亲热地说:“十几年了,都不来看看姐,我姨每次来,都要求咱们走上亲戚。”
姨姐拉着孙蛋的手,怜爱地摸着他的头,笑着说:“上一次来你还是个女子,这次来都带上娃来看姐了!”
进了院子,姨姐的女子小丽正在洗衣服,看着妈妈热情的神色,她用陌生的眼光不解地打量着桂琴母子。桂琴说自己给生产队收鸡蛋,到了舅家,过来看看姐姐。姨姐说:“晚上住一个晚上,明天早上再回去!”
不等桂琴开声,姨姐对着小丽说:“你姨来了,到镇上买点韭菜豆腐回来。”
小丽站起来,应了一声,抖了抖手上的水珠,轻快地走出去了。
姨姐夫骑着自行车回来了,走进屋门,看见桂琴来了,高兴地跺着脚,对老婆说:“叫娃买菜去,给他姨做饭。”
姨姐说桂琴要收鸡蛋,他说没问题,等一下他到村子转一下,就是一笼鸡蛋。看见儿子甸伟回来了,姨姐夫给了儿子一块钱,让甸伟带着孙蛋到镇上玩。甸伟牵着孙蛋的手,出了村子东头,向镇子跑去。来到供销社,典伟手里攥着钱,买了几个米花糖,给了孙蛋两个。他们又跑到街道上,看着卖嚼嚼糖的担子,又买了几块。来到新华书店,看着柜台上摆着的一排小人书,孙蛋指着说要买一本《渡江侦察记》。甸伟说他有那本书,回去送给他。出了镇子,他们来到抽水井旁,孙蛋从井口看下去,明晃晃的井水有七八米深,想到自己家里搅水,一辘轳的筋绳缠得满满的,他觉得不可思议。他跑到出水口,掬起一手心水,用舌头舔了舔,甜甜的凉凉的。甸伟用树枝在渠水里摆弄着,笑着说:“喝,没有问题!”
走到积水的土坑前,看见一群蝌蚪摆着尾巴游动着。孙蛋蹲在地上,双手撑着脑袋,凝望遐思着大自然的神奇和美妙。
晚饭是酸汤面,还炒了一碟豆腐和鸡蛋,热腾腾的酸汤面上面漂着一层汪汪的油,还有几块肉。孙蛋咽着口水,碗放在面前时,他已经有点把持不住了。看见大人端起碗,他将碗移过来,放在胸前的桌子上,筷子在碗里飞快搅动着,呼啦啦几下就吃完了一碗面,眼睛不停地盯着桌子上其他没有吃的碗。一会儿,他的脸上开始冒汗。姨夫爷抽着烟,看着他的吃相,笑着说:“慢慢吃,面有哩。”
桂琴看着儿子的吃相,不好意思地说:“你看我们家的小孩,就像个饿死鬼!”
孙蛋停下筷子,扭头用责怪的眼神望着妈妈。吃完饭,甸伟拉着孙蛋来到厢房,他从柜子里抱出一摞书,放在炕上,让孙蛋挑选几本。孙蛋趴在炕上,入迷地翻着成堆的连环画,好像在看电影。姨姐揭开柜子,拿出一个包袱,放在炕上解开,取出一件军上衣和一双军用胶鞋,递给桂琴说:“老大部队提干了,放了几件衣服在家里,这衣服和胶鞋你带给孙蛋他伯吧!”
桂琴笑着说:“不给他,给孙蛋和毛蛋留着。”
夜里,孙蛋用军装包上连环画,枕在头下,睡梦中露出了甜蜜的笑容。
老五养了一辈子的猪,村子相好对劲的人买卖猪,都会问老五的意见。快要长成的母猪,将来能不能生猪娃,他蹲在猪边上,思谋着看上一会儿,会给出八九不离十的意见。他做过几年生猪买卖的经纪,来到猪市,好多人都认识他,有时买卖双方价格谈不下来,会请他过去评价。
老五带着几个人来到猪市,交代大家分头去看,先不要说出买的意向,更不能让别人觉得今天咱一定要买好多猪回去。咱们碰在一起,也要装作互相不认识。几个人分头在猪市上遛了一圈,心里都有了个谱。回来后,大家蹲在镇东头的麦草垛子前,每个人将自己看中的猪讲一下,几个人都看重的就是今天购买的猪。老五交代道:“你们每个人选定一头猪,出价低一些,先和卖猪的人黏上。我装作闲逛的样子,价格讲不下来,就招呼我过去!”
太阳偏西,猪市临近收市。老五一伙开始出手,买了五头猪。这几年有米猪,就是猪杀了后,猪肉的断面上有白色米粒大小的白点点,这样的猪肉不能吃,他找来一根棍子,撬开猪的嘴巴,看看猪吐出来摇动的舌苔上,是否有米粒一样的东西。马家十一是一队的能人,他走过来对老五说:“那边有头老母猪,你看行不行!”
十一走在前面,和卖猪的人聊着价格。老五背着手,走过去蹲在边上,看见那头母猪足有一米四五,两条松弛的乳带拖在地上,他知道那是一头老得不能再生娃的猪。农村人有时为了多卖斤两,会将老母猪喂肥交给公社的收购站,本地人即使没有肉吃,也很少买老母猪的肉。十一正和卖猪的人讲价,不停地给老五使眼色,老五装作没有看见,起身走开了。十一追回来,生气地高声问:“老五,咋回事?”
老五淡淡地说:“洪武给厂子办事,咱不能让人家回去骂咱们!”
十一摇着手里的烟锅,晃着脑袋说:“给顺发说一声,剁肉的时候,用刀将母猪的乳带掠掉不就行了!”
老五执拗地说:“那事我做不出来。”
十一嘿了一声,拍着大腿,蹲在地上抽起闷烟来。
过了两天,两台红色的解放牌汽车开进了村子,车上装着化肥。三个堡子的人走出家门,小孩跟在汽车后面跑着,扬起的灰尘粉了孩子们的脸,就露出两只咕噜乱转的眼珠子。孙蛋喜欢闻汽车排出的汽油味,每次村子有汽车来,他总跟在后面喘着气,大口呼吸着汽油味,觉得特别提神。汽车停在二队饲养室前面,几个人从驾驶室跳下来。智亮跟着洪武迎上去,大省让智亮安排师傅们吃饭。洪武给一个小伙说了几句,他跳上汽车,解开上面的帆布,用脚踢着边上的袋子。大省和宏斌举起手,卸下了一个袋子。洪武解开袋子,抓了一把好像红糖一样的东西,对大家说:“这就是我们厂生产的化肥!”
社员们围了过来,伸出手在袋子里抓摸着,黏黏的沙沙的感觉就是红糖。海军高兴地在袋子里摸来摸去,他记得嫂子生小孩的时候,她娘家来看望,就是拿了一包这样的东西。看着妈妈冲了一碗红糖水,端进嫂子屋里,他当时连续咽着几下口水。他攥一把,回到家里,放在碗中用开水冲开,筷子搅拌了一会儿,端起来准备喝,一股尿臊味扑鼻而来。他放下碗,感到那就是红糖水,他睁大眼睛,屏住呼吸,找到了喝中药的勇气,刚喝了一口就喷了出来,吐着舌头哇哇叫了起来。
大省让宏斌给饲养室前的槐树上接了两盏电灯。电灯随着树枝晃动着,社员们吃完晚饭,撂下饭碗,聚在老槐树下,看着地上自己晃动的影子,围着汽车转悠着。志发从西头走到村子东头,一路喊着开会了。社员们到齐了,大省和一队队长合计了一下,站在粪堆上,大声说:“现在天慢慢热起来了,明天天亮,听队里的铃声,男社员集中起来杀猪,女社员将鸡蛋装筐。天黑以前要保证装好一车货,准时发车。”
志发站起来说:“每家拿一个脸盆来,明天下午给大家分猪血。老人和能干活的小孩也可以来装鸡蛋,给大家记工分。”
人群嚷嚷起来,叨咕着吃猪血一定要有蒜。
下午四点多,一车货装好了。孙书记和德文骑着自行车来了,围着汽车转了两圈,走到饲养室后面,看着垒得像小山一样的化肥,高兴地拍着捏着。大省走过来,笑着说:“孙书记,兰州的师傅等一下要走,我们安排了一顿饭,一起吃吧!”
孙书记看了德文一眼,摇着头说:“你们吃吧!我们等一下就走了。”
大省递上一根烟,探过头来,压低了声音说:“你是书记,和兰州的客人见个面,也算是对这件事情的态度。”
孙书记擂一拳化肥袋子,痛快地说:“既然这样,那就吃吧!”
装鸡蛋的时候,打破的鸡蛋集中在一个脸盆,盛了满满一盆蛋汁。除了给兰州客人炒了一盘鸡蛋,最后每家都分了一勺蛋汁。村民们回到家里,用辣子蒜水伴上猪血,又有一盘炒鸡蛋,围在一起开心地吃着,感觉好像又过了一个年。
孙书记和德文陪着兰州客人吃了一顿酸汤面。大家打着饱嗝走出洪文家的大门,兰州客人深深吸了一口烟,对他们说:“我们兰州人就知道兰州的牛肉面最好吃,谁料想关中塬上的酸汤面更是一绝!”
智亮笑着,用加重了鼻音的腔调说:“我离开兰州二十年了,回想起兰州的牛肉面,常常会流口水。”
兰州客人说:“这话我爱听,我们兰州人出差回来,首要的事情就是赶紧吃上一碗牛肉面。”
两个司机上了车,汽车突突响了起来,灯亮了,将整条街道照得白啦啦的。司机和送行的人挥着手出发了。天已经黑了,孙蛋裹在人群里,和小孩一起追着汽车,盯着汽车后面忽明忽暗的尾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