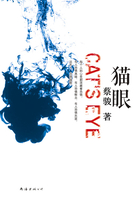柳一明说你就莫破费了,给我个面子,高抬贵手把梅贵放了吧。马朔风一愣,说梅贵的事你咋也管?柳一明说以前是邻居。马朔风说,哦是这回事呀,所里也缺司机呢,他走了……柳一明打断马朔风的话,笑道现在满大街都是司机,梅贵走了,你还可安排一个关系户呢。马朔风听了也笑说,你这嘴从来就不饶人。柳一明却收了笑,指着盒子说我给你带了个瓶子,你看看。
马朔风说一明你看你,你看你也给我来这一套,却打开纸盒,取出,是一只灯笼瓶,白地粉彩,构图严谨,施色淡雅,高古别致。瓶底有“洪宪年制”楷书款,是袁世凯称帝时烧制的瓷器。马朔风心里惊喜,刚欲说句感谢的话,却见柳一明嘴角撇出一抹讥笑,想这小子莫不是弄个烂瓶子来捉弄我吧?心里吃不准,就一语双关地说,多谢老弟了,这情分愚兄却之不恭,不过我收了,也得让它到该去的地方呆着。柳一明笑说,那你不会拿它去谋顶子吧。
马朔风听了不悦,正要开口,见到菇琴在门口探了下头,肚子里的气一下就跑了,得意地想你柳一明嘴损中屁用,你不是最珍爱菇琴奶子吗,可如今这奶子没你的份了。马朔风立马对柳一明有了一种优越感。也多了几分胸怀。两手一摊,作无奈状说,你看真是拿了人家的东西手短呢,看来梅贵我是非得放了。就从文件夹里拿出梅贵的调动手续,龙飞凤舞地签了字。
柳一明刚出门,马朔风就又迫不及待地拿起灯笼瓶,见胎体洁白,釉质细润,实非一般粗俗之物可比。正欣赏间,马朔风突然想起在一本藏玩手记中曾提示说袁世凯称帝时订制的瓷器,均用篆书题“居仁堂”三字,凡题有“洪宪年制”四字楷书款的,为民国年问的伪作。顿时,马朔风就气不打一处来,恨不得一下把灯笼瓶砸了。又想如砸了柳一明见不着瓶子,他还认为我真当珍宝藏起呢。好好好,你既不仁我也不义,我也得想法子让你再丢人显眼一回。眼睛转了几转后,竟将灯笼瓶盛了水,还往里倒了口水,又放了一支秃笔。做完了这些,坐到皮椅上,将两腿架到写字台面,点了支烟,自得地欣赏起自己的杰作来。此时,他就盼望快点来人,好羞辱柳一明。没想第一个来的人是菇琴,经过上次变故,茹琴俊秀的脸上失却了青春的活力,蓄着沉水般的淡漠。她放下资料,就转身欲走,马朔风忙放下双脚说,小琴你看我这瓶子怎样?菇琴这才看到了桌上的瓶子,说真好看,你怎用来洗墨呀?马朔风阴阳怪气地说是柳一明刚才送的,我不用对不起他呢。菇琴听了一怔,便用手轻轻抚了又抚,说是古瓷吧?
马朔风对菇琴的举动很上火,说狗屁,三十块钱的烂瓶子,把我当傻瓜呢。菇琴听了说,他在收藏上是不会骗人的。马朔风想她这是还念着柳一明呐。心里那个气呀顶得牙根发胀,恨不得扇她两个耳光。
几天后,马朔风把柳一明送的假瓶子当笔洗的话,就传到柳一明耳里,柳一明很吃惊,好一会儿才不阴不阳地打着哈哈说,也就是他才能想得出。
到了三月底,文史馆开始申报副高以上职称了,这天,王向阳给马朔风送了一幅字,说这字是一明给我的,他说是赝品,不值钱。我知你喜欢字画,就给你拿来了。马朔风知道王向阳与柳一明关系不一般,这幅字他也曾在柳一明书房见过。是清成亲王永理的书法,价值不菲。也知王向阳送字是为了副高职称。收了就得办事,拒了又心有不舍。为难问,见王向阳眼睛盯着灯笼瓶子看,心里一动,就说向阳你的意思我清楚,不过你这字我不收,君子不夺人之所爱,我能做这既伤感情又违法的事嘛。
王向阳急了,说馆长你要是不收下,就是对我有成见,有戒心。我就当你的面把这字撕了,那屁职称我也不评了。说着就要动手撕字。马朔风见了忙说别别别,你的心意我收了,这字我就留办公室挂吧,可我怎么也得给你找件相匹配的玩什吧。说了眼睛就盯着瓶子看。王向阳就惊诧地直叫唤,说哎呀馆长这么好的瓶子你咋用来洗墨呀?马朔风立马接着王向阳的话茬说,向阳,来而不往非礼也。你要喜欢那就把瓶子送你吧。这也是一明送我的藏品呢。
王向阳急摆手说,这么贵重的瓶子我哪能要呢。
马朔风说陶冶心情的东西,谈不上贵重。你拿去得了。
王向阳说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马朔风就亲自倒了灯笼瓶里的污水,用它换了王向阳的成亲王的字。
到了四月上旬,大敦煌拍卖行来城里举办春季拍卖会,请收藏协会出面协办,马朔风、柳一明、罗布衣都被聘为顾问。总顾问是柳凡夫。首席鉴定专家是西部收藏协会秘书长白圣陶先生。四月下旬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拍卖行将顾问们都请了去,先是在每人面前放一红包,然后通报了筹备情况,介绍参拍品。马朔风见宣传册页上赫然印着一只令他眼熟的灯笼瓶,底价一万元。悄声问与他相熟的注册拍卖师李鹏,果然是本市藏家送来的拍品。马朔风起了猜疑,装着上洗手间的样子,去外面打了王向阳的手机,问:那个灯笼瓶呢?
王向阳说卖了。
卖了?多少钱?卖给谁了?
王向阳说卖给一个收古货的,一千块,我正想请你去吃烤鸭呢。
你糊涂呀,那么好的瓶子,咋一千出手了?要值上万元呢。
王向阳听了,喊天呼地得叫起屈来:你咋早不给我说呢,我看你用来洗笔,以为不值钱,还说遇了个冤大头呢。